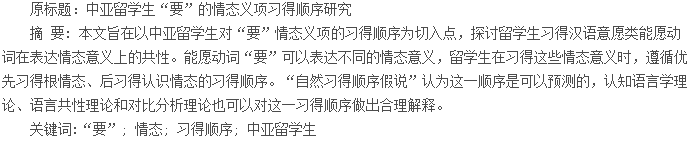
本文提出的新术语““概念对喻”,组合了两个学界熟知的概念,一是莱考夫与约翰森(Lakoff& 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另一个是宋人陈骙提出的“对喻”。
莱考夫和约翰逊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和莱考夫1987 年出版的《女人、火和危险的事物》(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两书详细讨论了“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通常一般的隐喻与词语结合得很紧,不能脱离特殊的词语安排,由此常成为“成语”或“熟语”(cliché)。而概念隐喻是一种特殊的隐喻,不拘于某种语言表达方式,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效果类似,因为它们是“概念”性的,也可以用表情、图像、舞蹈、音乐等非语言媒介来表现。 对喻,不是简单的两个并列的比喻。宋代陈骙的《文则》一书列举出十种比喻,第五种为“对喻”:“先比后证,上下相符。”他的例子是《庄子》中的“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荀子》中的“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两个喻本分别各自生发出两个比喻,形成对照。本文论述的“概念对喻”之所以卷入社会文化问题,正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各种使用语境,因而有多种延伸变体。一个常用的“概念对喻”,说女人与男人,就像藤与树,可说成“女人是藤”,也可说成“男人是树”,亦可说成“他们就是藤与树”,甚至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简单地说“藤与树”。无论何种说法,对喻的四项关系都很清楚,表现方式却可以变化多端。“概念对喻”在下面这首客家民歌中,衍生枝蔓,反复咏叹,绵延展开。
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哥系路边大榕树, 妹系紫藤树上缠。树高一寸缠一寸, 树结藤干便了然。
藤与树是中国歌词中古已有之的原型式“概念对喻”。《诗经·唐风·葛生》:“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葛”即是“葛藤”,藤的一种。女为葛藤,男为树干,一旦在歌词中几千年反复使用,就发展为“原型意象”,即“在文学中反复使用 , 并因此有了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原型化的“概念对喻”,只消点出意象,就会在解释者的记忆符码集合中引起反应。“原型一旦产生, 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复制, 不断强化。它甚至逐渐脱离了具体作品的桎梏, 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徽号”。
这种成对形成的概念比喻,不仅表现形式千变万化,其“比喻点”也可以多种多样,常常超出简单的“相似性”。用钱锺书《谈艺录补丁》中提出的术语来说,就是“同喻多边”,只是“概念对喻”的多边超出大部分比喻,含义更为丰富。 譬如“藤树”这个很通俗的“概念对喻”,可以喻指许多观念:女次/男主,女边缘/男中心,女柔软/男刚强,女细弱/男粗壮,女依赖/男可靠,女纠缠/男被缠,男女共生同死生死相依,如此等等。“概念对喻”的指向模糊,给歌词的发挥增加了许多联想方向,而这种“多边”也正是“概念对喻”的力量所在。
一、中国歌词中的“概念对喻”
“概念对喻”是一种类比思考方式,应当说是全世界各民族的通例。但由于中国文字单音节单字体的特点而造成的对偶美“,概念对喻”在中国诗词艺术中,使用得更为广泛频繁。
汉语的骈俪对偶,在格律文体(词赋、律诗、对联等)中几乎成为一种强制性修辞。一千多年前刘勰就已经在《文心雕龙·丽辞》开篇指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到20世纪,郭绍虞在《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中依然指出“中国语词因有伸缩分合之弹性, 故能组成匀整的句调, 而同时亦便于对偶; 又因有变化颠倒的弹性,故极适于对偶而同时亦足以助句调之匀整。因此, 中国文辞之对偶与匀整, 为中国语言文字所特有的技巧。”
这正是“概念对喻”在中国文化中特殊地位的一个精彩追溯。不仅如此,“概念对喻”还发展成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概念,最早来自自然界中的朝阳和背阴。春秋时期,阴阳被广泛地用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到五行说盛行的汉代,阴阳关系上升为宇宙间的根本规律和最高原则。在自然界中,它们是天地、日月、山河、水火等等。在社会中,它们是贵贱、尊卑、男女、君臣、夫妻、生死、利害等等。而在性别文化中,凡是刚性的、动的、热的、上位的、外向的、明亮的、亢进的、强壮的等等均为阳;凡是柔性的、静的、寒的、下位的、内向的、晦暗的、减退的、虚弱的等等均为阴,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尽管其他民族也有性别对立的原型“概念对喻”,例如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在其著作《新生儿》(1975)中列出的二元对立表。但没有一个民族把性别对立扩展到阴/阳这样大规模的宇宙论“概念对喻”。两种性别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分工明确。从初生伊始,男女的性别规定就是地位、职责、文化角色的严格区分,社会文化进而加强了两者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班昭《女诫》云:“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中国文化之依赖于原型“概念对喻”,可谓根深蒂固。通过“概念对喻”形成的性别文化对照,作为中国哲学和社会伦理的根本出发点,反过来又承传到歌词中,成了一个民族文化最基本的构成元素,深入到人们的思想中。本文主要讨论中国现当代歌词中的“概念对喻”及其变化,但这个现象是中国歌词始终一贯的特色。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原型,在歌词中表现特别明显,因为歌的基本结构是呼应。“我对你唱”是其基本表意格局,而爱情又是歌曲从古至今的最主要主题。因此,性别“概念对喻”在歌词中既是主题内容,又是形式结构。情歌最早的起源,“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就已经孕育歌的基本呼应结构。正如上文刘勰所说的“自然成对”最早在民歌中出现,这种源头悠远的表意形式,因为流传不息而不断加固、定型,从而成为歌词基本表意和结构原则。歌词中对喻式的呼应,存在于词与词之间,也存在于句行与句行之间、段与段之间,由此构成一种由小到大的顺序递增结构。稍一注意,就会发现每一层呼应,从词到段,都可以有“概念对喻”。
20 世纪中国最早的现代歌曲之一,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中,以天配地,天地相应: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她?
而在20世纪90年代,黄桂兰作词,林隆璇作曲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那英原唱)依然是相似的性别对峙概念比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像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
“天”与“地”,“白天”与“黑夜”,是阴阳二元对立的演绎,古已有之,只不过“概念对喻”的语言多变特点,使它顺利进入现当代的语言艺术。可见人类性别思维中的对应联系,成为歌的呼应结构中显性形态,而通过歌曲,原型对立又得到进一步强化。
“概念对喻”在歌词已经成为常态结构,成为一种自然的思想方式,以至于可以出现简写的“单边显现”现象,即只消说到一边,另外一边隐于联想中,使得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含蓄变化。歌词中的男女形象,本是言说主体对他者的欲望诉求,是与“我”相对的“你”,因此,也会反照出言说主体的性别形象,这两者之间是互塑关系。正如朱光潜指出的“用排偶既久,心中就无形中养成一种求排偶的习惯,以至观察事物都处处求对称,说到‘青山’,便不由你不想到‘绿水’, 说到‘才子’,便不由你不想到‘佳人’。”
比如这首当代歌曲《棋子》(潘丽玉作词,杨明煌作曲,王菲原唱):我像是一颗棋子,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
歌中出现的“我是棋子”这个隐喻,并加以曲喻性的展开,暗含了“概念对喻”的另一边“你是棋手”。
当代歌曲的发展,随着主体意识觉醒,隐喻逐步向主观化、个性化方面发展,但歌词基本的呼应结构依然存在。又如近年广为流传的一首歌,张超作词的《荷塘月色》,歌手组合中的女歌手这样唱道: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 ,荷花依然香。
女性依然扮演着离不开“水”的“鱼”的角色,保持着传统的“被供应者”姿势,而男的是供应者,是生命养料的提供者,是生命意义的保证者,但在歌词中出现的只是“鱼”。
二、“概念对喻”的“标出性”偏边
标出性(markedness)原是语言学术语。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俄国学者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在给他的朋友雅科布森(Roman Jakobson)的信中首次提出这个术语。指“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是二元对立中次要项的特殊品质。而在文化符号学中,赵毅衡则提出“中项偏边”原则。“非此非彼”与“亦此亦彼”的场合,被称为“中项”,中项是文化的正常形态。中项的非标出性,来自于意义上认同正项,从而意义被正项所裹挟,合起来组成文化的“非标出集团”,共同排斥标出项。例如,英语中男人man 与女人woman的对立中,man为非标出项,woman派生自man。而成为标出项。但是非此非彼的“人类”一词用mankind而不用womankind,根本原因即是男性的社会宰制。是男性社会权力使男性为裹持中项的“正常”词项。
在汉语中,指一批有男有女,或不明性别的人,则用“他们”,而不用“她们”,二元对立就产生了标出性。在歌词中,不太会出现“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项偏边,区分标出性的原则是“文化重要性偏边”。歌词中的性别标出性,是一种明显的“意义偏边”,这也是中国歌词自古以来的传统。流传于中国西北部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花儿”中,就有“哥是金砖妹是瓦”。这显然与《诗经》中“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遥相呼应,男女区分,三千年不变,在文化价值上,就是床与地之别,裳与裼之别,璋与瓦之别。一种价值不对称还不够,还要再三对比来强调文化重要性的偏边。
“概念对喻”既然是两个概念对立,就必然有偏边,使得其中一边成为标出项,另一边成为“文化上正常”的非标出项。歌词中的性别对喻,对建构性别文化的影响极大。我们倾向于将语言视为一种表达的技巧,却没有意识到语言首先分类和安排好了产生某种世界秩序。歌中对喻让我们感觉到自然,实际上它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控制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体验,即使这种对喻变形到不容识别。钱锺书在《老子王弼注》论卷中有长文引魏源《古微堂集》:“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正一副。”魏源发现文化中的对立项之间普遍不平衡。钱锺书评论说,魏源这段话是“三纲之成见,举例不中,然颇识正反相对者未必势力相等,分‘主’与‘辅’”。他敏感地挑明了这种文化重要性不平衡偏边,是意识形态性的。例如动物与植物的“概念对喻”:歌词中男女“概念对喻”的喻体,如果是动物/植物,那么女性几乎多为植物,以示静止。男性大多为动物,以示力量,如此对比鲜有例外。这里的“概念对喻”的标出性,来自力量中的主动性。这首青海民歌:青石头青来蓝石头蓝,花石头根里的牡丹;阿哥是孔雀虚空里旋,尕妹是才开的牡丹。
动物/植物的概念对立,在东西方似乎是一致的。瑞士心理学家维雷斯分析,男性和女性这种植物和动物性的类比,来自于人类的原型思维。而日本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在其著作《女性的人生双六》一书中写到“:女性是植物,男性是动物,如此对照性的认识植根于深层的文化之中。动物和植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植物一直生长在地面,而动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移动。这就是被认为男性有行动的自由,女性没有行动的自由的理由。因而形成了以植物和动物的隐喻来认识女性和男性的说法。”
但不同的民族使用各有特色,在上引歌里,女性被比作地面上的“牡丹”,男性比作天空中的孔雀,天地遥相呼应,牡丹与孔雀形成对喻。在这里男性不仅比作有翅膀能行动自由的飞禽,而对“花儿”流传的青海地区人们来说,牡丹是熟悉的身边之物,孔雀则是珍奇鸟禽,对当地人只是传说。
因此,标出性的使用虽然是普遍的,但在不同文化或不同语言中变化多端,简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各种形态,使“概念对喻”的意义模糊而多元。除了上面讨论的动/植“概念对喻”外,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其中的几对概念对照:主动/被动;消费/被消费,依赖/被依赖等等。下面这首高枫作词作曲的《双双飞》(思雨、思浓原唱):草儿沾露珠,蝴蝶花中飞,何时我与你这样共相随。风筝线上走,鸟儿把云追,何时我与你这样共依偎。
“花”处于“蝴蝶”的追逐之中,就像“风筝”在“线”上那样一则被动一则主动,就像“云”被“鸟”追那样一静一动;就像“草儿”接受“露珠”那样一接受一给予。这种同意义比喻累加现象,在“概念对喻”中得到动态的延伸与衍义,而且不断有新的艺术家在旧对喻中进一步推出新的标出方式。
在以创新为贵的现当代歌词中,更是如此。当代商品化社会中,“概念对喻”中女性传统形象在歌词中会有重大变异,但在文化标出的方向上很少有所变动。比如这首《女人如烟》(穆真作词作曲,魏佳艺演唱):你说过今生与烟为伴,你说过女人如烟你已习惯,你说过聚散离合随遇而安,可我来世还要做你手中的烟,想我了 就请你把我点燃,任我幸福的泪缠绵你指尖,化成灰也没有一丝遗憾,让我今生来世为你陪伴。
歌中“烟/抽烟者”对列,依然是“被消费者/消费者”的类比,只是用比较“时代感”的形象表现出来:女人是供男人点燃消费的香烟。女性“为男人牺牲也心甘”传统意义,说的更为有趣一些,有“时代感”的只是喻体形象,而不是喻旨意义。再如女歌手刘力扬演唱的《提线木偶》(唐恬作词,张艺作曲):破旧的木偶,提着线,被操纵,玻璃的眼球,表情空洞,谁提着我的手和谁告别,他掌控我灵魂我的笑脸。
歌词中唱出的女性的被动以及被操纵地位,已经是历几千年而不变,这样的歌词感叹,让人觉得十分自然。
三、当代歌词中的“概念对喻”标出性翻转
上面三节的讨论,似乎是说,几千年的人类文化的性别差异,已深深渗透到人的意识中,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但正像女性主义理论家伊利格雷提出的,性别差异“并不是一种事实、一种根基”,相反,“它是一个问题,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或许文化标出性不会完全翻转,传统稳固的标出性只是渐渐淡化,但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化标出性的翻转,或许不可避免。
当代歌词的发展中,也出现了“概念对喻”摆脱固定标出性格局的努力。这首歌《囚鸟》,是当代女词人十三郎为其丈夫歌手张宇打造的一首情歌,一般说,歌手的性别,决定了歌曲在大众传播中的“文本性别”。既然是张宇所唱,这也就是一首男性情歌,唱者“我”的听者“你”是女性。但这首歌中“鸟”与“城堡”的对喻,翻转了“正常”的女性与男性的关系。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
这里的“小鸟”,可能原先是女词人十三郎的自况,与男人为“城堡”形成对喻,没有脱离“依赖/被依赖”的类比模式。但一旦歌手性别颠倒,由男歌手演唱,整个歌的语意场就翻转过来,因为在当代歌曲以歌星崇拜为中心的文化中,歌手对文本性别几乎起了绝对的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歌曲的“文本身份”往往由“原唱歌手”性别决定。但这与李玉刚男扮女装唱《新贵妃醉酒》,霍尊故意模糊性别的装扮和声音唱《卷珠帘》很不相同。他们演唱的女歌文本身份与扮演的女性身份是一致的,并不能将女歌文本翻转成男歌文本。此类演唱表演除了满足这种“观看”需要外,更进一步强化并定型了他们所唱的“女歌”文化传统。
当代对喻通过性别换唱而造成的原有标出性被颠覆,我们可以把这种标出性翻转,称为“概念对喻”的使用翻转。造成这种“概念对喻”标出性模糊化的原因,是“跨性别歌”,即男女歌手通用的歌之大量出现。在传统中国社会“跨性别歌”是很少的,男读书人写“艳词”,让女歌手演唱。因此宋词元曲大部分是“女歌”,表现的也的确是女子心理。但在当代,歌手已经男女数量相当,男女都可唱的“跨性别歌”在当代增加很快,跨性别歌已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就为标出性的翻转创造了一个初步条件:价值对立模糊化。性别关系的标出性,其原型思维方式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能说明传统社会和文化中的思维模式之顽强,但当代文化演变之迅疾,说明标出性并非不能改变。女词人姜昕作词,虞洋作曲,姜昕演唱的《我不是一朵随便的花》,是另一个例子:于是我知道自己不是随便的花朵,只为梦幻的声音而绽放,希望我是特别的,不随着时间放弃,那些在我的心里,曾显得更加重要的声音。
女词人写出的“我”,立誓做一个“不切实际”的人。由此,被翻转的不仅是内容词句,更明显的是核心的“单边“概念对喻””:既然女子拒绝做“随便的花朵”,男性听者“你”也做不成任意采花的人,传统的“概念对喻”“花开堪折直须折”至少在这首歌里被颠覆了。而林夕作词,王菲演唱的《邮差》: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最后一双脚,惹尽尘埃。忙着去护送,来不及拆开,里面完美的世界。
信应当是被动物,被邮差主动搬动递送,在这首歌里翻转过来:女的是邮差,男的是信。而周杰伦演唱的《珊瑚海》干脆说“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这种绝对的不对称性,完全打破了惯有的性别“概念对喻”“。概念对喻”是语言整体的一部分, 但它并不只是一个工具, 而是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方式。文化的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隐喻思维构建了人类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反过来又改变着人的文化。既然所有的性别伦理体制都试图建构一整套性别言说规则,以此控制社会人的性别角色,让这些分野落在预订的文化标出性中,那么本文的论证可以引向一个有意义的结论:歌词中正越来越多出现的“概念对喻”标出性翻转,表征了当代文化令人深思的重要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