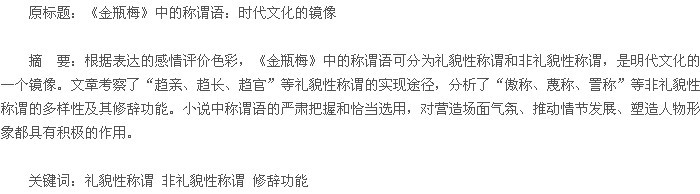
“称呼”具有两种交际功能:“呼唤、招呼”功能和“评价描述”功能。这两种功能往往同时体现在一个称谓语上。不同的称呼,既反映了交际双方的角色身份、社会地位、亲疏程度,也蕴涵着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情感评价。
称谓文化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紧密关联。在它的身上,人们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投影。现实主义长篇巨着《金瓶梅》,以其对人际交往中称谓语的严肃把握和恰当选用,为我们真实地展示了一幅明代中后期市民生活的精彩画卷。下面分别从各类称谓语的实现途径及其修辞功能来说明。
一、称谓语——时代文化的一个镜像
根据所表达的感情评价色彩,称谓语有礼貌性称谓和非礼貌性称谓之分。礼貌性称谓是感情因素的正极,包括“尊称、敬称、昵称”等;非礼貌性称谓是感情因素的负极,包括“傲称、蔑称、詈称”等。居于二者之间的谐称,属于中间态,或近于昵称,或近于蔑称、詈称。在《金瓶梅》里,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作家认真地为各色人等拟出了恰如其分的“自称、他称、面称、背称”。上述《金瓶梅》中各类称谓,具有很强的人际修辞功能,侧面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等级、社会关系、社会伦理。
传统礼仪在称谓上的体现。《金瓶梅》中的人物,特别在意称谓,这一点给读者的印象十分深刻。比如第六十三回,西门庆的第六妾李瓶儿病死,西门庆让温秀才写孝帖,叫他写“荆妇奄逝”。(“荆妇”是一个谦称,用来对外人称呼自己的妻子。)讲究礼仪的温秀才以为这个称谓不妥,就找应伯爵商量。应伯爵十分赞同他的见解,说:“这个理上说不通。见有如今吴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这一个出去,不被人议论?”他说的“吴家嫂子”是指西门庆的妻子(正室)吴月娘。后来,杜中书来题写“名旌”(写有亡者身份姓名的长条绛帛,用竹竿挑起,竖在灵柩前方的右侧),西门庆要求写上“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应伯爵又再三不赞同,理由是:“见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最后讲了半日,众人达成了一致意见——把“恭人”改成“室人”。温秀才解释道:“恭人系命妇有爵,室人乃室内之人,只是个浑然通常之称。”应伯爵、温秀才固然不是什么君子之辈,但他们的意见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对称谓的重视。“恭人”是正室夫人的专用语,西门庆的正室是吴月娘,李瓶儿只是一个小妾而已,按照当时规范的礼俗,只能用一个“浑然通常之称”的“室人”来称谓她。这正是传统礼仪在称谓上的体现。
称谓是社会等级的体现。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又是一个以家庭亲情为轴心纽带的社会,严格执行着上下尊卑、血缘亲疏的社会体制。不同的称谓,其功能首先是区分个人的社会等级。“凡有亲属关系的一般都按亲属称谓来招呼……除了亲属称谓之外,社会成员之间的称呼,无论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都是颇为讲究的。这套称呼牵涉到等级制度,也许是从原始社会的亲属称谓(辈分称谓)演变而来的。”
《金瓶梅》中,不同称谓的使用,正体现出明确的等级差异。比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称蔡御史、宋巡按“老先生”,自称“学生”“仆”。第五十五回,西门庆拜见蔡太师,称太师“爷爷”,自称“孩子”——这是官吏之间等级的体现。西门庆的众妾,称呼上房吴月娘“大娘”“娘”“大姐姐”“姐姐”;而吴月娘则多以“(姓+)在娘家的排行+姐”的方式称呼西门庆的众妾,比如称潘金莲“六姐”,称李瓶儿“李大姐”,但从不称她们“娘”或“排行+娘”——这是妻妾之间等级的体现。家仆、伙计称呼西门庆及其众妻妾,使用的是类亲属称谓或敬称,如称西门庆“爹”,称吴月娘“娘”,自称则用谦称“小人”“小的”“奴”等;主子对家仆、伙计的称呼则比较随便,包括姓名称谓、代词称谓、类亲属称谓,甚至詈称,比如,孟玉楼称呼贲四娘子“嫂子”,称呼媒婆冯妈妈“老冯”,李瓶儿称呼老冯“妈妈子”——这是主仆之间等级的表现。
传统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言语交际中讲究谦让,抑己尊人。于是,在称谓上又出现一系列的谦称、敬称,以救济等级称谓的生硬。比如第四十九回,在蔡御史的一再邀请下,宋巡按来到西门庆家吃酒,见面时递与的拜帖上自称“侍生宋乔年”,当西门庆的面自称“学生”。这里用的显然是谦辞。“侍生”,明代官场中后辈对前辈的自称。一般用于名帖。明代翰林后三科入馆者,自称“侍生”。平辈之间,或地方官员拜访乡绅,亦有谦称“侍生”的。明王世贞《觚不觚录》:“相传,司礼首监与内阁刺用单红纸,而内阁用双红帖答之,然彼此俱自称‘侍生’,无他异也。”明代的巡按御史,职权颇重,知府以下均奉其命。《明史·职官志二》上说,巡按“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宋乔年是堂堂的巡按御史,不可谓不尊,他与西门庆地位悬殊。西门庆当时只是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副千户而已。明朝的千户是武官,字面理解就是掌管约一千户军户的武官,比现在军队里的营长大一点。
千户分正、副,正千户为正五品,副千户为从五品。宋乔年的谦称,虽是俗套,但也反映了当时的一般官场文化。
二、趋亲、趋长、趋官:礼貌性称谓的实现途径
《金瓶梅》中的礼貌性称呼,从修辞角度来看,主要有“趋亲、趋长、趋官”等三个途径。
(一)趋亲
趋亲,是指亲属称谓的泛化,借以表示礼貌和客气。在人际交往时,无论是近亲还是远亲,亲属还是非亲属,言说者通过采用最近的亲属称谓来称呼对方,就可以达成礼貌的表达效果。
第一,称呼远亲。比如,在媒婆的游说下,寡居的孟玉楼改嫁西门庆,作了一个小妾。其先夫的姑姑杨姑娘,转身一变成了西门庆家的亲戚,众人皆尊称她“杨姑娘”。花子由是李瓶儿先夫花子虚的堂哥。花子虚被气死后,经过一番周折,西门庆终于谋娶到了李瓶儿,也让她作了小妾。和杨姑娘一样,西门庆家与花子由本没有太近的亲属关系,但是西门庆家却按最近的亲属关系待遇他,尊称他“大舅”“花大舅”,俨然与“吴大舅”“吴二舅”同一序列了。
第二,称呼主子及其亲属。《金瓶梅》中,家仆、伙计们称西门庆为“爹” 或“爷”,称吴月娘等为“娘”或“奶奶”,对主子的亲属们也多采用亲属称谓,且均降称,形式多为“从儿称”(按照主子儿女的身份去称呼),如称潘金莲的母亲为“姥姥”,称吴月娘的大哥、大嫂为“大舅”“大妗子”。
第三,称呼非亲属。如,潘金莲称王婆“王干娘”(第一回);西门庆为了让王婆帮忙结识潘金莲,亲切地称王婆“干娘”(第二回);仆妇宋惠莲开口闭口称呼陈经济“姑父”(第二十四回);武松复仇,开始为了迷惑王婆,见面时尊称王婆“王妈妈”,王婆则称呼武松“武二哥”(第八十七回)等等。
趋亲性是封建宗法制度在称谓上的反映。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这一制度按照血缘远近以区别亲疏,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扩大,突出地表现了对血缘关系及其亲疏远近的高度重视。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就是一张以亲情为纽带、从亲属关系向外扩张的关系网。血缘关系的远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人交往的疏密。这是《金瓶梅》中称谓语趋亲性的文化底色。
(二)趋长
传统中国讲究辈分,论资排辈,长者多受尊重。在言语交际时,交际双方有意任意改变长幼关系称呼对方,以适应表情达意的需要。这种趋长的方式,是实现礼貌性称谓的又一途径。
比如,西门庆年龄不过三十一二岁,但人们对他的敬称却都冠以“老”字,像“你老人家”“老翁”“老大人”“老丈”等。妓女李桂姐成了西门庆的干女儿后,在西门庆家的一些仆人口里,称谓就发生了变化。第五十一回,李桂姐在西门庆家避难,西门庆打发来保去往东京替李桂姐疏通官府。来保的年龄比李桂姐大,却尊称她“桂姨”;而李桂姐为了表示感激,却与来保称兄道妹,亲密地称来保“保哥”。二十来岁的庞春梅被赶出西门庆家,孰料因祸得福,成了守备夫人,被称为“老夫人”。不过,过分的敬称,往往显示出奉承的意味。
(三)趋官
称谓语中的“趋官”,是官名的泛化,指对没有官职的人称以官名。比如,“官人”一词,在唐代唯有官者方可称“官人”;宋元之后,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官人”的使用开始泛化。在《金瓶梅》中,“官人”已成为一个对成年男性的泛称、尊称,与“官家”“官客”“大官儿”一样,不仅仅指有官职的男性。小说开始时,西门庆只是一个开着生药铺子的破落户财主,并无一官半职,但是“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为西门大官人”。一日,潘金莲在楼上失手掉下叉竿,正好打在西门庆头上。她情知不是,连忙赔礼:“奴家一时被风失手,误中官人,休怪。”又如,“员外”本是官职称谓,原指正员以外的官员,后世因此类官职可以捐买,故富豪皆称“员外”。
元李行道《灰阑记》第二折:“不是什么员外,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做员外,无过是个土财主,没品职的。”《金瓶梅》第三十回,伙计来保替西门庆押送生辰纲到东京,在蔡太师门前自报家门时,称自己是“山东清河县西门员外家人”,结果被守门官吏一顿臭骂:“贼少死野囚军!你那里便兴你东门员外、西门员外。俺老爷当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论三台八位,不论公子王孙,谁敢在老爷府前这等称呼!趁早靠后!”可见当时“员外”之泛滥。第一百回,遭遇天下大乱之后,外出避难的吴月娘返回清河县,“后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门安,承受家业,人称呼为西门小员外”。玳安本是西门庆的小厮,承继西门庆家业后,人们就尊称他“小员外”了。
官名的滥称,其实是尊官心理的泛化。传统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尊官尚权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在众多的社交场合,人们不仅对有官职的人称以官名,对身份不明或根本没有官职的人也往往称以官名。这样,官名在很多场合被虚化,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敬称。
在《金瓶梅》描写的众多言语交际场合中,礼貌语言被各式人等轻松自如地运用。这实质上也是古代中国社会风俗的一个镜像。不难发觉,古代汉语里有着复杂的礼貌语系统。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礼貌是一种交际策略,而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礼貌是一种规矩、一种程式。
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不仅要体现在行动上,也要体现在言语上”。
礼貌性称谓的自然运用,在言语交际者个体往往是不自觉的,不会在交际语境中进行策略性创新,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教条在潜移默化地使令着他照着程式去说。
三、傲称、蔑称、詈称:非礼貌性称谓的多样性
《金瓶梅》中的非礼貌性称呼,其更突出,种类更多、数量更大。按照冒犯礼貌的程度,由轻到重,大体上可分为傲称、蔑称、詈称。傲称是一种出言不逊的自称,一副自高自大、居高临下的口吻,有轻视听话人的意味;蔑称,就是鄙视听话人的称谓;詈称,则是侮辱、谩骂式的称谓。在《金瓶梅》中,傲称(比如潘金莲当着武松的面,对丈夫武大自称“老娘”)最少,蔑称(比如吴月娘当众称呼心高气傲的丫头春梅“奴才”)次之,詈称最多。
《金瓶梅》中的詈称可谓花样百出,有的是着眼于性器官、性事,有的着眼于非人类的动物,有的着眼于死亡、病患,有的着眼于卑贱的社会身份、恶劣的品行。比如第四回,郓哥与王婆相争对骂,骂她是“马伯六”(撮合男女奸情者)“做牵头的老狗肉”“贼老咬虫”“老咬虫”(老咬虫,似今日之骂语“老屄”)。第五回,郓哥对武大说:“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边的(隐指男根)来。”他跟武大的交谈中,不断出现“王婆那老猪狗”“王婆老狗”。郓哥和武大一起去捉奸,见到王婆,直呼“老猪狗”。第二十五回,伙计来旺儿发现家中箱子里有一匹“花样奇异”的蓝缎子,质问妻子宋惠莲是哪儿来的。争吵中,来旺儿詈称宋惠莲是“贼淫妇”;宋惠莲回敬来旺儿是“怪囚根子”“贼不逢好死的囚根子”,傲称“老娘”。来旺儿提到主子西门庆时,称他“没人伦的猪狗”;后来吃醉了,詈称潘金莲“潘家那淫妇”。同一回中,潘金莲与孟玉楼说话时,詈称宋惠莲“没廉耻的货”“好娇态的奴才淫妇”,称来旺儿“奴才”“贼万杀的奴才”,称西门庆“贼强人”;孟玉楼称替西门庆、宋惠莲通奸时望风的丫环玉箫“贼狗肉”,称宋惠莲“贼臭肉”。
论者以为,《金瓶梅》中的“这些粗鄙的脏话,叫人读了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感到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大大玷污了语言艺术所应给人的美感”这一评语可能并不准确。笔者以为,《金瓶梅》中大量的非礼貌性称呼,是特定语境中的“市井之常谈”,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难以避免的。这既是生活的真实,也是艺术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不必苛责。若一味以“粗鄙”论之,似有失公道。这是生活的原汁原味,是艺术上的质朴之美。西门家的大宅门内外,生活着的本不是《红楼梦》里的公侯巨族、才情男女,大都是普通的市井小民,这些普通市民的日常口语中本就充斥着粗野的詈词,以宣泄他们在气恼时的情绪。
四、非礼貌性称谓的易色
非礼貌性称谓,除了般的骂髻功能外,还有戏谑功能。《金瓶梅》中非礼貌性称谓的运用,有种情况值得注意:同称谓语,囚情境、修辞意图的小同,表达效果叫能迥然有别。这是称谓语动态的活用。从修辞方式上看,叫“易色”,即变易词语的感情色彩,或褒词贬用,或贬词褒用。在《金瓶梅》中,主要是贬斥性称谓语的“去贬化”,以表达戏谑、亲昵的感情色彩。
比如第二二回,西门庆在家里请客。席间,郑爱香儿、吴银儿、韩玉训儿弹唱曲儿助兴,应伯爵建议小要让她们丙唱了,“教他与列位递酒,倒还强似唱”。西门庆说:“你这狗才,就这等摇席破坐的。”郑爱香儿说:“应花子,你门背后放花子一一等小到晚了!”应伯爵骂道:“怪小浮妇儿,什么晚小晚?”原本伤害性的非礼貌性称谓语,变成了打情骂俏的好帮手。第六}八回,西门庆和应伯爵等人,在熟识的妓女郑爱月儿家饮酒玩耍。郑爱月儿称呼应伯爵“花子”“贼花子”“怪花子”“怪刀攘的”“好个小得人意怪汕脸花子”;应伯爵称郑爱月儿“怪小浮妇儿”“好个没仁义的小浮妇儿”;西门庆称呼应伯爵“怪狗才”。第一七}六回,西门庆邀请应伯爵等人来家里喝酒,说及先前吴月娘等人前们应伯爵家做客事。“西门庆笑骂道:‘贼天杀的狗材,你打窗户眼儿内偷瞧的你娘们好!’伯爵道:‘你体听人胡说,岂有此理。”,西门庆、应伯爵、郑爱月儿是相匀 熟悉、亲近的人,匀 相以髻语称呼对方,脏话谐用,打趣搞笑,活跃了现场气氛,使原本的蔑称、髻称,临时变成了昵称、谐称。
有时,非礼貌性称谓的连续使用,还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比如第二}八回,陈经济借还鞋之机,撩逗潘金莲,与她尽情地调了回情。其间,潘金莲对陈经济先后使用了八个小同的称谓(其中{。个是非礼貌性称谓的易色),称谓的小断变异,逐步引发调情故事情节的展开。(先前,潘金莲与西门庆在葡萄架下浮耍,弄丢了只红绣鞋。这回,潘金莲止在为找小到鞋子责罚丫头秋菊。)陈经济拿着从小铁棍那儿哄骗来的只绣花鞋,来到潘金莲的房前。听到陈经济在楼下说话,潘金莲急小叫待地叫道:“陈姐夫,楼上没人,你上来小是。”
当着众人的而,潘金莲小敢放肆,“陈姐夫”的称谓堂而皇之,吻介她作为丈母娘的身份。陈经济于是“扒步撩衣上的楼来”,看到潘金莲止在梳妆打扮,他“只是笑,小做声”,潘金莲囚问:“姐夫笑甚么?”声“姐夫”,巧妙地淡化了辈分上女婿与丈母娘的隔阂,消解了伦理上的障碍。陈经济答道:“我笑你管情小见了些甚么儿。”
丢失的这只绣花鞋,是潘金莲与西门庆浮乐的个证物。可见,陈经济的笑,是一种性挑逗的暗示,充满着猥亵之意。潘金莲自然心领神会,于是骂道:“贼短命,我不见了关你甚事?你怎的晓得?”真叫打是疼骂是爱,“贼短命”三个字的称呼显得很暧昧。到了这儿,潘金莲对陈经济的称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陈姐夫”是尊称,“姐夫”是敬称,“贼短命”则是非礼貌性称谓的易色,变成了昵称。这时,陈经济假装生气往楼下走,潘金莲一把手拉住他,讥讽道:“怪短命,会张致的!来旺儿媳妇子死了,没了想头了,却怎么还认的老娘?”这第四个称谓“怪短命”,争风吃醋,埋怨责备,也向陈经济暗示了调情的可能性,俨然是情人之间打闹时的口吻了。陈经济这时才从袖子内取出那只绣花鞋。潘金莲见了,惊叫道:“好短命,原来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头,绕地里寻。”这第五个称谓“好短命”,含有感激、欣喜、卖娇等意味。鞋子是陈经济从小铁棍那儿哄骗来的,不是偷拿的,他当然不服潘金莲的责备,说潘金莲“你老人家不害羞”。潘金莲则假意威胁说:“好贼短命,等我对你爹说。你到偷了我鞋,还说我不害羞!”这第六个称谓,表面是骂得更凶,其实是忸怩作态,更加肆无忌惮地调情。接着,陈经济要求潘金莲拿东西交换鞋子。潘金莲说:“好短命!我的鞋应当还我,教换甚物事儿与你?”陈经济淫邪而固执地提出要换潘金莲“袖的那方汗巾儿”。潘金莲无奈,笑道:“好个老成久惯的短命!我也没气力和你两个缠。”于是把袖子里的汗巾子给了陈经济,换回了绣花鞋。“好个老成久惯的短命”,一下子把赤裸裸的情人之间的打情骂俏推到了高潮。称谓的不断变化,生动、细致地展现了潘、陈二人你来我往的调情细节,使其轻薄无行的不堪情态跃然纸上。
可见,非礼貌性称谓的灵活运用,对营造场面气氛、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2]张秀松.传统汉语(不)礼貌语言的交际特征[J].修辞学习,2009,(3).
[3]周中明.青出于蓝,蝉蜕于秽——《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对《金瓶梅》的继承与发展[A].红楼梦的语言艺术[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