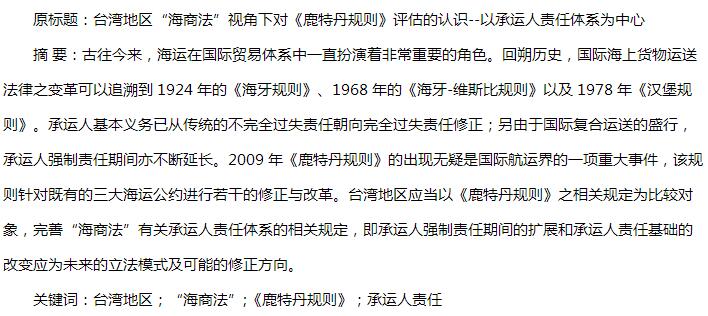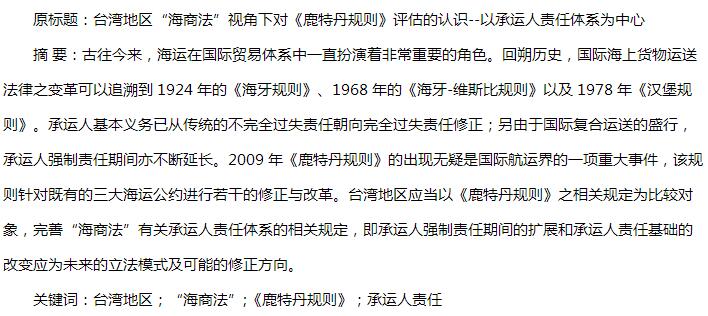 一、台湾地区“海商法”承运人强制责任期间之界定
一、台湾地区“海商法”承运人强制责任期间之界定
所谓承运人强制责任期间,系指运送人在该段时间内,不得以特约免除或减轻其运送责任。目前台湾地区“海商法”针对承运人履行保障运送货物避免毁损灭失的注意义务种类,可以区分为船舶适载性义务与货物照管义务。前者规定于“海商法”第 62 条①,后者规定于“海商法”第 63 条②。
对于“海商法”第 63 条所称的“装载、卸除、搬移、堆存、保管、运送及看守”,有学者认为系依运送作业的顺序为排列,继而与“海商法”第 76 条做整体的解释③,即认为此等搬移货物的运送作业必须与履行海上运送契约相关。换言之,承运人必须在海上运送阶段或在商港区域范围内进行货物照管义务,才有“海商法”强制期间的适用。针对前述观点,有研究认为,结合“海商法”第 63 条及第 76 条的规定,“海商法”对于运送人强制责任期间已可以被解释为由传统《海牙规则》的“钩致钩原则”扩充至《汉堡规则》的“港至港原则”①。但检视“海商法”第 76 条的规定,其第 1 项谓“有关运送人因货物灭失、毁损或迟到对托运人或其他第三人所得主张之抗辩及责任限制之规定,对运送人之代理人或受雇人亦得主张之”,并未提及是否扩张至陆运阶段;又其第 2 项仅谓“对从事商港区域内之装卸、搬运、保管、看守、储存、理货、稳固、垫舱者,亦适用之”,应解释为仅适用于商港区域内的运送人之代理人或受雇人可以适用运送人的主张抗辩或责任限制规定,其亦无法导出“海商法”关于承运人强制责任期间已实行《汉堡规则》的“港至港原则”的责任形态,故“海商法”第 76条应该是喜马拉雅条款的法条化,目的是在海上货物运送,承运人就其承运货物所可以主张免责抗辩或责任限制抗辩,运送人的代理人或受雇人也可以主张或援用,其立法目的系为保障运送人之履行辅助人。②所以,此规定是否扩张了“海商法”关于承运人强制责任期间的范围,进而与《汉堡规则》采取相同的“港至港原则”,显有疑义。
又从“海商法”第 62 条所规定承运人对于承运货物的照管义务内容观察,其包括“装载、卸除、搬移、堆存、保管、运送及看守”等七个项目。可知,本条应是沿袭《海牙规则》第 3 条的规定,该规则第 3 条内容为“除第 4 条另有规定外,运送人对于所承运的货物应该适当且谨慎地装载、搬移、堆存、运送、保管、看守以及卸除”(Subject to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Ⅳ, the carrier shall properly andcarefully load, handle, stow, carry, keep, care for, and discharge the goods carried.)。又观察 1924 年《海牙规则》及 1968 年《海牙-维斯比规则》的强制责任期间,参考前述规则第 1 条第 5 款规定:“货物运送,包括自货物装载上船至货物自船舶卸除的期间”(“Carriage of goods”covers the periods from the timewhen the goods are loaded on to the time they are discharged from the ship③);换言之,由《海牙规则》关于货物“装载”及“卸除”的规定,配合货物运送界定为海上期间的规定,构成了承运人强制责任期间限于所谓的“钩至钩期间”.因此,前述定义所示期间系指货物挂上起重机之吊杆索具开始,而非指货物实际上已装载上船的时后才开始;而“卸除”系指货物已卸于驳船或岸上,自货物脱钩时止。比较“海商法”第 62 条有关承运人“装载”及“卸除”之货物运送义务,显然与《海牙规则》第 3 条规定之内容相同。于当前“海商法”是否适用《汉堡规则》所实行的“港至港原则”尚有疑义之前提下,本文倾向认定“海商法”关于承运人货物照管责任之强制期间同于《海牙规则》的“钩至钩原则”.
综上,“海商法”关于承运人强制责任期间应限于“海运阶段”,而“海运阶段”之前或后的“非海运阶段”,应如同《海牙规则》一般,属未规定之范围,委诸各国国内法规定(例如“海商法”第 75条)。如各国国内法未设规定,双方当事人可本诸契约自由原则,约定适用《海牙规则》或《海牙-维斯比规则》。
二、台湾地区“海商法”运送人之基本义务
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关于运送人之基本义务可汇整为“提供适航能力船舶义务”(“海商法”第 62 条)、“货物照管义务”(“海商法”第 63 条)及“禁止偏航义务”(“海商法”第 71 条);同时,此三种义务具有强制性,不得以合同条款减轻或免除,承运人对此三项基本义务之履行与否,将可能与其是否能主张免责事由之利益有关,本文以下将侧重探讨船舶适航性义务与货物照管义务之关联性,并兼论货损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