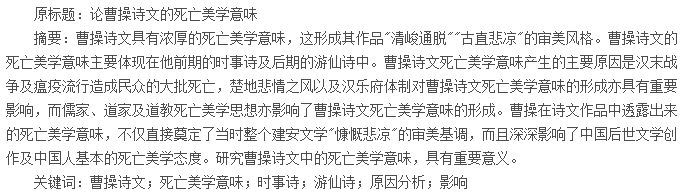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重要开创者,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评价建安文学的审美特征时曾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①"梗概多气"被刘勰视为建安文学最主要的审美特征。作为建安文学重要的代表作家,曹操的文学作品整体上表现出"清峻通脱""古直悲凉"等审美特点。
南宋敖陶孙在《臞翁诗评》中谈及曹操的诗歌创作时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②顾随在《东临碣石有遗篇---略谈曹操乐府诗的悲、哀、壮、热》一文中特别突出了曹操乐府诗"哀"和"悲"两个审美特征,他说:"有些地方,我到底不能不同意刘勰和钟嵘对曹诗所作的批评:'哀'和'悲'."从近年来的曹操文学作品研究来看,大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渗透在曹操文学作品中哲学思想的分析,如,探究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等对曹操作品的影响;二是对曹操作品文体形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曹操乐府诗、五言诗、四言诗、杂言诗以及散文等文体形式的研究上;三是对曹操诗文作品中美学思想的分析,如,对曹操作品中深刻的生命意识、忧患意识、自然意识及功业意识等展开研究。当然,也有一些论者主要着眼于曹操作品艺术特征的分析,如,善用质朴的形式披露胸襟,作品风格清峻通脱等。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曹操文学作品的基本内容及美学意蕴具有重要意义,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曹操的文学研究。
但笔者认为,曹操诗文所呈现的"古直悲凉""哀""悲"等审美特点,一般的评论角度还不足以把其内在的精神透视得更加深刻,因而,对它的解读应该引入一些新的思路和视角。笔者认为,曹操诗文作品之所以会呈现出"古直悲凉""哀""悲"等审美特点,与曹操对死亡的深刻体悟直接相关,换言之,正是曹操对死亡有独特的感知,才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深厚的死亡美学意味。因此,我们不妨采取死亡美学的视角,来探察和体味蕴藏在曹操诗文内部的审美意蕴。死亡美学,顾名思义,即是基于死亡作为人的内在必然的生命经验,思考死亡对于人生和现实生活的积极建构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悲怆痛感甚或审美愉悦,特别劝慰人"怎样以他的自由精神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和困顿",①进而积极筹划自我有限的人生,最终通过对死亡进行深刻的哲思,来解蔽人的非本真生存状态,使人回复到生命的本真性与整体性。
一、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之体现
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的体现,我们可以按前期作品和后期作品这两个部分来进行探察。
关于曹操文学作品的历史分期问题,目前依然存在分歧,比如,陆侃如和冯沅君根据诗歌的形式体制,认为曹操的游仙诗,如《气出唱》《精列》以及《秋胡行》等,属于第一时期的"模拟古乐府"时期;而《步出夏门行》《苦寒行》《短歌行》等一些抒情诗和政治诗属于第二时期的"借乐府以说自己的话"的时期。②但更多的论者,如清人陈祚明,近人黄节、丁福林等,皆认为游仙诗系曹操晚年所作,"陈祚明于《采菽堂古诗选》中称《精列》一诗'当年暮之感,徘徊于心'而作。黄节考证《秋胡行》二首乃建安二十年,诗人61岁高龄所作。后又有丁福林等多方论证曹操其他几首游仙诗的写作年代,认为游仙诗属于曹操晚年作品".③笔者基本认同后者的观点,即游仙诗大概为曹操晚年作品。而《薤露行》及《蒿里行》这样的时事诗,却大致为曹操前期的作品。因为《薤露行》描写的主要是何进谋诛宦官、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之事,因此,这样的时事诗应是初平元年(190)所作,时年曹操36岁。而《蒿里行》中因有"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事情,这首诗大致写于建安二年(197),时年曹操43岁。
就曹操前期作品看,即浸染有一种深沉的死亡美学意识,这种死亡美学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国殇之感及对人生短促的慨叹。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薤露行》《蒿里行》及《短歌行》等诗文中。
首先就《薤露行》及《蒿里行》两首诗来看,这两首诗的体制都是汉乐府旧题,本来就是一种丧歌,形式本身自蕴一种悲哀的情调。晋人崔豹《古今注》(卷中《音乐》第三)曾对此解释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
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曦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④曹操似乎明晰这两首乐府旧题诗的体制、格调,两首诗一为哀君,一为哀民,表现的都是深重的死亡主题。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言:"《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无论表现的是一种国殇之情,还是伤生之叹,我们都认为其深深体现了曹操浓厚的儒家情怀---仁民爱物,恻隐天下。"铠甲生饥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里内隐了一种深重的忧愤和哀伤。
曹操虽然"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⑤尚刑名之说,崇墨子之俭,但他的主体思想实际上秉具一种热诚天下的儒家情怀,这不仅表现在《蒿里行》中,而且表现在《对酒》《短歌行》(其二)中,以及一系列政令如《修学令》《整齐风俗令》《以高柔为理曹掾令》《告涿郡太守令》《赡给灾民令》等中。值得强调的是,《薤露行》与《蒿里行》这两首汉乐府古辞本为感慨人生的短暂与无常,意境深而狭,曹操则予汉乐府以旧题写新事的革新,扩大其气象与格局,悲慨国家之倾覆与生民之涂炭。
其次再来看《短歌行》。《短歌行》亦是汉乐府旧题,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寿命长短定分,不可妄求也。"⑥也即是说,《长歌行》和《短歌行》题制本来是言人寿命短长的。宋人郭茂倩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所谓长歌、短歌本指歌声长短,非言人之寿命短长。叶嘉莹则折中二人看法,认为"最早的短歌、长歌,只是表示歌声的长短,与寿命并无关系。
但曹操的这首《短歌行》慨叹了人生寿命的短促,所以后世的仿作就都受到曹操这一首诗的影响,都来表示这种慨叹了".⑦由于《古今注》距汉未远,似应以《古今注》解释为准,即《短歌行》主要言人寿命短长,无可妄求。据《乐府解题》的说法,《短歌行》主要言"当及时行乐"的主旨,但通篇看来,隐隐表达了曹操建功立业、延揽人才的热望,其中蕴藏着无限的死亡美学思想。诗文开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让人生发出对生命短暂的无限慨叹。而这样的死亡美学思想早在《古诗十九首》中就得到了大量表现,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飙尘""人生非金石,焉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等。曹操无疑深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表达人生如寄的感慨。
但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曹操的死亡美学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表现人生短促的哀感中,往往还"结合有英雄的志意",以及"一种惟恐这志意落空的忧愁".①这样,曹操关于死亡的理解就具有了一种昂扬的情调,而不仅仅是一种低回哀伤的情感。他赋予死亡以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嗣死亡美学思想的超越,亦是对《左传》"三不朽"思想的有力继承。在谈到对死亡恐惧的超越时,培根曾经这样说:"人类可以召唤许多伴侣,帮助人克服对死的恐惧---仇忾之心压倒死亡,爱情之心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哀痛之心使人奔赴死亡,而怯懦软弱却会使人在死亡尚未到来之前心灵就先死了。"②曹操通过选择责任与荣誉超越了死亡对人生的限制,重建了人类的尊严,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民生的拯救。
从曹操前期作品中对待死亡的美学态度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曹操是客观的、积极的,他企图通过建功立业来超越死亡,并在一定意义上是无神论的。且他的死亡观远远超越了个体生命的阈限,建立在对民众普遍的同情之上,从而不同于《古诗十九首》那种沉陷于个体生命对命运、死亡不可避免性的无限忧伤。
与前期作品相比,曹操的后期作品对死亡的理解显然有了不同。一方面,对死亡的认知更多的是从个体生命的感受出发,认识到死亡是一种私人性很强的个体事件,而不像前期更多的是从国家层面出发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对死亡的超越方式也有了明显改变。在前期,曹操主要通过建功立业的方式来超越死亡;到晚期,则主要通过导引、辟谷、房中术等方法来超越死亡。这种死亡观深刻地影响了曹操的游仙诗创作。
首先,面对有限的人生,晚年的曹操不由发出"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的感喟。《精列》云:"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周孔圣徂落,会稽以坟丘。"《秋胡行》其二曰:"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却东西门行》言:"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步出夏门行》曰:"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其次,面对死亡,曹操希冀通过养生来达到神仙境界,这表现在其游仙诗中就是多了一份脱去俗累的逸气,少了一份沉重的悲郁之情。
如《气出唱》其一言:"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精列》则云:"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思想昆仑居。见期于迂怪,志意在蓬莱。"《陌上桑》曰:"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秋胡行》亦云:"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沉吟不决,遂上升天。"曹操的游仙诗固然一方面受到了汉乐府游仙诗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对庄子逍遥游及楚辞远游思想的继承。所以,曹操的游仙诗与其说是体现了道教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宗教美学思想,不如说是更多地体现了曹操对庄子、屈原美学思想的追寻,即对一个深挚、纯粹、自由世界的渴望,这一点从曹操游仙诗中大量的审美意象,如"昆仑""螭龙""芝英""秋兰"等可看出。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曹操诗文作品中渗透着的死亡美学意味,深刻地体现了曹操对待死亡的基本美学态度,即死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可以被书写且被超越的,无论是"立功"还是"方术",都是曹操超越死亡的基本姿态。体悟这一意味,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体味到曹操作品"慷慨悲凉"的美学风格。
二、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之产生原因
曹操诗文作品中死亡美学意味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汉末战争不断及瘟疫流行,造成民众的大量死亡,是曹操诗文作品中死亡美学意味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汉末,自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两京涂炭,典章残落,文教板荡。袁绍、袁术、刘表、刘备及孙权等割据一方,征伐不断。对此,孔融有诗云:"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惨惨心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曹操在《蒿里行》中的诗句,也是曹操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种悲惨的社会景象激发起曹操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沉重思考,即死亡作为一种存在,不是遥远和偶然的事件,而是普遍存在于现实人生。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生命脆弱易逝,充满无常,整个社会由此也充满了伤生之叹,沾染上哀怨难抑的气息,甚至出现"乐生逸身""及时行乐"的哲学思想,这一点在《列子》一书中可见端倪。
在《列子·杨朱篇》中,"宴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宴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①《列子》虽是伪书,但鲜明地体现了魏晋人关于生命和死亡的基本态度。曹操自然不可逃逸出这样遍地充满死亡景象以及及时享乐思想的社会氛围,这深深影响了曹操诗文作品的创作,并对其"慷慨悲凉"诗风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作用。鲁迅在分析曹诗"慷慨"的特点时说:"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②由此看来,文学并非高蹈于尘世之上的虚构性存在,而是隐藏着现实生活的浓重阴影。
其次,楚地悲情之风也影响了曹操诗文中死亡美学意味的产生。汉代文化直接继承南方楚文化而来,楚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至深。楚文化相对于北方的中原文化,尊火崇凤,信鬼好祠,与尊土崇龙、务实理性的中原文化明显不同。大致说来,楚文化有三大特点值得注意:一是鲜明的巫文化色彩;二是凄怆的悲文化特色;三是浮艳的楚骚文风。就楚文化重"悲"的特点来说,与楚文化对死亡的敏锐感知有密切关系。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如庄子、屈原等,对死亡都进行过深沉的思考。在庄子看来,人的生命的展开和消失在本质上都不过是一气的化合而已,"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死只不过意味着人又回归到自然大道中,是非常自然的行为,更何况人活着"终身役役,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③因此,死亡对于人来说意味着一种绝对的解脱和休息。④对于庄子来说,死亡不但不令人恐惧,而且让人无限向往。
庄子的这种"乐死"死亡观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楚文化对于死亡的基本观念,即死亡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普遍而又自然,楚文化由此浸染上深深的悲情色彩,从而与"未知生,焉知死"的北方中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屈原在《离骚》中也表现出深深的死亡情结,他一方面叹"日月忽其不淹兮""老冉冉其降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另一方面又看到"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于是,决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身沉汨罗江。屈原的《离骚》表现出深深的死亡本能冲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屈原的"死亡情结"和"美人情结"共同构成了其创作的鲜明特点,使他的创作表现出郁伊怆怏、缠绵悱恻的审美特征。无疑,以庄子和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死亡思想对曹操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次,汉乐府体制对曹操诗文作品死亡美学意味的生成也具有重要作用。就曹操目前留存的诗歌创作看,全部采用了汉乐府体制,由此可以看到汉乐府对于曹操创作的重要影响。但曹操对于汉乐府旧题并非一味的继承,而是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写法,并不拘囿于汉乐府的旧题,这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启示。游国恩认为,从曹操的"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承的发展".⑤第二,汉乐府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曹操诗歌的美学情味,使曹诗呈现出悲慨的情调,但曹诗却大大扩充了汉乐府诗的气象,使之显得雄浑朴质,豪放自如。比如《薤露行》《蒿里行》《精列》和《短歌行》等由于本身就是一种丧乐,大多属于汉乐府中来自民间的、风格凄怆哀怨的"清商乐"⑥,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曹操诗歌的审美情调,增加了曹操诗文作品中的死亡美学意味。但曹操却把"清商乐"提高到了国家叙事的层面,在其中寓以宏大主题,抒写自己建功立业、平治天下的抱负,这不仅扩大了汉乐府的题材,而且提升了汉乐府诗歌的境界。但无论如何,一些汉乐府旧题所内蕴的死亡主题及悲哀情调却是不可被抹杀的,它们客观上还是决定了曹操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选择及色调设置。
最后,曹操诗文作品中死亡美学意味的形成还与儒、道死亡美学思想的影响有关。先来看儒家的死亡美学思想。中国儒家文化重生乐生,对死不予过分关注,孔子以"未知生,焉知死"来拒绝对死亡的深入思考。儒家文化只提倡一种情境下的死亡:当仁义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才成为唯一的选择。对于死亡,儒家提供了两种超越的手段:一是通过肉体层面的繁衍来超越,后来发展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核心的孝文化;二是通过"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来超越。
儒家死亡文化中尤其是崇实黜虚、远离鬼神以及"三不朽"的思想,对曹操无疑具有极大影响,使曹操不言天命,不语鬼神,且悲悯众生。曹操生活于汉末,谶纬迷信之风盛行,但曹操从不虚言谶纬之事,并严拒淫祀。中平元年(184)任济南相时,曹操不仅奏免了八名阿附贵戚、赃污狼藉的官吏,且"禁断淫祀",由此奸宄逃窜,郡界肃然。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中,曹操曾自述"不信天命之事".至于《春祠令》中"祭神如神在"之类的话,最多不过是对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思想的继承罢了。再来看道家及道教的死亡美学思想。道家文化全真养性,重生重死,至庄子甚至轻生乐死,对死亡采取了齐物论的态度,无生无死,方生方死,生死为一。后来的道教文化扬弃了庄子的乐死思想,更多地继承老子修身重生及渴求长生久视的思想,又汲取神仙学说中羽化成仙的思想,从而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死亡美学观。
道家及道教死亡美学思想中特别是庄子全真养性的思想、逍遥游思想,以及道教长生久视、羽化成仙的思想与神仙学说中"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的思想,对曹操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影响了曹操的死亡观,而且直接影响了曹操游仙诗的创作。曹操晚年更直接信奉了方仙道。方仙道是战国末期的神仙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方术与道教的合一,其特点是重视方术养生,以期长生不老。在《与皇甫隆令》中,曹操曾问皇甫隆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①后来张华在《博物志》卷五《方士》篇曾记载武帝对皇甫隆提供的养性法信奉不已,并"行之有效".其实,何止皇甫隆,甘始、左慈、封君达等,"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
虽然至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起,经学失势,儒教零替,社会风尚以"通达"为旨,追求清谈,儒家死亡美学思想从而有所衰落,但儒家"仁"的思想及死亡美学观念与道家及道教的死亡美学思想还是影响曹操甚深,从而共同铸就了曹操独特的死亡美学观。后来的曹丕进一步发展曹操的死亡美学观念,喊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③的口号,把"立言"而不是"立功"作为超越死亡的不朽盛事。
三、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之影响
曹操诗文中流露出的死亡美学意识,无论对当时的建安文学,还是对后世的中国文学创作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并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基本的死亡美学态度。
首先,在一定意义上说,曹操的死亡美学思想直接奠定了当时整个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审美基调。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评论曹操文章的特点时,曾说曹文虽缺少曹丕、曹植的"华丽壮大",然"清峻通脱",卓然众人。这看法大致不错。但曹操以古直苍浑、不屑翰藻之故,被贵气尚词丽的钟嵘列于下品,可谓不公允。但钟嵘言"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把曹操诗歌的特点界定为"古直""悲凉",亦可谓抓住了曹操诗歌的根本特质。曹操诗文的这种审美特点当然与其死亡美学思想密不可分,故其诗文创作处处沾染上死亡美学的气息。
曹操诗文的这种死亡美学意味对当时影响甚大,对"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作用,整个建安文学都普遍具有"慷慨悲凉""梗概多气"的审美特点。建安文学作品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大都"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具有拂之不去的无限哀愁与伤感。曹丕的《悼夭赋》《寡妇赋》,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建安七子"孔融的《杂诗》"远送新行客"、《临终诗》,王粲的《七哀诗》等,都具有深厚的死亡美学意味。如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整个诗篇都沉浸在因任城王之死引起的郁郁悲惋气氛之中,诗歌采取"辘轳体"的写法,将"忧虞之感、离别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隐衷惋绪,使人读之不觉叹惋。孔融的《杂诗》"远送新行客"则写悼子之情,情真意切,令人伤痛欲绝。余不赘述。
其次,曹操诗文作品中流露出的死亡美学意味还深深影响了中国后世文学创作及中国人基本的死亡美学态度。曹操的文学创作开创了一种面对岁月流逝、英雄迟暮而功业未竟、企图一展怀抱的英雄叙事模式。这种企图通过"立功"来拯救民生、超越死亡的英雄叙事模式影响后世甚深,无论是初唐的陈子昂,盛唐的李白、杜甫,还是宋时的苏轼、辛弃疾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曹操英雄叙事模式的续写者。如,李白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辛弃疾的《摸鱼儿》《菩萨蛮·书江西口造壁》《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曹操英雄叙事模式的书写,是对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思想的继承,虽有死亡的逼迫,但还是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人主体性的意志胜利。在对待死亡的美学态度上,曹操实现了儒家和道家、屈骚美学思想以及道教的合一。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曹操主张实行薄葬,这固然反映了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的性格特点,也部分反映了曹操体恤民生的深厚情感,但其实质上是反映了曹操对死后世界的淡泊。曹操诗文中流露出的死亡美学意味,对中国人的死亡美学态度也起到了重要影响,使中国人在死亡面前不卑顺、不柔弱,而是挺然而立、亢然而行。
综上所述,曹操诗文的死亡美学思想虽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汉代思想范畴,但把对死亡的超越方式同建功立业结合了起来,无疑大大发展了汉代的死亡美学思想。研究曹操诗文中的死亡美学意味,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曹操诗文内在精神的深刻理解,而且对魏晋时期普遍存在的死亡美学思想也可有一个概观,这对于我们研究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及哲学思想亦具有很大帮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曹操诗文中流露出的死亡美学意味进行省思,可以使我们更坦然地面对死亡,进而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建构我们的自由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