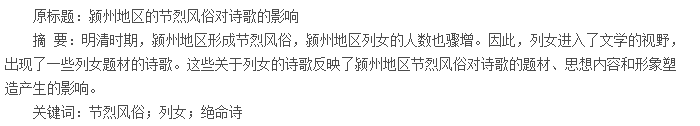
明清时期,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颍州地区形成节烈风俗。从此,列女不仅作为社会上一个普遍而特殊的社会群体,还成为诗歌的抒写对象。《颍州府志·艺文志》中收录的六首关于列女故事的诗歌以及《明清安徽妇女着述辑考》中辑录的方氏两首《绝名词》和郎氏十首《绝命诗》,这些诗歌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节烈风俗对列女题材诗歌的题材、思想内容和形象塑造三方面产生的影响。
在这里做一些必要的说明:方氏,据清朝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卷十八记载:“方氏,安徽亳州人,梁俊业室,俊业早亡,只遗一子,甫四龄而夭,氏以身殉。”郎氏,《民国阜阳县志续编·文艺·诗文》中记载:“吕克昌妻郎氏,邑庠生郎锡类女,聪慧工诗。年十九归克昌,事孀姑以孝闻。夫勤读得痼疾,扶持调护,日夜维谨。夫病久不愈,侍汤药衣不解带数月。夫殁,殓后,集族党立夫兄德昌子嗣。竣,从容坠楼殉节,仅伤臂,未死。越数日,服铅粉、复吞金戒指,又遇救未死。忍待葬夫回,隔日即乘间投渠死矣。濒死前一夕作书别母,并赋《绝命诗》。 ”
根据这些资料可知,方氏和郎氏具有列女中节妇和烈妇的特质--夫死殉夫,所以她们应该分别属于节妇和烈妇。而且她们的籍贯是亳州和阜阳,这两个地方隶属于颍州地区。
一、颍州地区节烈风俗
风俗,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中自发的逐渐形成的一种历代相传的社会习惯。它作为一种浅层的民族精神文化反映着人们对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共同看法和做法。
因此,风俗是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风俗会随着社会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颍州地区的风俗也是如此。
据《颍州府·舆地志·风俗》记载: 旧志云:“士励读书,民安耕凿,女子慕节义,殉夫者接踵。”明清时期,颍州地区形成一种崇节尚烈的社会习惯。颍州地区的节烈风俗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颍州地区广大女性亲身的实践使颍州地区特殊的女性群体更为庞大--列女。列女是一个群体集合名词,根据不同划分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颍州府志》中的列女分为贤母、孝女、孝妇、贞女、烈女、烈妇、节妇七个类别。她们主要生活在明清时期,据统计,明朝颍州地区共有列女 529人。清朝(1636 年-1752 年)时共有 810 人。明清两代颍州地区列女总计为 1339 人。
二、颍州地区节烈风俗对诗歌的影响
文学是由文学创作的主体创造的,而文学创作主体是在或大或小的民俗环境中生存和成长的,风俗文化传统必然会对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性情等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这种影响通过他们的作品展示出来。同样,颍州地区的节烈风俗对明清时期颍州地区的列女题材的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节烈风俗对诗歌题材的影响
在颍州地区节烈风俗的影响下,颍州地区的女性通过世代相传、互相仿效、不断重复的方式,成就了上千位列女。列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她们拥有自己的价值追求,自己的爱恨痴怨。孝女孝妇的至孝,烈女烈妇的刚烈,贞女节妇的坚贞,这组成了另一幅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画卷。文学来源于生活,毫无疑问,这幅生活画卷应该成为诗歌的描写素材。因此,节烈风俗开拓了诗歌的题材。
《颍州府志·艺文志》中收录的六首关于列女故事的诗歌,描写的分别是孝妇、烈女和烈妇。《吊烈妇熊氏》、《孝妇篇》这两首诗的描写对象与《颍州府志·列女传》中的列女是同一人;另外四首诗歌描写的女性在《颍州府志·列女传》中都有原型。
如:高翼耀诗《吊烈妇熊氏》:熊家有女石家妇,髫年食贫毫无有。枭寇一朝揭地来,刈人如草不停手。石家烈妇深匿藏,痛失所天甘碎首。收拾骨骸同棺骨,七日饥魂天共久。寄语翻颜禄仕人,何如一饿名不朽。《颍州府志·人物志·列女·列女六烈妇》:熊氏,石球妻。球为寇伤,氏七日不食,扼吭而死。《颍州府志》中的六首诗歌是男性在列女死后写的,而方氏和郎氏所写的绝命诗是她们殉夫前的用诗写成的遗言,是对列女死前心理、思想、感情的生动刻画。
(二)节烈风俗对诗歌思想内容的影响
1.诗歌反映了列女的价值追求
《颍州府志·艺文志》中收录的六首关于列女事迹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五位诗人都用大量的笔墨热情的歌颂了列女的行为。在《烈女程学孟哀歌》中:“呜呼世上富贵人,男佩金貂女玉玦。生平受尽庸庸福,死后骨化名亦裂。”诗人将张郎和程氏“生死相随”的爱情与富贵男女的爱情进行对比,并认为富贵男女的爱情婚姻生活是庸碌的,最后造成了“身败名裂”的后果。采用对比的手法,赞扬了张程的爱情,更赞扬了程氏的刚烈行为。
其他五篇诗歌中更突出的是赞颂的笔墨,例如: 《张孝子周烈妇》:“是夫得是妇,青史双不朽。鼎篆垂斯文,丹魂绿蝌蚪。” 《贞烈李母刘儒人歌》:“孤松翠柏高苍苍,百尺无枝骄凤凰。阿母精英贯大荒,万年彤管犹皇皇。” 列女们的肉体虽然消失了,但精神却永存。她们以这种方式使自己像为国建功立业男性一样永垂青史,这也是她们的价值所在。
方氏在诗歌中直接提出自己的价值追求,并使她从容地面对死亡。例如:她的《绝名词》其一中写到:“闻说殉夫同殉国,太真曾碎老莱衣。”女性为夫而死和男性为国而死具有同等的价值,她抓住了这种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其二中:寄语家园第与兄,等闲闻变莫相惊。孔仁孟义曾为读,此事从容自在行。
诗人在临死前,写诗劝慰和开导自己的亲人,听到自己殉夫的消息不要感到惊讶。因为曾经读过孔子和孟子这样的圣人追求高尚的道德操守而付出的努力,所以为了自己的道德追求,献出自己的生命,她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并感到自豪。
2.诗歌表达了三纲五常的思想
《孝妇篇》通过吴氏之口,说出“此事坏纲常也”并且说出纲常是指“古来但有孝子典身为父埋,安有翁因儿妇典身当。”诗人描写了孝妇吴氏为赎公公,想尽一切办法筹集金子而差点献出生命的行为。“这里的”纲常“只要是指”父为子纲“.在《贞烈李母刘儒人歌》中诗人自己说出:”形影俱单目肯双,惟留只眼纲常立。“这是列女为表自己为丈夫守节的决心,也是为了坚守”夫为妻纲“.
其他四首诗是描写女子夫死殉夫的行为。列女种种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就是她们思想深处的”三纲五常“.
3.诗歌宣扬了阴祸神罚之论
在《孝妇篇》中,当吴氏含冤而死后,有一段充满神话色彩的描写:”是夜举家皆梦见,切嘱敞棺尸休殓。父子夙兴述未毕,殷殷天上轰雷电。忽见阿婶跪棺旁,死手握金若隐现。妇从棺里苏苏起,婶掌金挥不用取。孝妇回生转不忍,即用己棺殓其婶。噫嘻吁!人心天理自昭明,三川此事真奇绝。“一种神秘的力量吴氏能够托梦给自己的家人,证明了吴氏的清白,并使吴氏死而复生,而且惩罚了偷金子的人。
这个梦成为事件发展的转折点,梦中的嘱托推动故事向前发展。人们也都相信梦中的事情,吴氏的公公和丈夫遵从了吴氏梦中的托付,”父子夙兴述未毕“.在古代,人们对梦满怀敬畏之心,因为他们深信梦是会应验的。既可以是吉验,也可以是凶兆。这是一种梦兆信仰风俗。这也应验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俗语。
在文献记载中,先秦时人己多持阴德、阴祸、善恶报应的论调。这种记载最早出现在《老子》一书中,如《说苑·敬慎》引老子语曰:”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深。“在现实生活中,有善行者会得到君主封赏和民众拥护,有恶行者会招来法律制裁和民众唾弃等,但又认为人的行动受着冥冥中的神灵的监视,它们会根据人的行为善恶分别施以福祸。同样,它们是民俗信仰的一种表现。
4.诗歌展示了内心情感的冲突
每个人都有决心、抱负、追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各种羁绊。同样,列女也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通过郎氏的十首《绝命诗》,我们可以洞察列女死前的内心世界。从上面的记载,我们了解到郎氏为殉夫自杀了三次,这在诗中也有所反映,足以看出她殉夫的决心。毫无疑问,她是一位烈妇,然而她还是一位孝妇。一方面她心中牵挂自己的父母和公婆,另一方面随夫而去又是她的人生追求。女性面临的是节孝难两全的境地。
当一个人面临困境时,这时的选择才能暴露人的本质和追求。郎氏在诗中鲜明的指出”节“和”孝“的矛盾,但最终是”节“战胜了”孝“,但是这一取舍过程充满着痛苦。郎氏自己深有体会,在诗中也对这种选择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如《绝命诗》五:两全节孝自商量,难舍双亲几断肠。誓死一言如可改,负君终是负高堂。
诗人在心中暗自衡量着亲情和爱情,觉得舍弃自己的父母痛苦就像是割断肠子一样。但是殉夫的誓言不能更改,因为辜负丈夫最终也辜负了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和教育。又如《绝命诗》八中:”鸠毒吞来苦刺心,低头不忍看双亲。“以及《绝命诗》九中:”可怜最是孤孀母,哭子方休又哭侬。“世界上最大的痛苦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这种痛苦自己的公婆要经历两次。
(三)节烈风俗对诗歌形象塑造的影响
这些关于列女的诗歌,为我们塑造了”烈“、”孝“、”节“三种女性形象。她们各自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吴氏是一个坚决维护夫家名誉和顺从丈夫、孝顺公公的孝妇;程氏是未嫁夫死,不顾父母兄嫂的劝解,最终殉夫,献出她十七岁如花的生命的烈女;李氏是一个夫死为夫守节,为守住自己的贞洁采取自毁容颜的极端行为,并抚养幼子成人的节妇。郎氏是一位烈妇,根据记载,她曾采取跳楼、吞金戒指和投河这三种方式自杀了三次。家人几番救护,这其中包含了家人的关心和爱护;族人又为她过继了子嗣,这其中包含了责任和义务。她自己内心也有斗争,她不舍自己的父母和公婆。但是,一切没有挽留住她,最终她还是选择殉夫。这种行为在我们看来有些盲目和荒谬,但这正是她们的特殊之处,正是她们的价值追求。
颍州地区的节烈风俗使得列女的节烈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列女题材的诗歌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一方面节烈风俗促使列女的节烈行为进入文学的描写视野。另一方面文学对节烈行为的赞扬,促进节烈风俗的渗透、加强和巩固。
参考文献:
[1] 傅瑛。《明清安徽妇女着述辑考》[M].合肥:黄山书社,2010:4-5.
[2](清)刘虎文、周天爵修李复庆等纂。《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志辑》[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615.
[3] 刘锡钧。《风俗文化与道德建设》[J].天津师大学报,1997(2):7.
[4] 王敛福着。《颍州府志》[M].合肥:黄山书社,2006:62、1101、828.
[5] 昝风华。《论汉代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D].山东大学,2001:25、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