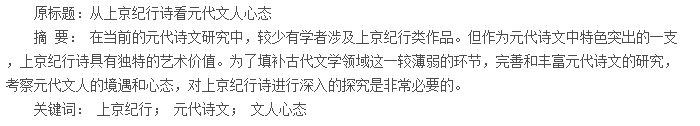
0 引言
有元一代,诗歌数量可观,上京纪行诗是其中独特的一支。元朝有限的百余年的历史中,文人们创作了大量上京纪行诗。上京纪行诗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元朝统治者的两都巡幸制度,元代实行两都制,有大都、上都两个都城,大都位于今北京市,上都则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两都相距四百余公里。
蒙哥汗时期,忽必烈掌管汉地事务,命刘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忽必烈将府邸建于蒙古草原南缘,加深了与汉地的交流,也受到更多汉文化的影响。忽必烈即位后,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遂改燕京为中都,后改为大都并定为都城,同时亦保留上都。从元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在定都中原以后仍保留草原之上的旧都城具有多重意义:元代统治者是蒙古人,其文化的根基在北方草原,就此来看,上都实为不能抛弃之故乡; 再者,习惯于北方寒冷气候的统治者对大都夏季的燠热难以适应,故将上都作为避暑之地,巡幸上都亦称为清暑。因此,两都巡幸成为元统治者的一项重要活动,“大驾岁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宫府侍从宿卫咸在,凡修缮供亿,一责于留守之臣”.巡幸上都一般在每年四月到八、九月间,元朝皇帝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在上都清暑,因而上都成为元代一座重要的都城。
上都又称上京,在两都巡幸的过程中,扈从大驾的官员中有一部分汉族官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南文人,在随幸上京之前他们大多从未去过北方草原,对于他们来说,扈从上京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沿途壮丽的风光、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都给这些文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前往上京的途中,文人们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尤以诗歌居多,这一类诗被称为上京纪行诗。现今对上京纪行诗的研究中,有学者将其归为“同题集咏”,或是考虑到上京纪行诗在题材上的相似性以及许多诗人表达出的同类的情感。但关于上京纪行诗的研究,当下仍没有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著,在现有的学术论文和专著里,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上京纪行诗所展现的异域风情,虽然也有对文人心态的探讨,但尚未深入研究。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元代文人在上京纪行诗中表现出的情感比较复杂,虽然很多诗篇从正面表现了扈从上京途中的见闻,对山川风物的赞美溢于言表,但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存在悲观情绪,一些作品中对国家的看法也显露出疏离,反映了当时随幸的汉族文人的矛盾心理。同时,随幸文人的诗作里大都表现出对旅途风光的新奇感受,同时表达了作者在随幸上京途中的思索与情感活动,这也体现出他们心中存有对未知的北方的向往,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期许。
1 对统治者的赞颂与仕进的愿望
上京纪行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元朝的歌颂,或是对统治者所举行的大型活动的描写。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文人们对元代统治者的肯定,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元代文人对上京纪行诗是给予较多重视的,从揭奚斯的《跋上京纪行诗》可以看出创作上京纪行诗在当时是随幸文臣们的一项重要活动:右翰林编修胡君古愚《扈从上都纪行诗》五十首,学士虞公以下跋语十五篇。自天历、至顺以来,当天下文明之运,春秋扈从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词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詠,然未有若明君之多者,诸公又皆能扬英振藻,极形容之美,可谓一时之盛,千载之下,观者当何如其想象而景慕也。予旧读胡君《京华杂兴》刻本,欲拟作数首,辄罢不能,今复观此卷,而志意衰耗有甚於前者,岂能复可彷彿哉!
唯增感叹而已。至顺四年二月四日.
由此可见,文人作上京纪行诗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目的。他们通过上京纪行诗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一些诗篇里也显露了文人出仕的渴望。文人们通过上京觐见、结交权贵等方式以求仕途顺利,其中一部分人达到了目的,但很多文人并未能实现愿望,如廼贤。
比较特殊的是,创作上京纪行诗的文人中亦有少数民族诗人,如马祖常、廼贤、萨都剌等。其中色目诗人廼贤是一个身份比较复杂的诗人,廼贤,字易之,西域葛逻禄氏,别号河朔外史、紫云山人。廼贤虽然属少数民族,却生于汉地,特殊的出身让他的思想独具一格,既不同于色目诗人,也不完全与汉族诗人一样。廼贤是生活在中原的第三代葛逻禄氏,他的思想已经汉化很深,如他的《还京道中》就表现了自己作为北游的南方士子的心情: “客游倦缁尘,梦寐想山水。停骖眺远岑,悠然心自喜。……”与其他一些随幸文人一样,廼贤在他的上京纪行诗中表现了出仕的愿望,如《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
鸡鸣涉滦水,惨澹望沙漠。穹窿在中野,草际大星落。风高马惊嘶,露下黑貂薄。晨霞发海峤,旭日照城郭。嵯峨五色云,下覆丹凤阁。琳宫多良彥,休驾得棲泊。清尊置美酒,展席共欢酌。弹琴发幽怀,击筑咏新作。生时属承平,幸此帝乡乐。愿言崇令德,相期保天爵.
诗中不仅赞颂了天下承平的国势,也表现出诗人希望出仕朝廷的志向。廼贤游大都、随幸上京确有仕进的目的,他关心时事民情,也渴望实现自己的壮志,但随幸上京并未给他带来进入政权核心的机会,而后来诗人的作品也表现了仕进无望的郁闷之情。
2 游览异乡的新奇之感
对塞外风光的描绘和欣赏是上京纪行诗中最常见的内容,山川风物、北方风俗等旅途见闻是上京纪行诗重要的主题之一。廼贤的五首《塞上曲》即从各个角度描写了草原上清新、自然的风光和淳朴的民俗。草原美景在上京纪行诗中不可或缺,如袁桷的《送王继学修撰马伯庸应奉分院上都二首》之二:浅坡平叠碛漫漫,拂岭青帘罨画看。毡屋起营羊胛熟,土房催顿马通乾.
诗中描写了一派草原风光,清新淳朴,格调明快,诗人的心情也跃然笔端,对北方风情的感受是新鲜的,使整首诗歌带有游记的性质。又如柳贯的《度居庸关》:居庸朔方塞,始入两崖张。行行转石角,细路縈涧冈。层壑倒天影,半林漏晨光。崎嵚里四十,所历万羊肠。千辕络前后,两轨通中央。谷开稍夷旷,在险获康庄。岂唯遂生聚,列廛参雁行。激流或机硙,架广亦僧坊.旅途中的艰难险阻描写得细致生动,有李太白《蜀道难》的影子,表现了诗人出行北方时的激动心情,也反映了随幸文人共通的情绪: 期待旅行带来的新奇见闻与感受,既怵于路途的艰险,又将其作为值得回味的体验和谈资。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中,学者大都注意到诗人们对北方草原风光的描写,其中也有一些学术论文中将上京纪行诗与其他时代相关的作品进行比较,如与唐代的边塞诗比较而谈,也有学者将上京纪行诗归为元代的边塞诗.但上京纪行诗与边塞诗又有不同,上都本身称不上边塞,它位于蒙古草原南缘,靠近汉地,就元代的版图来说并非处于边疆的位置。之所以会有学者将上京纪行诗归入边塞诗一类,应是从汉族士人的角度出发而谈。但是从现有的上京纪行诗来看,诗人们的心态与唐代边塞诗人的心态还是有所区别的。唐代的边塞诗所描写的大都是边关的生活和自然风景、人文风情等; 而上京纪行诗描写的主体是上都地区,对汉族文人来说,他们虽然也和唐代的边塞诗人一样能体验到与中原迥异的风土人情,能看到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风貌,但对他们来说上都之行并不是去往荒凉的边塞,而是到了元帝国的另一个重要都城。有元一朝,自忽必烈时代始,上都就一直作为陪都而存在,它是矗立在北方草原上的一座繁华城市,元朝统治者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活动、接见外国使臣,上都堪称大都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随幸上京与出使边关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文人的所见所感也有明显的差别。如袁桷《次韵继学伯庸上都见寄二首》( 其一) 所述: “陰陰椶殿水云苍,鳷鹊风微夏日长。浑似醴泉宫畔境,千官齐立从文皇.”描写了皇都的盛景。在上都,文人体验到的不仅有草原风光的壮美、少数民族民风的骠悍,更多的是这座北方都城的繁华、皇室活动的宏大和热烈。在许多诗中都有所表现,如廼贤的《失刺斡朶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描写了上都“诈马宴”的盛大场面:上林宫阙净朝晕,宿雨清尘暑气微。玉斧照廊红日近,霓旌夹仗彩霞飞。锦翎山雉攒游骑,金翅云鹏织赐衣。宴罢天阶呼秉烛,千官争送翠华归.
“诈马宴”又称“质孙宴”、“济逊宴”、“只孙宴”,是元统治者每年巡幸上都时举行的盛大宴会,可一连持续三日,王公贵族均着华服参加,场面蔚为壮观。元代上京纪行诗里常出现对诈马宴的记载和描述,可见随幸文人们对这种充满异族风情的大型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也从侧面反映出元朝实力的强盛。
大体来说,元代汉族文人对扈从上京的描写更近似于游记,他们的上京纪行诗也更像一篇篇诗体的游记,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壮美的北方景色和元上都的别样风俗,正如柳贯在《上京纪行诗并序》中所写的: “自夏涉秋,更二时,乃复计其观途覧历之雄,宫籞物遗之盛,凡接之于前者,皆足以使人心动神竦。”众多文人皆以诗文记录沿途所见,清晰地勾勒出扈从的行程,也将随幸文人的心情充分表现出来。又如柳贯《同杨仲礼和袁集贤上都诗十首》( 其二) :雨水渐衣黑,云砂际目黄。烟开才黯惨,日出已苍凉。徇俗高檐帽,清心小篆香。端居万里念,萱草情微芳.
诗中尽显北方的苍凉雄浑,也衬托出诗人在文化、习俗,甚至语言都完全陌生的异乡孤独的心境。
3 民族隔阂与文人的自身定位元朝统一中国后,汉族文人们虽已接受新朝,但他们与居于上等人地位的蒙古族之间仍有一定的疏离感。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文化的不同造成的隔阂,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对汉族文化了解甚少,在统一之初对汉族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十分轻视,虽然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实行了以汉法统治汉地,有一些汉族文人得以入仕,但总的来说汉族人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因而他们对新朝缺乏归属感,情感上比较疏离。其二是元代汉族文人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元代统治者曾一度废止科举,阻断汉族文人的仕途。元代后期虽然恢复科举,但却分两榜取士,蒙古、色目一榜,汉人、南人一榜,汉人、南人参加科举的人数多,他们的试题难度也明显高于蒙古人、色目人,但两榜取的人数却一样,这种科举对汉族士人十分不利,故而被汉族文人所讽刺调侃,也让众多汉族文人从心理上远离元朝政治核心,常表现出置身圈外的旁观者心态。而这样的情况也同样表现在上京纪行诗中,扈从上京的文人身份地位各不相同,而其中汉族文人的作品最多,在他们的诗中,排斥和伤感的情绪时有流露。
在这一类作品中,虞集的上京纪行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虞集名列元诗四大家之首,他生活的时代已是元代中期,但他的诗中仍不时流露出不愿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会有“南渡岂殊唐社稷,中原不改汉衣冠”的感叹。虞集的上京纪行诗中也体现出这种深切的异乡人的感受,如其《题上都崇真宫壁继复初参政韵》:
故人一去宿草寒,而我几度南屏山。琳宫素壁见题字,辄堕清泪如洄湾。文章百年世何有,如以钝拙镌孱颜。瞥然有感亦易散,奈此细读多高闲。沈思不见托魂梦,何异落月留梁间。走为麒麟飞为鸾,黄金作玦玉作环。重来岂无造化意,我以白发迟公还。
虞集当时已出仕元廷多年,但他始终不能融入蒙古族的文化圈子,而将自己定位成一个游离于统治阶层核心以外的汉族人,能够让他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只有同是汉族人的友人们。
纵观整个元代,民族的隔阂一直是影响文人心态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元代文学特点形成的主要因素,如因科举废弃而使众多文人流连于市井、从事戏剧的创作; 又如元末文人乐于雅集活动等。而即使是有机会随幸上京的文人,他们同样能体会到因民族不同而造成的身份不平等,能感受到汉族知识分子受到的歧视,这也是上京纪行诗中常表现出作者疏离心态的主要原因。
4 结语
综观元代诗文,上京纪行类作品的存在是一个独特而有趣的现象。上京纪行类作品分散于各种文学体裁中,不仅诗、文,甚至曲中都有其影子,而上京纪行诗是最丰富、最突出的一类。我国历史上少有如元代这样保留两个重要都城的时代,而元朝又恰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这更使得上京纪行诗这种特别的文学作品具有不一样的文学价值。上京纪行诗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整个元代文学的研究更完整,还可以进一步探寻元代文人的心态,从而能从时代特点和文人心态两个方面对元代文学进行更准确的把握。
参考文献:
[1]宋濂,王祎。 元史·刘秉忠传[M]. 北京: 中华书局,1976.
[2]虞集。 上都留守贺惠愍公庙碑[M]/ /道园学古录: 13卷。 四库全书本。
[3]申万里。 元上都的江南士人[J]. 史学月刊,2012( 8) : 37- 47.
[4]杨镰。 元诗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揭奚斯。 跋上京纪行诗[M]/ /胡助。 纯白斋类稿附录。
[6]廼贤。 金台集[M]. 元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