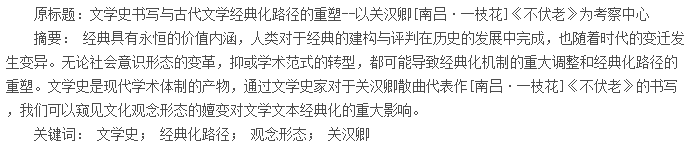
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属于历史的产物,无论内容抑或形式,无不打上鲜明而又深刻的“过去式”烙印,然而,对其经典化路径却不能完全作如是观。古典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经典化路径的中断,传统的文学经典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经典地位,必须经由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新路径。经典通常具有永恒性的内涵价值,人类对于经典价值的发掘与认识绝非一蹴而就,只有时间才给经典以证明和实现价值的机遇,按照布鲁姆的观点,除了色情作品之外,“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 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算经典”[1]24.我们理解中的“重读”,即可指个体成员对同一作品的“再读”行为,也包括不同时代的读者群体对于同一文本的具有继承性的阅读与评判。重读是在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中完成的,时间对于经典的重要影响,不仅在于因生命的自然更迭而导致读者群体的根本性置换,更体现于变化激荡的时代政治风云,不可避免地会带给经典化机制强烈的冲击,甚至改变经典化路径内在功能与外在表现形态。
随时而变,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一个重要特征。古代,这种变化以渐进的方式呈现,由少到多,由单一到多元。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不仅有新的路径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而出现,传统路径也因历史风云的激荡冲击而发生明显变异,每一次社会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革,随之而来的便是经典化机制的重大调整和经典化路径的现代重塑。按照西方建构主义理论的观点,经典非自然形成,而是被建构起来的。参与经典建构的因素具有多样性,本文拟以学术研究的现代转型为背景,以文学史写作为考察中心,通过元代关汉卿散套[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经典化路径的现代重塑,具体回答“经典是如何建构的”这一问题。
一、《一枝花·不伏老》经典化的历史回顾
文学史( literary history) 作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开辟了古代文学经典化的一条新的路径。文学史“本是由西方转道日本舶来的,以‘文学史’的名义,对中国文学的源流、变迁加以描述,在中国,始于 20 世纪初”[2].通常只有被认定为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才具有成为文学史描述对象的可能性,当然,经典的标准因人而异。在考察文学史家如何认识和书写《不伏老》套曲之前,有必要回顾关汉卿散曲在中国古代经典化的历史状况。关汉卿散曲在古代的经典化主要体现于选家的遴选。元人杨朝英辑录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和《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前后集录入关氏散曲十数首,另有佚名《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卷上也录入其[双调·新水令]一套。从古至今,选家遴选都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路径之一,经由选家认可和推荐的作品,往往作为文学教材而传世,成为后世读者学习写作的必修篇目和文学创作的模拟样板。而能够成为文学教材恰好是经典性的具体体现。
毋庸讳言,就整体而言,关汉卿散曲在元明清三朝的经典化程度并不高,传世作品的历史际遇也不尽相同。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今人高度赞赏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明显遭到冷遇,著名选本中仅有明人郭勋《雍熙乐府》卷十录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为文人士大夫群体所忽视,未能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人不甚看好的[仙吕·醉扶归]《嘲秃指甲》( 或题为《秃指甲》) 却先后被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明程明善《啸余谱》、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王骥德《曲律》、张禄《词林摘艳》、卓人月《古今词统》、冯梦龙《古今譚概》、田艺蘅《留青日札》以及清褚人穫《坚瓠集》等著作收录。
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经典性的表现之一为陌生性,“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3].笔者认为,[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遭受冷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关汉卿于套曲中所塑造的“浪子”形象,对于封建文人士大夫而言,具有高度的“陌生性”,且属于第一种可能性的典范作品,它表达了一种反传统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对古代知识分子传统人格形态的解构,诚如当代学者李昌集先生所言: 该套的意义在于标举出一种新的人格,作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元代特有的‘玩世’哲学,从而打碎了‘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文人人格典范”[4].正是套曲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及其呈现的人格形态的“陌生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获得封建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广泛认同。
《不伏老》属于关汉卿中晚年时期的作品,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一位都市“浪子”“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的生活方式以及能力特长。文本中所提到的诸如寻花问柳、歌舞弹琴、赏月饮酒、下棋踢球之类的行为与嗜好,大致可归纳为吃、喝、嫖、赌、玩五个方面,除了关汉卿,我们也能在其他作家身上找到某些对应点,似乎可以视为文士风流的表征。
然而中国古代不少著名作家的风流嗜好并未占据其人生追求的核心,至少从他们的诗文中可以寻觅到入世济民、建功立业的心理轨迹,很少有人如关汉卿表述得如此极端。李白也饮酒也狎妓,可是他从来不曾掩盖自己“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也从未放弃“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远大抱负; 仕途失意的柳永,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不过他毕竟是仁宗朝的进士,毕竟担任过屯田员外郎之类的官职,并没有彻底做到“忍把浮云,换了浅斟低唱”.如果说杜牧式的“赢得青楼薄幸名”,作为风流的表征足以使后世文人艳羡和效仿的话,那么关汉卿式的“眠花卧柳”则因传达的是一种偏离主流话语系统的愤激呐喊而显得“陌生”,故难以获得众多的回应。
元人邾经在《青楼集·序》里说: “我皇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5],关已斋即关汉卿,已斋叟乃其号。关汉卿等人没有仕进的经历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因此就认定他们主观上“不屑仕进”则未必完全符合事实。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关汉卿的生卒年月无法准确的掌握,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推算他大约生于金朝末年,卒于元大德年间或者稍后。元朝从太宗九年( 1237 年) 至仁宗延祐二年( 1314 年) 停止科考 77 年,断绝了大部分读书人的仕途升迁之路,关汉卿的主要人生经历就处在这一历史时期,他根本不可能得到仕进机会。当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模式被粉碎,通往理想的人生道路基本中断,原有的安身立命之根也不复存在,儒家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指导意义,丧失了终极追求,灵魂便无处安顿,于是只能成为思想的漂泊者。
为解决生计问题,饱读诗书、多才多艺的关汉卿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走上了一条与民间艺人相结合的道路,参加书会,从事杂剧创作。至元、大德年间,关汉卿活跃在杂剧创作圈中,不仅大量编剧写曲,而且“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 臧晋叔《元曲选·序》) .人是需要有社会归属感与尊严感的,而这一切他通过杂剧创作和演出得到了,同时获得的还有反抗传统、挑战社会的勇气与力量。如果说关汉卿最初的选择从本质上讲具有被动性质的话,那么他后来的行为就明显地体现出主动和自愿的特点,抛弃蔑视倡优戏子的传统观念,不仅与之交友,而且全身心投入到杂剧创作之中。为了表现对社会现实的抗争,他无所顾忌地展示自己浪子的风流行径与面貌,公开宣扬装疯卖傻、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他之所以在《不伏老》套曲中以滔滔不绝的语势、酣畅淋漓的笔法歌唱浪子情怀,显示铮铮不屈的才子傲骨,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向整个社会表明一个被弃者的自主选择和最终归属。
随着朱明王朝的建立,汉族士人群体的生存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所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人生重大课题也随之改变,诸如君臣关系、出处关系等都存在重新审视与调整之必要,即使是同样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清朝汉族文士亦如此。新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关汉卿经历的不可复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在另一意义层面上剥夺了知识分子人生自主选择的权力,社会主流话语系统向传统的强势回归发挥着矫正和纠偏社会价值取向的文化功用,凡此种种,深刻地影响到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不伏老》展示的是一种偏离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人生态度,而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在总体上已呈现回归传统的趋势,加之套曲所呈现的个体自我放逐之态,对统治者而言意味着不予合作或彻底背叛,故难以获得社会自上而下的普遍认可。邾经看到了关汉卿等人因“嘲风弄月,留连光景,庸俗易之”而遭到“用世者嗤之”的社会现实,事实上,嗤笑关氏的“用世者”不仅存在于元朝,后世也大有人在。催生杜牧式名士风流的文化土壤依然存在,故明清两代类似“往来朱邸风流甚,岀入青楼薄幸多”( 王穉登《赠翟德甫》) ,“从来莫问扬州杜,旧是青楼薄幸人”( 吴绮《与楚云》)的吟唱不绝如缕,而《不伏老》却因鲜有人喝彩而基本被排除在文学经典的行列之外。
二、文学史书写与关曲经典化路径的现代拓展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被现代学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这种终结以批判和否定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文学彻底摆脱传统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独立为标志。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观念的嬗变直接导致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文本评价的重大变化以及部分传统经典身份的转换,20 世纪初期和中期问世的多部文学史集中反映了这一点。能否成为文学史书写的对象,取决于书写者的文学观念与经典遴选标准,早期文学史的撰写者普遍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良好的学术声誉,作为专家,他们具有权威性的描述与肯定,实质上构成了文学经典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现代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必须在现代语境中重建对文学的描述,因此,他们立足于文学本位的立场,努力扭转长期存在的单纯从道德政治层面去品评文本的倾向,大力提倡从文学的层面去发掘文本的价值。如此一来,不少传统经典作品的标签被改写和置换,原本作为儒学思想经典存在的著作,经过“去经学化”的阐释后被认定为文学经典。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诗经》阐释的权威《毛诗序》遭到现代文史学家的抨击和否定,他们极力发掘和强调《诗三百》的文学本质,旗帜鲜明地将其定位于“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6],在对三百篇之首《关雎》的阐释中,“情歌”说取代了“后妃之德”说。同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孟子》也被置于文学的视角之下,开始作为文章写作的典范看待,反映在文学史写作中,便出现了“‘曾点浴沂'一章,颇近文学的技工”,“《孟子》其中多用比喻,以润色枯淡之伦理说,实有功于儒教普及之大文学家”[7]之类的分析。
其时,陈独秀、胡适等人对白话文学的大力推崇,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重新认识和定位的热潮。胡适欲将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白话文学提高到文学史的中心地位之上,旗帜鲜明地提出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正统的观点,他说: “中国俗话文学( 从宋儒的白话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 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在代表中国文学革命发展的自然趋势。”[8]
加之其时西方文学虚构理论的引入,胡适等人对“写实主义文学”大力提倡,树立起文学经典遴选的新标准,从另一角度提高了国人对于原本长期处于非正统地位的古代小说和古典戏曲的重视程度。于是,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对“文学”的界定,出现了诸如“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9]之类的言说,随之而来的便是,元代杂剧的文学史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成为史家书写的重点。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元代文学“可指为特色者,实惟通俗文学,即小说戏曲之类是也”[10],“元之文学有杂剧、传奇二种”,“元代之文学所重者杂剧、传奇、小说之轻文学,即通俗文学,实开中国文学之新生面”[11].在大力推崇杂剧的学术潮流中,关汉卿的杂剧尤其是《窦娥冤》和《救风尘》作为创作范本,得到了多位文学史家的较高评价,其经典价值得以广泛承认。
问题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未给[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经典化带来历史转机。相对于杂剧,元代散曲受到的冷落异常明显,问世于 20 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多部中国文学史,论及元代文学时,纷纷采取忽略散曲不写的策略。间或有著作对散曲进行了专章或专节介绍,但对关汉卿及其《不伏老》套曲的评价始终不高。陆侃如、冯沅君于 1932 年完成的《中国文学史二十讲》推举张可久为清丽派曲家的领袖( 与之相对的是以马致远为领袖的豪放派) ,而将关氏置于张可久旗下,《不伏老》“黄钟煞”出现在所举“丽”曲代表作之列,且一笔带过。赵景深完成于 1935 年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同样将关汉卿归于清丽派,对[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则是给予负面评价,称之为“简直是享乐主义者王尔德的口吻”[12].显得与众不同的是郑振铎先生,他在完成于 1932 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称关汉卿为散曲历史开场的“第一人”,高度赞赏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认为“无论在小令或套数里,所表现的都是深刻细腻,浅而不俗,深而不晦的”[13],所举代表作有《一半儿·题情》《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以及《一枝花·题杭州景》等,遗憾的是只字未提《一枝花·不伏老》。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即使经过新文学革命运动的推动,《不伏老》套曲仍然缺席于文学经典的行列。
文学史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出现,属于典型的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使用白话写作是其现代性的重要形式特征,而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则是其现代性的重要内核之一。产生于文学转型时期的多部文学史,之所以不同程度地体现出重杂剧、轻散曲的倾向,显然与学术界日益重视白话文学和叙事文学研究的时代风气有着直接关系。同时,由于多数文学史家的思想意识和学术观念并未真正完成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文学观念的转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表面化或简单化的倾向,他们对什么是“文学”或者“纯文学”明显缺乏明晰的认识与科学的界定,对古人称之为“词余”的散曲也未能给予正确的历史定位,一旦得出“元世纯文学之粹,杂剧、传奇二者也”[14]之类的片面结论,弃散曲不论便在情理之中。加之个别学者甚至认为关汉卿等人“不过是拿散曲来做他们消遣的副业,他们的专业一本在杂剧上[15],对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自然不可能给予《不伏老》套曲文学经典的地位。
在此,必须再次提及《不伏老》陌生化的问题。由于时间所产生的距离感以及现代反封建意识的强化,明清两代文人群体普遍难以接受的“铜豌豆”形象,对于现代文学史家而言,不仅仍然具有相当的“陌生性”,甚至因其鲜明的“浪子”身份标签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当今学者的学术视野中,《不伏老》套曲的最大价值在于塑造出一个具有颠覆传统人格形态的新型士人形象,而这一点恰好是当时多数具有传统文化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吃喝玩乐”总是给人以不务正业的印象。加之该套曲的艺术风格独具一格,既难以完全纳入豪放派论之,也无法整体视为清丽派,故弃而不论或是文学史家最明智的选择。
三、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与关曲经典化路径的当代延伸
1949 年后,[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经过半个世纪不断深入的研究,最终无可争议地进入到文学经典的行列。就目前情况而言,该套曲经典化的标志同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教材的经典,多部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使用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了重点介绍,由此成为大学中文专业课堂讲授的必选篇目之一,发挥着语文示范功能。二是作为遴选的经典,以王季思《元散曲选注》( 北京出版社 1981 年) 为代表的数十部元散曲或古代诗歌选本或给予了全录或节录,对于经典的普及和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作为批评的经典,出现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权威专家的肯定性评价,他们的观点被广泛引用,有助于提高和巩固该套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通过文学史可以了解和把握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考察《不伏老》的经典化历程,不难发现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变革给予文学史编撰者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史”[16],到 70 年代受评法批儒思潮影响,将是否具有反儒倾向作为评判作品的重要标准,视《水浒传》为“一部鼓吹儒家’忠义‘思想,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17]; 从 80 年代开始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例如肯定古代神话在中国美学史的重大贡献,认为“在表现悲剧美和崇高美方面,它们对后世艺术起了示范和奠基作用”[18],到 90 年代强调人性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文学史所显示的文学历程应该是“怎样地朝着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19],文学史撰写者的观点、立场、视角以及方法,无不折射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嬗变。
文学史的撰写,是一种对过去文学的述说活动,要求客观、准确的还原文学发展的历史场景,然而由于“当下”文化氛围的影响以及个人立场的存在,撰写者的述说必然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主观色彩,他们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以及评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文学发展的时代水平以及自身的价值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居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承担起改造社会、塑造人心的历史任务。
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提倡阶级分析方法,发扬阶级斗争精神,批判封建主义糟粕,……凡此种种,在开拓出古典文学研究诸多新局面的同时,也给广大研究者造成思想上的困惑以及方法上的偏差,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围绕古代文学史撰写中反映的诸多问题( 例如怎样认识人民性、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 所展开的大讨论,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极左思想带来的弊端可以从不少令今人完全无法接受的结论中看出,例如,资产阶级一般“不喜欢白居易,不喜欢《水浒传》,甚至不喜欢《西游记》,他们更歧视和蔑视民间文学”[20].
当然,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学界前辈对推进元散曲和关汉卿散曲研究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其时,他们跟从必须高度重视民间文学的主导思想,通过认真梳理和还原元曲与民间曲调的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时期在民间文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元曲( 其中包括散曲、杂剧两部分) 却大放异彩,它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成为元代文学的灵魂”[21].元散曲的文学史地位因此得到提高。同时,又以现实主义反映论为指导思想,从文本抒情主人公形象与作家自身的思想、性格之关系着眼,去发掘《不伏老》套曲内涵的积极因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不伏老》套曲反映了关汉卿性格的一个方面,“坚决与一切危害他的恶势力作斗争,中年以后仍然不甘示弱,这种永不衰退、越战越强是精神委实象’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22].“他的坚韧、顽强的性格在这首著名的作品中表现得相当突出。正是这种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的创作,写出了许多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反抗精神的作品。”[23]
经过如此推理和联系,《不伏老》开始在文学史写作中获得了虽然有限、但毕竟是正面的肯定。
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意识形态领域内极度泛滥的极左思潮,严重干扰了国人对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作品的阶级性、政治性被强调到第一甚至唯一的地步,有违文学的本质。用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进行衡量,《不伏老》一方面因作家立场人民性的缺失而难以得到较高评价,另一方面又因文本呈现的生活场景非无产阶级化而导致批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认为: 元散曲“多以自我为中心,发抒个人的失意和愤懑”,这是“当时文人病态心理的一种表现,最终只能导致人们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这在散曲作品中几乎形成一种时代风气,连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也未能免此”[24].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更加明确地指出: 此套曲“描写一个书会才人的生活道路,同时流露了作者及时行乐的思想和滑稽、放诞的作风”[25].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不伏老》的经典化程度显然不高。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党全国围绕真理标准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最终达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破除了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更新观念,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步得以实现。以此为背景,文学史编写者明确认识到必须“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中的流毒和影响”[26],自觉反思和认真总结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身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深化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 以袁行霈、章培恒版文学史为代表) .通过不断拓展学术视野,丰富与更新研究方法,吸纳并转化西方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得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更加科学,也更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得益于良好的学术氛围,元散曲研究取得的成就堪称空前,《不伏老》套曲也随之加速了经典化的步伐,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均将它作为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加以介绍,编撰者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进展与突破。
首先,引入现代学术话语,对《不伏老》套曲进行富有现代性的阐释。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认为,此曲塑造的“浪子”形象体现了“任性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27].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指出,《不伏老》套曲以夸张的形式表现了关汉卿的人格形态,即“让高度自由的生命和世俗化的玩世享乐结合起来,把避世的闲放情绪转化为玩世的放浪不羁[28]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肯定关氏在《不伏老》中所描写的市民享乐生活,认为像这样“对享乐的顶礼颂赞在我国文学史上真称得上前无古人”,这种享乐态度反映了曲家的生活热情以及对生命渴求[29].引文中出现的“生命意识”“自由”“人格形态”等,均是现代哲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修史者根据自己对生命和自由的理解去沟通古今,达成情感的共振,用具有现代性的解读去激活古代文学文本所蕴含的价值因子,为活在当下的人们提供生活乃至生命的样板。文学史撰写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再次得到有力的映证。
其次,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进一步发掘文本所具有的、而过去被相对忽略的艺术价值,改变了过去对文本阐释只重思想内容的倾向。《不伏老》所使用的夸张的手法、泼辣的语言、生动的比喻研究以及奔放的气势得到各种版本文学史的普遍肯定,或曰: “全曲在叙事状物中流露诙谐风趣,语言尖新泼辣,谐中见庄,具有豪放之风。”[30]或曰: “全篇语言泼辣,大量使用排比,随心所欲地加入衬字,形成一种泼辣奔放的气势。”[31]
其中,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针对作家对于字、句的运用发言,颇有艺术见地,充分体现了文学本位的立场,最具代表性。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与同为经典的元曲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相比,《不伏老》套曲经典化程度不及它们。由于文学经典化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成为后人文学创作的范本,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今人模拟《不伏老》的散曲作品。关汉卿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以“自泼污水”的手法塑造富有叛逆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借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该文本产生的社会效应如“对好入座”式的解读,难免使现当代多数散曲创作者有所顾忌,他们肯定而不效仿,充分体现了《不伏老》套曲的特殊性与不可复制性。
参考文献:
[1][3]( 美) 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 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 江宁康,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2011: 24,2.
[2]戴燕。 文学史的权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
[4]李昌集。 中国古代散曲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503.
[5]元·夏庭芝。 孙崇涛等笺注。 青楼集笺注[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20.
[6]胡适。 谈谈诗经。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23.
[7]葛遵礼。 中国文学史[M]. 上海: 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 10- 11.
[8]胡适。 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文集: 第 18 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32.
[9]刘大白。 中国文学史[M]. 上海: 大江书铺,1933: 10.
[10]曾毅。 中国文学史[M]. 上海: 泰东图书馆,1929: 238.
[11]葛遵礼。 中国文学史[M]. 上海: 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