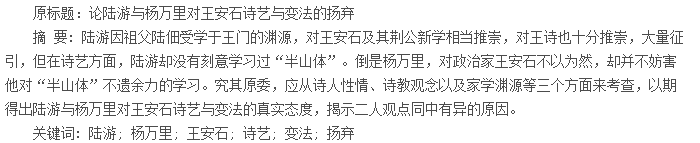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前后期有较大不同。早期,他多以诗针砭时事,怀古讽今,言辞激愤,风格浓烈; 晚年,多作诗吟啸讴歌,怀古悼今,意境闲远,诗风恬淡。南宋陆游与杨万里对王安石的诗艺称赏不已,尤其是杨万里,在诗歌创作上大量师法荆公暮年小诗的流丽风格,清新隽永,别具风神。陆游作诗虽并不模习“半山体”,但其诗强烈的感时忧世与王诗中积极的淑世精神相近,加上祖父陆佃为王门生徒,故对王安石的学者身份与变法舛差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 杨万里得王诗之深婉不迫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这样记载: “杨廷秀在高安,有小诗云: ‘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晓退之诗。’予语之曰: ‘此意古已道,但不如公之详耳。’廷秀愕然问: ‘古人谁曾道?’予曰: ‘荆公所谓“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是也。’廷秀大喜曰: ‘便当增入小序中。’”这段史料透露了两层信息,一方面,暗合的诗句表明杨万里与王安石有着相类的艺术旨趣,杨氏因己作与王诗偶合而“大喜”,从侧面折射出他对王安石诗艺的认同; 另一方面,能够迅速从杨诗中挖掘出王诗的因素,也足足反映出陆游对王安石诗歌的熟稔。
确如《笔记》所言,杨万里对王安石的诗艺多予赞赏: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寄边衣曰: ‘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吊古战场曰: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折杨柳曰: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三百篇之遗味,黯然犹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
杨万里认为诗歌“去词”“去意”后仍有余味,而在诗中流淌着这种不灭余韵的,除了晚唐诗歌,有宋一代,惟有王安石之诗堪当此誉。在诗歌创作中,杨万里更加直接地表明了对王诗的喜爱:
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
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
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
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
抛开评价的公正性暂且不论,仅就个人的诗歌旨趣来看,足以证明杨万里对王安石诗艺的推崇。这种文学上的肯定使他不自觉地在创作中融入了王诗的特征,“犬知何处吠,人在半山行”“青天何处了,白鸟入空无”有着“半山体”的淡远;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不是白云留我住,我留云住卧闭身”又与荆公晚年的闲适心态契合。诗人观察细致,触物兴感,面对湖天暮景,写下了“坐看西山落湖滨,不是山衔不是云。寸寸低来忽全没,分明入水只无痕”; 而当晚归遇雨,又记录了“略略烟痕草许低,初初雨影伞先知。溪回谷转愁无路,忽有梅花一两枝”。诚然,这种收获与杨万里偏向大自然对诗思的触发密不可分,自然景致经诗人裁剪被赋予人格,获得新生,故有了“老夫问柳柳不知”等人与自然的对话,也就难怪“岸柳垂头向人揖,一时唤入诚斋集”了。对此,杨万里曾自负地说: “好诗排闼来寻我,一字何曾拈白须。”后村亦有“放翁,学力也,似杜甫; 诚斋,天分也,似李白”的知人之论。然而,诚斋并未自恃其才而不加勉励,“诗吸三江卷五湖,雕琼为句字为珠”一语道出了学力的重要。杨万里不但从自然中觅取诗材,而且注重学术的滋养,他承嗣荆公,又加以变革,将江西诗派的“活法”演绎到极致。秉持着这样的诗论主张,杨万里创作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此等超迈半山的绝句佳什。
观上,读者极易获得这样的认识,杨万里原来是一个吟咏性情的闲散诗人,下笔多作内蕴浅切、率意而为的诗歌。
事实上,诗人未曾一刻忘怀国事,清人潘定桂即揭示了杨诗易被忽略的风采:一官一集记分题,两度朝天手自携。老眼时时望河北,梦魂夜夜绕江西。连篇尔雅珍禽疏,三月长安杜宇啼。试读渡淮诸健句,何曾一饭忘金堤?杨万里生前将自己的诗歌 4200 余首编入九部诗集,如方回所言“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
虽然当初杨氏未必有以诗记史的意图,但是九部诗集还是动态地呈现了其行藏用舍。对此,丁功谊先生作《杨万里各诗集创作时间考证》一文,通过厘清成集时间,使人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诚斋体’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观照出杨万里文学思想演变的轨迹”。
潘氏极富见识,短短数句便抓住了杨诗两个层面的生命力,一是“河北”“金堤”等关乎社稷江山的内涵意旨,二是师法“江西”而作“活法”的艺术追求。这种全面恰切的解读,正合乎杨万里本人的诗论,杨氏在《和李天麟二首》其一中曾透露出这样的主张:
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衣钵无千古,丘山只一毛。
句中池有草,子外目俱蒿。可口端何似? 霜螯略带糟。
“句中池有草,字外目俱蒿”即指作诗要兼顾思想内涵与艺术旨趣,既不可失之粗糙,又不能流于空泛,要文质相得。而这种透脱的诗艺追求,不正与荆公晚年的诗歌理解相契吗? 在《雪后寻梅》中,他托物言志,“诗人莫作雪前看,雪后精神添一半”便赞颂了梅花不畏摧折的傲岸姿态,杨万里晚年虽多言老病,却不工愁苦,梅花的精气神正是诗人的传神写照。
荆公晚年对梅花亦情有独钟,故有“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此等传神之笔。论者常将王安石《梅花》与陆游《卜算子·咏梅》并举,并视二人为论梅的同调中人,他们借花品题,透过梅花的品质传递出人的精神,虽然同样经历倾轧、诬谤,王氏在搁笔“福建子”后尚能释怀,绽放淡远,而陆游却始终给人留下失意志士的兀傲印象。这是因为王安石虽退居金陵,但政治抱负毕竟得以施展,而陆游却因不附当权派的主和论调,屡遭打击,久不见用,读到“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一句,放翁心声宛然可见。
的确,古典诗词的上乘之作大多别有寄托,就像咏梅,有些甚至“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杨万里虽注重艺术锤炼,但更看重诗意的蕴蓄,无论是“老农背脊晒欲裂,君王犹道深宫热”中的悲悯,还是“老去情怀已不胜,愁边灾患更相仍”里的忧患,抑或是“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的感喟,这种深沉的感时愤世流淌在字里行间。临终前他曾写道: “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
这“万古心”中包孕了国土日蹙的焦灼,贻误收复的愤懑,怨而不怒,含蕴深曲,绽放出《诚斋集》的耀眼光芒。因此,品读诚斋诗,只知其雅丽清新的半山一面,实在是误读甚深。
而与杨万里同时的陆游,同样服膺王安石的诗艺,领悟却有所不同,对此,杨理论在《中兴四大家诗学研究》一书中指出,杨氏偏向自然景物对诗思的触发,性灵色彩突出。陆游同样积极走入自然,触物感兴却不及杨氏幽默诙谐,天真活泼。这是因为陆游还大力提倡生活阅历对诗歌的玉成作用,此等客观公允的创作态度必会使之缺少杨氏的独特与创新。
那么,陆诗与王诗究竟有无交集,陆游对王安石又有着怎样的认识呢?
二 陆游得王诗之直抒胸臆
陆游《入蜀记》曾九次提到王安石的诗,涉及风物冠名,如小轩木末,土山培塿得名于王诗“木末北山雪冉冉”,“沟西顾丁壮,担土为培塿”,亦兼及史地考证,陆游亲临诸地,如谢安墩、瓜步山、牛渚、天门山等等,形势皆与王诗记载吻合,王氏治学之谨严对陆游影响极深。最高的评价莫过于卷三游九华山一则,“九华本名九子,李太白为易名。太白与刘梦得皆有诗,……惟王文公诗云: ‘盘根虽巨壮,其末乃修纤’,最极形容之妙”。
在《老学庵笔记》中,陆游另有十处言及王诗,其中八处是对王安石诗歌或诗学的正面之论,这些记载足以彰显陆游对王安石诗艺的认同。在卷十中,陆游先后将白居易、晏殊与王安石三人对蝉声的歌咏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三用而愈工”;在卷八中,王荆公化用颜廷年“微音远矣,谁箴予阙”,一变而为“子今去此来何时,后有不可谁予规”“师其意不师其辞”,陆游誉之“青出于蓝”。
然而,认可并不意味着必作赞歌,有时,查漏指正一则更能反映论者对诗人成就的真正理解,二则也能彰显论者的学术襟怀,而陆游就是这样胸怀坦荡的学者,对王诗既乐道其长,亦不掩其失。如《笔记》卷四借曾几之口指出荆公之于渊明,师其辞不师其意,稍显不足; 卷八称赞韩驹“推愁不去还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一联,熔铸王安石与刘禹锡诗句,而愈加工整。不独对王安石,对自己的父亲,陆游亦有着公正的评判。如《笔记》卷八记载了陆宰与晁以道对黄庭坚《乞猫诗》有着不同理解,结果是陆宰所解有误,《笔记》中便留下了“偶不扣之为恨”的实据。
和杨万里一样,陆游对王安石的诗艺也十分赞赏,常常化用王句。“万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风”出自“万事因循今白发,一年容易即黄花”; “即今禾黍连云处,当日帆樯隐映来”源自“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有时,甚至仅一字之改,如“莫作世间儿女态”出于“更作世间儿女态”。虽然化用王诗成句,但是,陆游并没有沿袭“雅丽精绝”的半山诗风,而是另辟蹊径,在南宋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奏响了爱国主义的悲歌。时事跌宕成为陆游创作的不竭诗材,这种取材倾向贴近王安石早期的诗路,尤其与王氏的政治讽喻、咏史怀古之作不谋而合。荆公咏史诗“最于义理精深”,这与王氏的学养修为、人生志趣以及时代土壤等密切相关。可是,陆游的时代,王业偏安,国境日蹙,民族矛盾尖锐,于是,“生希李广名飞将,死慕刘伶赠醉侯”“闭门种菜英雄老,弹铗思鱼富贵迟”“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属櫜缚裤毋多恨,久矣儒冠误此身”,这些诗句承载着匡时济世的浓烈情绪,喷薄而发,与王安石精研义理、千帆竟过的淡泊心境截然不同。
不仅与王氏殊异,即使与杨万里相比,同样感慨国土沦陷,杨诗仅止于悲歌讴吟,陆诗的郁怒情绪却更加凸显,故而频频发喟杀敌报国的雄歌,“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救河山”“丈夫无成忽老大,箭羽凋零剑锋涩”,便是怒火迸发的出口。况且,南渡之初,万事草创,外交上和战不定,内政上分歧亦多,士人心态极为复杂。当壮志难酬时,陆游不得不借助“新亭”“迁都”“遗民”等意象表现世运盛衰、山河兴废。只不过,陆游的情绪貌似不可遏制,但却一直收束在成熟的用典与对偶中,正如刘克庄所言“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
同样精于对偶,半山的形式或许更加工严,但是放翁的节制更为难得,体现了宋人作诗高度理性的精神。虽然笔底怒翻波澜,可是,章句之学并非志向,经世致用方为夙愿,在这一点上,杨万里与陆游心意相通。二人相比,陆游更渴望政治抱负的实现,这也为他能够客观评价王安石的人格与治绩奠定了基础。
三 二人对政治家王安石的不同态度
相比起对文学家王安石的交口称赞,人们对政治家王安石却是聚讼纷纭。陆杨二人身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历时八十年。前四十年,南宋一朝承接北宋党争余蓄,呈现出“党元佑”与“主安石”的分歧,王安石的声誉在蔡京一党的庇佑下尚得以保全。而在后四十年里,饱受压制的元佑学术抬头,它以濂洛道学与苏黄文学相结合的方式对荆公新学进行前所未有的清算,一时间,王安石的吏治、学术甚至心术被全面否定。是时,杨万里也步入其间,讨伐王氏: “王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论,创为法度,谓之新法,天下大扰。”
杨氏反对尽弃祖宗法度,主张针对现实将“大坏之坏”的毒瘤切除,对于“补而未全之坏”的缺陷,则可以纡徐改革,不可仓促操切。好在杨万里只是客观纠正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失误与实施弊端,并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偏狭层面,但是,卷土重来的道学派却没有放过王安石,其践踏、攻讦之势推助了两宋党争的恶性循环。虽然有学者意识到这种畸形斗争的不良后果,意欲弥合两派矛盾,但都是杯水车薪,几无效果。对于党派倾轧,陆游深感痛心,“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原乱后儒风替,党禁兴来士气孱”“大事竟为朋党误,遗民空叹岁时遒”,这些诗句无不蕴含扼腕之痛。
在这样的背景下,陆游对王安石却依然多加维护,即使是在论述王安石寻常的赏玩癖好时,他也不允许别人对荆公有着声色之徒的误读。在古代,竹根以其天然的韵致受到文人的偏爱,王安石得到了友人耿宪竹所赠的竹根冠,“爱咏不已”,作《和耿天骘以竹冠见赠四首》歌之,其中“玉润金明信好冠,错刀剜出藓纹干”描摹了竹根冠的物态,而“无物堪持比此冠”“不忘君惠常加首”更是道出了赏爱之情。对此,陆游却不忘铺垫“王荆公于富贵声色,略不动心”的前提。事实上,作为宰相的王安石的确无暇有所嗜好,南宋朱弁在《曲洧旧闻》中就曾澄清王氏喜食獐脯一事。王安石因思虑国事,席间无意吃光了距离自己最近的菜肴獐脯,属下窃以为得宰相口味偏好,幸亏王妻命人更换菜品,荆公同样一扫而光才得以辟清。那么陆游此处对王安石的回护,除了他本人对王安石人格的认同,恐与其家学渊源亦关系密切。
陆游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绛帐横经二十秋”的弟子,对荆公学问极为仰慕。陆佃尝记荆公讲学情形,“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余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荆公讲学,掀起“诸生横经饱余论”的盛况,堪与胡瑗比美。
陆佃出于王门,却不支持新法。熙宁三年,王安石主政事,垂问陆佃对新法的态度,陆佃的回答坚定有力,“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这样回答,一方面肯定了王安石变法的初衷,维护了师道尊严; 另一方面客观评价了新法实施的扰民倾向,指斥其弊端。关于陆佃的为人,安石得势,他并不沦丧附议; 安石失势,亦不避之不及,而是率众祭奠。正因如此,北宋当局两次罗织党人名单,陆佃都榜上有名,第一次与新党同列,第二次却入旧党名单,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陆佃虽不支持新法,但在《〈神宗皇帝实录〉叙录》中却有这样的表述,“既而储积如丘山,屋尽溢不能容,又别命置库增广之”,“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余财羡泽,至今蒙利”,这些细节无不是对王安石的声援,生动记载了新法聚敛生财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张祥浩、魏福明认为“绝不能说起到了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或者说富民的作用”,却“必然是向人民搜求的结果”。
毕竟,“天下财力日以困穷”的窘况是否改善,归根结底是以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标尺的。要之,陆游与杨万里诗歌的艺术触角深植于不同的土壤,故其感发差异极大。就承袭王安石诗风来看,杨万里偏向晚期王诗的“深婉不迫之趣”,陆游则更欣赏早期王诗的“直道其胸中事”。但是,对于王安石的“博观而约取”,二人都深为赞同。刘克庄即言: “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
陆游在《答陆伯政上舍书》云: “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 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 纵然“所慕在经世”的抱负郁郁不得抒,但其揽辔澄清之志已然通过九千多首的惊人产量,实践了人能的极致,流芳百世。
参考文献:
[1]陆游. 老学庵笔记[M]. 北京: 中华书局,1979: 13,127,107,65.
[2]辛更儒. 杨万里集笺校[M]. 北京: 中华书局,2007:3332,479,1582,648,1922,2062,199,2242,4287.[3]吴文治. 宋诗话全编[M]. 南京: 凤凰出版社,1998:8377,8375,8376.
[4]湛之. 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1964:92.
[5]方回. 瀛奎律髓[M]. 合肥: 黄山书社,1994:21.
[6]丁功谊. 杨万里各诗集创作时间考证[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132.
[7]唐圭璋. 全宋词[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1284.
[8]杨理论. 中兴四大家诗学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2012:210.
[9]陆游. 入蜀记[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24.
[10]屈守元,常思春. 韩愈全集校注[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050.
[11]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34.
[12]丁福保(辑) . 历代诗话续编[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320 .
[13]杨万里. 诚斋易传[M].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8:69.
[14]陆佃. 陶山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6: 38,165,3,118,119.
[15]脱脱,等.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10917.
[16]张祥浩,魏福明. 王安石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447.
[17]李之亮. 王荆公文集笺注[M]. 成都: 巴蜀书社,2004: 21.
[18]逯铭昕. 石林诗话校注[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93.
[19]陆游. 陆游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76:2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