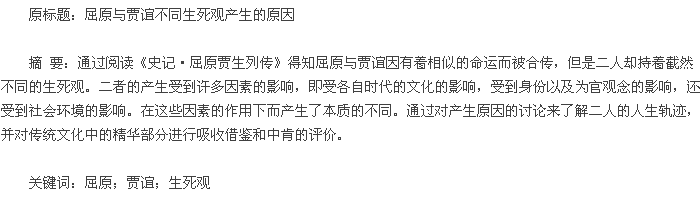
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1]中司马迁将屈原与贾谊合并于一传,是因二人有着类似的人生轨迹,即早年有异才受到君主的重用,却因谗佞的陷害而后被冷落,甚至流放他乡。虽然二者的人生轨迹大致相同,但是在种种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也看到二人对于生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屈原的生死原则就是无论如何他都要留在楚国尽最大的能力帮助楚国重新富强起来,虽然最终也无法实现这样的人生理想,但是他却以死明鉴,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殉其国、其志。而贾谊则对其做法存有异议,在《吊屈原赋》中提出屈原在看见自己的人生理想无法在楚国实现之时就应该离开楚国去别的国家谋发展,认为“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兮,摇增翮逝而去之”。这样截然不同的生死观其产生是什么原因呢?本文即对此进行分析讨论。
一、文化的影响
在文化的承接与延续上,二者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成为两位文学家在生死观上产生差异的原因。
屈原身为楚地人,必然受到楚地文化的影响,而楚地的文化中巫文化最为盛行,而且屈原官居三闾大夫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以及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的,因而其文学观念上必然受到巫文化的深刻影响,这在屈原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汤漳平先生在其《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歌>》中就提出了:“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可见其受到巫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巫文化中有一方面是受到很大的重视的,即为人的灵魂的归属问题,人死后的灵魂的归属,关系到后代子孙的生活,一直从事宗庙祭祀事业的屈原也是如此,如其创作《国殇》就是为了让阵亡的将士能够回到祖国,不至于灵魂没有归属而四处游荡。所以基于其对这方面的重视,屈原便不会远走他乡,并且当国家灭亡的时候,也要在此地还被称为楚地的情况下投江而死,灵魂永久的归属于自己的祖国,便是巫文化的影响表现。
而贾谊则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并且二者在其生死观念的形成上发生作用。贾谊少年时期跟随荀子的徒弟张苍进行学习,受到荀子观念的影响,荀子的观念中体现得最深刻的就是一种务实的精神,这一点也被贾谊所继承,认为有才华无论是游说哪一个国家都能受到君主的赏识,自己的才华能够得到施展,而不会荒废掉。在贾谊看来才华的施展才是最主要的,人死了才华就尽失了,这样因为社会的污浊而将自己弄脏是不明智的,凤凰尚且览辉而下,人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而且在生死观上贾谊还受到道家旷达精神的影响,认为不应该被世俗的情感所拖累,万物即与我为一,那何必一定要固守此处呢,天地之间便皆是我能生存之处。另外,贾谊的思想还受到湖湘地区文化观念的影响,当地的文化强调“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的熏染下贾谊在去留问题上也更加的自由、任性,不受国别的约束。这些思想因素的影响,使得贾谊在对屈原进行悼念时肯定了他的人格的高尚,但是无法理解屈原以死殉国的做法,产生了与之不同的生死观。
二、身份与为官观念的影响
屈原在《离骚》中对自己的“内美”进行了描述,认为作为朝中的一员他是相较于他人比较有涵养的人,并且能主动地去完善自己,去修能,在做到了这样的为官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他还有比任何人都要坚定的忠于君主的决心,再加上他还是一位诗人,是一位重于用感情去思考问题的诗人,因而他追求的是一种符合浪漫主义的情感寄托,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明达的君主在屈原看来就应该重视有才能,并忠于自己的人。而这一理想却屡次遭到打击,一次又一次地让他的世界观受到冲击,诗人又是倔强的,他们只会用最感性的思维去顺从自己内心的思考问题,所以在自己最终也无法实现自己内心所愿时,他的忠与情都让他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就这样灭亡了,笔者认为屈原对自己是有一种“怨”的,他怨自己不能挽救自己的国家,怨自己没能阻止国君的种种推进国家灭亡的行为,像他这样有内修并无比忠君的人不会怨君主的昏庸,只会怨自己没能陪在君主的身边去抵挡那些奸佞小人的谗言,因而认为像他这样有愧于国家、有愧于君主的人只能以死补过。所以抱着这种对自己的怨和亡国的痛,他的选择只能是与国家同生共死。任何人都不会在失去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的时候,还能在别处空守着躯壳活下去,更何况是屈原这样刚烈的伟人。诗人的气质性情再加上他忠诚的为官观念便都促成了其舍生就死的生死观。
贾谊就与之不同。贾谊的为官观念受到荀子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响,更加强调现实的人生,否定理想精神,立足于现实生活,理性地、顺从现实地去思考问题,所以贾谊便主动地压抑了自己的悲哀的情感,而用道家的旷达态度去面对现实,认为在不能够得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时便可以去别的地方需求机会。而且贾谊还十分向往春秋时期那种自由的入仕观,赞同“楚材晋用”的行为,认为春秋时期的那种主动寻求机会趋向于贤明君主的观念是值得推崇的,虽然春秋时期的这一入仕观不能忽视促其必然形成的历史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但是贾谊对这一观念的吸收和利用充分地体现了其为官理念,并且十分深刻地影响着其对生死的态度。再者,贾谊是一位文学家的同时又是一位政论家,其政论文的创作,体现出了其逻辑与理性的思维能力,如其《过秦论》的创作,用一种叙事的手法来进行议论,不是掺杂自己的情感去导引别人,而是用历史事件来说服别人,其“去就有序,变化因时”的观念,不单单用来劝诫君主,还体现了他的思想观念的整体结构,这些都在他的生死观上产生影响。
三、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战国纷争割据的时代,楚国通过南征北伐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成为“战国七雄”中的翘楚,楚国强盛时期曾经地跨十一个省份,在《战国策·楚策一》中有这样一段话:“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
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国土面积了。楚国成为了当时最大国,并且这种强盛持续了七百年之久,直到楚怀王时期才因为采用错误的政策导致国力衰落。国力的强大使其国民产生了一种大国的胸襟,其包容广大的情怀影响着国民的心理,国家的广大和繁荣又使得人民形成了一种对祖国的共同的认知,一种民族意识在国民内心中渐渐成型,最终形成了共同的爱国心理,这一切也都影响着屈原的人生观、世界观。
然而,有着强烈爱国意识的屈原却眼看着楚国的鼎盛戛然而止,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屡屡受到外强的侵扰却无能为力,这种种对其民族心理和本土意识的打击在屈原的心中激起层层的悲愤的情绪,其创作也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但是由于长时间在社会环境和民族心理的影响之下,又作为一名楚国王室成员,屈原的爱国情怀比普通的百姓更加的深沉,那种忠君的思想也更加的执着,所以影响着其生死观,国灭之时也必然成为了屈原殒命之日。
贾谊生活则在西汉初年,汉朝刚刚稳定下来,逐步地开始走向兴盛,这是一个平稳向上的过程,国家开始重新兴建,鉴于秦亡的教训,西汉初年治国施行黄老之术,强调“无为而治”,这种“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实行一定的政策时要尽量做到不干预人民生活,不为追求强大而去劳动黎民百姓。用“无为”而达到“有为”的目的,这种思想影响着西汉的社会政治环境,并产生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贾谊的思想也受到了黄老之学的影响,使其旷达自适,黄老之学所提倡的观念在其政论文中也有所体现,如“省苛事、薄赋敛,勿夺民时”这一观点就是其创作《过秦论》时看待豪强夺地、盘剥百姓、刑法残酷等社会现象的标准。而黄老之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被贾谊所吸收,就是治身与治世都应顺应自然秩序。加之其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观念的指导下多次总结前代的教训,吸取经验,也接受了如春秋自由入仕等有益的观点,结合起来对其“轻去就”生死观的形成产生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二者,充分地肯定了屈原的文学成就,也认同他的伟大的志向,在触及贾谊对屈原的评价时,从司马迁的叙述中可见其在二者的生死观上更加倾向于屈原的那种“同生死,轻去就”的观念。这也是时代和其自身经历的总结后的最终体现,无关对错,是一家之言。
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我们也会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二者的生死观,基于现实社会环境,我们的身份以及文化等等方面的影响,便会对其中一人产生认同感,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忽视另一方闪烁着中国精神光辉的地方,既要吸取屈原“忠”的部分,也要借鉴贾谊“才”的方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而被摒弃掉。客观的看待,虚心的学习,塑造我们自己的生死观、价值观,并为理想而奋斗终生,这样才不枉费前人为我们尽力保留下来的思想财富。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战国策 [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洪兴祖,撰.楚辞补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萧统.昭明文选 [M].南京:广陵书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