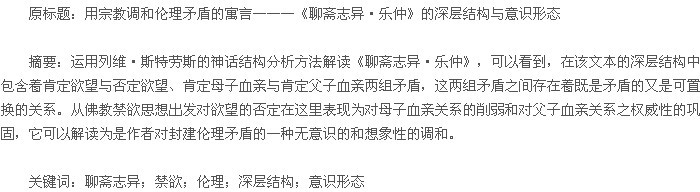
一
宗教思想在古典志怪小说中的存在和意义是志怪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们关于佛教思想对《聊斋志异》创作的影响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佛教思想与《聊斋志异》的关系也日渐复杂化了。吴九成曾在文章中论及蒲松龄的“摇摆不定的信佛态度”。他指出,一方面蒲松龄作为文化素养极高的知识分子,对于佛教学说主要是从学理上研究和欣赏,对其教义本身是持保留态度的;另一方面,他生活穷苦而与下层民众交往密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宿命论和因果报应等思想。”紧接着,他又说道:“同时,他立足于上位文化层次所作的唯心主义哲学思考中,包含着企图实现社会道德完善化的强烈愿望,这也极容易把他导入对佛教思想的哲学崇拜”。吴九成所作的这三个判断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是合情合理的,而第二个则大可商榷。从《聊斋志异》的文本来证明蒲松龄的佛教信仰,关键是要看佛教思想在这些文本中是作为思想主题出现,还是仅仅作为情节结构的形式要素出现。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佛教思想被作为内容加以表现,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是出于信仰而宣扬这种思想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佛教思想不过是艺术化地表现生活的手段,那么我们就不能证明作者是否信仰这种宗教思想。而吴九成在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佛家思想对《聊斋》创作的影响,最显而易见的是在题材、情节等外在形态方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聊斋志异》中,佛教思想主要是作为艺术手段而不是思想主题而存在的,蒲松龄对佛教教义的信仰因此也是大可怀疑的。
然而不得不承认,吴九成所作的另外两个判断是极其有价值的。
佛教思想对于《聊斋志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为作家的艺术想象提供了思想依据,而且与蒲松龄的社会理想有着重要关联。
刘敬圻在《〈聊斋志异〉宗教现象读解》一文中也曾详细地研究了佛教、道教、民间宗教迷信、与儒家正统思想在《聊斋志异》中的混融情况。他指出,《聊斋志异》中纯粹宣扬正统宗教观念的篇目是很少的。他举了三个“虔心向佛”的文本:《乐仲》、《长清僧》、《菱角》。他说:“《乐仲》等‘向佛’篇程度不同地给人以崇高感,让无心为善而又无所不善的人们进入随心所欲的圣洁境界,还传达了‘行高乃不堕落,性定乃不动摇’的佛教哲理”。这句话用在后面两个文本上是确切的,而用在《乐仲》上却值得商榷。在《乐仲》中,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明确说道:“断荤戒酒,佛之似也。烂漫天真,佛之真也。”
可见,蒲松龄是无法接受那个以“断荤戒酒”为正统教义的佛的。不过奇怪的是,在这个文本中,佛教禁欲思想的确被用于情节建构,从而使故事本身与作者的观点形成了矛盾。
这种矛盾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宗教思想在志怪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实际上,吴九成和刘敬圻的文章分别从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中国文化的客观发展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在《聊斋志异》中,儒家思想是“体”而佛教思想是“用”,佛教思想在根本上起着协助伦理道德教化的作用。这个观点本身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有些笼统。因为,佛教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是跟儒家思想难以调和的,那么,这些方面是不是就被排除在《聊斋志异》之外呢?
比如说,佛教的基本教义禁欲是与儒家伦理思想尖锐对立的。那么,佛教禁欲能否起到协助道德教化的目的呢?它又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我认为,宗教思想除了在作者的“有意识”的层面上影响他的创作之外,还会在“无意识”的层面渗透进叙事,从而产生一种与作者观点迥然有别的潜在的意识形态。《乐仲》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实际上是宗教禁欲思想在文本中的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之间的错位。本文将借助于法国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方法对《乐仲》这一文本进行分析,希望能够找到佛教思想与蒲松龄的“实现社会道德完善化”的愿望相结合的“无意识”的方式,从而为志怪叙事中的宗教思想研究开辟新的思路。
二
《乐仲》是《聊斋志异》中篇幅最长的文本之一,它讲述了乐仲、雍辛父子两代人的故事。乐仲的故事占据了文本的大部分,具有鲜明的奇幻色彩,雍辛的故事则现实得多。乐仲是遗腹子,事母至孝。他天生嗜饮,却又不爱女色。娶妻顾氏,三天之后便把妻子逐出家门,声称“夫妻之事是天下最肮脏的事情,我实在不觉得有什么乐趣”。在去往南海祭拜母亲的途中乐仲遇到了贬谪人间的散花天女琼华,两人做了二十年的假夫妻,期间乐仲受琼华点化顿悟,最后一同升仙。雍辛则是顾氏改嫁雍家后六个月所生,顾氏病死之后,雍辛被雍家逐出,在乐仲从南海返回的路上父子相遇。
父母死后,乐姓族人为得到遗产与雍辛打官司,官府不能肯定雍辛的身份,欲将遗产分为两半。雍辛的外公顾老翁寻找外孙,途中得到琼华的指点,于是到官府讲清原委,雍辛才顺利继承了父亲的财产。篇末,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说道“:断荤戒酒,是佛的假象;烂漫天真,才是佛的真质。乐仲待琼华,只是做旅途中香洁伴侣,没有温柔乡的想法。三十年住在一起,像是有情,也像是无情,这是菩萨的真面目,世俗之人如何能猜解得透呢?”
如我们一开篇所说的,从《聊斋志异》的总体倾向来看,蒲松龄对宗教禁欲思想是持反对态度的,《乐仲》篇末所谓“断荤戒酒,佛之似也;烂漫天真,佛之真也”也证明了这一点。主人公乐仲能够升仙就是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天性”。他孝顺母亲以至于割股啖母,母亲死后他悲痛欲绝,用刀子割自己的大腿,这是他的天性;他天生嗜饮善啖,并不因母亲礼佛而改变,母亲死后甚至焚毁佛像,在去往南海祭拜母亲的途中,结香社者戒荤戒色,他却“牛酒韮蒜不戒”,甚至跟妓女(琼华)寝食与共,毫不在乎世人的鄙笑,这是他的天性;他天生不爱女色,娶妻三日而逐妻,与琼华做了二十年假夫妻,这也是他的天性。可见,张扬天真的人性,反对宗教禁欲思想,这可能就是蒲松龄“有意识”地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蒲松龄的这一观点不能概括这个文本的全部意义。比如,我们如何理解文本中雍辛的故事?如何理解与这个观点无关的其他细节呢?就拿乐仲、雍辛父子的不同寻常的身世来说吧。乐仲是“遗腹子”,即父亲死后,母亲才生下的他;雍辛则是母亲改嫁之后所生,虽然姓雍,实则是乐家骨血。这两种情况具有一个共同点,即“父亲缺席”的现象(当然,仅仅是现象,而不是实质)。在乐仲那里是“生理性”的“缺席”,在雍辛那里则是“社会性”的缺席。这种区分也为情节所证实。围绕乐仲所发生的事情大多与“生理”问题(食、色)相关;而围绕雍辛所发生的事情则与他的身份问题相关,也就是说,与他和乐仲的父子血亲关系相关。这些有趣的细节作为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应该被忽略掉的。下面,我们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方法,把《乐仲》文本中的全部细节做一番重新整合,也许能够得出蒲松龄“无意识”地表达给我们的信息。
按照列维·斯特劳斯“重新洗牌”的方法来整合《乐仲》的情节要素,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组(每一组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A)乐母礼佛不食荤酒;乐母悔恨破戒绝食而死;乐仲娶妻三日逐妻;结香社者戒荤戒色;乐仲与琼华寝食与共而毫无所私;乐仲与琼华做二十年假夫妻;乐仲顿悟“不复饮市上”;乐仲与琼华死后升仙。
(B)乐仲嗜饮善啖;乐母病中思肉;乐仲焚佛像;乐仲纵酒不羁;去往南海祭拜乐仲不戒荤酒;琼华是妓女。
(C)乐仲割左股啖母;母死乐仲割右股欲死;母亲魂魄抚摸乐仲为其疗伤;乐仲祭拜南海母亲现身莲花之上;乐仲大腿伤痕变为莲花;乐仲死时“光明生于股际”。
(D)乐仲为遗腹子;顾氏改嫁后六月生雍辛;乐仲家产被子侄们掠夺;乐仲破产被子侄疏远生“无嗣之戚”;顾氏死后雍辛被逐行乞;乐仲雍辛父子相认;乐家子弟与雍辛争夺家产;顾老翁证明雍辛身份使其继承家产;顾老翁六十余生一子。
这样的整合之后,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归于每一组的事件都有其共同点,它们是构成文本深层结构的要素(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神话素”)。(A)组的所有事件都涉及到对肉身欲望的否定和禁除,无论这种禁除是出于宗教观念(如乐母、结香社者),还是出于天性(乐仲),这些事件都表达着同一种意义,即对肉身欲望之价值的否定。(B)组与(A)组相反,涉及到的是对肉身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无论这种肯定是因为什么,或者以何种方式表现,它们都包含着与禁除欲望相反的“义素”。(C)组事件涉及到亲密的母子关系,这种关系还是以极其夸张的肉身事件表现出来的,所有的事件都似乎在表现母子的肉身关系,因此可以将其归结为是对母子血亲关系之生理性基础的肯定和张扬。(D)组又与(C)组相反,涉及到的是父子关系。我们发现,围绕父子关系所发生的事件具有明显的非肉身性。我们前面谈到的乐仲与雍辛的身世时,就指出,他们与父亲的肉身关系在表面上是缺失的。(D)组中其他的事件都把父子关系与财产和权力联系起来,尤其是雍辛的故事主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组归结为对父子血亲之社会性功能的肯定和张扬。
于是,我们得到了两组矛盾:否定肉身欲望———肯定肉身欲望;对母子血亲关系之生理性基础的肯定———对父子血亲关系之社会性功能的肯定。那么,这两组矛盾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回顾前面列的四组,我们会发现,(A)组和(B)组尽管矛盾,但都涉及到了“肉身欲望”;而(C)组和(D)组则都涉及到“亲属关系”。另外,(A)组中除了包含“禁欲”的义素之外,还包含有“宗教”的义素,也就是说,对欲望的否定是从宗教角度来讲的。乐仲天生不爱女色尽管是出于天性,但就其最后的“升仙”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散花天女琼华被贬谪人间做妓女乃是对她的一种惩罚,可见在宗教的范畴中,禁除色欲是升仙的条件(乐仲戒饮并没有全戒,“从此不复饮市上,惟日对琼华饮”,可见即使在宗教的范畴中,适量饮酒还是允许的)。(D)组中除了对父子血亲之社会性功能的肯定之外,还包含有“制度”的义素,也就是说,对父子血亲关系的肯定是从社会秩序之维持或破坏的角度来讲的。(B)组中除了肯定肉身欲望之外,还包含有“自然天性”的义素,即主要是从人的自然天性的角度来肯定肉身欲望的,它集中体现在礼佛吃素的乐母“病中思肉”的情节中。(C)组中除了肯定母子血亲的生理学基础之外,还包含有“伦理”的义素,即主要是从“孝母”的道德角度来肯定母子血亲关系的。于是,我们得到了另外两组关系:(A)组与(D)组较多地“文化”的范畴;(B)组与(C)组较多地属于“自然”的范畴(“孝母”的道德规范是可以在自然现象中得到支持的,所谓“乌鸦反哺、羊羔跪乳”就是在自然的范畴中肯定“孝母”的道德合法性)。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两组关系束,这个关系束就是《乐仲》文本的深层结构:
(一)矛盾关系:否定欲望(A)———肯定欲望(B)肯定母子血亲(C)———肯定父子血亲(D)文化(A)(D)———自然(B)(C)
(二)置换关系:否定欲望(A)———肯定父子血亲(D)肯定欲望(B)———肯定母子血亲(C)肉身欲望(A)(B)———亲属关系(C)(D)通过对《乐仲》结构的分析,这个文本空前地复杂化了,它表现为“欲望”、“宗教”、“伦理”和“社会制度”四种潜在因素在叙事中的置换和冲突。列维·斯特劳斯说,“构成神话的成分并不是一些孤立的关系,而是一些关系束,构成成分只能以这种关系束的组合形式才能获得表意功能”,这话也适用于小说。那么,这个结构表达了怎样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结构中出现的矛盾反映了怎样的一种社会问题?这个结构又表现了怎样的意识形态呢?这要从《乐仲》的故事情节中并没有直接表现,我们也一直没有解释的母子血亲与父子血亲的矛盾关系上来讲。
三
封建社会的家庭制度和伦理制度是以父子血亲关系为核心的,它决定性地表现在权力继承和财产继承两个方面,即宗祧继承制度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和财产继承中的男性血亲继承制。这里,父子血亲关系是在严格的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讲的。《乐仲》中,顾氏死后雍辛被雍家逐出家门,就是因为雍辛与雍家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他根本算不上是雍家的一员。相反,他在乐家却有不可剥夺的权力。可见,在权力和财产制度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父子关系是在生理学的意义上界定的。然而,对生理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的强调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母子关系的相应强调。因为,从经验的层面上来说,母子之间的生理性关系相对于父子关系要更为直观。子女乃由母体产生,母子之间的血肉亲缘是在能够直接看到的生理现象中得到支持的。但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中,母子血亲关系又是不起作用的。相反,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制度中,对于母子血亲关系的过分重视还会反过来妨碍父子血亲关系及建立起的伦理社会秩序。这突出地表现为财产继承中的嫡庶之争的现象。在《曾友于》中,蒲松龄讲述了一个父亲死后同父异母兄弟为继承财产而发生争斗的故事,篇末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愤然骂道:“天下惟禽兽止知母而不知父”。在《仇大娘》中,蒲松龄讲述了仇大娘帮助异母兄弟重整家业的故事,篇中有人问仇大娘:“异母兄弟,何等关切如此?”仇大娘说:“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兽如此耳,岂以人而效之?”
可见,嫡庶之争的背后是父系血亲与母系血亲之间的权力冲突。撇开性别矛盾不说,父子血亲与母子血亲的这种冲突就其实质上来讲,可以归结为父子关系的社会性与它的生理学基础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家庭制度和伦理制度本身是超越生理的,它是人性的和文化的;然而这种人性和文化的秩序又建立在生理的和自然的基础之上,于是,较之于父子关系更直接的母子关系便成为了父亲权威和整个父系社会秩序的隐患。可以说,这种矛盾和不平衡的状况在男权主导的社会历史时期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但是,对这种深层矛盾的意识又压迫着人们去想象性地缓和它,《乐仲》便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案,即通过弱化父子血亲关系的生理学基础,从而相应地弱化母子血亲关系在权力分配和财产分配中的影响,从而实现对父系血统之权威性的巩固。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就《乐仲》中存在的家庭模式加以对比的话,上述的观点会更加直观和确切了。在《乐仲》中出现过四种相互对立的家庭模式:(1)由乐仲和他的母亲组成的单亲家庭。这是一个父亲缺席的家庭,其结果是“家日益落”。(2)由乐仲和雍辛父子组成的单亲家庭。这是一个母亲缺席的家庭,其结果是“家计日疏,居二年,割亩渐尽,竟不能蓄僮仆。”(3)由雍辛及其母亲和他的继父组成的家庭。这是一个由亲母子加上一个非血亲父亲组成的家庭,其结果是在母亲死去之后,雍辛被逐。(4)由乐仲、雍辛和琼华促成的家庭。这是一个由亲父子加上一个非血亲母亲组成的家庭。结果是家道重振“、日益繁盛”。这四种家庭模式都有其极端性,但是其中的优劣之分是极其明显的。(3)(4)两种家庭模式以极端对立的方式表现了父子血亲对于家庭秩序的重要性,与它相比,母子血亲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此,第(4)种家庭模式作为一种理想的、当然也是幻想的家庭模式,就把“母子”关系的生理性方面彻底抛弃掉了,“母亲”被安排在一个仅仅是功能性的边缘的位置上,她类似于一个仆人,其作用就是帮助“父子”料理家务,而事关权利继承和财产继承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另外,《乐仲》的整个故事以“父早丧,遗腹生仲”为开端,以雍辛继承父亲家产为高潮,以顾老翁“六十余岁,生一子”为余续,不也很明显地体现了对父子血亲关系的强调吗?
这样,我们便能够理解《乐仲》这篇小说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之间的关系了。围绕乐仲所发生的“纵欲———禁欲———升仙”的事件系列与围绕雍辛所发生的“被逐———寻父———继承财产”的事件系列之间也就有了必然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乐仲与他的母亲之间的一系列事件隐含地表现出来的。
从一开始乐仲割股啖母、母亲的魂魄抚摸乐仲、在南海母亲化身莲花之上而在最后乐仲的股伤又变为莲花,这一系列事件都具有双重性:它们即具有强烈的肉身性,同时又是伦理性的。母慈子孝的伦理理想在这里以母子肉身的密切关系体现出来,肉身符码与伦理符码成为可置换的,而正是这一系列事件暗示了“禁欲”主题与“寻父”主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父子血亲的生理学基础的削弱在《乐仲》的叙事中被想象性地置换为对个体肉身欲望(食、色)的禁除,它最终是为了强化父子关系的超生理的社会性和权威性,而它所压抑的是母子血亲关系对父系权威的可能的破坏(如《曾友于》)。
综上所述,宗教禁欲思想在《乐仲》的深层结构中表现为调和伦理矛盾的手段。从佛教禁欲思想出发对欲望的否定在这里表现为对母子血亲关系的削弱和对父子血亲关系之权威性的巩固,它可以解读为是作者对封建伦理矛盾的一种无意识的和想象性的调和。这一观点表面显得有些牵强,而实际上是符合思想体系本身的存在规律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作为意识形态并不是由其自身教义的正确和错误而决定的,而是由它与具体的现实问题的关系所决定。只有当一种思想体系切实地发挥着想象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的时候,它才是意识形态。当然,这也意味着,任何思想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消亡,这不是因为有人信仰它,而是因为它总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去想象性地解释一些具体的社会现象,想象性地解决一些社会矛盾。在中国明清时代,佛教禁欲思想不是一种被信仰的对象(尤其不是士人阶层信仰的对象),但是它会在人们思考和解决具体的伦理矛盾时被无意识地“征用”,从而突破其自身存在的领域(宗教)而在其他现实领域(伦理)中切实地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乐仲》可以称作是一篇用宗教调和伦理矛盾的寓言。
参考文献:
[1]吴九成.论佛家思想对《聊斋》创作的影响[J].蒲松龄研究,1991,(1).
[2]刘敬圻《.聊斋志异》宗教现象读解[J].文学评论,1997,(5).
[3]蒲松龄.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4](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