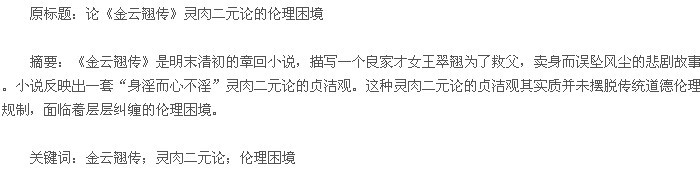
一、引言
《金云翘传》是明末清初的章回小说,描写一个良家才女王翠翘为了救父,卖身而误坠风尘的悲剧故事。小说不但反映出明清社会女性处于被操纵、贩卖的残酷现实,也反映出一套灵肉二元的贞洁观。作者用“身淫而心不淫”的说法来化解女主角的伦理困境,这种说法的前提就是“灵肉二元论”。
二、灵肉二元的贞操观
《金云翘传》(以下简称《翘传》)一书正文前有一篇《序》,落款是“天花藏主人偶题”,一开始就提到一个核心问题,即“贞”与“淫”的问题。
闻之天命谓性,则儿女之贞淫,一性尽之矣。何感者亦一,而应者亦万端?又若夫其性之所能尽者,始知性其大端也。而性中之喜怒哀乐,又妙有其情也。唯妙有其情,故有所爱慕而钟焉,有所偏僻而溺焉,有所拂逆而伤焉,有所铭佩而感焉。虽随触随生,忽深忽浅,要皆此身此心,实消受之。
而成其为贞为淫也,未有不原其情,不察其隐,而妄加其名者。大都身免矣,而心辱焉,贞而淫矣;身辱矣,而心免焉,淫而贞矣;此中名教,惟可告天,只堪尽性,实有难为涂名饰行者道也。故磨不磷,涅不缁,而污泥不染之莲,盖持情以合性也。
这段话,有三层含意。
第一,贞与淫,可以从身心两方面来加以界定。
第二,有身淫而心不淫者,也有身不淫而心淫者,千万不可“不原其情,不察其隐”,就随便给人戴上贞或淫的帽子。
第三,像莲花一般,在污泥而不染者,这是“持情以合性”的结果,也就是难得的真性情。
这一段表达的基本上是“灵肉二元论”。在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架构下,女性的贞节是女性人格的重要保障。而王翠翘沦落风尘之中,事实上已无贞节可言。但心灵的活动往往居于主导的地位,心灵是一个独立操作的单元。《翘传》序的作者认为,王翠翘是“身淫而心不淫”,因此,就王翠翘的发心而言,她应该是一个“贤女子”,不应该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娼妓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给王翠翘定位,《翘传》序的作者自然对她赞叹有加。
翠翘一女子,始也见金夫不有躬情,可谓荡矣。乃不贪一夕之欢,而谆谆为终身偕老计,则是荡而能持,变不失正,其以淫为贞者乎?亦已奇矣。及遭父难,则慷慨卖身,略不顾忌,虽眷恋其人,亦不过借李代桃,绝不以情而乱性,此不为尤难乎?难者且易之,故视辱身非辱也,行孝也;茹苦非苦也,甘心也。何也?父由此身而生也,此身已为父而弃也。
此身既弃,则土也,木也,死分也;生幸也,何敢复作闺阁想?
迨后,抱书生之衾裯,作虎狼之伴侣,岂其情之所钟焉?卉风花无主,暂借一枝逃死耳。故一闻招降,即念东南涂炭,臣主忧劳,殷殷劝降,此岂溺私恩而忘公义者哉?此岂贪富贵而甘作逆者哉?了可辨也。若明山一死,我实误之,不忍独生,又其内不负心,外不负人之馀烈也。略其迹,观其心,岂非古今之贤女子哉?
这一段话强调,王翠翘的性格是“绝不以情而乱性”,她虽然沦落风尘,毕竟是“卉风花无主,暂借一枝逃死耳”。因此作者以为,对于王翠翘,应该“略其迹,观其心”。《翘传》序的作者,显然要从身心二元的角度来化解王翠翘的伦理困境。王翠翘最后投江遇救,得与家人乃至爱人团聚,这是老天爷对她忠孝两全的酬答。
至于死而复生,生而复合,此又天之怜念其孝其忠,其颠沛流离之苦,而曲遂其室家之愿也。乃天曲遂之,而人转道而不尽速,以作贞淫之别。使天但可命性,而不可命情,此又当于寻常之喜怒哀乐外求之矣。因知名教虽严,为一女子游移之,颠倒之,万感万应而后成全之,不失一线,真千古之遗香也。
《翘传》序的作者,甚至于认为“名教虽严,为一女子游移之,颠倒之,万感万应而后成全之,不失一线,真千古之遗香也”。把王翠翘形容为颠覆儒家名教的奇女子。
印度的诗哲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第73首诗中有这么一句表达:Chastity is a wealth that comes from abundance oflove.(贞操是充沛的爱情所带来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贞操,至少有三层含意。
第一,贞操与爱情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贞操是一种心态,而不是指身体器官的状态。
第三,贞操通于男女,不是男性对女性的片面要求。
从泰戈尔的角度来界定贞操的意义,显然是更贴近人性的。
三、灵肉二元观念的伦理困境
《翘传》第二十回有一段王翠翘与初恋情人金重洞房之夜的描述,反映出王翠翘重返正常生活之后面临的伦理困境。
金重叱退侍妾,重剔银灯,再将翠翘细视,只见星眼朦胧,红蕖映脸,不啻烟笼芍药,雨润桃花,宛然如昔。因为轻松绣带,悄解罗襦,相偎相倚,携入鸳帏。还指望抚摩到情浓之际,渐作贪想。谁知翠翘思则如胶,爱则如漆,情则如冰。
只言及交欢,便正色拒绝道:“委此身残败,应死久矣。以郎爱我出妾格外,故含羞忍辱以相从。若不及于亵狎,使妾忘情,尚可略施颜面以对君子;若必以妾受辱者辱妾,以妾蒙羞者羞妾,则是出妾之丑也,则妾惟有骨化形消,委精诚于草露,再不敢复调脂腻粉,以待巾栉矣。妾言尽于此,乞郎怜而保全之,则妾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这一段夫妻对话,把王翠翘的心理障碍表露无遗。王翠翘可以接受丈夫的拥抱,但拒绝“交欢”。
第一,她认为自己“此身残败”,不配为妻。
第二,她认为丈夫如果与她行淫,那就是“以妾受辱者辱妾,以妾蒙羞者羞妾,则是出妾之丑也”,也就是等于用她过去娼妓生涯中受辱的方式来对待她。
第三,这是她最后的坚持,请不要逼她。
从第一个理由来看,这就是王翠翘长期娼妓生涯所累积的自卑感。这个自卑感不是一夕之间可以改变的。她接受丈夫的拥抱,这表示,她需要真爱的支持。性行为对她而言,早已成为一种人格受辱的酷刑。更严重的是,性行为将立即引发她深刻的罪恶感。王翠翘拒绝与丈夫行房,深入地去看,本质上就是罪恶感的另外一种表现。
王翠翘的“罪恶感”的发生,其实质就是一种潜在的传统道德伦理规制,面对的是与灵肉二元观念层层纠缠的伦理困境。王翠翘被骗为娼,她一度寻短,但心中又怀着哪一天可能与父母和情人重逢的想望,因而忍辱偷生,随时盘算着如何脱逃。这一连串的“具体的行为意图”都指向道德的“善”。
所以说,王翠翘自责道德之误,表现了她自己对道德之善的坚持。她拒绝行房,也表现了她的坦诚。《翘传》接着又有一段对话。
金重道:“夫人励名节,诚足起敬。但思至私者,莫如夫妻。闺阁之私,犹有甚于此者?何夫人偏于至私者,而转立至公之论?”
翠翘道:“至私者虽妻夫,而你知我知,则至公者,又夫妻也,妾公而不欲私者,非为他人,即为郎也,即为妾之心也。
使妾有私而郎隐之,不独妾愧郎,而郎亦愧妾矣。倘邀郎爱,便妾既私而尚有不私者在,则白璧虽碎而犹可瓦全也。且妾受辱之贞,惟此一线。倘郎必并此一线而污灭之,是郎非爱妾也,是仇妾也,妾又何感于郎哉!倘曰欢无所寄,嗣无可求,自有妾妹相承,何必以再生之薄命妾为有无哉!”
金重听了,不胜惊讶道:“原来夫人非女子也,竟是圣贤豪杰中人。我金重一双明眼,自以为知夫人矣。今日方知知夫人不尽矣,夫人既以千古烈妇自得,我金重再以眼前儿女相犯,狗彘不如矣。”翠翘听了,忙坐起身来,重衣上衣服,向金重深深下拜道:“谢知己矣。”金重急披衣跳下床来,抱住道:“夫人何郑重如此?”二人讲得投机,又唤侍儿再烧银烛,重倒金樽,相偎而饮。
这一段对话,可说是《翘传》中最令人伤感的对话。所谓“受辱之贞,惟此一线”,也就是王翠翘在娼妓生涯中,内在那一份始终不妥协的对于“贞操理念”的坚持。这个“受辱之贞,惟此一线”的表达,忠实地描绘出王翠翘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对王翠翘而言,正常的性生活,几乎已经不可能。
只要她心中还有罪恶感在,只要她失贞的污秽感没有消失,只要她在自己的伦理困境中得不到化解,她心中的伤口就会继续让她伤痛。在她那个时代里,她还没有能力去采取任何反抗的行动。她能够活下来,能够在历经十五年的沧桑之后还保有那么大的爱心与正义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