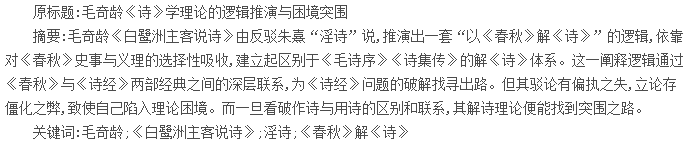
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甡,字大可,号秋晴,萧山(今属浙江)人,以郡望西河,故又称西河先生。他身处明清鼎革之际,以经学傲睨世间,挟博纵辩,务欲胜人,故能对晚明王学末流“束书不观”的治学风气深加抵斥,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经学痛下批评,并以崇尚考据、宗主汉唐的风格开清代学术之先河。毛氏遍通群经,于《诗经》学亦颇多造诣,著《国风省篇》《毛诗写官记》《诗札》《诗传诗说驳义》《续诗传鸟名》等书。这些著作多为考证札记,或解决某类专门问题,在《诗》学理论方面缺乏系统意见。唯独《白鹭洲主客说诗》(以下简称“《说诗》”)一书,虽仅一卷,却屡见惊警之论,并且能通过较为缜密的逻辑推演出一套独具特色的解《诗》理论,在清代《诗经》学坛亦能独备一格。
《说诗》成于康熙十七年(1678),其编纂缘起于一场学术辩论。时宣城施闰章(号愚山)任江西参议,讲学于吉安城南之白鹭洲书院。恰逢杨洪才(号耻庵)率徒求访,施便招毛氏前来。
诸人盘桓之日,多论及《诗》学,杨、毛二人观点不合,遂起争议。后来,毛氏将此次辩论的内容记录下来,便成是书。此书可看作一部短小的学术笔记,体例非常独特,以“阳干”甲、丙、戊、庚为客,以“阴干”乙为主,“客不一而主一”,彼此辩难应答。全书共三十条,后八条或为字词、名物杂考,或为“笙诗”问题专论,与毛氏其他《诗》学著作性质无异。但前二十二条呈现出较为完整的理论推演过程,系由“淫诗”问题切入,逐步转入对解《诗》方法的探讨。杨耻庵赞成朱熹“淫诗说”,并主张以词句为解《诗》之门径;毛西河则认为“《郑风》无淫诗”,并主张以史事为解《诗》之依据。正是在与杨氏师徒的辩难中,毛西河最终提出“《春秋》解《诗》”说。毛、杨的对决中,可以看到汉、宋两大阵营之间的交锋,一场关于“淫诗”和解《诗》方法的争论便由此徐徐展开。
对此,蒋见元、朱杰人《诗经要籍解题》为《说诗》作了解题,对毛西河大加抨击,未能理解到毛氏的真切用意。戴维在《诗经研究史》中辟出专节对毛奇龄的《诗》学观点加以解说,剖析了毛氏对“淫诗说”的看法,但仅局限在较浅层面上,并未发掘出解《诗》方法这一层面。近年薛立芳发表论文,将毛奇龄的观点挖掘得更深,已触及到“解《诗》方法”的问题。前人研究不断深入,但一直都没能充分认识到毛西河《诗》学观点的复杂性,也未能揭示出“《春秋》解《诗》”这一方法论,因此对毛奇龄《诗》学思想的认识也就显得偏激或片面。本文将详细分析毛奇龄的逻辑演进方式,并指出其理论的逻辑困境以及突围之法。
一、由“淫诗说”展开的论争
《诗经》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源头,又是历代儒家学者树立社会伦理的经典依据,一身兼具文学与经学双重路向。其中有很多诗篇是围绕男女情爱展开的,这既是对人类情感的热烈表达,体现非凡的文学价值;同时又涉及社会伦理的重要方面,关乎道德建设。有一些情感尤其强烈、内容尤其露骨的作品就集中显现了文学与经学这两重路向间的复杂关系。而与此有关的最重要的《诗》学命题,便是所谓的“淫诗说”。
汉代经学家普遍认为《诗经》经过孔子删订,不可能保留淫邪之作。以《毛诗序》为代表的儒家《诗》学阐释体系,常将爱情诗作包裹以后妃之德、君臣之义,进行百般净化与遮掩,以使其符合经学需要。但这些解释偏离了诗文本身的实际情况,而且《论语·卫灵公》明确记载了孔子“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的话语,似乎是直指《郑风》中大量的爱情诗,这些都注定了《毛诗序》的做法终会走向末路。宋代大儒朱熹终于直面这一挑战。他既要维护儒家思想的基本底线,又要符合《诗经》文本的实际情况,于是在经学与文学双重路向之间取得折衷,创造性地提出了“淫诗说”:“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夫子之于郑、卫,盖深绝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监戒于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
朱熹认为《郑风》中的这些诗篇本来就是“淫诗”,但被圣人拿来垂监戒以警世人。
此说修补了《毛诗》学说的不足,在学界激起了相当的波澜。自此,“淫诗”问题遂成为《毛诗》与朱熹,乃至《诗经》汉学与《诗经》宋学之间的矛盾焦点。我们探讨《诗经》学当中的汉宋之争与汉宋交融,就不妨以此为观察角度。
元明学者长期奉朱说为圭臬,对“淫诗说”的信奉尤其如此。但到明代中晚期,经学面貌发生整体转向,宋学遭到怀疑,汉学则日渐抬头。
这在《诗经》学方面具体表现为对朱熹《诗》说的反叛与对《毛诗》学说的回归。而在“淫诗”问题上对朱熹发难且见解精辟的学者,应首推杨慎。他说:“《论语》‘郑声淫’,淫者,声之过也。水溢于平曰淫水,雨过于节曰淫雨,声滥于乐曰淫声,一也。‘郑声淫’者,郑国作乐之声过于淫,非谓郑诗皆淫也。”
杨慎反对“淫诗说”理据有二:其一,“淫”应训为“过”,并非男女情欲淫乱之意;其二,“郑声”亦不可等同于“郑诗”,前者为音乐,后者为诗文,孔子批判者仅是音乐而已,与《郑风》文辞无关。一旦将孔子所说的“郑声淫”与《诗经·郑风》相剥离,就既可保持对孔子观点的信守,又可为以《郑风》为代表的“淫诗”洗脱罪名。
由于《毛诗序》对“淫诗”篇旨多作美化,而朱熹则竭力揭破其淫邪之处,似乎古代学者对“淫诗”的看法可以简单归结到他们对《毛诗序》的态度上:支持《毛序》者必定反朱并驳斥“淫诗说”,反对《毛序》者必定尊朱并提倡“淫诗说”。但实际情况是,在朱熹提出“淫诗说”之后,宋学阵营是否在反《序》的同时一致主张“淫诗说”,这姑且不谈,但至少在汉学阵营这里,尊《序》与反对“淫诗说”是可以分割开来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尤其到清代初年,《诗经》学的汉宋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汉学阵营的这种复杂性也集中暴露出来。这时,毛奇龄恰好充当了“汉学反朱派”的急先锋,他与杨氏师徒的这场论争正是从“淫诗”问题引入的。
《说诗》记载,杨耻庵师徒首先发难:“《郑风》多淫诗而夫子录之于经,何也?”所谓“夫子录之于经”,就是指“孔子删诗”说。毛西河认为“删诗说”乃不刊之论,由孔子亲手删定的三百篇必能“施于礼义”,而淫诗却不能如此,因此《郑风》并非淫诗。而他给出的论证却基本不出杨慎的框架,惟多出一点旁证而已。他以汉儒对《诗经》的态度为旁证,举出王式以三百篇为“谏书”以及龚遂劝昌邑王动静行为合乎三百篇这两个例子,从中看出《诗》三百皆可有助于匡正行止,辨别是非。而淫诗并无此功能,故《郑风》绝非淫诗。其实,无论是孔子删诗垂教,还是汉人以诗为谏,皆以《诗经》的总体特点来约束《郑风》,将“淫诗”排除在三百篇之外。
这种论证方式并未结合《郑风》诸篇的具体情况来谈,论证效力是有限的,我们大可以《郑风》篇少,不足以改变三百篇之全貌为由来反驳。
毛氏从正面做出以上论证后,又从反面攻驳朱熹的“淫诗垂戒说”,他说:“放弃其诗而反收之者,是明言佞人当远而反亲之也。若曰收之是垂戒,收即是放,则设颜子当时,乐则韶舞,既已作韶乐以示法则,又复作郑乐以示垂戒,韶、郑并作,观者将谓何?”
此处的“若曰收之是垂戒”便是暗指朱说。杨耻庵辈就此展开反击:“然而诗原有垂戒者,《小序》所谓‘刺淫’,非乎?”自中晚明以来,反朱之风渐起,人们常以《毛诗序》为利器,与朱子立异。而杨氏师徒为朱熹辩解的方法正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是用《毛诗序》来反驳毛西河。《毛诗序》就有不少“刺淫”之语,这不正是收淫诗以垂戒吗?如此一来,也不妨碍淫诗具有垂教和劝谏的功能了。毛氏为解释这一疑问,便从抒情人称的角度立论,将“宣淫”和“戒淫”区分开:垂戒诗必用戒语。如《小雅》“刺谗”、“刺暴”,皆傍人指数之,未闻谗暴者自道其谗态与暴状也,“刺淫”亦然。故《溱洧》、《东门》实有刺言,《氓蚩》、《蝃蝀》全用戒语,他皆非是。
且戒淫者欲使人读之而不淫也,乃读之而淫生焉,此谓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
他认为真正的刺淫诗应是旁人责数之词,有“刺言”和“戒语”,而非当事者自道其情,否则根本起不到垂戒的作用。但这一论证其实薄弱得很,甚至可以说是强词夺理,因为《郑风》中确实有不少女子自道其情的诗篇。杨氏师徒即抓住此点,反问毛氏:“夫读之而淫生者,以淫妇自道其所淫故也,郑诗多此。”面对这一质疑,毛氏终于摆脱了传统的考证方法,不再拘泥于诗歌的字面意义,他说:凡郑诗之所谓“叔兮伯兮”、“君子子都”,皆友朋相忆,托词比事。《离骚》所谓蹇修、姚妷,古诗所谓美人、君子,皆托比之词。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诬为淫妇赠淫夫,而不之察也……从来君臣朋友间,不相得则托言以讽之,《国风》多此体。而逞臆解说,锻成淫失,恐古经无邪之旨必不若是,此宋末儒者之言。
毛奇龄认为,“淫诗”中那些暧昧的词句其实都是君臣朋友之比兴。这就将诗篇的字面含义和实际含义做出拆分,给解诗带来相当大的自由度。但又引发出新的问题:为何一定要将诗歌解为君臣朋友之意,而一定不能解为男女之意呢?毛西河的解读路向虽具备可能性,却不具备必然性。
为此,他终于抛出其解诗方法论。他认为,朱熹将《郑风》解为淫诗,是因为太过专注于具体词句,但是“诗有关乎史事,不止词句”。他举出一系列春秋士大夫引诗赋诗的例证(即“史事”),发现《郑风》中那些所谓的“淫诗”被广泛用于诸侯、君臣、夫妇之间,皆取其正大光明之意,而殊无床笫琐亵之情。于此,“词句”与“史事”构成解诗方法上的一对矛盾。杨氏支持朱熹处,正在于前者,毛西河则以后者相抗:此正全不识诗而漫然以妄臆断之者也。诗人之意有故为儇语而实重,故为薄语而实厚者……且风人之旨意在言外,故言不足以尽意,必考时论事而后知之……凡以意逆志,须灼知其诗出于何世,传于何时,与所作者何如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若止就诗字、诗句仿佛想像,便凿然定为何诗,其为冤抑者不既多乎?
他告诫读者不可停留于词句,以片言只语自作主张,而应注重“考时论事”。毛西河提出这一主张,实质是在对整个宋学风气加以批判。宋人认为是以诗证诗,毛氏却斥为“仿佛想像”;宋人认为是疑经辨伪,毛氏则指为“妄臆断之”。而他所认为正确的解诗方法应是注重诗篇背后的历史信息,类似于“以史解诗”。而以史解诗的代表正是《毛诗序》。其解读诗篇时,便常常附会以史事,有些直接根植于《春秋》经传等史料,将诗歌背景坐实,有些则抓住零星细节捕风捉影,显得过于穿凿,这也就成为宋人废序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词意与史事之争及其引出的以史解诗之法,在《诗经》学史上都不新鲜,并不能使毛西河的《诗》学理论具备独特之处。但以上这些论述使毛西河由“淫诗”问题徐徐切入到一个重要的争议点,即如何看待《毛诗序》,尊之抑或废之?而在《郑风》中,这一争论尤其突出。西河发现,“胡安国作《春秋传》最为无理,惟《郑风》诸诗则特遵《小序》”。接下来,他就通过对胡安国《春秋传》(以下简称“胡传”)的评论,摆脱了尊序与废序之间陈陈相因的“口水仗”,而觅得了属于自己的富有特色的解诗理论———“《春秋》解《诗》”。
二、《春秋》解《诗》:核心理论的提出
《毛诗序》在《郑风》多个诗篇中,都将诗歌的历史背景聚焦于同一事件上,即“郑忽岀奔”。郑忽乃郑庄公之子。庄公薨,忽即位,是为郑昭公。其母邓曼位卑势薄,故使上卿祭仲辅佐之。忽有弟名突,其母为宋大夫雍氏之女,家世显赫。忽即位不久,雍氏便诱劫祭仲至宋,命其夺忽立突。祭仲不堪胁迫,遂拥立突,是为郑厉公。郑忽则被迫流亡卫国。此前庄公在世时,尝与齐僖公盟。僖公愿以女妻郑忽,忽却以郑小齐大,门第不当为由拒绝。后北戎伐齐,忽帅师救之,大败戎师。齐僖公为表谢意,又请以他女妻之,郑忽再次辞绝。而最终在与突争夺君位时,郑忽正是由于屡屡辞婚而坐失强援,才落得出奔异国的下场。这是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此事导致郑国陷入内乱,国力大损,也从此退出列强争霸的舞台。
《毛诗序》便将《郑风》的很多诗篇与此事相联系。《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大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山有扶苏》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萚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与贤臣图事,权臣擅命也。”这几条序文都对郑忽的行为提出批评,理由正是郑忽辞婚,坐失“大国之助”,导致了“君弱臣强”“权臣擅命”的结果。胡传在为“郑忽出奔”一事作传时,全取序说,并评论道:“夫以‘狡童’目其君,圣人犹录其诗,所以见忽之失国亦其自取,非独仲之罪矣。”
同样将失国之罪责指向郑忽本人。《毛诗序》和胡传对《郑风》诸篇的解释都将诗歌内容与春秋史事相关联,做到了重史事而轻词意。但他们均不认同郑忽辞婚之举,这些批评是从利害权衡的角度提出的,主要是痛感郑忽之举损害了郑国的战略利益,而非从树立正确政治伦理的角度立论,概而言之便是多言利而少言义。毛西河对此摆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站在“春秋大义”的立场上为郑忽辩护:予作《春秋传》,则甚以郑忽不取齐女为无罪。在《春秋》,正赏罚,只论理而不论势,用法而不用术,则断不宜责郑忽如胡氏所云。而在《诗》,则风人刺讥,但较成败,失势昧时,便亡倚赖。所谓辞婚本无过,亡援颇可惜。此当以《春秋》解《诗》,不当以《诗》解《春秋》者。
毛西河认为郑忽不娶齐女并无过错,既然《春秋》曾经圣人笔削,就应当论理而非论势,用法而不用术,不能因郑忽外失强援之利益损失就否定其辞婚之义举。《毛序》、胡传却单以成败论功过,背圣人之义远矣。毛西河进而提出其理论主张:应“以《春秋》解《诗》”,而非“以《诗》解《春秋》”。可能是为追求文字对称,毛氏于前后句皆称“诗”。但实则,前句的“诗”是指《诗经》,后句的“诗”是指《毛诗序》。一般的经学史论著总会将毛西河的学术立场概括为激烈的反宋崇汉。依此逻辑推演下去,会使人们草率地认为他在《诗经》学阐释中会自然而然地站在《毛诗序》一边,充当“尊序派”的旗手。但细观其《诗经》论述,就会发现在毛西河眼中,《毛诗序》并不具备权威性,相比之下《春秋》经传曾经孔子之手,满载着圣人的微言大义,则具备了更高的意义。在郑忽事件中,这种意义表现为利与义的交锋,毛西河通过对郑忽的翻案,告诫统治者应坚持人格操守,不为利益所左右。
在上例中,毛西河将笔墨集中在论证《诗序》之非,亦即不得“以《诗》解《春秋》”。此后,毛、杨双方辩争的焦点转入一篇具体的“淫诗”———《褰裳》,西河才终于对“《春秋》解《诗》”做出正面论述。《毛诗序》云:“《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
郑玄笺同序说。杨氏云:“《褰裳》诗:‘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惟男女相谑,其词甚安。若云郑突篡君,求救大国,可曰‘岂无他人’乎?”毛西河驳道:此非毛、郑之解,此春秋之诗,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者。当昭十六年,晋韩宣子聘于郑,是时郑方倚晋以拒楚。而宣子为晋上卿,且又甚贤。
乃复以郑商玉环之故,与宣子抗。则其郊饯时,赋诗言志,重申其倚恃大国之意,尚何敢以“岂无他人”自露其贰心于晋,别求荆楚,开郑罪戾?而子大叔赋《褰裳》而不为恧,宣子闻之而不为怪,且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
言必不烦求他人也。一似其言,固然有彼此相安而不之觉者,正以诗解,固如是也。正以作诗之本事,原求救大国而非有他也。正以风人之旨,言有甚傲而实殷,甚慢而实迫者,不必男女始安,非男女即不安也。不然,子大叔何人,而俨赋此诗。宣子何人,而且拜受之,而更为之辞。
读经至此而犹憪然不一省,真狂夫矣。故曰:诗义有在,必不当以陋儒之腹揣度词句,此其证也。
这可以说是“《春秋》解《诗》”的一次实践。毛氏以《左传》中韩宣子聘郑时的赋诗情形为证,说明“岂无他人”并非情人反目之辞,而实可用于向大国求助的外交场合。值得注意的是,毛西河说“春秋之诗,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这正是为“《春秋》解《诗》”做出的正面诠释。首先,“《春秋》解《诗》”是一种“考时论事”之法,区别于“以陋儒之腹揣度词句”。其次,这也区别于对《毛诗序》乃至整个《毛诗》学派的尊信,因为西河已明确说:“此非毛、郑之解。”
《褰裳》诗中,《诗序》认为求助大国是指郑人希望有大国能对忽、突二人争夺君位一事加以纠正;但《左传》中郑国子太叔赋《褰裳》,却是要借大国之力以自保。《左传》与《诗序》同是以史解诗,但具体说法不尽相同。如果我们只将毛西河的解诗方法论概括为“以史解诗”的话,就忽略了这种差异。在毛西河眼中,二者存在着地位的差别,他宁信《春秋》经传而不信《毛诗序》,是“以《春秋》解《诗》”,而非“以序解诗”,也不仅仅是宽泛的“以史解诗”。这就使我们明白,毛西河虽然反朱,却非《诗序》之佞臣。若直接将其归入所谓“尊序派”,就将问题简单化了。毛氏所倾心拥护的,其实只是《春秋》经传而已。
在这场辩争的最后,西河将问题从“淫诗”扩展到《诗经》的其他诗篇,且仍不忘以《春秋》经传解之。西河云:《序》何可尽信?予乡读《序》,取其合于他经他传者,而遗其不甚合者。如《硕人》“美庄姜”,此合于经传者也。《击鼓》“刺州吁”,此不合经传者也。何也?州吁时未成漕也,州吁不平陈、宋也,州吁伐郑,五日即还,无“不我以归”也。故予辨“淫诗”,以诗辨之,未尝以序辨之者。
毛西河首先表明,他对序说的信与不信,全以“他经他传”为依据。从其对《硕人》《击鼓》二诗的分析来看,所谓“合于经传”与“不合经传”,正是指《春秋》经传。而《硕人》《击鼓》皆在朱熹所定“淫诗”之外,毛西河“《春秋》解《诗》”之法虽由“淫诗”问题而引出,却并不限于“淫诗”这一特定范围内,而发展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经》阐释方法。
三、《春秋》解《诗》说的困境与突围
在对毛奇龄的解诗方法论有所了解后,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套方法呢?
首先必须看到,毛奇龄将《春秋》和《诗经》这两部经典紧密结合,解诗时依据春秋史事,参酌春秋大义,这并非出于偶然。从表面看,《春秋》与《诗经》所涉时代有所重叠,《诗经》中相当一部分篇章正是创作于春秋时期,而士大夫引诗赋诗的情节也屡见于《春秋》传文。
若要探寻诗篇本义,那么记载春秋史事最为详切的《春秋》经传自然就成为重要的依据。但问题是,如果仅因为所涉时代相近而援用《春秋》经传以解《诗》的话,那么《春秋》经传并不能占据某种核心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我们发现,同样记载《春秋》史事颇详的《史记》却没能获得毛西河如此的青睐,毛氏曾说:“夫《史》与《序》亦皆渺不可据矣。”
这并非取决于成书早晚,而是取决于书籍的性质以及内在负载的思想倾向。《春秋》经传不仅是史书,而且和《诗经》一样都是经书,是浸润着圣人大义的文字。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这两部经典不仅具有创作时间上先后相承的关系,而且都具备惩乱治恶的实际功用。换言之,若要判明《诗》之美刺,恰可从“春秋笔法”中找寻依据,获得材料与理论的双重支持。这就使《春秋》经传成为解读《诗经》内涵的一条必由之路,而非众多材料来源中的一种而已。毛奇龄以《春秋》释《诗经》,并不简单地是一种以一经证他经的方法,而是蕴含了他对《春秋》的特别看重,以及对《春秋》、《诗经》关系的独特看法。
以历时视角来看,会发现与毛奇龄同时期的朱朝瑛和姚际恒,也仅仅认识到“淫诗”说与《春秋》史事的矛盾而已,而且只是零星语及,且并未由此提炼出任何理论命题。而毛奇龄这套理论是对“淫诗”问题的系统思考,具备相当不俗的理论气质。可以说,毛奇龄是“淫诗”问题解说谱系中久失关注的重要一环,不仅弥补了《诗经》学史的空缺,而且足以使人眼前一亮。
不过,毛奇龄这套解诗方法是其理论节节败退的产物,因此多少带有一点仓促和狭隘。通过上文对《说诗》一书内部逻辑的梳理,我们可以为毛奇龄这套解诗理论找到最初的产生背景。由于“孔子删诗”说的存在以及《诗经》经学地位的不可颠覆性,历代凡反对“淫诗说”的学者都需要面对《论语》“郑声淫”三字所带来的难题。
当杨慎以对“声”和“淫”的重新界定破除这一难题后,“淫诗说”的反对者们仍要直面各篇“淫诗”本身的词句阐释难题,毛奇龄正是在此方面推进了杨慎的驳论,提出将史事与词意区别对待的观点,强调以史解诗的方法。但接下来,毛氏又要破解《毛诗序》所带来的麻烦,于是又进一步怀疑了《毛诗序》的正确性,使自己与一般的尊序派相脱离。而能够让他拥有足够理由反对《毛诗序》的,正是《春秋》经传的史实记载与内部深含着的微言大义。可以说,毛奇龄“《春秋》解《诗》”说的提出,是被一个个难题左右牵绊而最终脱困的结果,是被朱学支持者们穷追猛打而终于杀出的一条“血路”。我们了解到这一方法论时,会明显地感到其解释能力的欠缺以及证明过程的迂曲,这几乎都是源于这一特别的产生背景,这套理论是毛奇龄在理论上节节败退时使出的最后杀招,自然缺少了一点从容和淡定。这种仓促与狭隘使毛奇龄在以《春秋》解《诗》的过程中犯下了一些错误。
第一,毛奇龄在“词意”、“史事”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毛西河在《说诗》一书中严厉批判朱熹的“淫诗说”,并非揪住细节问题做详密考证,而是在解诗方法的层面上釜底抽薪,他反对宋儒那种揣度词句、以诗证诗的做法,提倡依托史实,以《春秋》经传为判别是非之标准。但从毛西河的其他《诗经》学著作(如《国风省篇》和《毛诗写官记》)中却又不难发现,他自己也常常仅靠诗篇词句来立论。这种现象又该如何理解呢?须知,毛氏之所以主张以《春秋》史事为解,而反对以诗篇词句为解,归根到底是缘于对“淫诗说”的反动。“淫诗说”正是朱熹从对诗篇词句的揣摩中得出的,因此若要反对朱熹,须从反对“以词句解诗”开始。若抛却“淫诗说”这一辩争背景,毛西河自己也未尝不以词句解诗。可见,毛氏主张以《春秋》解《诗》,自有其深刻原因;但在反对以词句解诗时却未脱偏执之弊,隐含着双重标准。
第二,毛奇龄在援引《春秋》经传解《诗》时,对材料的运用存在选择性忽视。我们知道,朱熹不仅提出了“淫诗说”,而且详细地圈定了二十余篇“淫诗”。其中有九篇见于《左传》,而被毛西河《说诗》一书所援引的共有七篇,即:襄公二十七年,晋侯享齐侯、郑伯,子展赋《将仲子》;同年,郑伯享赵孟,子大叔赋《野有蔓草》;昭公二年,卫侯享韩宣子,宣子赋《木瓜》;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大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春秋大夫在使用这七篇的时候,确实都没有表现出淫奔之意,恰可证明“淫诗”本来不淫。但《左传》所见九篇“淫诗”中还有两篇未被毛西河采用。一是成公二年,申叔跪讽刺巫臣:“异哉!
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杜预注云:“《桑中》,《卫风》淫奔之诗。”《左传》此处提及《桑中》,正用其淫奔之意,暗指巫臣与夏姬的私奔。二是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驷歂曰:“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左传》言“弃其邪”,即在暗示《静女》本义是邪的,而读者须从诗中截取出“彤管规箴”之义,才能达于“思无邪”的境界。
后一例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诗篇本义可以关乎淫奔,但读者尽可取其无邪之义,用以扬善抑恶,这才是我们对“淫诗说”所应秉持的态度。显然,这一例堪称朱熹“淫诗垂戒说”的绝好注脚。我们发现,前引七例皆未体现淫奔之意,毛西河将这些全都引入《说诗》中,当作反驳朱熹“淫诗说”的武器;但后两例却可为“淫诗说”张本,则被毛西河或无意或有意地绕开了。足见,毛西河对《春秋》经传的利用是片面的,他的“《春秋》解《诗》”说存在着狭隘的偏见。
毛奇龄恃才傲物、偏激刻薄的学术品性早已成为学术史上的定评,以上所揭示的这些偏见与错误当然与此治学风格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缘于毛奇龄对“思无邪”三字的理解过于僵化。
“《春秋》解《诗》”说所认定的“无邪”在宏观宗旨上是指诗人作诗与孔子删诗的无邪,而在阐释运作中具体为春秋士大夫用诗的无邪,遂表现为以《春秋》史料阐释《诗经》文本。毛奇龄之所以会出现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忽视的错误,就是因为他将宏观宗旨细化之后,却无法弥合《春秋》、《诗经》之间细节上的扞格,比如《左传》中中“弃其邪”的表述。其实两部经典并不矛盾,我们只需将作诗和用诗这两个环节分开看待即可。毛奇龄却以为二者均须无邪,这就与“淫诗”各篇的实际情况相差太大,难以实现。相比之下,朱熹“淫诗”说也只是说作诗淫,到用诗环节则认为孔子的“思无邪”都是无邪的,是垂监戒于世人。
若要从理论的困境中突围而出,则必须承认作诗与用诗的差异。毛奇龄以《春秋》为依据解读淫诗,那些春秋士大夫引诗赋诗的材料都可被放置在用诗层面上。而朱熹及其后学的“淫诗说”主要是针对作诗层面而言。二者其实并未真正形成针锋相对的态势。看穿这一点,才能对毛奇龄的解诗理论有清醒的认识,也才能为其错误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以《春秋》为依据,并非全无意义,至少启迪后人,淫诗是可以借由经学的思维加以净化的,而这种净化作用的依据来源于《春秋》经传,是与经学正统思想相贯通,并非脱离时代的迂腐之见。“《春秋》解《诗》”说还提醒我们,不能将《毛诗序》阐释体系与“以史解诗”简单划等号,同是“以史解诗”,却存在着《毛诗序》与《春秋经传》两套资源。
参考文献:
[1]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
[2]蒋见元,朱杰人.诗经要籍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83-84.
[3]戴维.诗经研究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502-507.
[4]薛立芳.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探微[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9-21.
[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〇: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72.
[6]朱熹.诗序辨说[M].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第14页上.
[7]杨慎.升庵集:卷四四[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799.
[8]胡安国.春秋传:卷六:桓公下[M].长沙:岳麓书社,2011:63.
[9]毛奇龄.国风省篇:卷一[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73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