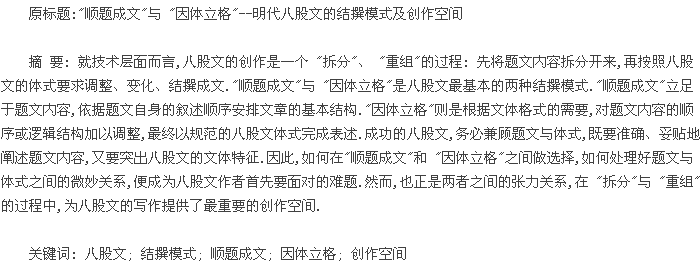
近十年来学界对八股文文体特征的研究已经颇为深入,①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八股文的创作机制.本文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阐述八股文最基本的两种结撰模式: "顺题成文"和 "因体立格".由此可知八股文写作所要遵循的基本法则,亦可知八股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拥有怎样的创作空间.
八股文以体制精严着称,却依然有着很大的创作空间.八股文的写作,义理阐释是断不可随意发挥的,体式上虽有一些选择的余地,变化空间也十分有限.那么其创作空间究竟来自何处呢? 这还要从其结撰模式及其与古文的异同说起.就技术层面而言,古文与八股文最突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文体要求将叙述内容安排到相应的篇章结构中,后者则要先将题文中的内容拆分开来,再按照八股文的体式要求加以调整、变化,并结撰成文.就此而言,古文创作是一个 "组装"的过程,而八股文的创作则是一个 "拆分"、"重组"的过程.古文创作虽然也要受到相应的文体规范的约束,但较之八股文创作毕竟灵活许多.八股文不但要受到文体的严格限制,还要受到题文的叙述顺序乃至语言结构的制约.尽管如此,八股文的创作依然可以在题文和体式之间觅得一些回旋的空间.
一类文章,主要根据题文的叙述顺序确定其结构方式,题文由两句、两段或两个主题构成,文章就写成两大扇,题文由三句、三段或三个主题构成,文章就写成三大扇.这种结撰方式,借用明清时期一个常用的批语术语,可以称作 "顺题成文".另一类文章,主要根据体式特征,尤其是标准的八股体,对题文的叙述顺序作出较大程度的调整,进而将题文内容安置于预定的文体模式中.这种结撰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 "因体立格". "顺题成文"和 "因体立格"是八股文最基本的两种结撰模式.然而,在实际创作中,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任何一篇八股文,都是两种结撰模式相结合的产物.有些文章是八股体式决定了其基本的叙述结构,但它们又必然受到题文内容的制约,这是由八股文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另外一些文章,题文内容的叙述方式成为决定其结构布置的首要因素,但这些文章也要符合八股文基本的文体规范,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八股文.事实上,"顺题成文"与 "因体立格",分别体现了题文内容和文体样式对八股文结撰方式的影响.八股文的创作过程,首先是寻求内容与文体之间平衡关系的过程.而八股文的种种技法及其审美意味,也正是在这种极具张力的关系中形成.以下通过一些具体的文章分析,说明两种结撰方式的基本特点、结合方式及其在八股文创作中发挥的作用.
一
通常来说,撰写两大扇文与三大扇文,首先考虑的自然是题文自身的叙述层次,同时又必须注意各扇文字之间的对仗或照应,以保证八股文最基本的文体特征.由于两大扇文中每一扇文字承载着较多的含义,且由于两扇之间大都是并列的关系,因而无论是在意义上,还是在形式上,每扇文字往往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但在两扇之间,却又必须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对应关系.因此,两大扇文往往具有板块拼接的结构特征.如何能在结构工整的前提下,又能做到衔接自然,这就要看作者的手眼了.关乎此,王鏊 《武王缵太王 及士庶人》一文堪称典范.其文如下:
《中庸》称二圣有继先绪而隆一统之尊者,有承先德而备一代之典者.(破题)盖德业创于前而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也.如二圣之所为,岂不有光于前人也哉! (承题)《中庸》述夫子之意谓: 夫欲知文王之无忧,当观武、周之善述.(起讲)夫文王既没,而不能作继之者谁欤? 盖太王、王季创于前,文王之业隆于后,而缵其绪者惟武王也.
观其身一着夫戎衣,师不劳于再举,而坐收一统之全功; 迹虽嫌于伐君,志非富乎天下,而无损万世之令誉.
且不独功名之俱盛而已,以贵则尊极一人,以富则奄有四海,而福有超于寻常也; 不独禄位之兼得而已,上焉则宗庙飨之,下焉则子孙保之,而业有光于前后也.
武王之继先绪如此,是以创业而兼守成,虽征诛而同揖逊矣,其武功之隆何如哉! (前一大扇)若夫武王已老,而受命承之者谁欤? 盖文王欲为而拘于位,武王得为而限于年,而成其德者在周公也.
观其隆古公之号为太王,加季历之称为王季,则近推乎文武之盛心; 祀组绀而上以王礼,迨后稷以下而皆然,则上追乎先祖之遗意.
于是推斯礼以及人,使有国而为诸侯,有家而为大夫者,咸得随等序而行其礼也; 达斯礼以逮下,使有位而为士,无位而为庶人者,皆得循礼度以伸其情也.
周公之成先德如此,是继述善于一身,礼制通于天下矣,其文德之备为何如哉! (后一大扇)吁! 武王缵焉而益隆,周公成焉而大备,此周家所以勃兴,而文王所以无忧也欤! (收结)①题目出自 《中庸》: "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称颂武王、周公,善于继承先人德业,成就丰功伟绩.
制义破题二句,紧扣 "善继"、"善述"之意,分言武王 "继先绪而隆一统之尊",周公 "承先德而备一代之典",全文即围绕此二句而展开.承题进一步强调 "善述"的重要意义,起讲则以 "观武、周之善述"领起下文.正文作两大扇,分别描述武王和周公之 "善述".前一大扇从 "夫文王既没,而能作继之者谁欤"说起,从而引出 "缵其绪者惟武王也",颇似一篇独立八股文的起讲部分.
以下以两组骈句分别训释 "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和 "尊为天子,富有四海.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单独来看,几乎就是严严整整四股文字."武王之继先绪如此"数句,是对此上文字的总结,依旧归结到 "继先绪"上,照应破题.后一大扇论周公之 "承先德",结构与前一大扇完全相同.
两大扇文字中,每一扇文字,都有领起、有展开、有收束,俨然是一篇独立的文章.然而,整篇文章依然严密、紧凑,并没有或松散或生硬的效果.这是因为,首先,文章的议题明确而集中.自始至终,全文紧紧围绕 "善述"而展开,绝无枝蔓旁生之现象.其次,文章的开篇与结尾反复将武王、周公并置而言,破题、承题两言 "二圣",起讲云 "当观武、周之善述",收结再度并称武王、周公之功业.如此则在整体上形成一种二元性的结构特征,故不觉两扇文字生硬.再次,两扇之间的衔接也颇为巧妙.后一大扇的首句 "若夫武王已老,而受命承之者谁欤",十分自然地从武王过渡到周公,以一种时间性的顺承,替代了空间性的并列,自然会冲淡那种板块式的印象.
可知,王鏊这篇制义,虽然是两大扇文,却显然是经过了作者的精心处理,于参差变化中对应整齐,明显区别于寻常的经传讲义.然而,有些制义文字,或者是太过受题目限制,亦或是刻意追求一种古朴风格,则不免影响了文体的规范性.如蔡清 《吾五十而志于学 一章》一文:
圣人希天之学,与时偕进也.(破题)夫学与天为一,学之至也; 然而有渐也,故与时偕进.圣人且然,况学者乎! (承题)若曰: 人生之初浑然天也,少长而趋于物欲,则丧其天.故吾于成童之时,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于学,务求纯乎天德而后已.
志学固知所用力矣,犹未得力也.加以十五年之功,三十而壮,则天德为主,而人欲不能夺之矣.
立则固守之矣,非固有之也.加以十年之力,四十而强,则心源澄澈,而渣滓为之浑化矣.
不惑固明诸心也,未及一原也.又十年而五十,而义理之所自来,性命之所自出,一以贯之而无遗矣.
知天命固与天通也,或未合一也.又十年而六十,则声入心通,若江河莫之能御矣.
吾未七十,犹未敢从心也,从之犹未免于逾矩,未与天一也.自六十而又进焉,然后天即我心,我心即天,念念皆天则矣.(六段正文)吁! 始而与时偕行,终而与时偕极,圣人之学盖如此.(收结)①题目出自 《论语·为政》: "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乃孔子自言其进学之阶.后世多认为圣人生知安行,固不必有此累积渐进之序,实则勉励学者勤奋向学之语.程子、朱子均持此种意见.
蔡清此文则依据经文的字面意思,将孔子进学之序落到实处,一层一层揭出其进学之因与成德之效.方苞原评称其 "段段于交会中勘出精意,实见得圣人逐渐进学并非姑为设教语意",即此之谓.
破题曰 "圣人希天之学,与时偕进也",拈出一个 "天"字,作为全文的题眼.承题强调 "与天为一"之境界,且需从 "与时偕进"的过程中来.此下根据年龄阶段,依次写出六段文字.第一段独立成文,讲 "成童之时",全力向学,"务求纯乎天德"; 中间四段,两两成文,描述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不同阶段不断精进之过程; 后一段又独立成文,讲圣人七十以后 "与天为一"的学养境界.
最后以 "圣人之学盖如此"收束全文.
此文具备八股文的基本特征: 六段文字具有同样的叙述结构,均是先紧承上一阶段之进学状况,从反面指出此一阶段学养之不足,然后针对其不足,从正面描述此期进学方向与效果; 中间四段,对应整齐,而有变化,与寻常的四股文字无异.然而,就整体结构而言,这篇文章显然不太合乎八股文的体制规范.因此,我们只能称其为八股文之变体,甚至是破体.虽然方苞看重其 "实理融浃"、能"体贴圣人功候",并将其置于典范之列,然而由于其体制不够规范,终究难以成为后世八股文制作之范本.
二
可见,单向度地强调 "顺题成文",有可能造成八股文文体特征的弱化.反之,如果严格遵循"因体立格"的结撰原则,刻意追求文体格式的整齐,而不能妥善地处理其与题文内容之间的关系,则有可能影响到其阐释经典的准确性或贴切程度.八股文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它具有相对固定的叙述程式,尤其是标准的八股体或六股体,要求每一层意义必须由一组对仗的文字表达.而题文内容,即八股文的阐释对象,其叙述层次大都与八股文的结构不相符合.因此,只有对题文的叙述顺序或逻辑结构做出适当的调整,才能较好地适应八股体式的叙述程式.然而,倘若调整不当,有可能会曲解题文的本义,这就与八股文阐释经典的文体性质背道而驰了.对于不甚高明的八股文作者来说,这必然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八股文,往往是经后世选家精心编选而流传下来,自然不会明显背离题文的原意.但从一些不甚圆融、略嫌滞涩的结构布置中,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因体立格"的结撰模式可能导致的弊端.以李东阳 《所谓故国者 一章》为例:
大贤慨齐之不得为故国,必详以用人之道歆之也.(破题)夫贤才者,国之桢也.用之而谨,则无患于失人矣,尚何忝于故国哉! (承题)且人君之立国也,近之有一代之亲臣,远之有百代之世臣.苟或不能任世臣以为故国之实,而徒恃乔木以为故国之荣,多见其不知父母斯民之道也已.然所谓任世臣者,岂可昔日进而今不知其亡矣乎? 又岂可以不才之难识而遂自诿矣乎? 亦惟慎之又慎,得国君进贤之心焉斯可耳.盖国君之进贤,(起讲)以尊卑变置,若甚亵者,不敢以易心乘之也;疏戚易位,若甚慢者,不敢以忽心临之也.(起二股)慎之于左右之所贤矣,而所以慎之于大夫者犹是焉.推其心必识其才,果可以尊且戚也而后用之耳.不然,其可以左右先容而遂徇之乎?
慎之于大夫之所贤矣,而所以慎之于国人者犹是焉.推其心必识其才,果可以尊且戚也而后用之耳.不然,其可以誉言日至而遂信之乎? (中二股)观于去邪勿疑者不可不谨,则任贤勿贰者不可不谨益见矣;观于天讨有罪者当察其实,则天命有德者当察其实益彰矣.(后二股)人君果能用其所当用,又谨其所当谨,则举错公而好恶协,将不谓民之父母乎哉? 夫至于为民父母,则民之永戴与国之灵长相为无疆矣.国之所以为故者诚在兹也,乔木云乎哉? 齐宣欲以故国称于天下,信当预养世臣以为之地矣.(收结)①题目出自 《孟子·梁惠王》: "孟子见齐宣王,曰: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之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 '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欤?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 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 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 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 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 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此系孟子论用人之道,其主要意图在于劝谏齐宣王,人才用、舍须慎之又慎.所谓 "故国"、"世臣",只是因齐王话端而引出下文,"左右皆曰可杀"一节,亦只是前一段文字的延伸.故惟有 "国君进贤"至 "然后去之"一段,才是此章文字的核心部分,也是经义文章应当重点阐述的部分.
李东阳的这篇制义,破题、承题均突出 "用人之道",应该说是把握住了题文的主旨.起讲由"故国"、 "世臣"引出"国君用贤之心",当 "慎之又慎",亦能体现经文的叙述意图.起二股以"尊卑变置"、"戚疏易位"之非常情形,强调君王进贤决不可草率为之.中二股讲进贤,须慎之于左右、慎之于大夫、慎之于国人,察其情实而后用之.后二股对应 "左右皆曰不可"、"左右皆曰可杀"二节,而最终归之于 "任贤勿贰"、"天命有德".收结部分,对应 "然后可以为民父母"一句,并照应 "故国"、"世臣",亦甚是周密.方苞称此文曰: "剪裁之妙,已开隆万人门户.其顺题直叙,气骨苍浑,乃隆万人所不能造."且不论其是否 "气骨苍浑",姑观其如何 "顺题直叙",而又得"剪裁之妙".
从起讲到收结,文章基本上是按照题文的先后顺序而展开.方苞称其 "顺题直叙",自然是就此而言.然而,文章的正讲部分,即六股对仗文字,虽其先后顺序未变,而意义层次却被拆分开来,又重新安置于三个结构层次中.
题文中的相应内容,包括两个层次、四个意义单元.从 "国君进贤"到 "可不慎欤"是第一层次,也是第一个意义单元,提出 "进贤必慎",总领下文."左右皆曰贤"、"左右皆曰不可"、"左右皆曰可杀"是三个并列的意义单元,共同构成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层次的具体阐述. "左右皆曰贤"是从正面说明进贤必慎,"左右皆曰不可"是从反而说明舍之勿用亦需慎之又慎,"左右皆曰可杀"则是承上节文字的语势而下,一段收煞不住的文字.文章中,第一个意义层次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化散行为骈行,构成起两股文字.第二个意义层次中的三个意义单元,则被压缩到两个结构单元中.其中,第一个意义单元化作中二股,通过句式变化,将 "左右"、"大夫"、"国人"分别置于两股文字中.后两个意义单元各作一股文字,结合成为后二股.
从相互关系来看,经文的三个意义单元之中,前两个是并列的、较为紧密的单元,分别讲人才之用与舍; 而第三个单元相对疏远,只是第二单元意义的延展.而在李东阳的这篇制义中,经过如上结构处理,形成前一意义单元独重,而后二单元并列居于较次要地位的格局.这种格局转换,本身就有导致误解经文之可能; 更关键的问题是,经此调整后的表述,非但无益于经文的解读,反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理解障碍.如中二股文字,经此一番曲折表述,反倒不如原文明白畅达,且不似传注文字能于经文有所发挥.如朱子注曰: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犹恐其蔽于私也.至于国人,则其论公矣; 然犹必察之者,盖人有同俗而为众所悦者,亦有特立而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亲见其贤否之实,然后从而用、舍之,则于贤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进矣."①合情入理,透彻圆融,自是极佳解经文字.此篇制义则只是变换文字,丝毫无益于诠释经文.既不如经文简易明白,又不如传注深入透彻,虽具 "剪裁之妙",却显然不能算是一篇十分成功的经义文.这就说明,过于关注八股文的形式因素,而忽视其与经文内容的结合,同样难以作出好的八股文.
三
此般评价,绝非吹毛求疵,苛责古人,乃是从对比中得来.李东阳的另一篇经义 《欲罢不能 一节》,即是将 "因体立格"和 "顺题成文"成功结合的一篇典范之作.其文如下:
大贤悦圣道之深而尽其力,见圣道之的而难为功.(破题)盖道可以力求,不可以力得也.大贤学之尽其力,而造之难为功也,其以是夫.(承题)昔颜子自言其学之所至,意谓圣人之道虽高妙而难入,而其教我以博约也,则有序而可循.
是故: (起讲)沉潜于日用之间,但觉其旨趣之深长也,虽欲自已不可得而已焉;体验于行事之际,但觉其意味之真切也,虽欲自止不可得而止焉.(起二股)钩深致远而致其博者,无一理之不穷,则已磬吾知之所能矣;克己反躬而归之约者,无一事之不尽,则已殚吾力之所至矣.(中二股)于是向之所谓高者,乃得以见其大原,如有象焉卓然而立乎吾前也;向之所谓妙者,乃得以识其定体,若有形焉卓然而在乎吾目也.(后二股)当斯时也,于斯境也,将勇往以从之,则几非在我,愈亲而愈莫能即,又何所施其功乎?
将毕力以赴之,则化不可为,愈近而愈莫能达,又何所用其力乎? (束二股)颜子之自言如此,可谓深知圣人而善学之者欤! 虽然,颜子之所谓末由者,岂其若是而遂已哉? 扩其所已然,养其所未然,优游厌饫,至于日深月熟而化焉,则亦将有不期而自至者矣.其终不克至是,而与圣人未达一间者,乃命焉,非学之过也.后之君子,尚无以至之难而自沮也哉! (收结)①题目出自 《论语·子罕》: "颜渊喟然叹曰: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卓立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题目取该章经文的后一节,文章亦围绕此一节文字而展开,却将全章意思一一照应.
破题、承题,概括题文尽力求道而力所难及之意.起讲以原题的方式,论圣人之道 "高妙而难入"、"有序而可循",分别照应前节文字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和 "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起二股讲 "欲罢不能",乃是由于于日用行事间体验到圣学之意味深长.此意据 《集注》吴氏注: "所谓卓尔,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间,非所谓窈冥昏默者."中二股讲 "既竭吾才",正因欲罢不能,故得尽其所能.既能钩深致远,克己反躬,虽未能遽得圣人之道,亦可循序渐近,穷物理,尽人情.实则暗中照应 "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一节.后二股讲 "如有所卓立尔",又回转照应 "仰之弥高"四句,既得夫子循循善诱,又能竭尽其所能,故于当日不可把捉之道体,已能识取其卓然之貌.中间四股,揆其大意,当是依据 《集注》胡氏之注,其注曰: "无上事而喟然叹,此颜子学既有得,故述其先难之故、后得之由,而归功于夫子也.'高'、'坚'、'前'、'后',语道体也; '仰'、'钻'、'瞻'、'忽',未领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诱,先 '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达事变; 然后 '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闻,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是以 '欲罢不能',尽心尽力,不少休废,然后见夫子所立之卓然."后二股讲"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从朱子注: "盖悦之深而力之尽,所见益亲,而又无所用其力也."② 收结部分,先是总论颜子 "深知圣人而善学之",又对 "末由也已"作补充说明,意谓颜子之所以与圣人"未达一间",乃短命之故,而学不足以达乎至境.盖取 《论语·子罕》中夫子之叹: "惜乎! 吾见其进也,吾未见其止也."此文结构,其叙述顺序与经文完全相同,故可谓 "顺题成文"; 每一层次,每一意义单元,均以对仗工整的一组文字构成,是极其标准的八股体,故又可谓 "因体立格"; 且能照应上文、融合经传、浑然无迹,实可谓意义、逻辑与文体格式的完美结合.
还有一种情况,把本来是散行的、并不对等的文字,通过意义的补充与结构的调整,化作两大扇对应的文字,更能体现 "因体立格"与 "顺题成文"两种结撰方式相辅相成之情形.如王鏊 《晋之乘 二节》一文:
大贤之论圣经,始则同于诸史,终则定于圣人.(破题)盖 《春秋》未修,则为鲁国之史; 《春秋》既修,则为万世之法也.圣人之作经,夫岂徒然哉! (承题)昔孟子之意若曰: 古之为国也,必有史; 史之载事也,必有名.彼晋尝伯天下矣,其为史也,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故名之曰 "乘"焉.楚尝伯天下矣,其为史也,兴于记恶垂戒之义,故名之曰 "梼杌"焉.以至鲁为中国之望,其史必表年以首事,错举 "春秋"以名焉.(起讲)于斯时也,《春秋》未经仲尼之笔,褒贬不明,亦一 "乘"而已矣; 芜秽不除治,亦一 "梼杌"而已矣.是故以其事言之,齐桓并伯于葵丘之盟,晋文继伯于城濮之战,其事伯者之事也;以其文言之,诸侯有言左史记之,诸侯有行右史记之,其文史官之文也.何异于列国之史哉?
(前一大扇)然孔子尝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则夫子以 《春秋》之素王,秉南面之赏罚,一褒一贬,皆圣心所自裁; 一笔一削,虽游、夏不能赞.中国而入于夷狄则夷之,凛于斧钺之诛也; 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宠于华衮之锡也.此孔子之 《春秋》.虽曰旧史之文,而实为百王之大法也.(后一大扇)嗟夫! 《春秋》之作,自姬辙既东,王室衰微,礼乐不由天子,征伐出自诸侯.泯泯棼棼,圣人忧之.于是笔削一经,垂法万世.然使鲁之史官,阿谀畏怯,君过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 《春秋》以法万世,将何所据乎? 此史之功高于伯,而孔子之功倍于史.(收结)①题目出自 《孟子·离娄》: "晋之 《乘》,楚之 《梼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之事,其文则史.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谓鲁国之 《春秋》,未经孔子笔削之前,与晋国之 《乘》、楚国之 《梼杌》,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以史官之笔,记录诸侯之事; 惟经孔子之手,方为传世之经典.《集注》: "尹氏曰: '孔子作 《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世之大法.'"此二节经文纯以散句行之,虽然其用意主要是肯定孔子的功绩,而主要篇幅却用来说明 《春秋》未经孔子笔削之前与 《乘》、《梼杌》之异同.
王鏊依据题文本来的顺序安排其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又调整叙述的详略与层次,进而结撰成一篇两大扇体的八股文.破题 "始则同于诸史,终则定于圣人",简明而准确地概括了题文大意; 承题以 "鲁国之史"与 "万世之法"对举,进一步突出圣人笔削 《春秋》的重要价值; 起讲以阐述晋史《乘》、楚史 《梼杌》和鲁史 《春秋》的命名缘由领起下文.此下依据孔子修 《春秋》之前后,将正文分作两大扇."于斯时也",紧承起讲,指孔子修 《春秋》之前.此时的 《春秋》只是鲁国之史而已,与晋史 《乘》和楚史 《梼杌》并无本质区别.此下从其所载之 "事"与运用之 "文"两个方面加以解释.经文中言 "事"则有 "齐桓"、 "晋文",言 "文"仅称 "其文则史"; 制义则以 "左史"、"右史"对举,以与 "齐桓"、"晋文"形成格式上的对应.后一大扇以孔子语 "其义则丘窃取之"引出下文,暗转入 "笔削之后"而不明言,过渡自然,了无痕迹.此下则充分发挥 "其义则丘窃取之"的含义,对孔子修 《春秋》的意义和方法详加阐述.前一大扇包含两股文字,先断后案,由略至详; 后一大扇同样是以两股文字构成其主体内容,亦先总括孔子修 《春秋》之意,再详述其笔削之法.于是,经文中原本散行的一段文字,就转化成对应整齐的两大扇文字.收结对正文做出一些补充说明,进一步强调孔子修 《春秋》的重要意义.
从整体上看,此文显然是依据题文顺序展开论述,却充分挖掘出末一句题文未曾明言而应有之意,并根据八股文体式的需要对叙述形式做出适当的处理,从而撰成一篇标准的两大扇文.由此文可以清楚地发现作者对 "顺题成文"与 "因体立格"两种基本结撰原则的权衡与结合,进而了解八股文的形成过程.
综上所述,八股文有两种基本的结撰模式,分别是 "顺题成文"和 "因体立格".通常而言,"顺题成文"是立足于题目内容,依据题文自身的叙述顺序安排文章的基本结构; 而 "因体立格"则是根据文体格式的需要,对题文内容的顺序或逻辑结构作出不同程度的调整,最终以规范的八股文体式完成表述.其实,任何一篇文章都不可能完全按照某种单一的方式结撰而成,必然会同时考虑到题文内容和文体格式.一篇成功的八股文,通常会根据题文的内容特征,选择一种最恰当的结撰方式安排其基本结构,兼顾题文与格式,既能准确、妥贴地阐述题文内容,又能突出八股文的文体特征.可见,"因体立格"与 "顺题成文"之间的张力关系,恰恰为八股文作者保留了创作的可能,为他们提供了各逞才情、争奇斗妍的技艺空间.明乎此,我们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八股文的创作机制和创作过程,或许也有助于我们对八股文的文体价值作出更加公允的判断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