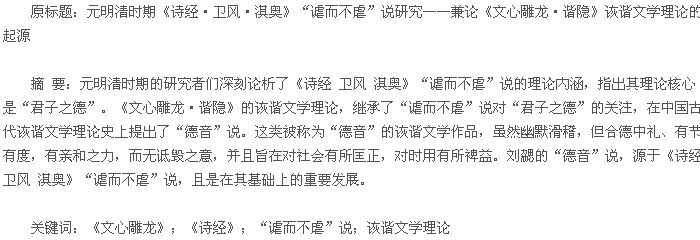
《诗经·卫风·淇奥》,是一首赞美卫武公的君子之德的诗,卫武公人品文雅,又能听从臣子、友人的规诲劝谏,能以礼法完善自身修养,加强自我约束,因此能够入相于周,成为周天子的卿士,卫国人为赞美武公之德而创作了这首诗。《诗小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
在对君子之德进行了详尽阐释的基础上,《诗经·卫风·淇奥》在全诗最后,提出了“谑而不虐”说——“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元明清时期的学者们在深入透彻地剖析君子之德的基础上,细致周详地阐发了“谑而不虐”说的要义和内涵,使这一建立在“君子之德”论的基础之上的诙谐文学观念,昭然明晰,影响后世。
一、元代对《诗经·卫风·淇奥》
“谑而不虐”说的研究元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卷三:“戏谑而不为虐,笑语卒获,出言有章是也。前二章犹有主敬之功,此则无事矜持,而皆出于自然也。凡人敛束之时,犹弓之张,舒缓之时,犹弓之弛。有德之人,严而泰,和而节,自不倚于一偏也……和易者,威严之反。威严而又和易,则是严而能泰也。此所以为德之成也……至于猗较则宽绰、戏谑则不虐,盖动作之间,无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朱公迁认为,“谑而不虐”,意指,君子的谈笑戏语能充分做到得当适宜、恰到好处,出言有规矩、章法。此处,朱公迁引用了《诗经·小雅·楚茨》“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的典故(毛《传》曰:“度,法度也。获,得时也。”郑《笺》曰:“卒,尽也。”孔颖达《正义》曰:“礼仪尽依法度,其为笑语尽得其时。”
南宋朱熹《诗集传》:“获,得其宜也。”今人高亨《诗经今注》引于省吾说,云:“获(获),读为矱,矱,规也。”),以《诗》说《诗》,匠心慧眼,深可称道。朱公迁引《诗经·小雅·楚茨》之句解说“谑而不虐”,意在暗示,合乎时宜、恰当适度、不失规矩的君子之戏谑,是以依遵法度的礼仪为前提的,而礼仪的本质是德,因为有德和礼的统摄,所以君子之戏谑才能做到看似随意,实则富有章法。
接着,朱公迁颇具卓见地提出了“自然”的概念,认为,君子之德不仅有以敬慎肃穆为主的一面,也有不务矜持的一面,而后者出自于君子的自然的天性本真。他认为,人在内敛拘束的时候,人性如张开的紧绷的弓弦,在舒息缓解的时候,人性如收拢的放松的弓弦,具有美德的君子,严肃而安泰,平和而节制,在张弛之间不偏向任何一个极端。他指出,和乐平易,本是威仪严肃的对立面,能把和乐平易与威仪严肃二者兼而有之,只有具备严肃而安泰的外在风貌的君子之德才能做到,能做到这一点象征着君子之德的最终成就,而“谑而不虐”正是这种经过不断磨练、培育而最终养成的君子之德在一举一动之间无处不表现出来的美盛的仪容仪范之一。
元刘瑾《诗传通释》卷三:“戏谑而不为虐,和易而必有节也。所以能然者,由其德之全备也……陈君举曰:‘古人张不废弛,屏不废逞(屏,隐藏,《尚书·金縢》:“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逞,显露,舒展,《论语·乡党》:“逞颜色,怡怡如也。”),肃肃不废雝雝(《诗经·周颂·雝》:“有来雝雝,至止肃肃。”南宋朱熹《诗集传》:“雝雝,和也。肃肃,敬也。”),僮僮不废祁祁(《诗经·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南宋朱熹《诗集传》:“僮僮,竦敬也。祁祁,舒迟也。”),有所拘者,必有所纵也。’愚按前章‘瑟僴赫咺’,张之时也;此章‘宽绰戏谑’,弛之时也。”
元刘瑾继承了南宋朱熹《诗集传》“和易而中节”的说法,强调“和易而必有节”,认为,“谑而不虐”,意指,既和悦平易、舒展放松,又能有所节制。刘瑾明确地指出,“和易而必有节”的基础,是君子之德的全面而完备。与东汉郑玄、唐孔颖达一样,刘瑾也试图从“张”与“弛”的角度,解说“谑而不虐”。刘瑾引用了南宋陈傅良(字君举)关于张、弛的论述来表达自己的主张。陈傅良认为:古人有紧张状态,但不废弃放松状态,隐藏而不废显露,敬肃而不废和乐,竦敬而不废舒迟,有所拘制,必有所放纵。刘瑾继承了南宋范处义《诗补传》的说法,认为,“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描写的是君子严肃紧张的状态,“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描写的是君子舒展放松的状态。元刘玉汝《诗缵绪》卷四:“既咏成德,则不可不见其进德之功与其进德之序……故末特以处己待人、动容中礼者言之。”
刘玉汝认为,《诗经·卫风·淇奥》主要描述卫武公的君子之德的不断磨练、培养、进步直至最终成就的过程,“宽兮绰兮,猗重较兮”描写端居卿士之车的卫武公宽和容众,性情绰缓,这是君子之德的“处己”的一面,而“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则是君子之德的“待人”的一面,君子无论是自处,还是与人接触交往,动容周旋之间都能合乎礼制,这是“谑而不虐”所欲表达的中心意旨。
二、明代对《诗经·卫风·淇奥》
“谑而不虐”说的研究元末明初梁寅《诗演义》卷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谓盛德之君子,言无非礼,虽戏谑之言,亦不为暴虐。盖言之当理,则不为暴虐,侮慢之言,则为暴矣。夫德既盛矣,其善戏谑者,亦君子之言也,非常人之戏谑者也。”
梁寅认为,“谑而不虐”,意指,具备美盛的品德的君子,他的言谈无不合于礼,即使是诙谐戏谑,也能掌握分寸,恰到好处,而不会刻薄伤人。他继承了南宋黄櫄在《毛诗李黄集解》中提出的“妙理”之说,强调了“理”这一概念,分析说,话语言谈只要在“理”上做到了恰当、合宜,合于“理”而不违背“理”,就不会成为刻毒的恶言,反之,不合于“理”的侮辱、轻慢他人的话语,就会伤害他人的感情。可以看出,梁寅所谓“理”,实际上是一种对语言分寸感的把握,是一种对交流方式、方法的选择。梁寅指出,在君子之德已经具备的前提条件下,即使是诙谐戏谑的话语,也可以成为有德之言,而不同于寻常人的戏谑。
明季本《诗说解颐·正释卷五》:“戏谑者,混俗之言,同于污世。本欲开导人心,未尝流于纵肆,则戏谑乃为善耳。若接人之际,厉色严声,指斥其短,即是虐矣。虐与戏谑,相反而善,则戏谑之不失正处,见其与人之乐易也。此四句皆言德之安身善俗,见其密而动容周旋无不中礼也。”
季本认为:诙谐戏谑,本是混迹尘俗之中的话语言谈,与污浊的俗世相通。只有意在开导人心,从不流于肆意放纵的戏谑才可称为“善”。如果在与人接触交流之时,疾言厉色,痛斥苛责对方的短处,这就是“虐”。
只有在“虐”与“谑”相反时,在“谑”彻底脱离了“虐”时,诙谐戏谑才能达到“善”的境地。达于“善”的戏谑,不失其正,没有丧失其开导人心的本意,可以表现出待人的和乐平易。“谑而不虐”体现出的是君子之德的既能高雅又能“善俗”,动容周旋无不合礼的周至细密的特质。
明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卷二:“‘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此方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地位,此乃为德之成也。”
姚舜牧引《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典,认为,“谑而不虐”意指,君子已经达到了即使任性而为、随心所欲、流露本真、率性自然,也不会超越礼仪法度的境界,这象征着君子之德的最终成就。
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戏’者……人之举止散诞。‘谑’,《说文》亦训‘戏’,但字从‘言’,则当为戏言耳。‘善戏谑兮’者,颐气解言,不立崖岸,载色载笑,与孔子‘莞尔’之戏同……‘虐’者,戏谑之过,必至任情凌物。玩一‘善’字,已是中节。特言‘不为虐’,以足之耳,非二时事。”
何楷从分析字义入手,指出,“戏”,是指人的行为举止散漫、荒诞,“谑”,是指戏言,也就是说,“戏谑”包括着言、行两个方面,这在“谑而不虐”的研究史上是富有新意的创见。何楷认为:“善戏谑兮”,意指,保养精气,倾吐郁积,在合礼合德的范围内对言谈形式、内容不更设藩篱,尽可喜形于色,欢笑忘我,以远绍《论语·阳货》中孔子“莞尔”戏言之风。“虐”,是指戏谑的过度状态和失控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中的戏谑,达到了任意放纵情感,凌侮外物的地步。“善”字,强调的就是对戏谑的节制,就是主体对戏谑行为的自控能力,以便使戏谑适当适度,不至于落入“虐”的境地。何楷化用了南宋陈傅良“谑而善,已是中节,特言不为虐,以足之耳”之语,指出,“善”字已经概括了君子之戏谑的“中节(符合法度)”的性质,“不为虐”只是对“善”的补充说明,二者实为一体,密不可分。
明张次仲《待轩诗记》卷二:“戏谑,谈笑诙谐之谓。欢而戏谑,易生陵侮者也,公则以礼自持。此言其和敬递施,宽严互见也。”
张次仲认为:戏谑,说的是谈笑诙谐。在欢乐的时候,做出戏谑的言行,容易滋生对他人的凌辱、侮慢,而卫武公在这方面则能够用礼制来把持自我。“谑而不虐”,即指,具备君子之德的卫武公能够做到,和乐与敬慎交替施行,宽缓与谨严相互映衬。
三、清代对《诗经·卫风·淇奥》
“谑而不虐”说的研究明末清初冯班《钝吟杂录》卷二:“‘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君子之戏,如虚舟之触,可喜也,而不可怒。戏语,毋伤人心。人有所讳,不可不避。好讦人之讳,忌祸之道也。”
在“谑而不虐”说的研究史上,冯班提出了“君子之戏”的概念,认为君子的戏谑,应如“虚舟之触”。此处,冯班引用了《庄子·山木》之典,《庄子·山木》有云:“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人能虚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此典意指,面对空无一人的船的碰撞,即使是心胸狭窄之人也不会动怒,因为来船无人,无处发怒,有鉴于此,人应像虚舟一般,无心于事,在社会上与他人交往才能避免受到伤害。冯班认为,君子之戏,应当像《庄子》所说的“虚舟之触”一样,不给他人带来刺激,造成不快,引起愤怒,而只带来喜悦和快乐,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虚舟”之“虚”,即君子之戏谑,应当无功利心,无目的性,去做作,去私欲,去锋芒,去恶意,有关怀。冯班所云“君子之戏,如虚舟之触”还蕴藏着另一层含义,即,君子之戏基于君子之德,经过磨练修养最终成就的君子之德,方圆内化,德性合一,圆善通达,亦庄亦谐,虚己寡欲,自然超脱,就如同虚舟一般,以之游世,从心所欲,游刃有余,而不逾矩,能达到被称为“游”的处世最高境界。在“谑而不虐”说的研究史上,冯班以道家学说阐释儒经中的“谑而不虐”,赋予其新意,是积极的创新。冯班进一步分析说,戏谑的语言,切忌对他人的心灵造成伤害,他人的忌讳,一定要规避,喜欢揭露他人忌讳的隐私,是招致憎恨、灾祸的行为。
清李光地《诗所》卷一:“卒章称其戏谑而不为虐,盖谨言之效也。”李光地认为,君子之德,要求谨言慎行,言若失德,便为失言,“谑而不虐”即是谨言慎言的效果、功效、证明。清世宗钦定、王鸿绪等编《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卷四:“陈氏傅良曰:‘谑而善,已是中节,特言不为虐,以足之耳。’…张氏彩曰:‘《诗故》云:…欢宴而至戏谑,易至陵侮者也,武公则以礼自检,是皆刚柔方圆之相济者也。’……《朱子语类》:‘三章但言宽绰戏谑而已,于此可见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礼之意。’”
王鸿绪等引用南宋陈傅良之语,认为,戏谑而称为“善”,善于戏谑,是指戏谑能够符合法度和分寸,“不为虐”是对“善”的补充说明。王鸿绪等借用明代张彩所引明代朱郁仪《诗故》之语,认为,欢乐的飨宴会导致狂欢戏谑,容易产生凌辱、侮慢他人的言语行为(《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便是卫武公讥刺周幽王宴饮无度之诗),卫武公能够用礼法来自我检视、自我约束、自我限制,使戏谑虽放纵但可控,以避免失礼失德,这是刚与柔、方与圆的互补相济。王鸿绪等引用《朱子语类》之语,认为,“谑而不虐”意指,有德君子从不做作,从不刻意追求矜持肃穆,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进退揖让、应对交际,无不自然地符合于礼制。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御纂诗义折中》卷四:“虐,害也……赫咺之久,降而和易,故有时而戏谑。然虽有戏言,终不害理,则不矜持而自不逾闲也。盖敬之熟,而忘其敬,忘其敬,而自无不敬,此则学修之极致,盛德之形容,非可作而致也。”
清高宗认为:君子在容止仪态上具有盛大显赫、威仪宣着的特点,但这种高姿态的仪容特点经营维持既久,必然会使人既内感疲惫又外显做作,因此君子会选择降低姿态,宽和平易,不时以戏谑自娱、娱人。然而,君子即使有戏谑之言,也终究不会妨害于“理”,这样,君子就能做到,不刻意矜持修饰,发乎心性地从容应对,自然而然地符合尺度分寸,不逾越界限范围。(此处,清高宗引用了《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之典。唐孔颖达注云:“闲,犹法也。”清高宗意在指明,唯有基于君子之德的戏谑,才能不超越礼法范围。)君子长期以敬慎肃穆之礼要求自己,达到了娴熟习惯的程度,敬慎肃穆已经内化为君子个人性格、素质的一部分,这时君子就会忘记礼仪礼制的具体条框,而按照自己的敬慎肃穆的本性而行,自然而然地无不合德合礼,这是学习、修养的最高境界,是美盛的品德的外现,不是可以通过刻意做作能达到的。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不为虐兮’,(毛)《传》:‘虽则戏谑,不为虐矣。’瑞辰按:虐之言剧(剧),谓甚也。如《终风》诗:‘谑浪笑敖’,即为虐矣。《书·西伯戡黎》:‘维王淫戏,用自绝’,《史记·殷本纪》作‘淫虐’,昭四年《左传》亦云:‘纣作淫虐’,淫虐即淫戏也。淫,大也,大戏即为虐矣。又襄十四年《左传》:‘臧纥如齐唁卫侯,卫侯与之言,虐。’虐即此诗‘不为虐兮’之虐,谓戏谑之甚,故纥云:‘其言粪土’,谓其言污也。杜(预)注训为暴虐,失之。”
马瑞辰从文字学的角度,指出,虐与“剧(剧)”通。他又通过考据,认为,“大戏即为虐”,虐的特征是“其言污”。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五:“戏谑不为虐,所以成戏谑之善。”
陈奂继承了南宋陈傅良和明代何楷的说法,认为,“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中,“不为虐”是对“善”的诠释、注解和详细说明。他又继承了明代季本的说法,认为,戏谑而可称“善”,全在其“不为虐”。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四:“篇末又言及善谑,以见容止语默无不雍容中道。”
方玉润认为,“谑而不虐”,能够表现出,君子的仪容、举止、言谈、恬静,无不温文尔雅、自然大方、平易豁达、从容不迫,合于“雍容中道”的君子之德。
四、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全面审视、详细分析元、明、清时期“谑而不虐”说的研究史,可以将《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的要义和内涵,归纳、整理如下。
第一,“谑而不虐”,是君子之德的“以礼自防”、“以礼自持”、“以礼自检”原则的表现(明张次仲《待轩诗记》、明朱郁仪《诗故》),合于《论语·阳货》“子之武城”莞尔之戏的“圣人之心”(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合于《孟子·尽心下》“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之义(元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元刘玉汝《诗缵绪》、明季本《诗说解颐》),体现着戏谑之间寄寓的“理”、“妙理”(元末明初梁寅《诗演义》、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御纂诗义折中》),源于君子之德的“全备”(元刘瑾《诗传通释》),折射着、反映着经过不断磨练、培育、修养的君子之德的最终成就(元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明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第二,君子之戏谑,体现“君子之德,有张有弛”(元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刘瑾《诗传通释》),发乎自然,无事矜持,因其将德、礼内化为性,依天性本真行事,故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元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明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清世宗钦定、王鸿绪等编《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御纂诗义折中》),体现了“德之善俗”(明季本《诗说解颐》),应“如虚舟之触”,无功利心,无目的性,去做作,去私利,去锋芒,去恶意,有关怀(明末清初冯班《钝吟杂录》)。经过归纳整理、综合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的要义和内涵的核心,是“君子之德”。
《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是《文心雕龙·谐隐》的诙谐文学理论的起源。《文心雕龙·谐隐》的诙谐文学理论,对《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的继承,就体现在,对“君子之德”的重视、关注、强调方面。《文心雕龙·谐隐》的诙谐文学理论,继承了《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对“君子之德”的关注,发展了《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的以“君子之德”论为基础和核心的要义和内涵,在中国古代诙谐文学理论史上,寄意深远、用心良苦地提出了“德音”说。
“德音”这一概念,源自《诗经》,自先秦以来,就一直与“君子”一词紧密相联、密不可分。
《诗经·秦风·小戎》:“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傚。”《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德音不已……乐只君子,德音是茂。”《诗经·小雅·隰桑》:“既见君子,德音孔胶。”西汉毛亨《诗诂训传》注《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云:“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德音”在《诗经》中,有两重含义:第一,美好的名誉、声誉。南宋朱熹《诗集传》注《邶风·谷风》云:“德音,美誉也。”注《豳风·狼跋》云:“德音,犹令闻也。”第二,有德之言,善言。东汉郑玄《毛诗笺》注《小雅·鹿鸣》“德音孔昭”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唐孔颖达《毛诗正义》疏之为“先王道德之音”。南宋严粲《诗缉》注《小雅·鹿鸣》云:“有德之言,甚昭明矣。”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注《小雅·鹿鸣》云:“德音,善言也。”在《诗经》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中,美誉、善言,皆来自于美德。因此,在《诗经》中与“君子”紧密相联的“德音”,实际上就是“君子之德”之音。
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借用《诗经》中的“德音”概念,继承《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对“君子之德”的强调,提出了诙谐文学理论领域的“德音”说。
《文心雕龙·谐隐》曰:“曾是莠言,有亏德音……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刘勰将那些“无所匡正”、“无益时用”而一味“诋嫚媟弄”、嘲戏调笑的诙谐文学作品,称为“莠言”。如,“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人因俳説以着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拚推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晳《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瑒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
这些被《文心雕龙·谐隐》称为“莠言”的诙谐文学作品,或挖苦他人的外貌,或以嘲弄他人取乐,千姿百态,光怪陆离,但它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都超越了适中、适度、中道、中和的界限,流于了肆意、放纵、毫无节制的刻薄和刻毒,违背了张弛有度的君子之德,达到了“谑而不虐”说中的“虐”的地步,而且无所匡正、无益时用、无补于事、空戏滑稽。刘勰对这类“莠言”,持坚决的反对和批判的态度,他通过历数、列举“莠言”类作品“诋嫚媟弄”之失,证明它们违反了合于君子之德的“虐而不虐”原则,并指出它们空作戏言、只图滑稽,认为这严重地亏损、败坏了君子之德,就像莠草一样有害。刘勰提倡与“莠言”截然相反的“德音”,这类被称为“德音”的诙谐文学作品,虽然幽默滑稽,但合德中礼、谑而不虐、有节有度、适中适当,有亲和之力,而无诋毁之意,更重要的是,这类作品,旨在对社会有所匡正,对时用有所裨益。刘勰的“德音”说,除了强调君子之德的“张弛有度”、“谑而不虐”之外,又增加了君子之德的匡正时弊、有益时用的意义,这是在《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的基础上的重要发展。
《文心雕龙·谐隐》“德音”说,是《文心雕龙·谐隐》的诙谐文学理论对《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的诙谐文学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在中国古代诙谐文学理论史上,以“德”规范、衡量诙谐文学的一次重要理论尝试,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孔颖达. 毛诗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14.
[2] 朱公迁. 诗经疏义会通[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75.
[3] 刘瑾. 诗传通释[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423.
[4] 刘玉汝. 诗缵绪[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239.
[5] 梁寅. 诗演义[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24.
[6] 季本. 诗说解颐[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461.
[7] 姚舜牧. 重订诗经疑问[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