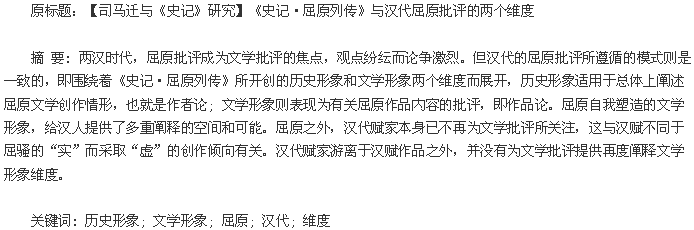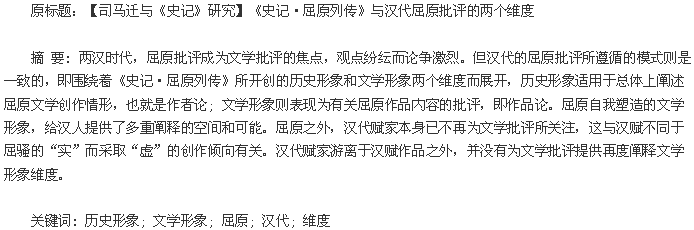
两汉的文学批评,屈原批评成为热点和焦点,贾谊、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均先后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由于经历、思想、立场以及关注的角度有异,各家意见纷纭乃至针锋相对,甚或同一个人在批评屈原时亦会出现自我矛盾、龃龉不可解之处。其实,汉代屈原论者在评屈过程中皆是从屈原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两个维度着眼的,历史形象主要适用于“知人论世”的层面,是汉人用作阐释屈原文学创作的钥匙;而汉人所评论的屈原则主要是屈原在其作品中自我塑造的文学形象。因而,汉代屈原批评实际包括两个层面,即“知人论世”的作者论和作为文学形象的作品论。由于史料缺乏,屈原的历史形象显得极为简略;而文学作品是屈原在其个人的感情色彩、立场倾向、道德评判等前提下的自我表达,因而屈原的文学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形象,呈现出多侧面、多种特征混合的样貌。同时,屈作的理想化属性和“香草美人”式的隐喻手法,又使得汉人在对屈原文学形象的接受和解读时形成了各不相同而又各有侧重的局面。
尽管屈原的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一方面展现出了极简略与极复杂的反差,但另一方面二者又具有客观真实性与文学虚拟性的不同。对于这两种形象的差别,汉人是有着清醒认识且严守其界限的,作者论主要据历史形象立论,作品论则是对文学形象的解读和评论。在作者论中,各家观点基本一致,而作品论中,则彼此互异。所以,揭示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对于理清汉代屈原批评的线索和方法,对于探讨屈原文学形象在汉代的接受历程及发展演变,对于揭示屈骚与汉赋“实”与“虚”的创作倾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史记·屈原列传》:屈原的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
如果撇开“屈原否定论”和《史记·屈原列传》“尤其不可靠”等观点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关屈原生平事迹最为可信的记载当属《史记·屈原列传》。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以文系人,以人系史,尽管存在着他文窜入、叙事不清、逻辑混乱等问题,但基本上展现了屈原历史形象的大致概貌。
《史记·屈原列传》的文字明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记载屈原的历史遭际,一是载录及评论屈原的文学创作,此即刘永济先生所说的“述屈子行谊之文”与“论屈子行谊文章之文”。前者的内容包括: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深受怀王信任;怀王令屈原造为宪令而为上官大夫谗毁,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既绌之后,在张仪的欺骗之下,楚国绝齐、失地,怀王客死于秦;顷襄王即位之后,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等历史事实。屈原的一生可谓怀才不遇、饱受谗毁,他用自沉汨罗的方式谱写了一曲忠臣为昏暗社会吞噬的壮烈悲歌,因而屈原的历史形象表现为怀才不遇的忠臣形象。
司马迁记载屈原的生平经历是为了引出其文学创作,《屈原列传》中“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一段与“屈平既嫉之,虽放流”一段,即是阐释《离骚》的写作背景、写作动机以及对《离骚》中的屈原形象加以评述的文字,“屈原至于江滨”一段是根据《楚辞·渔父》的改编,接着便是对《九章·怀沙》的直接引录。这些文字除了评述《离骚》艺术成就的部分外,皆为对屈原的评论,概括来说约有四点:
(1)“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之情;(2)“志洁”“行廉”的高贵品质;(3)“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存君兴国”的忠贞态度;(4)不忍浊世,以死坚守“初本”的不屈精神。显然,立论基础是《离骚》《渔父》《怀沙》等文学作品,因而,此四点综合起来就是经《屈原列传》的阐发后而形成的屈原的文学形象。
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是具有自叙传性质的抒情之作,多角度、全方面展露了屈原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屈原以此塑造了一个自我形象,也即文学形象。尝试言之,约有:(1)超世绝俗的高洁品行,(2)强烈的宗族自豪感,(3)忠君爱国的精神,(4)振兴宗国的“美政”理想,(5)与谗佞小人及污浊社会抗争的勇气,(6)以身殉国、坚守理想的崇高气概。这种文学形象可以丰富和补充屈原的历史形象,但是屈原自我塑造的文学形象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抒情视角,带上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与其历史形象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由于艺术上使用“香草美人”的隐喻表达,当屈原的文学形象被阐释、解读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读者或批评者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批评者心目中屈原文学形象的千差万别,既不完全同于屈原的历史形象,也与屈原自我塑造的文学形象有不甚一致之处。以《屈原列传》为例可以发现,记载屈原的历史形象是为了引出其文学创作,研究屈原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而前述评论屈原文学形象的四个层面,既没有强调“怀才不遇的忠臣”这一历史形象,同时也忽略了《离骚》中那种强烈的宗族自豪感和深厚的爱国精神,正如赵敏俐先生所指出的:“但是在通读《屈原贾生列传》时,我们对于司马迁的这种写法多少也感到有些遗憾。因为在屈原的作品中,还有一种更为深沉的东西,司马迁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那就是屈原对于楚国的无比热爱和眷恋。”
所以,《屈原列传》中,对屈原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的批评视角并不相同,历史形象主要用于阐释屈原的文学创作,文学形象则是批评者对屈原所塑造的自我形象进行“以意逆志”的结果。
二、汉代屈原批评的两个维度
《屈原列传》是一篇典型的文学批评之作,遵循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记载屈原的历史形象是为了“知人论世”地引入屈原的文学创作,可以称之为作者论;而其中屈原的文学形象既是司马迁(包括刘安)“以意逆志”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屈原之作内容的阐释和批评,也就是作品论。这两条线索并行不悖,代表两个批评视域,屈原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成为批评的两个维度,汉代的屈原批评也大致沿着这两个维度而展开。
班固的屈原批评如下:
《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终不觉悟,信反间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
(《离骚赞序》)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离骚序》)这两段评述看似自相矛盾,实际上是从不同的维度上展开的,《离骚赞序》在于阐明《离骚》《九章》的写作背景及写作意图,需要结合屈原的生平遭际知其人而论其世。这段材料与《屈原列传》的相关记载如出一辙,所评的屈原乃历史上的屈原,即“怀才不遇的忠臣”。《离骚序》是针对《离骚》而发的,尤其是为了反驳司马迁(刘安)高度评价《离骚》和屈原的观点,如前所述,司马迁(刘安)推崇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是对《离骚》中屈原文学形象的解读,而班固在解读《离骚》时有了与其不同的感受,即“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忿怼不容”、不能明哲保身的“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这表明,屈原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在班固那里出现了严重错位,屈原作为忠臣的历史形象已为班固所接受,但由于《离骚》具有多角度的阐释空间,加上班固个人的思想与立场倾向,经过班固解读后的屈原的文学形象已走向了历史形象的反面。
再看王逸的屈原批评: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谗毁之。
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衺,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
(《离骚经序》)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值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讽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
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离骚经后叙》)可以看出,前段文字除了多出三闾大夫的职掌外,基本与《屈原列传》及班固《离骚赞序》一致,同样是从历史形象的维度上探讨屈原的文学创作。
另外,班固和王逸都认为《离骚》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九章》等作于顷襄王之时,依据似乎也是《屈原列传》的相关记载,表明《屈原列传》已为班固和王逸所取信并征引,这从一个侧面可证《屈原列传》并非“尤其不可靠”。王逸高度赞扬屈原、批驳班固的立论依据则是“优游婉顺”的“屈原之词”,王逸对屈原的文学形象作出了与班固截然不同的解读。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同样是王逸评论屈原时的两个维度,只不过王逸将“怀才不遇的忠臣”之历史形象与“膺忠贞之质,体清洁值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之“俊彦之英”的文学形象进行了有机整合,使二者高度一致。
屈原不仅具有历史形象,还自我塑造了一个文学形象,所以从两个维度上进行屈原批评就成了通常的做法。汉代还有些评屈者并没有全面探讨屈原文学创作情况,只是单纯发表了关于屈原的看法,各家观点不甚一致的情形表明其立论依据是屈原的文学形象,因为屈原文学形象巨大的阐释空间造就了解读的多重指向。
《吊屈原赋》是汉代最早评论屈原的作品,贾谊对屈原处于“谗谀得志”“方正倒植”的时代深表同情,他认为屈原既然生不逢时就应该“远浊世而自藏”,可以“历九州而相其君”,因而“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贾谊所针对的怀念故都、拘守楚国的屈原,乃是《离骚》中“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晲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以及“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等诗句,是对屈原文学形象中以死殉国、眷念宗族这一特质的不同看法。扬雄无论是赞扬屈原“如玉如莹”的崇高品质,还是“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
的批评,都是对屈原“爰变丹青”之作品的解读,缘于扬雄“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情感体验,亦是在文学形象这一维度上的评论。至于《楚辞》中的“拟骚”诸作,如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采用第一人称代屈原立言的抒情方式,袭用《离骚》等屈作的诗句,其中的屈原形象很显然都是依据屈原自塑的文学形象的再度阐释。
总体来看,汉代屈原评论包括历史形象维度上的作者论和文学形象维度上的作品论,《屈原列传》、班固、王逸的评论因涉及到屈原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两个维度线索分明。而贾谊、扬雄、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的屈原评论中,主要体现出文学形象这一维度,历史形象维度上评论并不明显,原因在于:首先,他们的批评没有涉及作者论的部分;其次,大概因为屈原“怀才不遇的忠臣”的历史形象基本固定,可供阐发的空间有限。虽然如此,指出汉代屈原批评存在两个维度则是比较大致可信的。
三、从屈原批评的两个维度看楚辞与汉赋“实”与“虚”的创作倾向
两汉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除了屈原引起人们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外,其他作家的品行皆不为文学批评所涉及。其实,汉代作家的品行问题在后世亦被强烈批评过。《文心雕龙·程器》曰:“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颜氏家训·文章》曰:“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有些批评过于严厉,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是却与两汉时期对屈原的指责如出一辙。朱熹更是有见于扬雄对屈原颇有微词而反唇相讥:“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
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反离骚》)乃《离骚》之谗贼矣”。刘勰、颜之推对古今作家的激烈批判,是以其严苛的文德观为标准的,在这种标准下,屈原与汉代作家一样成为被否定的对象,并没有区别对待。
可是,汉代的文学批评却将矛头集中于屈原一人身上,对两汉作家置之不提,个中原因恐怕还得从汉代屈原批评的两个维度方面去找寻。如前所述,汉代屈原包括历史形象的作者论和文学形象的作品论,屈原在汉代激起争议甚至非议乃是文学形象维度上的,屈原在作品中自我塑造的文学形象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给汉人提供多重“以意逆志”的指向。相比之下,汉代作家在赋作的创作过程中,自我并没有参与到赋的内容之中,只是依靠虚构的方式在天地上下驰骋想象,虽有主观的讽谏意图,但是假托问答的结构、铺张扬厉的风格却造成了“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效果,可以说汉赋是外在于创作主体的,赋中没有可供阐释的自我形象。
因而,对汉代作家的批评仅限于历史形象维度的作者论,而无文学形象维度的作品论。本质上说,屈骚与汉赋“实”与“虚”的创作方式造成了文学批评领域屈原与汉代赋家被区别对待的现象。
屈原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是自我文学形象的载体,创作主体与抒情主人公的重合使屈作具有“实”的精神实质。而汉赋“虚辞滥说”“闳侈钜衍”则是极“虚”的体现,刘熙载曰:“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如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至模山范水,尤其末事。”
易闻晓先生《汉赋“凭虚”论》对此有过详尽的论述:“大赋‘凭虚’,要在铺陈,其本质要义是显示炫耀,其叙述视角则假托虚拟,其主导倾向为夸丽藻饰,其虚夸目的在悚动人主,其才学施为在虚设空间,其铺排充实在名物事类,其祖述取用在殊方异物。”
可谓精当之论,然其认为汉赋“凭虚”倾向乃源于屈骚“篇幅的滋蔓、遭语的敷衍、名物的摛写,盖铺陈必将包罗物事,多称虚无”,则似有待商榷。不可否认,屈骚中确有如班固所指出的“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但这只不过是屈原托物抒情的手段,不可拘泥于表面文字,正如胡应麟所云:“‘餐秋菊之落英’,谈者穿凿附会,聚讼纷纷,不知三闾但讬物寓言。如‘集芙蓉以为裳’,‘纫秋兰以为佩’,芙蓉可裳,秋兰可佩乎?”更重要的是,屈骚虚夸的形式下隐藏着鲜活饱满的作者自我,《艺概·赋概》论曰:“《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
所谓不变者就是创作主体的情感世界。《诗薮》又云:“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鉅为工。”骚的“复杂无伦”即谓有虚有实,本质在实,赋“夸张宏鉅”则连文字与精神都是虚的产物,根本原因在于创作主体是否参与到作品内容之中。
屈骚实的创作倾向表现为屈原塑造了自我的文学形象,使得汉代屈原批评具有了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这两个维度,汉人对屈原文学形象的再度阐发便出现了不同观点的论争。而汉赋“凭虚”的创作倾向,使汉代作家进入文学批评时只有历史形象的作者论这一个维度,文学维度的缺失使汉代作家游离于作品之外,因而也就不为文学批评所关注。
参考文献:
[1]胡适.读楚辞[M]//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上海书店,1989.
[2]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3]赵敏俐.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的再认识———兼评屈原否定论者对历史文献的误读[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1):5-9.
[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汪荣宝.法言义疏[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8][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0]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宋]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清]刘熙载.艺概注稿[M].袁津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易闻晓.汉赋“凭虚”论[J].文艺研究,2012,(12):45-52.
[14][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