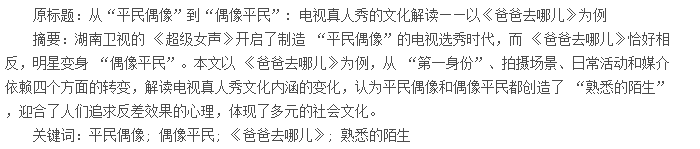
一、从平民到偶像: 电视选秀的神话
湖南卫视的 《超级女声》开启了制造 “平民偶像”的电视选秀时代。普通的参赛者展示才能,获取“专家评委”和 “大众评审”的好感,经过筛选淘汰,胜者为王,变身偶像,开启星途。电视为造星仪式提供了作为 “神坛”的夺目舞台,当选秀者走上“神坛”的那一刻,便被赋予了明星地位,完成了从平民到偶像的华丽转身。网络和手机提供投票渠道,共同形成制造 “民星”的 “流水线”。
经过近十年的繁盛,电视选秀制造出一批批平民偶像,有的登上了春晚舞台,有的签约演艺公司成为职业艺人。而当太多类似的 “超女快男”们令人疲惫厌烦时,出现了以浙江卫视 《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 “明星导师” + “草根学员”的选秀模式,再次掀起制造 “民星”的娱乐狂潮。但没多久,一批高度同质化的节目就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不仅内容编排如出一辙,就连音响、灯光、舞台的布置也大同小异———比如象征着权力的 “导师”转椅。
平民偶像的制造反映出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影响下人们心态的变化以及对张扬个性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观众不再满足于坐在电视机前看明星表演,还要成为主体参与其中,或投票选出自己心中的偶像。怀着对公平和平等的渴求,不但每个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走上标志着明星身份的神坛,而且谁走上去也由观众说了算,话语权力从精英转移到了平民。 《中国好声音》将实力作为考量选手的唯一标准,四位导师背对选手,仅凭声音表现决定是否转身,摒弃了以貌取人的偏见。白岩松说 “我觉得 《中国好声音》正在鼓励越来越多人,不是通过抱怨,不是通过暴力,妄图使自己的命运发生多大改变,而是希望在公平规则之下,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而改变。”
如果说 《中国好声音》模式是作为 “导师”的专业歌手决定作为 “学员”的普通人的命运,那么2013 年 1 月湖南卫视播出的 《我是歌手》 就实现了权力的反转。参演者从 “平民”变成了 “偶像”,职业歌手相互竞争,像普通选秀者一样被考核、批评、淘汰,决定他们去留的,正是普通观众。除了室内现场演唱还有外景跟拍,增加了歌手的排练和生活等内容,歌手表现出的紧张情绪让观众觉得很真实,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淡化了明星角色,强化了选手身份。但是,参演歌手从事的还是专业活动———演唱,只不过以竞技真人秀的方式呈现而已。
二、从偶像到平民: 《爸爸去哪儿》的转变
2003 年 10 月,湖南卫视播出从韩国引进、经本土化改良的明星亲情互动节目 《爸爸去哪儿》,由五位男明星带着他们的孩子体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将明星的身份还原为父亲的身份,暂时 “去神圣化”,实现了从偶像到平民的回归。
1. “第一身份” 的转变: 从明星到父亲
五位男明星分别是林志颖 ( 歌手、演员、赛车手) 、田亮 ( 运动员、演员) 、郭涛 ( 演员) 、王岳伦( 导演) 和张亮 ( 模特) 。平时,职业角色是他们的首要身份,但在节目中他们均被还原为 “父亲”的身份。转变 “第一身份”的方式是父亲和孩子处于同一空间,并且是实实在在的地理空间,而不是通过媒介 “在场”。因为父亲是一个相对的、互动的角色,如果孩子很久不出现,父亲的身份就被忽略了。
当某位男明星也是一位父亲时,观众一般不会以父亲的角色标准来认识、理解和评价他,仍关注他的职业身份; 有些亲子节目设置父子/父女同台表演、电话连线等等,观众对明星爸爸暂时有点印象,但很快就忘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职业特征太突出,与普通人差别很大,而父亲是一个相对平常的身份,理论上大多数男性都能够成为父亲,但不是谁都能成为明星; 另一方面,在传统的 “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人们更加关注男性的职业、收入和地位等,将这些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却不太关心是不是一个 “好爸爸”,近年虽有改观,但整体而言,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父亲的家庭角色缺位,在孩子抚育和成长的关键时刻,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明星的生活更加特殊,经常在外演出拍戏,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少,甚至连见面都难。林志颖说 Kimi 不愿离开爸爸独自完成任务可能是因为 “经常他一觉醒来,我就已经不在他身边了,就出国了”。
《爸爸去哪儿》中的父亲和孩子不但处于同一环境,还共同完成任务,爸爸给孩子做饭穿衣讲故事,孩子关心体贴爸爸,彼此有大量互动。这无时无刻不提醒观众他们的父子/父女关系,观众对父亲角色的印象越来越深,父亲身份被强化,职业身份被弱化,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从明星到父亲身份的回归。
明星们显然十分重视自己的父亲身份,努力争取孩子的认可。捕鱼那期,为了不让王诗龄失望,张亮帮王岳伦捕了一条小鱼,王诗龄立刻骄傲地说“我爸爸也捕了一条鱼! ”郭涛更是在其他爸爸都回去后还努力捕鱼,而石头一直陪在他身边。星爸萌娃参加 《快乐大本营》时,主持人何炅说田亮的人生有三次成功,第一次是世界跳水冠军,第二次是从运动员转型为艺人,第三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是“森蝶她爹”。虽是调侃,却也不无道理。好爸爸的价值不亚于功成名就,世界 500 强企业退休 CEO 们回答 “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什么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问题时,前 10 大企业老板的回答竟然相同——— “一定不放弃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可见,父亲这个看起来普通的身份,其实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普通。
从明星到父亲的身份转变,让明星从神坛上走下来,走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是从偶像到平民的第一步,也是最直接和最典型的身份转换方式,并在去偶像化的同时,体现了男性家庭角色重构的重要价值。
2. 拍摄场景的转变: 从演播室到大自然
从电视真人秀节目类型来看, 《爸爸去哪儿》兼具生存挑战型和情境体验型的特征。 “生存挑战型真人秀的主要特点是将参与者设计在一个特殊的艰苦环境中,借助有限的苛刻的条件去完成各种难以完成的使命……环境越艰难,选手的表现空间会更大,其命运也更引起人们关注”。
由于 《爸爸去哪儿》的参加者比较特殊,明星爸爸的生活料理能力不强,还有五个需要照顾的孩子,加之节目更追求娱乐效果,所以条件并没有一般的生存挑战型真人秀苛刻,所谓 “艰苦”的环境只是生活有些不便利。比如在沙漠中生活两天却只有 10 瓶水,用 50 元买两天的食物,打鱼卖鱼换取回家的路费等,挑战是相对的。
拍摄地点分别是北京灵水村、宁夏沙坡头、云南普者黑、山东鸡鸣岛、湖南平江镇和黑龙江雪乡,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征: 人工建设的痕迹少,朴素自然的状态多,与精美的舞台和繁华的都市形成强烈对比。因此父亲和孩子们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接受的适应过程。第一期节目中 Cindy 一直大哭,后来啜泣着问田亮 “为什么农村是这个样子的”; 天天不愿意和大家一起看房间,因为村里牲畜的气味让他觉得“太臭了,头晕”。但是后来孩子们却适应了更艰苦的环境,而且苦中作乐,爱上了自然。与光鲜亮丽的演播室相比,大自然是陌生、奇异而新鲜的。对星爸萌娃来说是这样,对看腻了音响灯光舞台的观众同样如此,节目播出后不少人想去拍摄点旅游。
偶像的诞生通常伴随着相对统一的、固定化的仪式,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化程序,也是对偶像化地位的赋予和维护。而演播室正是偶像建构仪式的重要空间,通过构筑光彩夺目的舞台,运用专业化的光影特效打造梦幻般的封神仪式。平民走进演播室,意味着变身为偶像的机会和可能,偶像走出演播室,象征着还原为平民的意识和愿望。因此,从日常生活中走进演播室与从演播室走向大自然,恰好是偶像仪式的建构与消解这样相反的程序。走出人工制造的隔离和封闭的空间,走进大自然,也就拉开了偶像仪式消解的序幕。
3. 日常活动的转变: 从表演到生活
根据拍摄地的特点,爸爸们的任务有捕鱼、挖藕、糊房顶、堆雪人等,做饭则是每一期都要完成的指定项目。宝贝们的任务有寻找食材、陪伴老人、洗晾衣服、照看婴儿等。这些普通人家司空见惯的活动,但对从事演艺的星爸和衣食无忧的萌娃却是不熟悉乃至陌生的,职业技能派不上用场了。星爸们大多不会做饭,照顾起居有点笨拙,面对大哭的孩子急躁不安,呈现了生活中真实的状态。观众看到爸爸们不完美的一面,不仅不会认为他们不优秀,反而觉得更“接地气”、更可爱了,王岳伦讨价还价的经典段子“4 块 5”甚至为他增加了更多粉丝。而孩子们更是本色出演,既不需要也没有刻意展现和遮掩某些方面,一举一动尽显童真童趣。
作为情境体验式真人秀,《爸爸去哪儿》以生活场景为主,戏剧性不强、动作性不强,更多依靠参与者和观众之间的 “关系”推动情节发展。
人们有了解和窥视他人生活的欲望,明星的生活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但是 “真”和 “秀”之间的分寸很难把握,过于 “作秀” 太虚假,没人爱看; 足够的“真”能够满足观众的窥视欲和好奇心,但有可能暴露和侵犯参与者的隐私。《爸爸去哪儿》的内容设置和拍摄剪辑较合理地平衡了真和秀的程度,在保护隐私的基础上呈现了星爸萌娃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每对父子/父女组合都有摄像机不间断跟拍,郭涛为换衣服不得不用衣服遮住摄像机镜头,可见节目的真实性; “换爸爸”那期,孩子们熟睡后又换回自己的爸爸,比较人性化。节目的每一个细节都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每一个生动的表情,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被如实记录,这些特写加深了观众对爸爸和孩子们生存环境和内心状态的印象。
《爸爸去哪儿》并不是当时唯一在播的亲子互动节目,但许多节目走的仍是以表演为中心的老路,孩子台上表演父母台下加油,内容是精心设计好的,看起来光鲜亮丽,却缺少新鲜感,缺少冲突,缺少真挚的情感表达。事实上,看过太多包装后的 “完美”明星形象,观众更希望看到他们自然真实的生活状态。从表演到生活,正是褪去偶像外衣、回归平民身份的核心环节。
4. 媒介依赖的转变: 从虚拟游戏到真实游戏每期节目开始,父亲和孩子们必须将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交给栏目组保管,除了录制设备外,暂时脱离了电子媒介的包围,与亲人通话只能借用编导的手机。意外的是,第一次交电子设备时,依依不舍的不是平常需要手机的父亲,而是将电子产品作为游戏机的孩子。比如天天迟迟不愿意交出 iPad,直到张亮偷偷告诉他 “我还有手机呢”,而当被告知手机也要交出,天天着急得哭了。孩子片刻离不开手机,可见对电子媒介依赖的严重程度。
这种依赖使情感的表达更加间接、原子化的个体更加孤立了。人机互动时间远远超过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即使面对面,各看各的手机也是常态。越来越多的网络 “强迫症”患者离开手机和电脑就无法生活,iPad 被称作 “电子保姆”,父母无暇陪伴孩子时便给他们 iPad 打游戏、看动画片。日复一日,父母和孩子都习惯了各玩各的电子设备,即使有时间也想不起来互动。虚拟电子游戏很有吸引力,与促进感情交流的真实游戏相反,虚拟游戏让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忘了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
对星爸萌娃而言,情况尤甚。明星需要借助电子媒介与外界 ( 尤其是粉丝) 联系互动,在旅途中用电子设备打发时间; 而 “星二代”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从小有机会接触和使用各类电子媒介,媒介信息接受程度更高,父母陪伴的时间却更少; 他们的一举一动倍受关注,出于隐私保护,不能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经常与小朋友玩耍,很多同龄人熟悉的游戏都没听说过,却可能是电子游戏高手。
因而,《爸爸去哪儿》以最简单的 “丢手绢”“干瞪眼” “萝卜蹲” 等游戏代替虚拟的电子游戏,朴素的游戏形式让集体参与性变强了,与抱着手机独自打游戏相比,不仅增加了父亲与孩子的感情,还促进了五对组合之间的友谊,的确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最后一期在雪乡,爸爸们包饺子,孩子们玩游戏,仿佛回到了没有手机和电脑的年代,通过共同参与进行感情交流,用王岳伦的话说 “就像过年一样”,语气中透露出对从前纯朴生活的怀念。
媒介依赖的短暂转变有助于星爸萌娃更好地体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更接近乡村的生活。而同样被电子媒介包围的观众虽然通过电视或电脑收看节目,但是对去电子媒介化的设计十分认同,产生了情感共鸣。这实现了从都市生活到田园生活的短暂回归,让整个节目更加简单质朴,更加平民化,更有人情味儿。
三、平民偶像化与偶像平民化: 熟悉的陌生
从平民偶像到偶像平民,看起来是完全相反的过程,其实二者有同样的思想根源,即人们求新求变的心理。电视真人秀巧妙地制造反差,创造 “熟悉的陌生”———故事是熟悉的,但是故事的过程和呈现故事的方式是我们所陌生的,而陌生的关键就在于故事中的 “人”是独一无二的。
平民偶像和偶像平民就是熟悉故事中的 “陌生人”,他们反转了日常的身份,与以往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前一秒还在普通的职业岗位上,是医生、工人、农民、学生……下一秒就可能通过电视选秀变身家喻户晓的草根明星,新鲜刺激不言而喻。明星恰好相反,观众习惯了他们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把他们看作有一定距离的、高高在上的偶像和象征着财富、优裕、地位、荣誉的符号,甚至忘记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电视媒介通常呈现具有一定 “社会地位”的人或事,似乎平常事不值得 “上电视”,而在电视上看到明星被还原为平民,从事洗衣做饭这样平常的活动,明星的权威、财富、地位和声望被消解,情理之中却意料之外,趣味之余,也消除了由于距离而导致的偶像光环。
人有猎奇、求新、求 变的心 理,喜 欢看角 色“反串”和反常的事物,因为打破了平淡的生活节奏,司空见惯之事却出乎意料,所谓 “新鲜”。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 “陌生化效果”,目的是“剥去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戏剧的陌生化效果是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实现的,而真人秀节目的陌生化效果不是编剧编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是天然的 “陌生化效果”。平民偶像化和偶像平民化是陌生化效果的典型,如星爸萌娃获得陌生体验的同时,观众也随其引导进入了陌生的生活,拍摄地点借景而不造景,走进相对陌生的大自然 ( 而且专门选择不热门的地点) ,使平淡的生活变得新奇独特,常识和经验被打破,那些 “理所当然的因素,也就是人们凭经验在意识中接受的特殊形象……重新被分解。一种图解式的推论在这里被推翻了。个人的自我经验可以对他从整体那儿照搬来的东西进行体验和纠正。”。生活的惯常逻辑是经过辛苦劳动获得成果,而电视选秀在真实的框架下打破了这种逻辑,成名的方式与现实不同,生活的秩序发生了变化。
与之思想相似而途径相反, 《爸爸去哪儿》等真人秀则通过对明星身份的消解重建生存主体,挑战人们的思维惯性。按照皮亚杰的图式理论,陌生化效果就是不符合原有图式的那部分,修正了以往的认知结构,对大脑和心理产生新的刺激,因此人们愿意接触和尝试。
无论平民偶像还是偶像平民,都创造了一种熟悉的陌生,用差异性的内容表达人类的普遍感情与普适价值,比如对亲情友情的重视、对公平平等的渴望、对自我价值的张扬等等,是 “差异”与 “普适”的结合,是对日常生活经验和规范的打破,是对社会秩序无伤大雅的颠覆,体现了人们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和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