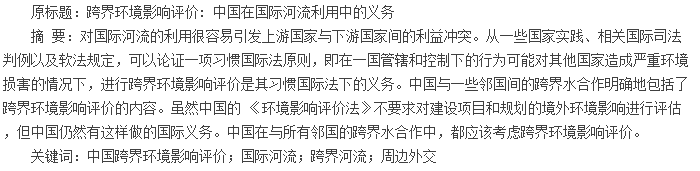
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这一资源正因为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气候变化等原因变得供应不足。所以,国家对国际河流的开发和利用就变得日益敏感,成为沿岸国普遍关注的事项。 “国际河流”最初指受条约制度管理的多国河流,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协约国和各参战国对德和约》 (又称 《凡尔赛和约》) 中时,指的是对一切国家均开放供自由航行的多国河流。
后来这一概念被泛化,到 1966 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 《国际河流利用规则》(又称赫尔辛基规则) 时,国际河流被定义为 “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水系的分界线内的整个地理区域,包括该区域内流向同一终点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虽然《国际河流利用规则》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国际河流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本文中,国际河流指流经一国以上,在水系的分界线内流向同一终点的地表水。
由于国际河流的上下游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所以国际河流法的理论和规则的发展一直非常缓慢。片面地强调对上游国家有利的领土主权论,或者对下游国家有利的领土完整论,都无济于解决上下游国家间在水利用问题上潜在的利益冲突。虽然无论在条约法体系内还是在习惯法体系内,国际河流的实体法规则都没有明显的发展,但在程序法方面,却有引人注目的演进。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程序规则发展的意义。程序性规则与实体规则之间有 “功能性联系”,即履行程序性规则是评判实体规则下的义务是否得到履行的标准之一,不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性规则,就难以证明国家履行了勤勉 (Duediligence) 的义务。程序性规则的发展对国际水法实体规则的发展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在国际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程序性规则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在国际河流利用中的环境损害评估的规则,这也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文章的视角是我国应该怎样对待国际河流跨界环评的国际法规则。
我国的国际河流有 110 多条,其中重要的有 15 条。
最近十几年,我国加大了对国际河流的利用。一些水利工程的规划和建设引发了下游国家的担心,比较突出的是西南地区的国际河流上的水利建设项目,如澜沧江上的水坝项目和规划中的怒江及雅鲁藏布江上的项目。类似的开发和利用已经引发了下游国家对中国的国际河流利用活动和规划的严重关切,以及对中国开展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强烈期待。以 2005 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为契机,中俄双方自 2006年起对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和兴凯湖等跨界水体展开了联合监测。俄罗斯是 《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公约》 (也称埃斯波公约,Espoo Con-vention) 的签字国,其国家杜马已经表示将批准该公约。所以,俄罗斯非常期望中国在中俄跨界水合作中也能够尊重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哈萨克斯坦是 《埃斯波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是伊犁河的下游国,对于中国伊犁河的利用也十分担心,在中哈跨界水合作中,哈萨克斯坦也盼望中国能够对跨界水的利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我国在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和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邻国以及南亚的印度等国家也十分关注中国在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的水利开发计划,期待中国能够公开更多的跨界水利用的信息,并且对水利工程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
中国作为国际河流的上游国家,有合理利用河流的权利,同时负有不使自己的利用给下游国家造成严重损害的责任。如何判断对下游国家有无损害或者损害的大小,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是最科学的工具。客观和科学的评价能够防患于未然,防止因对国际河流利用不当而导致邻国之间的猜忌、指责或纠纷。
然而,根据我国 2002 年颁布的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条,我国只对境内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那么,即使某些建设项目可能对境外的环境产生影响,也并不在法定的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之内。本文认为,我国应该扩大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对境内建设项目的境外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如果在一国管辖或者控制下的活动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严重不利的环境影响,国家有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
一、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是国家在习惯国际法下的义务
在国际水法领域内,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条约。这种情况凸显了习惯法作为这一领域内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国际法规则的作用。根据 《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国际法的渊源包括 “国际习惯,作为一般实践的证据被接受为法律者”。国际习惯是国际法最古老的渊源,对于国家具有普遍的拘束力,只有自始至终的反对者除外。
本文的研究发现,国家在利用跨界水时,对于可能产生严重环境损害的项目和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国家的一项习惯国际法义务,中国也应该遵守。本部分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一习惯国际法义务的存在。根据布朗利教授的观点,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有很多,包括国家立法、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和其他国际文件中经常重复的内容。
(一) 先例的开创和随后的国家实践
最早的环境影响评价规则载于美国 1969 年的 《国家环境政策法》,现在有很多该法律适用于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案例,但这些案例总体表明,这一国内法在规范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以美国的 《国家环境政策法》为蓝本制定的 《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价法》则在跨界适用方面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该法第 47 节直接而明确地规定了对建设项目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 如果加拿大境内的项目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严重不利的环境影响,外国政府或者其行政分区政府有权向加拿大环境保护部和外交部请求对项目的跨界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实施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典范无疑应属 《埃斯波公约》的45 个成员国 (截止到 2014 年 3 月) 。该公约的缔约方承诺,在批准可能产生重大不利跨界影响的项目时,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践行了跨界环评。根据 1995 年签订的 《湄公河流域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协议》,该协议的成员国———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在开发和利用湄公河之前,要通知湄公河委员会,并与相关方协商,取得湄公河委员会的同意。
在中国的邻国里,环境影响评价的实践并不限于湄公河国家。2010 年经缅甸政府同意,泰国电力公司和中国水电公司合作,计划在萨尔温江流经泰缅边境的主河道上修建哈吉大坝 (位于缅甸境内) ,泰国电力公司对该工程可能给缅甸和泰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价,并且报告已经公开。这类实践对于在该地区开展类似工程的公司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印度在其与巴基斯坦共享的印度河支流———杰赫勒姆河上修建基申甘加水电站时,也对电站项目进行了环评,并考虑到电站项目对巴基斯坦的影响。
(二) 有关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司法判例
在一国的行为可能给其他国家造成严重环境影响的情况下,各国纷纷通过立法,要求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这些实践推动了一项新的习惯国际法的形成。而在国际司法判例中,权威法庭关于跨界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表述,为这一习惯国际法的存在提供了 “宣示性”的证据。
国际司法机构在宣布环境影响评价已经成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方面,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对这一新的习惯法规则的肯定,最初只是出现在一个案件的异议部分。在 1995 年的核试验案中,国际法院的法官维拉曼特里 (Weeramant-ry) 在其异议中认为,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正得到支持和接受,已经达到普遍接受的水平,国际法院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该案的专案法官帕尔默(Palmer) 也认为,“习惯国际法已经发展出这样的规范: 当国家的活动对环境有重大影响时,应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仅仅两年之后,对这一规则的肯定,出现在另一案件的判决正文中: 在 1997 年裁决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大坝案中,法庭确认,争议的当事国有保护自然和维护多瑙河水质的持续性义务,“在评估环境的风险时,应该考虑现在的标准”。在上述两个案件对环境影响评价规则进行初步阐述之后,2010 年,国际法院在阿根廷与乌拉圭之间的造纸厂案中明确提出: 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是国家在习惯国际法下的一项义务。该案法庭裁定:当拟议的在共享资源上的工业活动可能产生严重的跨境的负面影响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已经被视为一般国际法的一项要求,这一点最近这些年已经得到很多国家的承认,当事国之间的条约应该根据这一实践来进行解释。此外,如果在河流上规划工程的当事国,没有就工程对河流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者就工程对河水质量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就不能被认为履行了谨慎和警惕的职责以及它们所包含的预防责任。
2011 年,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在关于国际海底采矿的咨询意见案中也重申: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仅仅是成员国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06 条下的义务,同时也是国家在习惯国际法下的义务。在 2013 年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关于巴基斯坦诉印度基申甘加水电工程仲裁案中,仲裁庭要求印度提交其对争议的水电工程所做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而此仲裁案是巴基斯坦根据 1960 年与印度签订的 《印度河水条约》(Indus Waters Treaty) 提出的,条约中并无缔约方须就印度河水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但仲裁庭仍然认为印度有义务对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仲裁庭认为,“国际环境法 (关于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在解释条约时是必须被考虑的,即使是解释在那一原则形成前缔结的条约,这是一项广为接受的实践。”
国家有责任确保自己管辖和控制下的行为不对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管辖控制以外区域的环境造成重大损害,这一原则长期以来被广泛接受。它在 1941 年的特雷尔冶炼厂案中就得到了仲裁庭的肯定,在 1948 年的科孚海峡案中又得到了国际法院的重申,随后在 1956 年的拉农湖仲裁案中又再次得到该仲裁庭的重申。
国际法院在 1996 年发布的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案中,明确指出: “国家有确保其管辖和控制下的活动不危害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管辖以外区域的义务,这一义务的普遍存在是与环境有关的国际法的一部分。”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是建立在该原则基础上的,是实现该原则的程序性保证。没有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国家就很难确切地知道其管辖和控制下的行为是否会对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造成环境损害。
(三) 有关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软法证据
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拘束力的国际法文件。虽然没有强制拘束力,但某些软法文件表达了对国家行为的清楚期待,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有一系列国际文件强调和重复这一原则。1972 年通过的 《斯德哥尔摩宣言》 第 21 条规定: “国家有……责任确保其管辖和控制下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这一规定反映了国际法上的睦邻友好原则和勤勉原则。
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是实现该原则的必要的程序性规定,没有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国家就难以确定自己管辖和控制下的行为一定不会给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造成环境损害。1987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颁布了 《环境影响评价的目标和原则》,并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该文件直接提到了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其目标之一就是 “鼓励国家之间当计划的活动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环境产生重要的跨界影响时,制定互惠的信息交换、通报和协商程序”。UNEP 的环境影响评价原则要求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就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规定了如何确定哪些活动应该进行环评,以及环评的程序和标准。
二、中国对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接受
(一) 中国通过多边条约接受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
中国批准或加入了一些含有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国际条约,这表明中国在那些条约所管辖的事项上对跨界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接受。作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 的缔约国,中国承诺: 如果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计划中的活动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污染或引发重大和有害的变化,将在实际可行范围内就这种活动对海洋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做出评价,并提供评价结果的报告。
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的爱尔兰诉英国的 MOX (MixedOxide Fuel,混合氧化物燃料) 工厂案涉及该公约第 206 条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范围问题,该案的专案法官沙克利 (Szekely) 在其发表的单独意见中认为,环境影响评价是国家预防环境损害的核心工具。
根据执行该条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中国同意在开发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和底土时,对开发活动所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在关于担保国在海底采矿活动中的责任问题的咨询意见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强调,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 “公约第 206 条下的直接的义务”。
中国是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本身虽然没有关于跨界环境损害评价的规定,但该公约缔约国在 2002 年通过决议,要求缔约方对于在湿地上进行的任何项目,都要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公约缔约方在 2008 年进一步通过决议,更新了 2002 年版的环境影响评价和战略环境评价指引。
中国的某些湿地是 《国际湿地公约》所认可的国际重要湿地,同时是很多迁徙鸟类的重要繁殖地、停歇地或过冬地,中国不但应该评估自身的经济建设和开发活动对本国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还应该考虑对这些迁徙类物种的影响。中国还是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成员国,该议定书要求,出口转基因活生物的国家,应该向进口国提供拟出口的转基因活生物的相关资料,以便进口国就拟进口的活生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人类健康的影响进行评价,进口国也可以要求出口国承担这类风险评估,并承担相应的评估费用。
根据中国 1993 年批准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定,中国应该采取适当的程序,对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以期避免或尽量减轻影响,并酌情允许公众参与此种程序。很多的水利工程都对河流的生态系统或者依赖河流生活的生物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如有学者证明,澜沧江大坝的不同选址将对某些洄游鱼类产生重要影响。根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成员国应该评估这些水利工程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该公约还鼓励成员国在互惠的基础上,就其管辖或者控制范围内的活动对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进行通报、提供信息和进行磋商。
如遇中国管辖或控制下起源的危险即将或严重危及或损害其他国家管辖的地区内或本国管辖地区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情况,中国应立即将此种危险或损害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并采取行动预防或尽量减轻这种危险或损害。就水坝工程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这一点而言, 《生物多样性公约》可能是直接与国际河流上的水利工程相关的一个条约。中国及其各陆地邻国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还有自己的争端解决程序。
(二) 中国在区域性条约中对邻国承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
虽然中国的环评法并没有要求跨界环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对其邻国完全没有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中国在跨界水合作方面与数个邻国签有多边或双边条约,其中一些内容涉及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或者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条件。
中国明确而直接地在国际河流合作中承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是 《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准则谅解备忘录》。1995 年,中国、蒙古、朝鲜、韩国和俄罗斯在纽约签署了该备忘录。其第 1. 2 条规定:缔约各方将进行联合 (定期更新) 区域环境分析,对经反复研究的整体地区发展规划在当地、国家、区域以至全球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并联合制定区域环境调节与管理计划,以防止调节对环境的危害,基于区域环境分析及其他相关数据促进环境的改善。(黑体为笔者所加)缔约方在该备忘录中承诺的不仅仅是跨界环境影响评价,而且还是联合进行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这是非常紧密的、信任程度很高的合作模式。虽然大图们经济合作计划进展并不顺利,但这个备忘录的意义仍然十分重大。它显示了缔约方对于经济开发对环境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关心,以及缔约方对于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可持续地发展经济的庄严承诺。该备忘录也是中国第一次明确在国际河流的合作中承诺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
(三) 中国在双边条约中承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
1994 年 4 月 29 日,中国和蒙古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保护和利用边界水协定》,该协定第三条规定了双方专家对跨界水进行联合调查和测量,以及互换资料和信息的义务。该协定第四条第 1 款则规定:“缔约双方应共同保护边界水的生态系统,并以不致对另一方造成损害的方式开发和利用边界水。任何对边界水的开发和利用,须遵守公平、合理的原则,并不得对合理的边界水使用造成损害。”缔约方如果不对自身的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实际上就不能确切地知道自身的经济活动是否会给边界水的生态系统造成损害。因为我们在条约中承诺了这样的内容,我们对于在中蒙边界地区进行的大型建设项目,实际上进行了对蒙古环境影响的评价。
为了帮助湄公河国家防洪减灾,中国早在 1993 年 7 月 15 日就与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签署了备忘录,向后者提供水文情报以利湄公河下游的防洪预报工作。2002 年,该备忘录得到续签,2008 年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与湄公河委员会关于中国水利部向湄委会秘书处提供澜沧江—湄公河汛期水文资料的协议》。类似地,中国水利部与印度水利部在 2002 年签署了 《关于中方向印方提供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汛期水文资料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向印度提供雅鲁藏布江汛期的水文资料。
2001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签订了 《关于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合作协定》,双方在该协定第五条约定,将 “研究共同防止或减轻由于洪水、冰凌和其他自然灾害影响的可行性; 并研究跨界河流水量、水质的未来变化趋势”。这些目标也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成立的联合委员会的谈判内容之一,目前谈判仍然每年定期进行。
2008 年 1 月 29 日,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 《关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的协定》。该协定第 8 款规定,双方将 “按照事先商定的程序,相互通报在跨界水上修建的和拟建的可能导致重大跨界影响的水利工程,并采取必要措施,以预防、控制和减少该影响”。这是中国明确表示将对 “可能导致重大跨界影响的水利工程”,采取必要的预防、控制和减少影响的措施。
从上述条约来看,中国对其邻国所承诺的环境影响评价是不均衡的。总的来看,对东部和北部边境的朝鲜、俄罗斯和蒙古所做的环评承诺内容确定、具体和详细; 对西北部的哈萨克斯坦只承诺愿意就包括环评在内的合作事项展开谈判,并且在实际协商中,也有一个谈判和协商的平台; 对南部的几个邻国,除了承诺提供一些河流汛期的水文资料以外,没有做出过任何与环评相关的承诺,而且水文资料的提供也只限于给印度和湄公河委员会,对缅甸则不提供,虽然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都源自中国。这种在邻国间厚薄不均的待遇可能引发南亚国家的不满和担忧。虽然在理论上,中国给予某一邻国的条约利益,不必也提供给其他邻国,但对河流利用的环境影响评价不同,它是一个关系到下游国家生态和环境安全的事项,不是锦上添花式的利益。而且,根据前文的论证,如果国家管辖或者控制下的活动可能对邻国造成不利的环境影响,该国有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法义务。
三、中国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实践与国际义务之间的差距
(一) 现行环评实践的评估范围窄
中国现行的 2003 年颁布的 《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照本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该条款仅对被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的地域范围进行了限定,而并没有限定应评估的影响的地域范围。所以,仅仅根据这一条,并不能解释为对建设项目的域外影响,法律不要求评估。但是,根据笔者多方了解,我国现行的实践是,仅对建设项目的域内影响进行评估。虽然那些在我国边境地区建设的项目,其环境影响可能不限于我国境内,但对那些项目对境外环境的影响,并不在执法部门所要求的评估范围之内。2009 年中国颁布了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该条例第二条规定的规划环评范围包括“流域……开发利用规划”,“流域”比 “河流”的范围要大得多,如果对河流的开发利用规划应该将其对全流域的环境影响考虑在内,对于国际河流或者界河而言,不考虑其对境外流域产生的影响,似乎很难解释为是一种全流域的环评。不过从现在的实践来看,我国的规划环评也没有考虑对境外的影响。鉴于对国际河流或界河的利用很可能影响下游国家的利益,我们应该考虑在对流域规划进行环评时,也将对下游流域的影响一并考虑在内。如仅西藏一地,就将投入 1. 6 亿元编制包括雅鲁藏布江在内的 44 条河流的流域开发规划,“改善西藏水资源分布不均、区域性、季节性、工程性缺水等问题”。
(二) 中国应制定履行国际承诺的国内法规则
如上所述,无论是在多边国际条约中,还是在双边河流合作协议中,中国都有一些实施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承诺,这些庄严的承诺构成了中国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我国现在还没有实施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或指南,所以,这些国际义务的落实还非常不确定。
根据其他国家实施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经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可以由环境影响起源国独自完成,也可以由起源国和受影响国共同完成。前者如罗马尼亚罗西亚·蒙他那金矿有限责任公司金矿扩建项目环评。
由于在冶炼黄金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氢化物,因而可能影响地表水的质量。该矿区所排放的水经过处理后将首先排入阿布鲁德河,它是阿希耶河的支流,后者又是穆列什河的支流。从矿区到穆列什河流出罗马尼亚边界,大约有 500 公里。穆列什河在流出罗马尼亚边界 20 公里后,汇入蒂萨河,蒂萨河在塞尔维亚汇入多瑙河。蒂萨河/多瑙河盆地是中欧水质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过去罗西亚·蒙他那公司的老金矿项目加重了该区域的污染。该公司金矿扩建项目的环评是由建设方独自完成的,该金矿在扩建的过程中,对老的设备和工艺进行了升级,使原有的有害物质排放量减少,虽然扩建会增加新排放,但减少的排放量大于新增加的排放量,环评表明,该金矿扩建后,并不会增加向河流中排放的氢化物的总量。
这一情况通报给邻国匈牙利后,匈牙利没有异议。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都必须由所涉国家联合实施。类似的单方进行跨界环评的案例还有印度对基申甘加水坝工程的环评。当然,如果通过对环境影响的筛查,项目确实可能对邻国造成不确定的环境影响,比较理想的方式就是进行联合环评。联合环评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北溪输油管道项目的环评。
该项目由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和德国五个影响起源国发起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四个受影响国家共同参与。事实证明,公开和透明的环境影响评价对于成功建设全长 1222 公里的北溪输油管道项目非常重要。跨界环评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磋商,有效地消除了对项目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的没有凭据的猜忌和担忧,对于发现的风险,九国也一起探讨了减少风险的方案,并制定了长期的风险监控计划。
中国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可以独立开展,从而提高效率; 对于由多国共同实施的复杂的工程和项目,应该考虑由项目合作方联合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实际上,虽然我国法律并无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一些进行跨国项目经营和建设的企业,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已经开始自愿仿效国际惯例,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为主建设的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就通过招标,请泰国 IEM 公司对项目进行了环评。我国一些学者也积极主张国家在具有跨界影响的项目上开展跨界环评,并探讨了不同的构建思路,也对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但由于缺少强制性的法律的约束,跨界环评在我国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同时,我们也没有要求邻国的建设项目在可能对我国产生严重的跨界影响时,向我国通报项目的环境影响信息。
四、结 论
国际环境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一国管辖和控制下的活动,不能对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造成严重的环境损害。当国家管辖和控制下的活动可能对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造成环境影响时,对这类活动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是一国在习惯国际法下的义务。近几十年的国家实践和权威的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重复和重申了这一国际习惯法规则。
虽然中国的国内法并不要求对国际河流的水利工程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但事实上,中国在跨界水的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并不排斥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中国曾经在图们江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明确承诺与邻国联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中国与俄罗斯在界水利用和保护的合作中也包括对界水的联合监测,类似的承诺还存在于中国与蒙古之间。
中国是数十条重要的国际河流的上游国家,其对国际河流的开发力度正在加大,这已经引发了邻国的关切。中国对国际河流上的水利项目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是邻国的热切期待。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在中国的邻国间广为接受,如哈萨克斯坦对 《埃斯波公约》成员国承担了明确的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俄罗斯也是 《埃斯波公约》的签字国,实践中与该公约的欧洲成员国有良好的环评合作。中国在南亚的邻国也积极支持和实践跨界环境影响评价。
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科学决策工具,是保证国家履行不造成重大损害的国际环境法原则所必要的程序。中国应该把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包括在其与邻国的国际河流合作中。我国学者认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机制并不全然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负面约束,它也是一个推动中国实现国际性跨界河流开发过程中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如何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可以由中国的国内法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