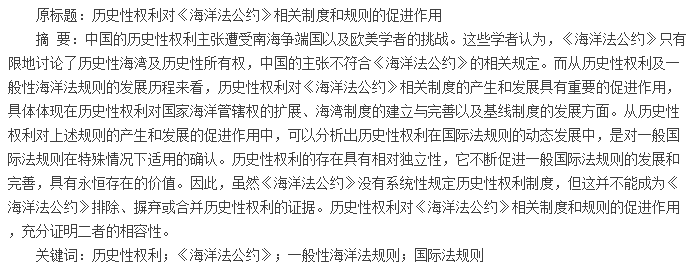
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正在遭受南海争端当事国以及欧美学者的挑战。这些学者认为,历史性权利并没有在《海洋法公约》中占有一席之地,《海洋法公约》只有限地讨论了历史性海湾及历史性所有权,历史性权利与《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上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是格格不入的,选其一必然意味着舍其一。这种论调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的罗伯特·贝克曼(Robert Beckman)为代表,他认为,当中国批准《海洋法公约》时,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对现已成为他国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上自然资源的历史性权利,还意味着实际上已放弃所有传统捕鱼权,除非《海洋法公约》中存在承认这些权利的特别规定;由于南海争端的“六国”均是《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所以,中国实际上不能依据历史性权利理论在南海主张相关的权利。而 2013 年 1 月,菲律宾在其发起的强制仲裁程序的诉求中,也明确要求仲裁庭裁决中国九段线权利主张不符合《海洋法公约》而无效。
因此,无论是当前为澄清有关理论纷争进而消除国外相关论调的负面影响,还是为未来中国在南海U 形线内提出明确、合法的权利主张,探讨历史性权利与《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海洋权利主张的关系,即历史性权利主张能否在《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继续发挥作用及其效力问题尤为重要。
一、历史性权利对《海洋法公约》扩大海洋管辖权的促进作用
毫无疑问,历史性权利的实践首先确认了国家通过长期行使权利获得的、超出了某特定距离标准海域的那部分权利,为国家扩大海洋管辖权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丰富了确认国家海洋管辖权的标准与方法。
在 19 世纪中后期,历史性权利兴起和发展之时,由于国际海洋法对管辖权的层级区分不明显,只有领海与公海的划分,历史性权利在确认国家超出一般国家实践领海宽度外的海域享有特殊权利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制定所谓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来确定国家海洋管辖权范围,也就是对国家的海洋管辖权进行量化的确定,即制定统一的最大距离标准。距离标准的优点在于确定性极强,且简单公平,但也相应地难以在各国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之中确定统一的数值。到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之前,国际社会虽然确认了领海与公海的区分,但是对于领海宽度却没有形成习惯国际法实践,即确定国家海洋管辖权与公海的距离标准尚未形成统一的实践。然而,随着人类对海洋了解的加深,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人类有了扩大海洋管辖权的能力。一些发达的海洋大国,其控制、利用海洋的能力早已超出了他们所主张的领海宽度,即 3~4 海里。在领海宽度无法确定之时,历史性权利为保障这些国家在根据一般海洋法规则本该是一国或他国领海,甚至是公海的海域中已经基于历史上获得、长期实践并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权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这个角度上说,历史性权利在海洋管辖权确立距离标准尚未形成统一习惯法规则的年代,实际上丰富了确立国家管辖权的标准与方法,也为国家主张海洋的管辖权提供了法律基础。而在海洋管辖权距离标准确立之后,这种作用也仍然存在。相对于确定、机械的距离标准,历史性权利更考虑了独特的历史、地理、其他国家态度等具体因素,在个案中能更加精确而灵活地确定国家的海洋管辖权范围。
在《海洋法公约》的缔约过程中,历史性权利理论对《海洋法公约》扩大海洋管辖权的相关制度的建立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之前的国际法委员会 1956 年草案起,历史性权利理论对《海洋法公约》确定领海宽度制度的促进和协调作用逐步显现。一些大国虽然坚持 3 海里领海宽度,但是认为在历史性权利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将领海宽度延伸至超出 3 海里的宽度。1955 年英国在对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人报告(A/CN.4/77)发表的评论意见中曾经明确指出,领海宽度由历史、地理和经济要素决定。国际法院曾经明确论证过历史性水域制度,历史性要素由于历史性水域制度的存在而得以支撑。因此,英国建议,将领海宽度定为 3 海里,除非存在历史性水域的情况,否则不能延伸至 3 海里之外。此外,瑞典、美国也持有类似观点。可见,在这些国家看来,历史性权利理论并没有因为领海宽度的确定而消失,而是起到了一种协调作用,即历史性权利的存在是排除领海宽度确定标准发挥效力的唯一原因,也是在 3 海里领海之外扩大领海范围的唯一途径。
在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中,历史性权利的这种促进和协调作用体现更为明显,更多国家倾向于将历史性权利作为领海宽度距离标准的例外,从而达到在特殊情况下扩展领海甚至是其他性质的海洋管辖权的目的。荷兰认为,3 海里的规则仍然是领海宽度的普遍规则,但历史性权利的情形除外。西班牙认为,一些国家在大陆架与毗连区中的权利与历史性海湾类似,而这种对于海洋自由的减损的基础是国际社会的认同,因此,国家海洋管辖权不需要扩展,这些主张应当通过承认沿海国在历史性水域、大陆架和毗连区中的特殊权利而保障。英国也表示,一般国际法应当对领海宽度有上限规定,除非存在历史性的情况。沙特阿拉伯更提出提案,认为关于领海宽度的任何提议都必须将历史性水域作为例外。苏联认为,国家可以从 3~12 海里中,根据国家的历史、地理情况以及经济、安全利益自行选择领海宽度。乌克兰等国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各国关于领海宽度的讨论与历史性权利相交织,反映了国家在讨论领海宽度问题时,历史性权利不仅是国家扩大领海宽度的基础之一,也是协调不同主张之间的润滑剂。国家对历史性权利的倚重,反映了历史性权利与一般国际法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国家在谋求国家海洋权利扩大时,并没有将历史性权利作为对立的制度进行否定,也没有在领海宽度扩展后否定历史性权利的意图。
二、历史性权利对《海洋法公约》海湾制度的促进作用
历史性权利对海洋法制度的推动作用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对海湾制度的作用上。由于海湾特殊的地理构造,水域深入环抱它的沿岸,如果单纯按照距离标准,尤其是 18~19 世纪末期大部分海权国家所接受的 3~4 海里标准,就将使一部分公海深入沿海国的领土包围的范围之内,这给沿海国的安全利益和有效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问题。而事实上,许多国家在其领土所包围的水曲范围内通常享有传统性的权利。一些长期实施了有效、和平及持续管辖权的国家,通过历史性海湾的主张,希望国际法确认这种权利的合法性。历史性海湾制度由此形成。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性海湾的主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适用条件方面,证明历史性权利并非易事,且沿海国这种基于国家安全、有效管理和国民生活便利的利益并不应当仅仅依赖于长期行使权利的行为而存在,历史性权利主张个案性明显的特性不足以使国家的利益得到平等的维护。其次是历史性权利的基础来源于对权利的长期行使和巩固,这使得主张历史性权利的国家有一定的局限性。历史性海湾只能使历史悠久的老牌国家获益,而许多新兴国家,如拉美、非洲的一些国家通常无法通过历史性权利主张对海湾的主权。第三,历史性海湾主张中往往没有对湾口线长度等问题加以限制,容易过度主张。因此,一般性海湾制度的建立呼之欲出,这样不仅可以使海湾的沿海国受到约束,而一些老牌国家则可以通过历史性权利主张更大的海湾。由此,历史性权利理论从两个方面推动了海湾制度的发展。一是推动一般性海湾制度的建立,二是历史性海湾制度的建立及其与一般性海湾制度的关系。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国际社会出现了两种趋势并存的局面,即通过历史性权利主张对海湾主权的历史性海湾实践趋势与通过试图限定海湾条件而直接赋予沿海国主权的海湾制度雏形的实践趋势。趋势正如乔娅所指出的那样,“在海洋大国中出现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试图对可能出现的使符合条件的海湾具有更加精确法律标准的领海测量相关国际法一般规则进行减损;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制定一般国际法规则,允许对某些湾口不超过特定数值的海湾获得主权,例如 6 海里和后来的 10 海里标准”。
然而,历史性海湾之于《海洋法公约》海湾制度的贡献并不仅于此,它不但促进了一般性海湾制度与历史性海湾制度的形成,在三次海洋法会议中更促进《海洋法公约》平衡了一般性海湾制度与历史性海湾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海湾制度。在三次海洋法会议中,与会国家重点关注的即是历史性海湾与一般性海湾制度的相互关系,具体体现为一般性海湾制度的适用应不影响历史性海湾的实践。这种实用性的考虑推动了普遍性公约相关制度的讨论和建构,也完善了《海洋法公约》海湾制度的体系性。
三、历史性权利对《海洋法公约》基线规则产生的促进作用
(一)历史性权利对直线基线规则产生的促进作用
一些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根据之前的国际法获得了对某些海湾水域的特定主权权利,而作为领海基线通行做法的正常基线以低潮线作为领海的起点。为了让国家在长期实践中所获得的权利不被侵犯,国家要求正常基线在满足一定条件时能够被排除适用于本国的领海基线划定。国家一般根据历史上长期的实践和其他国家的态度来主张对海湾湾口线(当事国所划定的直线基线)内的水域主张主权。
这种实践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挪威在瓦朗格峡湾(Varangerfjord)的实践。瓦朗格峡湾的湾口约为 30英里。1881 年,挪威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在湾口划定了直线基线,禁止在从这条基线向大海延伸的一定距离内从事捕鲸活动。挪威做出这种命令的基础在于当地居民对峡湾长期的利用和他们的经济利益。
随后,挪威根据这条直线基线进行了一系列国内的司法实践。1911 年,挪威法院宣布一个英国船长因为在直线基线内进行捕鱼而获罪。挪威政府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挪威的海洋边界,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宣布,依据历史上的权利,瓦朗格峡湾是挪威专属渔区的一部分,而且其他的利益相关国以默认确认了这种权利。1934 年,挪威最高法院也指出,“瓦朗格峡湾是挪威领水的一部分”。在英挪渔业案中,英国并不否认挪威可以主张这些峡湾为其历史性海湾,而挪威也并没有这样去主张。相反,挪威通过历史性权利作为一套特殊的基线系统存在的基础。挪威认为这种特殊的直线基线系统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之一就是挪威享有的历史性权利以及这些水域与挪威内陆紧密的依存性和重要性。挪威放弃了直接对水域进行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而将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的法理基础加以运用。这是历史性权利向一般国际法规则靠近,并促进一般国际法规则新发展的有力证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领海基线的外推实质是对在其内部水域获权利的保护。而其后 1958 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及 1982 年《海洋法公约》对直线基线制度的确认也事实上通过领海基线的外推保障了沿海国根据历史上某些特定的情势而享有的既得利益,这实质上是在建立一般国际法规范的时候,首先对既得利益的确认和维护,以稳定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保障已经建立的利益平衡。
(二)历史性权利对群岛国基线制度产生的促进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之前,由于当时尚不存在专门的群岛国制度,群岛国对于其岛屿之间水域的主张大多是通过历史性水域为基础进行的。在群岛国基线制度产生的过程中,这种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61 年 5 月 18 日,菲律宾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An Act To Define the Baselines of the TerritorialSea of the Philippines No.3046),该法案为菲律宾划定了围绕其群岛的直线基线,美国对此通过外交照会进行了反对。而当时并不存在《海洋法公约》中的群岛国制度。1974 年,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菲律宾重申了这一主张,并解释该法案是以历史性权利理论作为划定此种直线基线的基础,并表示将继续行使美国和西班牙两国在长期行使主权中获得的主权。其后,菲律宾在各国讨论群岛国制度之时坚持了这一理论,认为基于历史性水域理论,菲律宾所有周边水域、在群岛之间并联系群岛的水域,不论其宽度如何,都是菲律宾专属的主权范围。菲律宾还将这种水域的地位与历史性海湾相比较。后来,这种对群岛国岛屿之间水域地位的特殊考量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形成了《海洋法公约》的群岛国制度。可见,沿海国历史性水域的主张对群岛国基线制度的诞生功不可没。
四、从历史性权利的促进作用看历史性权利的地位及其存在价值
(一)历史性权利的地位
1.有关历史性权利地位的两种学说及其评价。历史性权利的地位即历史性权利与一般国际海洋法规则之间的关系,目前学界存在两种理论。一种理论认为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规则的例外”621~623(Exception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即“国家只有在一般国际法规则之外才能通过历史性权利或时效建立对某水域的权利”。“历史性权利是对一般国际法的减损。……使那些与国际法相冲突的行为获得了合法性”。另一种理论认为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规则在特殊情况下的适用”(Application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to a Specific Case),即认为历史性权利并不是一般国际法规则的例外,它并不是将一个不符合国际法规则的情形合法化,而是一般国际法在特殊情况下的适用。因此,其合法性基础并不是其他国家的默许或容忍,而是一国和平、长期、有效地权利行使的实践。有关历史性权利地位的两种学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差异,但细究之下蕴藏玄机。从逻辑起点来看,这实质是对国家通过历史性权利所主张的权益是否违反国际法规则的分歧。认为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规则的例外”,实质上认为国家长期行使的权利本身是不符合一般国际法规则的,而国家长期行使权利本身和其他国家的默许,使这种不符合国际法的权利合法化了。而认为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规则在特殊情况下的适用”,实质上认同国家通过历史性权利所主张的权益本身即是符合国际法的,历史性权利只是对符合国际法行为的确认。而在确定的特殊情况下,必须适用此种国际法规则来确认与普通国际法规则看似不同的权利。由此,两种观点的推理之下,历史性权利的地位迥然。前者认为历史性权利是从属于一般国际法方能发挥作用,依赖于某些特定的规则将其合法化,而这些规则具有不确定性。而后者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必须适用历史性权利这种一般国际法,实质确认了历史性权利的习惯国际法地位。
2.从历史性权利对一般国际法发展的促进作用评估二者关系。关于上述两种观点,学界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1962 年联合国《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的报告首先对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规则例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在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作出评判之前,必须指出的是,主张历史性水域的权利是一般国际法规则的例外且由此得出主张历史性权利必须基于其他国家默认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难度”,“历史性权利与一般国际法规则都是基于惯例而存在的。……历史性权利所依据的国家实践,并不比一般国际法规则所依据的实践少;历史性权利中所存在的法理,也与所谓的一般国际法规则相当”。即使存在这样的一般国际法规则,那也只能在历史性权利的情况之外获得普遍适用的机会,因此不存在一般性规则优于例外规则的情况。例外规则与一般规则本来就是相对而言,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似乎并不存在关于海洋划界一般习惯法规则。因此,报告引用杰赛普的观点,认为务实的做法是将历史性权利当做独立的制度看待。但是报告也指出这种观点难以解释历史性权利需要其他国家默认这一构成要件。总体说来,报告基于当时的国际法发展背景质疑了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例外的理论,但是,报告的论点建立在当时尚未形成相关一般国际法规则基础之上。
(二)历史性权利的永恒存在价值
历史性权利总是独立于一般国际海洋法规则存在且发挥作用的,它揭示这些规则在某些个案中的不适用性,确认一般国际法在特殊情况下的适用,补充一般国际法规则在适用上的笼统性。
历史性权利的存在,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对于经过不断巩固且获得国际社会默许的权利的认可与维护,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而在于它对一般国际法的确认、补充、促进和检测作用。它提醒普遍性国际海洋法去关注那些被较强的确定性所掩盖的特殊情况,并探索为这些特殊问题制定普遍适用的特殊制度,甚至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一般海洋法规则正是通过这种作用方式得到完善、补充和发展。可以说,历史性权利正是促进普遍性海洋法公约诞生和发展的动力之一。正如一些国家在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所主张的那样,历史性权利对于国际海洋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海洋法规则的安全阀,是“其他制度的救济与补充”,并“按照自身的规则运行”。历史性权利不但是一种安全阀,它对于国际海洋法一般规则而言,也是推进器,永远促进其发展与完善。
一直作为一般国际法规则之外的促进力量而存在的历史性权利,始终在普遍性海洋法规则之外独立运行,并对这些规则进行补充与调节,在体例上也不宜出现在普遍性海洋法公约体系之中。
然而,普遍性公约制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各国放弃原有的历史性权利主张,而通过新的制度维护原来必须通过历史性权利才能维护的权利。这种现象并不是历史性权利为普遍性公约所吞噬或废除的证据,而恰是历史性权利作用于普遍性公约的结果。普遍性公约永远不可能完善至考虑到所有特殊情况,因此,历史性权利将永远通过这种作用方式促进普遍性海洋法规则的发展和完善。这是历史性权利作为一种理念的最大价值,即永恒存在的价值。
五、结论
历史性权利对《海洋法公约》相关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历史性权利对国家海洋管辖权的扩展、海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基线制度的发展方面。从历史性权利对上述规则的产生和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可以分析出历史性权利与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关系,并非如一些观点认为的那样,为一般国际法规则的例外,而在国际法规则的动态发展中,是对一般国际法规则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确认。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不断促进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因此,虽然《海洋法公约》没有系统性规定历史性权利制度,但这并不能成为《海洋法公约》排除、摒弃或合并历史性权利的证据。历史性权利对《海洋法公约》相关制度和规则的促进作用,充分证明二者的相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