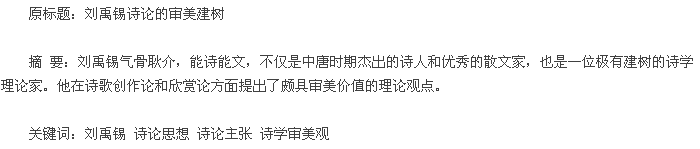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刘禹锡在《竹枝词·序》中说:“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沈德潜说:“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夫刘以风格胜,白以近情胜,各自成家,不相肖也。”(《唐诗别裁》)其文也别具特色,柳宗元称其“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刘禹锡在诗歌创作论和欣赏论方面,提出了几个颇具审美价值的理论观点:一是认为“文章与时高下”;二是提出“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三是认为“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四是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着名论断;五是认为“义与言”的关系是“义得言丧”.刘禹锡论诗,将创作和欣赏、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作统一观照,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明显地有别于“意为先”或“气为主”的传统说法,彰显了其诗歌理论的独特审美价值。
一、文章与时高下
“文章与时高下”是刘禹锡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当时政策的角度,对文学发展外部客观环境的探讨。他在《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中说:“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
刘禹锡以为文学的繁荣与衰落是受社会兴衰制约的,并以三代之文至南北朝而衰,至唐又复兴为例,证明“文章与时高下”的规律。他尤以唐德宗贞元年间文学繁荣的现状,从时代政策的角度探索文学的发展。他说:“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然如繁星丽天。”可见,刘禹锡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审视较之于以往的论者更有突破意义。
“文章与时高下”这一诗学思想,其理论开拓意义不容忽视,它对于引导作家正确认识时代氛围与繁荣创作的关系,对于启发当政者与作家对文学政策方面的思考都有拓宽理论视野的作用。尤其是后者,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影响更为深远,它强调当政者的态度及其所定政策是促进文学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这一富有开创性的理论探索,不仅明确了时代文艺政策的重要理论导向意义,而且为研究文学盛衰的变化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参照。刘禹锡的这一理论,既是对传统诗学观的突破,也是对诗学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的深入开拓。
二、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
刘禹锡继承了司马迁“发愤着书”的观点,他既从作家的创作心理探索其创作动因,也立足于欣赏者的心理流程,透视作品的艺术效应,从而为作品深层次地表现生活开拓了一条创作新路。他说“:昔称韩非善着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着于篇,显白其事。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固无以异于他书矣。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至邪!”(《上杜司徒书》)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司马迁因韩非所着《说难》《孤愤》情感激切,故将其事显白于《史记》;二是因司马迁同韩非所言之事有类似的遭遇,所以他才会领悟《说难》《孤愤》的深意,如果身无坎坷、仕途得意者观看韩非的着作,则绝无悲意可言。
刘禹锡的这番话,其实阐释了一个完整的创作心理流程,即由客观事物引发作家的创作欲望,再到创作动因的形成,最后将心理感受形之于笔端。
他对创作心理的这一理论探索,同样有助于揭示欣赏心理特征。所谓“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指明了有类似心理积淀的读者,结合自身遭际,能对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所以他说:“司马子长之深悲,迹符理会,千古相见,虽欲勿悲,可乎?”(《上杜司徒书》)刘禹锡对“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的理解如此深刻,这也正是他对自己创作经历的总结和剖析。
他一生坎坷,屡遭打击,自二十三岁开始便遭贬外地,现存八百多首诗大多写于遭贬之后。他与司马迁及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心理相通,所以他对人生经历与创作、欣赏心理的关系认识得尤为深刻。
刘禹锡的这一审美思想丰富了创作和欣赏的层次和视角。尤其是他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诗境浑远、含蓄隐微、情韵深藏、格调高迈的特征,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刘禹锡对诗歌美学的深入探索,使其诗歌创作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审美特征,因此在中国诗歌史上独占一席,放射出奇光异彩。
三、片言明百意,坐驰役万景
所谓“片言明百意”,是指用极洗练的只言片语表达极其丰厚的思想内容,这也就是所谓诗歌语言简洁凝练、思想情感容量大的特征“;坐驰役万景”,是指诗人进行艺术想象时,虽静坐于案几之前,可他的思维却调遣众多的形象于眼前,供其选择和取舍。
刘禹锡“片言可以明百意”的观点,是对前人尤其是陆机《文赋》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论点的继承和发展。陆机的原意是“:以文喻马也,言马因警策而弥骏,以喻文资片言而益明也。”(见李善《文选注》)由于刘禹锡与陆机立论角度的差异,刘是侧重于从创作论角度阐释形象思维的特征的,因而重在强调诗人在艺术构思中凝缩丰富的思想情感于“片言”之中。这里的所谓“片言”,就不只是指字句的警策,而是指它内在情感的丰富或哲理意趣的深刻。
可见,刘禹锡重视“百意”出之以“片言”的审美追求。
刘禹锡的这一审美思想对诗歌创作颇有启发意义,它引导作者既要讲究锤炼词句,又必须关注“片言”所蕴含的深意。这一理论探索对于摆脱专事雕琢的形式主义余风,纠正中唐诗坛沉渣泛起的浮藻文风无疑有积极作用。
刘禹锡的“坐驰可以役万景”说,从理论渊源上也借鉴了前人之见。陆机曾对形象思维的特点做过形象的概括,并提出了“精骛八极”的美学观点,他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昽而弥鲜,物昭晰而忽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刘禹锡的观点,从审美取向上明显导源于陆机之论,但他并非只作理论的转述,而是强调诗人在艺术构思中“役”使万景的能力和主动性,这就比陆机所论更为深入。刘禹锡从创作论的角度立论,并把这一观点视为能诗者必备的才能之一。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异,达于诗者能之。工生予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
从他的话中可知他重视形象思维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这与他重视诗的比兴手法一样,认为诗人只有具备艺术想象的才能,掌握比兴手法的技巧,两者相辅相成,才是完备的诗道。
刘禹锡诗歌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独特的风格,他能“役万景”于诗中,以“片言明百意”.如其抒写身世感慨之作,取意、写景皆不同凡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其一)他的政治讽谕诗也别开生面,构思奇特,如《聚蚊谣》《百舌吟》《有獭吟》《飞鸢操》等。在他所写的大量咏史诗中,形象思维也都运用得极其出色。白居易读其《石头城》诗,“掸头苦吟,叹赏良久”,认为“潮打空城寂寞回”使“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见《金陵五题序》)。薛雪赞其《西塞山怀古》:“笔着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一瓢诗话》)。刘禹锡所达到的高超的艺术水平,正是他“工于诗,达于诗”的体现。
四、定而得境,境生象外
刘禹锡对诗歌意境的构筑及其美学特征也有深刻认识。他在论述诗人构筑“意境”时,以“定而得境”来概括创造意境时的心理特征。他说:“能离欲则方寸之地虚,虚而万象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以降,释子以诗问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定而得境”的心理流程特征及意境凭词而显现的艺术表现全过程。
刘禹锡受佛教禅宗影响较深,又是写诗能手,他因此体验到了禅宗所谓“定”与诗境构筑的关系。佛门所言的“定”,即静坐敛心,摒除一切杂念,让心处于空无一物的状态,这与诗人创造意境时的心理活动相近似。于是他用佛家理论分析“境”的产生过程,把跳出现实世界的“离欲”和心地虚空视为“境”产生的前提,认为“翛然以情”的“境”的获得,是由于作者在观照客观景物时,全部精神都凝聚在物象上,杜绝意志和欲念的羁绊,以审美的态度使眼前的意象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所以“定”的实质是指艺术家投入创作时的虚静心理状态,其时没有名利干扰,没有得失之虑,神凝思专,感兴涌动,凭借入于心中的“万象”展开丰富联想,从而创造“韵外之旨”的艺术境界。
刘禹锡是较早论述诗境构成及其美学特征的先躯。汉代以前的“诗言志”说,六朝陆机的“诗缘情”说,都关涉诗境的初步研讨,至唐代诗论家们对此有较大理论突破,尤其是明确提出了“诗境”或“意境”概念,并开始对其进行多层探讨和论述。所谓“境”,是指客观物象,即创作主体运用想象、比喻、象征等诸多艺术手段,予以审美化的艺术表现,从而产生一种比艺术形象本身更广阔深远、更富审美趣味的美学境界。
应当指出,先于刘禹锡的王昌龄在《诗格》中已有“诗有三境”说,即“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他已指出“意境”通过“意象”的深化而构成心境应合、神形兼备的基本特征。刘禹锡对于“定而得境”的认识和把握较之王昌龄更为具体和深刻,他强调“能离欲则方寸之地虚”这种心理的虚静状态,以为无尘杂的自然物象,予以艺术化的再现,更能荡涤人的心灵,引发真善美的感受,即佛家所谓“悟入”境界的体验。由此可见,刘禹锡的“定而得境”说是对王昌龄“意境”说的进一步发展。刘禹锡的“境生象外”观与“定而得境”说,是对意境认识的较为完整的美学体系“.境生象外”是他对意境美学表现特征的认识。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这里所说的“境”指意境;所说的“象”指意象或艺术形象。刘禹锡在其论述中已隐含对“境”和“象”关系的认识及其各自美学特征的见解。
首先,他认识到了“境”生于“象”这个前提,认为“象”是诗人所描写的艺术形象本身,“境”是比“象”更富美学韵味的思维空间。
其次,他认识到“境”和“象”是一个艺术整体,它们互为联系、互相作用。“境”产生于“象”,但“象”只有借助于“境”才能脱离完全自然的状态,进入到艺术美的视野中来,才能显示其艺术形象的魅力。
第三,对“境”和“象”从创作和欣赏两方面予以审美观照:从创作的角度看,“象”是描写的实体,“境”是“象”外所生的虚幻审美空间,诗人由“象”而“境”展开形象思维;从欣赏的角度看“,象”是直觉感受,它借助于文字符号以显其艺术状态,“境”是通过想象、比喻、象征等手法,艺术化、审美化了的幻化虚体,须运用想象和富有个性的心理要素再创造,甚至于补充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
第四,“境生象外”还包含着对“境存象隐”的审美探索。诗人构思的审美追求,不外是凭借形象思维构筑理想化的诗境。刘禹锡“境生象外”的美学思想,尤为强调意境的最终构成,强调“境”在创作和欣赏中的审美意蕴。他以为“象”只是“意境”的一个载体,“境”生而后,“象”本身的意义显得并不重要,因为欣赏者只是把它视为探索“意境”蕴含的一个媒介。
刘禹锡对“意境”的创造及其美学特征的阐释,不仅为“意境”说的完备奠定了基础,而且在艺术实践上为诗歌的创作、鉴赏提供了审美参照,极大地开阔了创作和批评的视野。
五、义得言丧
在对文义与语言关系的认识上,刘禹锡更为重视义的艺术表现。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言丧。”所谓“义”是指文意之“意”,泛言之是对思想内容的概括,简言之是指诗歌借助于艺术形象所表现的作品主旨。所谓“言”是指文字所显示的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刘禹锡“义得言丧”的美学观点,大致蕴含着三层意思:一是指在作品中言是表,意是里,言是构成艺术形象的符号,艺术形象是表现意的媒介,作家对言的认识和把握不容忽视;二是说诗歌创作和欣赏的根本目的在于把握作品的主旨,只专力于对作品艺术形象的理解,对诗歌创作或欣赏来说都是误解,应达到“作者得于心,贤者会以意”的交流程度;三是强调诗人在创作中应追求“义得言丧”这个审美标 准 ,要 求“ 言 ”所 表 现 的 艺 术 形 象 确 实 是“意”的载体,即不能夸饰,也不能削弱,要表现得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才可谓“义得言丧”.刘禹锡的“义得言丧”说,是对庄子“言为意筌,得意忘言”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认识上和皎然“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之说极为相近。它们的共同点是指文学创作要借艺术形象来传达作者所要表现的主旨,因主旨不直接体现在形象之中,而是借助于形象的某种特点予以表现的,所以要达到“得意忘言”或“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美学效果,必须运用象征、比喻、暗示、想象等多种艺术手法作为媒介。皎然之说较之于刘禹锡之论更为详密,他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首,则居众妙之门;崇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但恐徒挥其斤而无其质,故伯牙所叹息也。”(《诗式》)。刘禹锡和皎然的审美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宋代严羽以禅说诗所提出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清代王士祯所提的“神韵说”,都与刘禹锡、皎然的观点有渊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