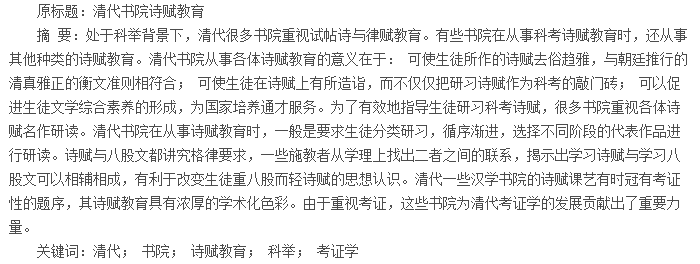
在清代书院文学教育中,诗赋教育是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如詹杭伦、许结、徐雁平、宋巧燕、张巍等人对清代书院诗赋教育进行过不同角度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许结指出,清代有些书院赋作课艺重视基础训练与才学培养,游离于科考律赋之外,对途径狭窄的科考律赋做了重要补救(43)。徐雁平指出,清代翰林院重视诗赋考试,清代一些书院强调诗赋教育与山长的翰林出身有所联系(443-47)。宋巧燕指出,诂经精舍重视以学为诗赋,诗赋课艺中的考据气息浓厚(226)。尽管目前学者在清代书院诗赋教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不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清代书院从事各体诗赋教育有哪些重要意义,清代书院在进行诗赋教育时如何凸显经典阅读以及提供怎样的研习方法,如何处理科考诗赋教育与八股文教育之间的关系,清代汉学书院以学为诗赋有何历史渊源,目前学者对这些问题或阙而未论,或论而未详。鉴于已有研究尚待开拓或挖掘的地方不少,因此笔者撰文对清代书院诗赋教育作补充论述。
引言
在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有古体与近体两种类型。唐代以前的诗歌在押韵、平仄以及句数、字数等方面较为自由,称为古体诗(后人对古体诗的模仿之作,也称为古体诗);唐代以后的诗歌在押韵、平仄以及句数、字数等方面较为严格,称为近体诗(又称为格律诗)。科考中的试帖诗是在近体诗的基础上形成的。唐代科考就已出现试帖诗,清代时期,试帖诗用于童试、乡试以及会试中。
试帖诗与近体诗有别,试帖诗重视切题与限韵,在写作上受到更多限制。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论及试帖诗与近体诗的区别时便指出,近体诗写作重在表现自我,试帖诗写作重在紧扣诗题,近体诗不可无我,试帖诗不可无题(261)。由于试帖诗是在应付科考这一外力的驱动下而作,作者并无主动的创作动机,因此徐复观将试帖诗等一些科举文称为外铄的文学(99)。赋是古诗之流,从楚辞发展演变而来,“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刘勰134)。赋的类型多样,主要有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等之分,其中,律赋重视对偶与限韵,用于科考中。唐代科考也已出现律赋,清代时期,律赋用于童试中(乡试与会试不考律赋)。
此外,试帖诗与律赋还用于博学鸿词科试、翰林院馆试等清代的各种考试中。
一、科考诗赋与其它种类的诗赋教育
就科举文而言,大凡八股文写作高手,并非拘囿于研习八股文之作,试帖诗、律赋写作高手,并非拘囿于研习试帖诗、律赋之作。若放眼开来,大凡文学创作高手,并非拘囿于研习文学之作,作家只有素养全面,方能创作上乘作品。在科举背景下,清代很多书院从事试帖诗、律赋这种科考诗赋教育。为了提升生徒的文学综合素养,也为了给生徒研习科考诗赋提供有益的帮助,一些书院在从事科考诗赋教育时,还要求生徒学习其他种类的诗赋,汲取诗赋方面的多种养料,培养诗赋写作的多种能力。有些施教者对应举士子如何学习古体诗作了具体说明。如河北清漳书院学规指出,学诗应先从国风、汉魏层累而下,然后次及晋宋齐梁,入于唐代格律。像时文研习需要宗古文一样,试帖诗研习也需要宗古诗,不过试帖诗研习宗古诗与时文研习宗古文有所不同。时文研习宗古文可从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古文入手,试帖诗研习宗古诗要从南北朝诗歌入手。南北朝诗歌虽为古体,但已渐次入律,应重视研习(章学诚678)。诗赋在写法上有别,诗重视抒发感情,赋除了重视抒发感情外,还重视藻饰铺陈,学习诗赋不可不明了此点。有些施教者在从事各体诗赋教育时,对诗赋的这种差别进行了揭示。如江西凝秀书院学规指出,研习试帖诗时既要重视形式规范,也要重视抒发性情,多讽诵古诗名作,审其结构,观其格律体裁以及遣词运事之法,以我之性情逆古人之性情。赋与诗不同,赋重视文饰,不只是陶写性情,生徒在研习诗歌之余,还要研习赋(朱一深38)。孔子论及文质时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晏邢昺卷六;23)。孔子主张,对待文质要取中庸之道,合理搭配方为理想。有些施教者以文质为喻告诫生徒,经义研习与诗赋研习不可偏废。如广东端溪书院学规指出,经义重本质而诗赋重文采,有质无文与文胜于质都不可取,经义与诗赋在历代科考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清代科考虽重经义但不废诗赋,在各省岁科两考外,别设经古学一场,兼试诗赋。生徒在研习试帖诗之余,还要研习赋以及各体诗(傅维森13)。试帖诗写作要比古近体诗写作更为严格,有些施教者由此主张,先研习古近体诗夯实基础,再研习试帖诗就较为容易。如四川学政张之洞认为,先读唐宋古近体诗,再学作之,然后学试帖诗,之所以这样安排,是由于,“令其胸中稍有诗情,则不以试帖为苦”(7)。在清代科考中,试帖诗比律赋的用途更广,相比较而言,试帖诗更能得到一些书院的重视。不过,重视试帖诗并非意味着这些书院抛开律赋以及其它种类的诗赋,从提升生徒综合素养的角度考虑,这些书院在教育时兼顾律赋以及其他种类的诗赋。由于科考诗赋是由古诗赋演变而来,二者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因此研习古诗赋有助于应付科考诗赋。一些书院在从事科考诗赋教育时也从事古诗赋教育,便有着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价值。
为了使生徒在研习科考诗赋时不忽视研习古诗赋,清代一些书院纷纷将各体诗赋纳入课试范畴。如福建鳌峰书院自道光三年(1823)起,每月十六日馆课,在八股文、试帖诗外,兼课经解、史论以及各体诗赋(来锡蕃110)。湖南龙潭书院每月三课,初五、二十五日课四书文与试帖诗,望日课五经文、杂文以及各体诗(陈谷嘉邓洪波1595)。
有些书院在课试八股文、试帖诗外,还专门课试各体诗赋,并对优秀者给予奖赏。如江苏宝晋书院规定,在月课外,另课诗赋杂体,对优秀者给予奖赏(贵中孚赵佑宸49)。湖南狮山书院规定,每月逢八日由山长别设一课,以经解、策论、诗赋各体命题,对优秀者给予奖赏(萧振声7)。在施教者的积极引导下,书院生徒不会忽视各体诗赋的研习。清代一些书院从事各体诗赋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意义:一,可使生徒所作的诗赋去俗趋雅,与朝廷推行的清真雅正衡文准则相符合。如台湾文石书院学规指出,“能为古近体诗者,其试帖虽不甚工,亦不致有尘俗气”(陈谷嘉邓洪波1562)。二,可使生徒在诗赋上有所造诣,而不仅仅把研习诗赋作为科考的敲门砖。如江苏娄东书院学规指出,“学诗者自当以成家为贵,不弟为科场计也”(王祖畲7)。由于一些士子拘囿于科考诗赋研习而对其他种类的诗赋漠不关心,因此甘肃陇南书院的施教者批判道,“今人学诗赋者,但读律赋数则、试帖百余首,不异于矮人观场,不能独树一帜”(邓洪波1724)。三,可以促进生徒文学综合素养的形成,为国家培养通才服务。如江西东湖书院从事各体诗赋教育的目的在于,“务期淹博通贯,以成全才”(邓洪波628)。有些汉学书院如诂经精舍、学海堂等不从事科考诗赋教育,而是从事科考诗赋以外其他种类的诗赋教育,这些书院在具体教育时就更为看重提升生徒的文学综合素养,功利化的思想也就更显淡薄。
二、经典阅读与方法指导
经典是众多着作的精华,具有永恒的价值,精读经典很有必要。美国教育家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就发起过阅读名着的运动,该运动对当时以及后来的美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有效地指导生徒研习科考诗赋,清代很多书院要求生徒研读诗赋经典着作,仔细揣摩,从中获益。如四川锦江书院学规指出,为了应付科考诗赋,生徒要研读《文选》、《文苑英华》、《唐人试帖》、《历朝应制诗选》、《凤池集》等作(邓洪波1447)。台湾海东书院学规指出,研习试帖诗时,宜取前代试帖诗如《国秀集》、《中兴间气集》、《近光集》以及近代试帖诗如《玉堂集》、《和声集》、《依水集》等,朝夕讽咏(邓洪波1745)。台湾文石书院学规指出,大抵试帖之上者,莫如有正斋,九家诗次之,七家诗又次之。生徒要汰其不合时式之作,选其尤佳者数十首仔细揣摩。研习律赋时,宜讲《律赋》及《赋学指南》二书(陈谷嘉邓洪波1562)。四川学政张之洞指出,学诗时要研读《唐人试帖》、《庚辰集》以及七家诗,学赋时要研读《文选》中赋、六朝赋、唐赋以及清代吴、鲍、顾、陈四家赋。此外,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古雅详备,能读更佳(张之洞7-10)。
上述施教者要求生徒研习科考诗赋名作时,既包括清代科考诗赋名作,又包括前代科考诗赋尤其是唐代科考诗赋名作。由于后代科考诗赋是从唐代科考诗赋演变而来,唐代科考诗赋要比后代科考诗赋典雅精湛,本着取法乎上的原则,很多施教者重视唐代科考诗赋。如湖南澧阳书院学规指出,“不读程朱书者,理不精;不读汉魏唐宋文者,气不厚;不读唐律、不临古人碑版者,诗字皆俗态”(邓洪波1205)。四川学政张之洞指出,“律赋之有唐赋,犹时文之有明文也”(张之洞10)。
一些书院要求研读科考诗赋名作时,还要求研读其他种类的诗赋名作。如上述锦江书院要求研读《文选》中诗赋,张之洞要求研读《文选》中赋、六朝赋、《七十家赋钞》。谚云:“《文选》烂,秀才半。”《文选》汇集了魏晋南北朝以前的诗文佳作,对后代科考以及诗文创作有着巨大影响,唐代杜甫不仅重视研读《文选》,还要求儿子熟精《文选》。清代一些书院在从事诗歌教育时,也很重视《文选》。如广东端溪书院屡次要求生徒研读《文选》,山长冯鱼山指出,诗自唐代以前要宗《文选》,唐代以后要宗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傅维森13),后来的山长刘朴石也指出,学诗之道贵在熟精《文选》,杜甫学诗悉本于此(傅维森18)。
从众多施教者的言辞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熟读经典着作是书院文学教育的不二法门,对书院文学教育起着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要想入为文堂奥,必须咀嚼以及消化经典着作,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二,经典着作之所以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既源于这些着作本身具有难以遏制的不朽价值这一内在因素,又源于施教者反复强调从而形成惯习这一外在因素,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交相作用所导致的结果。
赋为古诗之流,诗又源于《诗经》,因此《诗经》是诗赋的总源头。《诗经》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显赫,清代一些书院的施教者在从事诗赋教育时,重视梳理古代诗歌的演变过程,揭示出《诗经》的重要价值所在。如江苏钟山书院山长杨绳武梳理诗歌源流时指出,“诗原于《三百篇》,犹古文之原于《尚书》也。雅变而为风,风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赋,为汉魏乐府、古诗,实出于一原者也。”他认为,唐代很多诗人在创作上深受《诗经》的影响,“少陵之新乐府,诗之变大雅也;白香山之讽谕诗,诗之变小雅也;张文昌(张籍,字文昌)、王仲初(王建,字仲初)之乐府,诗之变国风也”(陈谷嘉邓洪波1493-94)。继杨绳武之后的钟山书院山长沈起元也指出,《诗经》尽万世诗学之变,自汉魏以至元明,作者接踵,诗体屡迁,而以合于《诗经》之旨者为大家名家,生徒学诗时要以《诗经》为法祖,“责之声响之间,辨之神味之外,岂特希风李杜,直当嗣音雅颂,亦在有志者耳”(邓洪波196)。有些施教者认为,《诗经》对后来的诗歌笔法有着重要影响,学诗时需要尊崇《诗经》。如浙江东明书院的劝学诗述及诗歌源流时指出:“陶情冶性仗诗篇,旨合风骚差可传。
扫却六朝宗汉魏,拟诸《三百》又相悬”(郑只恺36)。由于六朝诗歌没有汉魏诗歌高古,汉魏诗歌又没有《诗经》高古,因此研习六朝诗歌或汉魏诗歌都不如直接研习《诗经》,这正如宋代诗论家严羽所云,“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1)。《诗经》重视道德教化,其内容有着止僻防邪、祛恶从善的功效。如《论语·为政》云:“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何晏邢昺卷二;5)。《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郑玄孔颖达381)。有些施教者也主张,创作诗歌时要效仿《诗经》,不可越出道德教化的藩篱。如湖南岳麓书院的一首学箴为:“岂无虚车,偶游诗赋。骚耶辨耶,亦李亦杜。维《三百篇》,风人之祖。勿写佚情,名教是辅”(丁善庆57)。其中,“勿写佚情,名教是辅”一语表明,诗歌固然重视抒情审美,更应重视道德教化。广西道乡书院学规也指出,“诗则义本风雅,温柔敦厚,是其教也。若能随事讲求,始终不懈,何患德之不纯乎?”(陈谷嘉邓洪波1644-45)。该学规主张将诗教推及到日常生活中,勉励生徒以道德约束自身的行为,达到文行兼修的目的。总之,《诗经》在教化以及笔法上为后来的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学习《诗经》不仅可以提升道德修养,而且可以使创作扬风扦雅、直逼古人,因此,学诗者要想在诗歌上有所造诣,就毋容忽视《诗经》鸿作。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名作纷呈,学不得法,犹如治丝益棼,徒劳无益。清代一些书院在从事各体诗赋教育时,重视采取适当的方法,一般是要求生徒分类研习,循序渐进。如湖南岳麓书院学规指出,学诗要先专后博,以杜甫为则而后波及诸家,先律诗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渐进于风雅之林(陈谷嘉邓洪波1576)。江苏娄东书院学规指出,学诗时,宜先读中唐诸公诗作,次读李白、杜甫诗作,之后读韩愈、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诗作,要上溯汉魏六朝以浚其源,下及宋元明诸公以极其变,先作五律,后作五古、七古,然后作七律、七绝,此法可使功力易进而风骨遒上(王祖畲7)。台湾白沙书院学规指出,五古要读汉魏、六朝诗作,七古要读杜甫、温庭筠诗作,五、七律要读初唐诗作,五、七排律莫盛于本朝诗作,生徒要分类研习(周玺144-45)。江苏钟山书院学规指出,学诗要首分雅俗,次分工拙,先古而后律者多健,先律而后古者易靡(邓洪波196)。上述施教者在从事诗赋教育时,或由源及流,先古后今,或由流溯源,先今后古。由于诗歌主要有古体与近体之分、五言与七言之别,因此清代书院要求,将不同类别的诗歌分成不同的阶段进行研习。
为了防止出现盲目化,一般要求在每一类型的诗歌中,选择几位代表诗人的诗作进行研习。这种分阶段以及择典型研习的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便于生徒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的收获。
在中国诗歌史上,唐代诗歌登峰造极,深受后人推崇。如明代作家袁宏道认为,“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188)。现代作家鲁迅认为,“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612)。在唐代诗歌中,李白与杜甫的诗歌又倍受后人青睐。如宋代诗论家严羽认为,“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1)。“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168)。从上述事例中可知,清代一些书院在从事诗歌教育时,重视唐代诗歌尤其是李白与杜甫诗歌的教育。而康有为在广东万木草堂从事诗歌教育时,紧紧扣住李白、杜甫两位诗人,重点讲授两位以前的诗歌如何发展,两位以后的诗歌如何变化,列举纲要,娓娓道来(陈谷嘉邓洪波2378)。除了诗歌研习需要得法外,赋作研习也需要得法。如台湾白沙书院学规指出,“《三都》、《两京》、《子虚》、《上林》,雄厚丽则之正规也。
律赋始于唐,亦莫精于唐,宋人赋则单薄矣。读者于古赋、律赋,俱要寻求正路,不可扯杂”(周玺144)。由于汉代是赋作发展的繁荣时期,唐代是律赋发展的形成时期,因此白沙书院施教者要求生徒研习这两个朝代的赋作名篇。其中,“读者于古赋、律赋,俱要寻求正路,不可扯杂”一语显示出,学赋只有路径正确、方法得当,才能不误入歧途。路径正确、方法得当,再加之不懈努力,最终方能大有所获。
三、科考诗赋教育与八股文教育
八股文是清代科考主要文体,为清代科考的重中之重,应举士子要想得意于科场,就必须认真研习八股文。在清代科考内容的设置中,试帖诗与律赋是八股文之后的附带内容,二者的地位远远不逮八股文。有鉴于此,应举士子往往倾情于八股文研习而忽视诗赋研习,尤其是对古诗赋不闻不问。为了端正士习、净化学风,清代一些书院的施教者对这种不良现象进行了批判。如湖南玉潭书院学规指出,自从八股文成为科考主要文体后,乡里俗儒多半不讲古诗赋,“有皓首不知叶韵者,甚且以诗古为制艺蟊贼,戒子弟毋学,恐荒举业,以致少年英俊半汩没于烂熟讲章、庸腐时文之中”(周在炽9)。清代科考内容除了安排有八股文外,还安排有试帖诗、律赋、策、论、表、判等各种科考文体,各种科考文体都有着自身的价值与用途。清廷设置多种科考文体的用意在于,让应举士子在各个方面兼收并蓄,成为国家所需要的通才。为了让生徒端正学习态度,有些施教者对清廷的这种科考用意进行了揭示。如广东端溪书院学规指出,“二场之表以观其骈体,论以观其散体,判以观其律令之学。三场之策以观其时务。
进而为翰林,则有馆课之诗赋以观其韵语”(傅维森5)。
诗赋(尤其是诗)是清代科考的一部分内容,忽视诗赋会直接影响到科考结果,再者,中进士后若能进入翰林院,还会面临着更多的诗赋考试。如果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士子也应重视诗赋研习。贵州崧高书院学规就对诗赋的这两种价值做了具体阐发,观点如下:一,在院试、乡试以及会试中,衡文者如果觉得考生的八股文不怎么出色,就会仔细审阅考生的诗作。如果诗作清新俊逸、风雅典丽,衡文者便有怜惜之意,给考生判以较高的成绩。八股文虽是清代科考主要文体,但八股文佳而诗劣的考生在科考中落选的事例不胜枚举。二,士子登第进入翰林院后,散馆、大考等各种考试不用八股文,而是重视诗赋。一字不调,一韵不叶,即遭罢斥(徐鋐萧琯9)。崧高书院施教者从远近两个角度揭示出,诗赋研习不可偏废。
其思想可谓高瞻远瞩,其言辞可谓实而不虚。为了便于生徒进入翰林院后很快地适应诗赋考试,广东布政使王凯泰建议当地应元书院以翰林院散馆诗赋的格式来要求生徒(王凯泰26)。在上述施教者中,端溪书院山长全祖望、应元书院创建者王凯泰都是翰林出身,他们要求书院重视诗赋教育,与他们的翰林出身应该有所联系。
清代书院施教者不仅对诗赋的价值与用途进行了发掘,而且从学理上找出了诗赋与八股文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生徒正确地对待诗赋。八股文题目来自四书五经,重在阐发经学大义,宋代经义也重在阐发经学大义,八股文在内容表达上受到经义的影响。律诗重视格律要求,八股文也重视格律要求,八股文在外在形式上受到律诗的影响。
湖南玉潭书院山长周在炽论及诗、赋以及八股文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古赋为古诗之流,律诗为八股文之祖(8-9)。由于律诗为八股文之祖,因此清代书院施教者论及诗赋教育时,往往将律诗与八股文之间的联系凸显出来,以便生徒对照研习。
如贵州崧高书院学规对试帖诗与八股文在浅深、虚实、来路、结束等笔法上的联系做了说明,“律诗之法,其浅深、虚实、来路、结束,与八股大略相同。用韵须五字浑成,章法须一气贯注。一句有擎天之力,一字有倒海之功。以对偶起者,承须流走;以单句起者,承须凝重。起势平缓者,承须健拔;起势陡峻者,承须和平。中幅或分疏题面,用典须要恰当;或浑写全神,炼字须要工稳。写景须新,言情须真。说理毋腐,论事毋迂。咏物毋粘皮带骨,咏古毋拖泥带水。后路或推之愈深,或放之弥广;或以比例见义,或以烘托传神。结句须悠扬不尽,切忌直率;须冠冕堂皇,切忌衰飒。此应试律诗一篇之大略也”(徐鋐萧琯9-10)。试帖诗有六韵诗、八韵诗等各种类别,八韵诗与八股文在结构上有些相似。如安徽复初书院学规在分析六韵诗、八韵诗的写作技巧时,对八韵诗与八股文在结构上的联系做了说明,“大抵六韵者仍是一首五律,特中着四句,以足题理,使局面开展。故上二句不可上同于承,下二句不可下同于转。八韵势较宽,然大致亦复相同,其体裁略似八股,有起联,有颔联,有颈联,有腹联,有结尾,其法则浅深、虚实、起伏、照应尽之矣”(周广业15)。律赋也重视格律要求,有些施教者对律赋与八股文在笔法上的联系进行了揭示。如云南彩云书院学规指出,“律赋之法,其反正开合,亦与八股同。起宜挺健,结宜不竭,破宜赅浑,接宜超俊”(邓洪波1642)。上述施教者揭示诗赋与八股文之间的联系,其用意无外乎如下两点:一,诗赋与八股文在学理上有着相通之处,学习诗赋与学习八股文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若将诗赋与八股文联系起来学习,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二,学习诗赋与学习八股文二者实相资而非相妨,生徒学习八股文时不可忽视诗赋研习,尤其不能倾心于八股文研习而将诗赋抛之脑外。
四、汉学书院诗赋教育
清代书院数量繁多,类型多样。据陈元晖等人分析,清代书院主要有四种类型:或以理学教育为主,或以汉学教育为主,或以科举文教育为主,或以实学教育为主(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101-08)。其中,以汉学教育为主的书院(下文简称汉学书院)重视用考证的方法来从事研究。清代汉学书院往往寓考证于文学教育中,其文学教育具有浓厚的学术化色彩,这从诗赋教育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为了让读者正确地理解与诗赋有关的内容,诂经精舍、学海堂、经古精舍等汉学书院的一些诗赋课艺有时冠有考证性的题序。
嘉庆五年(1800),阮元任浙江巡抚。任巡抚期间,阮元在杭州创建诂经精舍。诂经精舍从事经史、诗赋以及文笔等教育,不课试科举文。自嘉庆六年(1801)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诂经精舍从事过八次课艺刊刻活动。其中,有些诗赋课艺冠有考证性的题序。如在《诂经精舍文集》中,徐养原在所作《咏葵》一诗的题序中征引《诗经》、《左传》、《尔雅》、《春秋繁露》、《东莱读诗记》、《农书》、《本草纲目》等作以及鲍照、白居易的诗赋等资料,对葵的种类、性能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考证(阮元,“诂经”卷十四;10-11),有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效。道光四年(1824),阮元任两广总督期间在粤秀山创建学海堂,学海堂的教育内容与诂经精舍相类似。自道光五年(1825)至光绪十二年(1886),学海堂从事过四次课艺刊刻活动。其中,有些诗赋课艺也冠有考证性的题序。如在《学海堂集》中,阮元之子阮福在所作《岭南荔枝词》四首诗作的题序中指出,杨贵妃所食荔枝为岭南所贡。他对苏轼等人所谓“汉贡交州荔枝,唐贡涪州荔枝”以及昔人所谓“(运送荔枝需要)七昼夜到长安”等观点进行了反驳,并征引《唐书·地理志》、《唐书·礼乐志》、杜甫诗作、白居易《荔枝图序》等资料加以论证(阮元,“学海”18-19)。针对运送荔枝如何克服岭南至长安路途遥远这一问题,阮福认为,需要先后采取两种方法:先运送连根带土的荔枝树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然后摘取荔枝过岭,飞骑至华清宫。采取这两种方法运送荔枝,可使荔枝新鲜而不腐坏。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后,江苏龙城书院分设成经古精舍与致用精舍。其中,经古精舍从事经史、文学教育,致用精舍从事舆地、算学教育。同诂经精舍、学海堂一样,经古精舍的一些诗赋课艺也冠有考证性的题序。如在《经古精舍课艺·丙申词章》中,吕景柟在《咬菜根赋》的题序中对北宋学者汪革的学术渊源、个人履历以及安贫乐道的高尚情怀等诸多内容进行了考述,尤其对汪革“咬菜根”一语的意义与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论说(缪荃孙华若溪34)。清代考证学的特点是,立义时重视证据,无征不信。这种学术的优点不少,“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梁启超,“清代”48)。从事考证研究,可使人在为学与为人两个方面都有所获益。诂经精舍、学海堂、经古精舍等一些汉学书院重视将考证用于诗赋教育中,此举既有利于增强生徒的考证能力,又有利于促进生徒优良品质的养成。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134)。“铺采摛文”这一繁缛藻饰的创作要求以博学为基础,尤其是要精擅于语言学。汉代时期,有些赋作家也是语言学家。阮元为浙江诂经精舍作记时,就对汉代赋作家精通语言学的现象做过评述,他认为,“诗人之志,登高能赋,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经诂。
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
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诂经”卷三;2)。其中,“相如”是指司马相如,“子云”是指扬雄(扬雄,字子云)。二位不仅在赋作创作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在语言研究方面造诣深厚,如司马相如着有字书《凡将篇》,扬雄除了着有字书《训纂篇》外,还着有方言学开山之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由于作赋基于博学,因此清代汉学书院重视作赋,对一些学识丰厚、考证精当的佳作给予表彰,这从《经古精舍课艺》的赋作评点中可窥一斑。如张潮的《刘子骏与扬子云书从取方言赋》所得评点为:“序考着书年岁,极有依据,赋首尾一气,自成章法。”吕景柟的《咬菜根赋》所得评点为:“削尽浮词,独标精蕴,学人之赋,异于词人者如是”(缪荃孙华若溪12、35)。王其倬的《孟敏堕甑赋》所得评点为:“才学并茂,声情激越”(缪荃孙华若溪2)。这些评语充分表达了施教者对生徒学识以及考证的肯定,毋容置疑,这种积极肯定的方法是鞭策生徒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清代汉学书院重视以学识为诗赋,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并非罕见。
历代不少作家重视以学为诗,将学识纳入诗歌创作的范畴,在他们的心目中,诗歌固然是感情抒发的载体,也是学识积累的产物。如杜甫认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1)。严羽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26)。朱彝尊认为,“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10)。沈德潜认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187)。清代汉学书院重视以学识为诗赋,只不过是将历代作家的这种思想进行了强化与推广。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往往与学识培养紧密偎依,文学教育也往往与学识教育密切联系,郭英德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旨在传授丰富的人文知识,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的鲜明特点”(4)。清代汉学书院在从事诗赋教育时,奉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指导方针,重视学识培养对诗赋写作的借鉴作用,有力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的鲜明特点。
考证学是清代主流学术,清代考证学可与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相媲美。自从清代初期顾炎武等人重视以考证作为解籍津筏后,步武者甚众。清代乾嘉时期,在惠栋、戴震、王鸣盛、钱大昕、赵翼、梅文鼎、段玉裁、崔述、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众多学者的推动下,考证学臻于鼎盛,考证这种诠释文本的重要方式普遍使用在经、史、子、集各个领域。梁启超论及清代考证学时指出,“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中国”24)。清代考证学的发展与繁荣,与众多人的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息息相关。在清代考证学的发展征途中,教育充当着重要推手,清代书院教育对清代考证学的发展有着推波助澜之功。诂经精舍、学海堂、经古精舍等众多汉学书院重视考证教育,力求将考证使用在经史、诗赋以及文笔等教育中。由于重视考证,清代汉学书院培养出了一批批精擅考证的生徒,有力推动了清代考证学的发展。
结语
要而言之,处于科举背景下,清代很多书院重视试帖诗与律赋教育。有些书院在从事科考诗赋教育时,还从事其他种类的诗赋教育。科考诗赋由古诗赋演变而来,二者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因此研习古诗赋有助于应付科考诗赋。一些书院在从事科考诗赋教育时也从事古诗赋教育,便有着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价值。清代书院从事各体诗赋教育的意义在于:可使生徒所作的诗赋去俗趋雅,与朝廷推行的清真雅正衡文准则相符合;可使生徒在诗赋上有所造诣,而不仅仅把研习诗赋作为科考的敲门砖;可以促进生徒文学综合素养的形成,为国家培养通才服务。为了有效地指导生徒研习科考诗赋,很多书院要求生徒研读各体诗赋名作。清代书院在从事诗赋教育时,一般是要求生徒分类研习,循序渐进,选择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进行研读。八股文是清代科考主要文体,士子往往倾情于八股文而忽视诗赋研习。一些施教者对这种不良现象进行了批判,他们要求书院重视诗赋教育,并对诗赋的价值与用途进行了发掘。诗赋与八股文都讲究格律要求,一些施教者还从学理上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揭示出学习诗赋与学习八股文可以相辅相成,二者实相资而非相妨,既有利于改变生徒重八股而轻诗赋的思想认识,也有利于促进诗赋的发展与传播。为了让读者正确地理解与诗赋有关的内容,诂经精舍、学海堂、经古精舍等一些汉学书院的诗赋课艺有时冠有考证性的题序,其诗赋教育具有浓厚的学术化色彩。由于重视考证,这些书院培养出了一批批精擅考证的生徒,有力推动了清代考证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