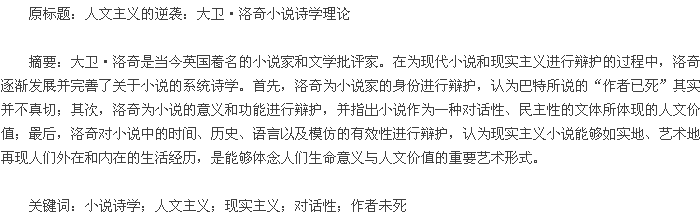
一、洛奇小说诗学形成背景
来自英国的大卫·洛奇(David Lodge)是一个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截至目前,他的小说作品和文学批评作品总数已有二十多部。在取得博士学位前,他已经发表了一部文学批评着作;开始在伯明翰大学工作时,他已成功发表了三部卓有名气的小说。从他的写作生涯开始至今,他一直以十分规律的节奏在小说批评与小说创作两个领域中轻松穿梭,所创作的小说作品和批评作品在时间上往往前后衔接,交替出版。这种跨界的创作经历令洛奇成为一个与其他作家不大一样的文人。作为创作型作家,洛奇深谙文学创作过程的机理和其中所蕴含的痛苦与喜悦;作为小说批评家,洛奇又对批评界里风起云涌的理论潮流有着切身体会;身兼两个身份,使得洛奇对小说创作与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更为细腻的洞见。他认为当前的小说创作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同时文学批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似乎也比以往带有更大的风险,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可能会危及人们长久以来对于人文主义的信念,而人文主义信念的倒塌则可能带来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出于这样的忧虑,洛奇尝试以他在小说创作中的探索和小说批评中的丰富经验为依托,构建起能够为陷入困境的小说创作指明方向的小说诗学,并为保存和发扬深陷危机的人文主义及其艺术的表现手法进行不断的实验和努力。
小说的发展注定会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已经走出了“现代”的边缘,进入一个难以以时代划分的当下。他们庆祝当下性的到来,庆祝雷威·斯托斯(Levi-Strauss)所谓的“介乎时间之外的原始存在”①。然而,这种“原始存在”失去了新鲜感之后,人们马上就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当历史可以以时代的方式进行划分时,历史总是以线性的方式向前推进,人们可以非常确定历史必然的进程。可是,一旦历史随着“现代”的终结而进入“当下”,历史接下来的前进方向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来说便有着太多的可能性,生活中时时刻刻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个令人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在小说创作领域,小说家们虽然为“当下”的各种可能性着迷,但是这些琳琅满目的选择同时也使得站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们难以做出自信的判断。作为小说家与小说批评家,洛奇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时代小说家们的困惑,在《历史主义与文学历史——现代时期图谱》(“Historic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Mapping the Modern Period”)中,洛奇就指出这个暂新的当下给小说家带来的可能性和挑战①。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Novelistsat the Crossroads”)一文中,洛奇对小说家面临的窘境以及应该选择的道路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洛奇对小说家角色、小说作品本质以及小说作品的表现形式等问题的探索直到他从伯明翰大学提前退休后还一直持续着,这些探索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又富有可操作性的诗学体系。洛奇的小说诗学体系以现实主义这一人文传统为根本落脚点,同时这一诗学体系的形成又以洛奇创造性地将巴赫金对话理论成功整合进他的理论体系,并因此建立起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对话的桥梁而告完结。
二、洛奇小说之辩
在20世纪,伴随着小说家们在十字路口的彷徨,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同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之前,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文学批评一般被认为是依附于文学创作上衍生的、二等的话语形式,批评家的功能也仅是挖掘文学家们在作品中隐藏的信息而已。这个时候如果说批评家们具有什么深远的抱负的话,那便是要建立起一个严谨的经典体系,从而实现保留住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所说的“一个文化中最好最有益的思想”这一批评的真谛。尽管这个时期的小说批评家们可能会关注小说主题以及形式上的不同特征,不过批评家们默认的一点是小说或多或少都是对现实的某种真实再现。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全然改变了。学院派文学批评已一跃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力量,而这股主要力量却又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主宰。批评家们对小说能否真实再现生活提出广泛质疑,作家对于自己作品的控制力遭受剥夺,小说作品独一无二的属性受到威胁。批评家开始在批评与创作的对话中取得主导地位,他们剥夺了原来萦绕在小说家头上的光环,高声宣判现实主义已死,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批评理论狂潮。在这些此起彼伏的狂潮中,学院派的批评家们乐此不疲地从一个学派跳到另一个学派,争先恐后地占领每一个新学说的阵地,却往往忘却了文学批评所要关切的文学本身。或许正是因为看到学院派批评界的这股喧闹,同时出于对小说创作以及小说批评的担忧,洛奇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前从伯明翰大学退休,成为一个自由作家②。这一近乎行为艺术的做法恰恰可以作为洛奇为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所有思考的写照,换句话说,洛奇小说诗学的构建过程,正是他为存在于当下、书写着当下、遭遇着当下种种质疑的小说和小说家辩护的过程。
1. 作者未死。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起初它的描述性要更胜于它的规定性,是一种阐释性更胜于破坏性的批评视角。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它开始变得激进,对传统文学和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失去兴趣。它关注叙事的潜在结构,关注语言而非言语。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与文本表达的丰富性在结构主义的视野下变得无关紧要。结构主义只看不同文本间的共性,而文学文本自身独具的特点和创作者的创造性则可忽略不计。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文学文本创作者根本无法对现存的结构做出任何新的贡献;这些创作者毫无例外都受到既存结构的“绑架”,他们只是按照既存结构所确定的范式,对已有结构进行小修小补式的演绎罢了。沿着结构主义的这一推理不难得出,其实不是作者创作了小说,实际上是小说创作了作者,换言之,作者的身份只不过是由潜在结构所规定的书写构建出来的意象罢了。
进入后结构主义时期,文学批评在解构的惯性下不断卷入到永无停息的理论“戏耍”之中,与文学本身的联系不断减弱。不少批评家们于这个时候所提出的理论对现实主义小说家来说,不可不说是一致命的打击,其中最为典型的说法便是来自批评界的泰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已死”说①。根据巴特的说法,在以前,小说家的经历一般被认为是其所创作小说的现实源泉,小说家就像是小说作品这个“孩子”的“父亲”一般,小说家经历了煎熬、思索等一系列艰苦的过程才“孕育”了他的作品,所以这个时候人们一般认为小说作品乃小说家经历与思想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之下,写作者其实与文本同时产生,两者的同时性决定了写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并不存在任何先在的思想和语意控制。文学文本不过是一个多维度的空间,在这空间中各种非原创的书写相互碰撞、相互交织,进而形成了相应的文本。总而言之,在巴特的意象体系下,作者作为一种语意的始发源头已经不复存在了。
洛奇觉得这样的说法固有其道理,但是过分地强调文本潜在的结构,必然会损害文本的独特性以及文本创作者独具的创造力。对洛奇而言,小说的作者不但没有死,而且还仍然在整个小说的孕育、创作和接受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作为一个小说家和文论家,洛奇觉得有必要就罗兰·巴特对小说家的“指控”进行辩驳。根据他自己的创作经验,洛奇认为他对自己的作品的确感觉到一种为人父母般的责任,这些作品的创作都是他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在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他的确为之思索并为之煎熬②。这些作品的出版也并非意味着创作者对这些作品的控制力就完全被剥夺,实际上在一个现代媒体盛行的时代,读者似乎对作品背后创作者的身世和经历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人们从报纸、杂志、电视、收音机、互联网等各种现代的渠道中网罗小说家们的访谈,窥探小说家们的生活经历,收看文学颁奖典礼,追逐新书发布会和签售会等等。各种新媒体的加入,不但没有消减人们对小说作品背后作者的好奇心,反而使好奇心得到成倍的放大。
所有这些均表明大部分现代的读者仍然认为小说家们是小说背后神秘的源头,小说家们具有着独特的才华和天赋,他们通过小说作品表达自己对于人生深入的洞察和感悟。除此之外,在诸如《小世界》(Small World)和《你能走多远》(How Far Can You Go?)等洛奇创作的元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作者的声音”更是洛奇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来回应对于小说作者巴特式的指控。
2. 小说的意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认为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小说的意义其实非常有限,因为它既不能丰富人类现存的表达结构,也无法真正掩盖隐藏于其中的潜在结构。这些批评家们认为小说中真实性因素所占的比例非常有限,小说家们往往要牺牲、剪裁甚至阉割真实的情节来适应于他们的叙事结构。受制于这些叙事结构所产生的限制力,小说家们经常得通过构建谎言来弥补叙事结构中存在的漏洞,以此推论,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者眼中,小说家们的所作所为显然就是“不道德的”。
针对这一说法,洛奇指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小说批评对小说潜在结构作出的规定在前提上存在缺陷。诚然,在人类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中存在很多人类行为和经历的原型模式,但是将这些原型模式形而上化,进而将其看成人类行为和话语普遍要遵循的内在结构,显然是不恰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经历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些深植于人类行为和经历中的原型也同样在经历着变化,有些老的原型可能要渐渐淡去,而新的原型可能会随着人们生活的进化和认识的提高而渐渐浮出水面。除此之外,在小说创作层面,一系列新的叙事手段被引入小说写作中,这也足以回应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对现代小说的批评。事实上,高明的小说家不需要构建谎言。当他们发现某个叙事结构已经不再适应他们所要描述的经历抑或某个结构已经“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么他们只需要戏仿这一结构,将这一结构镶嵌于别的结构当中,或是用不同的结构进行混搭,便能产生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与此同时,元小说的引入更是使得小说家们能够得心应手地突破既有叙事结构的束缚,他们甚至可以在叙事过程中站出来,以“作者的声音”亲自告诉读者该小说的叙事结构乃虚构,因而小说家便可以更大的灵活度来安排和组织叙事。
洛奇对后结构主义认定的小说意义的不确定性抱持保留态度。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能指与所指之间随机的、延宕的对应关系得到空前的重视,人们似乎不必再去探索一个能指所指向的所指,所有的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因为每一个所指本身又作为新的能指,指向着没有穷尽的所指,也就是说,每一个解码的终结就是另一次编码的开始。这一理论的产生瓦解了人们长久以来笃信的诸多人文观念。小说批评家鲍尔·德曼(Paul de Man)对小说意义的怀疑显然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他认为正是小说语言的不确定性,由语言所构建的小说便与小说表面上所要表现的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换言之,小说无法真实地表现现实①。对此洛奇觉得过分强调语言能指与所指间的延宕性将带来很大的弊端。他同意语言有能力构建起本质为虚构的意象,但是不管这一意象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多么遥远,不管这一意象经过多大的扭曲,其仍然可以从生活中找到直接的或间接的蛛丝马迹。理论上来说,当一个语言体系从它所存在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中脱离开来,那么这一语言体系中的能指与所指的确可以进行永不停息的语意的戏耍。但是,对于人们每天所使用的活生生的语言来说,人们所见到的词与它所表达的意义是密不可分的。他们生活在语言当中,语言融入他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塑造他们生活的基本要素,只要他们的生活是真实的,那么语言同样也是真实、确定和富有意义的。对于小说而言,人们更多关注的仍是小说揭示的小说背后的事实,小说与现实之间描摹、模仿的关系并没有终结。洛奇曾以自身的经历对此给予说明:
在每一部小说发表之后,读者问他的问题中最常见的莫过于“你的小说是关于什么?这部小说有自传的性质吗?这当中的某某人物是不是基于某个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知识分子或天主教徒真的会这样做吗?”②根据洛奇所说,这些问题的提出者并不限于“天真的”读者,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来源有不少是资深的学者,甚至是笃定的后结构主义者,他们阅读洛奇的小说,在阅读中,他们也和普通读者一样,乐于窥视在虚构这层轻轻的面纱下隐藏的隐私。
3. 小说的功能。一些唯物主义批评家,如陆森·格尔德曼(Lucien Goldmann)③以及洛奇笔下的女学者罗宾·潘罗斯(Robyn Penrose)④,他们认为小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步产生,小说围绕主人公与他周遭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矛盾展开。因为小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小说无法表现真实的现实,小说中充满过度的异化和碎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化身,只能沦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宣传工具。这一论断的必然结果是既然小说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载体,那么小说作品必然不可能颠覆它所依赖的价值体系,除非小说自身带有自杀性的本能。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小说不可能改变世界,相反,小说只是在美化世界。于是,批评家伦纳德·戴维斯(Lennard Davis)在《抵抗小说——意识形态与虚构文学》(Resisting Novels: Ideology andFiction)一书中表现出他对小说的失望。他认为小说并不是生活,它们所讲的故事和真正的生活经历迥然不同,它们的主题高度意识形态化,它们的功能也只是帮助人们去习惯现代世界所带来的异化和碎片化的生活。根据戴维斯的观点,小说在功能上存在问题,小说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只会阻碍改变的发生,因为小说会让读者苟安于现代生活中处处存在的异化①。
针对这些指控,洛奇对小说的功能进行了辩护。根据洛奇的看法,小说的功能在于阐释人们的经历以及人们生存的周遭世界,坚持人文价值并为这一价值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洛奇认为改变世界是重要的,但这更多的是社会活动家的责任,而不是小说家应该做的事;当然,尽管小说的功能仅限于阐释人们存在的本质以及人们生存的境遇,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就不重要②。实际上,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它比别的任何一种现存的话语形式都更善于刻划、叙述、再现和阐释人类的经历。关于小说的作用,洛奇完全赞同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的观点,认为小说家的地位要胜过于圣人、科学家、哲学家和诗人。尽管这些人亦都是人们生活经历中某一方面的大方之家,但是只有小说家才是各个方面的集大成者,而小说亦是生活之书,它对人们内心的影响要远远胜过诗歌、哲学和科学③。小说的优点体现在它的兼容并包上,它比诗歌、哲学和科学等现存的话语形式都能更为全面地展现和诠释当今人们的生活状态。不同于其他的话语形式,小说往往包含着诸多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刻划人们经历中的各种喜怒哀乐。正因为小说中包容着不同的视角和声音,因而洛奇认为小说的本质是民主的、进步的。在小说中,人们要的不是绝对也不是唯一,而是多种声音、多个音部所构建而成的完美和声。
4. 小说对话性的本质。在为小说的功能进行辩护时,洛奇首次提出小说兼容并包的民主本质,这个观点与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十分接近。洛奇将巴赫金的理论引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并认为民主对话性是小说最为显着特征和最为基本的创作原则。洛奇对巴赫金理论的浓厚兴趣源于他对20世纪诸多理论疯狂发展产生的忧虑。在简略回顾了20世纪文学批评发展的主要潮流之后,洛奇在《当今的小说——理论与实践》(“The Novel Now: Theories and Practices”)一文中认为如果我们想寻找一个能够超越人文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立的观点,一个能适用于整个小说的发展过程并证明小说的合理性的理论,那么这一理论显然只存在于巴赫金的作品中④。
关于语言的含义,人文主义者——尤其是浪漫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个人是所有语义的源头,而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如果语义仍然还存在的话,那么这种语义仅存于语义符号间存在的差异。与这些观点不同,巴赫金认为语义根植于语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根据洛奇和巴赫金的观点,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在我们使用之前就已充满前人赋予的意涵,而我们所说的每个词也都是或明或暗地指向将来某个真实的或虚构的他者。在真实的交谈中,某个词的使用亦都是明确地期待着某个与之呼应的词的出现。简言之,语义源于社会、文化和历史中的呼应和因果⑤。在文学批评中,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们认为作者的主体性是小说的源头,作者有权利决定小说的含义。相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否认作者的主体性作为小说的源头,小说的含义取决于小说潜层结构中体现的异同。与这两个观点不同,洛奇所倡导的巴赫金小说理论认为小说作品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话语,它的产生受启于之前存在的相关的历史和社会话语,与此同时,它也期待着与之相关的历史和社会话语的出现,进而完成一个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中进行的对话环路,而小说的含义也便在这样的对话中得以产生和确定。
对洛奇和巴赫金而言,小说无疑是一种独特的体裁。在诸如悲剧或史诗的文学体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个如上帝一般的作者,他的声音统治着整部作品,而其他的声音则只能作为配角,通过作者规划好的角度和顺序间接地呈现出来。与这些文体不同,小说对话性的本质允许语言和文化充满对话性的潜能得到最为真实和全面的发挥,而小说的对话性本质又可从小说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看。
从内部看,小说由一系列相互角力、相互作用的话语构成,是一种多音部的艺术形式。在小说中,人们不仅能够听到作者的声音,也能听到各个人物自己的发声,这些声音并非自言自语,在每个人的声音之间都存在着实际的或比喻意义上的“对话关系”,每个声音都在展现着自己观点,为小说主题的发展贡献一种可能性。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小说的作者也只是贡献了这一场场环环相扣的对话中的一个声音罢了。从洛奇对小说本质的概括上看,这一特点当属所有小说共同的属性,但在元小说的创作中这一特点有着最为卓然的体现。
从外部看,小说作为一个话语整体和文本外的话语存在着交互的对话关系。首先,这种对话关系往往体现在小说的互文性上,小说文本外的话语通常通过模仿、引用、暗指等多种方式进入小说中,与小说中的其他话语构成实质性的或隐喻性的对话。其次,小说作为一种话语,它与小说文本之外的世界同样存在着对话的关系。通过这层对话关系,小说成为多元的现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话语形式。最后,当小说原始的模仿理论被放置于对话理论中,小说对于现实的模仿也开始带上交互的性质,小说与生活间的关系再也不是简单的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生活经历被写进小说,同时越来越多的小说情节被搬到生活中来,小说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时而会变得模糊不清,两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则变得更为微妙多变。关于这点,洛奇通过对其笔下的人物亚当·亚博彼(Adam Appleby)的刻划对小说与生活间的模糊关系进行了戏剧化的演绎①,除此之外,洛奇本人作为学院派批评圈里的一份子,其生活经历与他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生活和经历的刻划无时不刻不在阐释着小说与生活之间这种复杂的对话关系。
洛奇认为鉴于小说对话性的本质,小说这种体裁天生就是民主和开放的,小说允许它当中不同的要素近乎狂欢般的交织和互动。心细的读者不难在小说中找到风格迥异的文字,比如说在洛奇自己的小说中,读者就经常发现在小说散文体的叙述中经常镶嵌有诗文的引用,日记、剪报、书信甚至是电影台词等等不同的文体也经常同时出现在一部小说中,风雅的对白与通俗的言语相互交织,迥然的要素相互辉映、穿插出现,俨然要把小说变成一场活生生的话语终极狂欢。当然,这样的特点并不仅限于洛奇的小说中。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里,小说的话语空间也不完全由叙述者的声音来主宰。认为小说作者的声音主导着小说作品意义的产生,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②。实际上,在大多数的小说中,小说的人物都可用他们自己独具的声音和语言来讲述他们自己的那部分故事,正如巴赫金所说,小说作品最为显着的特征在于它可以在一部作品中原汁原味地保留和采用一系列不同的话语,同时又不将这些话语简化为共同的分母①。小说民主的特点瓦解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和叙事。在小说中,没有一种因素可置于其他的因素之上,决定整部小说的最终含义。小说中的每个要素、每个人物、每个声音都会加入一种辨证的对话当中,而小说意义的产生正是因为小说中的每个要素、每个人物、每个声音都在这场对话里充分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这样的一种小说观,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是对存在本身价值的尊重。
洛奇将巴赫金理论引入到自己的小说理论体系中的缘由完全是出于他为保护人文主义价值和现实主义小说所做出的努力。在洛奇看来,当今人文主义的价值以及人们存在本身的意义均受到了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质疑。洛奇曾经在他的小说《好工作》中,通过罗宾·潘罗斯这个典型人物,对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人文主义的攻击进行了深入的刻划。罗宾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根据她以及影响她的作者们的观点,世界上根本没有资本主义文化和经典小说所赖以建立的“自我”这种东西,同时也根本没有什么确定的、唯一的灵魂或者特质来构成一个人的身份;人们唯一能找到的是在权力、性别、家庭、科学、宗教、诗歌等等无限的话语网络的节点中存在的一个个主体位置。类似的,世上根本没有作者这种东西,没有所谓的小说作品源头之说,因为小说除了小说本身之外,别无他物。世上没有所谓的起源,有的只是产生,人们没有天生的特质来成为人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仅来源于我们的语言当中——人们是谁并非决定于他们吃了什么,而在于他们说了什么。可以说,罗宾的哲学是一种语义唯物主义的哲学,身份对她而言是一种不再确凿的建构②。针对这些攻击,洛奇在他的文章《意识与小说》(“Consciousness andthe Novel”)中做出了详细的回应。洛奇认为西方所具有的自足的“自我”这一人文主义概念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会随着时间和人们观念的改变而产生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我”这一人文主义概念在当下已成明日黄花,实际上我们在文明社会中所崇尚的很多东西仍然还建立在“自我”的概念之上③。尽管个体之“自我”已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但是其主体性还仍然是屹立不倒的。个体之“自我”仍存在于不断的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之中,它经由与他人以及周遭世界的互动而得以塑造和再塑造,或者换用巴赫金理论的说法,“自我”产生于个体与其周遭社会和文化话语的对话之中。在这场对话中,个体的主体性来源于它与各种客观“他者”话语的对话;而对话之所以可以顺利进行,在于对话者之间的差异。对话者间的差异正是个体主体性与他者性划分开来的具体边界④。
在探索小说诗学的道路上,洛奇曾经简单回顾过自己走过的心路历程。他写道:“我对小说诗学的探求每次都会因为我接触到新的——或者对我而言是新的——文学理论。但是这个旅程止于我发现巴赫金的时候,有部分原因是他完满地回答了我给我自己提出的剩下的问题,另一部分原因是文学理论在进入后结构主义时代之后就对文学文本的形式分析缺乏兴趣,只把文学文本当成是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争辩罢了。巧的是——或许也不是完全的巧合——大概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八十年代晚期①,我从大学退休,变成全职的自由作家。”
三、洛奇的现实主义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在小说领域,现实主义传统面临着重重的困局。有人觉得现实主义小说所模仿的客观线性时间已不复存在,有人质疑现实主义小说所刻划的客观人类经验已经变得不再真实可靠,有人质疑现实主义小说是否能够再现人物的心理经验,还有人质疑语言到底还是不是现实主义表达的一种高效的工具。在洛奇的小说诗学体系中,洛奇承认现实主义小说在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他始终认为即便是当下人们经历着高度复杂的情况,现实主义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活力和潜能。
1.现实主义之辩。现代现实主义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在于人们面对时间和历史的困惑。人们对时间感到不确定的原因部分来源于对历史这一概念的模糊界定和现代生活经历展现出来的高度复杂性。洛奇在《历史主义与文学历史——现代时期图谱》中认为“现代”一词本身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代”字本来意味着一个时期的终结,但是“现代”却又强调着人们正在经历和感受的当下,换言之,在使用“现代”一词时,我们所说的时间同时指向了线性时间轴上的两个点,这在逻辑上是混乱的③。人们对于当下的感受与时代的划分愈发分裂,对客观历史的信任不断降低,甚至不确定对于客观世界的感知是否真实可靠。迈克·惠特华兹(Michael H. Whitworth)在《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一书中指出当人们对时间的客观感知已经无从获得,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将变得更具个人色彩,心理时间将比客观的时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④。现实主义小说所声称的对客观线性时间中事物的模仿,其可信度受到质疑,现实主义小说所模仿的客观事物和历史越来越受到主观心理时间的重新建构。
针对这样的质疑,洛奇认为尽管人们当前的生活经历可能鼓励人们对生活采取一种极端的或末世来临般的反应,但是我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在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时候,仍然认为现实主义所模仿的事实是确着存在的。历史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当我们赶不上火车或者某人发起什么战争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认为历史是虚构的了⑤。根据洛奇的看法,对历史和时间的哲学思考固然引人入胜,但是历史和时间并不是抽象的建构,历史和时间的真实性完全和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如果说人们能够塑造、改变以及重新建构抽象的时间,那么对于人们正在经历的历史和时间而言,它们是真实的,根本不会因为不同的哲学理论而发生改变。不管人们对时间的感受有何不同,客观的时间和主观的时间一样都是真实而不可否认的。人们共同的经历是真实感建立的根基,而这种真实感归根结底来说是现实主义小说所要模仿的东西。
现代现实主义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人们认为的经历的不确定性。现代社会人们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急剧增长,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代表的很多现代理论认为时间和距离不再是绝对的物理量,它们会随着观察者自身的运动而发生改变。这样的认识再加上弗洛伊德心理解析理论的广泛普及使得人们不太愿意到客观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找存在的真实依据,而更多地返向人们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在去寻找答案。洛奇清晰地看到了人们经历内化的趋势,认为这个内化的过程以及人们对于内在的关注其实正是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家所要刻划的内容。这些小说家和爱德华时期的小说家们不同。虽然他们反对现代主义的很多观点和信条,但总体上来说他们也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甚至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表现手法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养分,开始在现实主义小说中运用很多新的技巧和叙事策略①。在这些技巧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意识流的写作。根据洛奇的说法,意识流的写作就是“一种将小说叙事置于人物意识中心的趋势,让人物主观的想法和感受的再现来创造人物,而不是客观地描述、刻划人物”②。洛奇认为在小说作品中确认人物内在意识的真实性并将之如实地再现出来,这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原则和创作手段,现实主义作家只需微调他们原有的焦距即可做到。比如说,弗吉尼亚·伍尔芙就认为小说家应该如实地按照经历的“原子”轰击人们意识的顺序对经历进行记录。虽然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原子”并不以明确的先后顺序出现,它们会从不同的方向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但是不管怎么说,经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改进的意识流创作技法已经能最为精准地再现和模仿人们内心的意识。洛奇认为诸如意识流这样的创作技法正是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可大量采用的手法,只需辅以这样的手法,现实主义小说完全可以较为全面和准确地再现人们的现代经历。洛奇自己的小说中就不乏意识流的创作技法,比较典型的有《大英博物馆正要倒塌》(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和《思考……》(Thinks…)等作品。
当然,随着现代理论的发展,意识流的创作技法也受到一些理论家们的质疑。批评家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便认为现代作家处在由神话、梦幻、意象和原型构建的场域中,这些东西要求“虚构”而非“实证”的表述。他认为“通过意识流的手法,戏剧化人物内在生活,并以此刻划人物,这种模仿的冲动在通往人物内心堡垒的过程中经常会蜕化为神秘和印象主义式的书写”③。洛奇认为这样的想法显得太过于悲观,也忽略了人们在认知学方面重要的发现,即对人物意识进行精确刻划的可能性完全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建诸于人们可对构成意识的感质(Qualia)进行准确的分析。根据威廉·西格(William Seager)对感质的定义,感质是“人们感受到的意识的特殊属性,比如说人们看到的或想象中的红苹果的红,梦中交响乐演奏的声音,土司烤焦的味道等等。它们是构成人们栩栩如生的感觉的基础……是价值最终的源泉和根基”④。基于这样的属性,人们意识中的感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现实主义小说再现人们内心世界的理论和哲学基础。
现实主义小说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面对一些批评家对语言的非难,他们认为语言已经无法成为成功再现现实生活的媒介。批评家罗伯特·斯科尔斯认为既然语言在再现生活的时候突出的是被再现的生活,而不是语言本身,那么与其他真正透明的媒介相比,语言并不是有效的媒介。据此逻辑推断,既然语言的有效性受到质疑,那么使用语言作为媒介模仿客观世界的现实主义小说自然免不了遭受同样的非难。批评家雷蒙·达利斯(Raymond Tallis)在《现实主义之辩》(InDefense of Realism)一书中全面总结了斯科尔斯的观点⑤。斯科尔斯认为电影给了奄奄一息的现实主义小说致命一击。现实主义突出生活,忽略艺术,突出被表现的事物,而忽视表现事物的语言。
但是,论到表现生活,一幅图可顶上千言万语,而动态的图像就更是语言所无法比拟的了。斯科尔斯认为在面对电影等媒介带来的挑战时,小说应该放弃试图再现现实的想法,着重致力于突出语言能够启发人们想象的属性。
针对唱衰语言表现力的观点,洛奇希望人们不要忘了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属性。洛奇在《走向小说诗学》(“Towards a Poetics of Fiction”)一文中写到“意识的本质是概念的,语言的”①。尽管的确有非语言的或者先语言的经验存在,但是如果没有语言概念的帮助,我们恐怕很难对经验形成准确的意识。与斯科尔斯不同,洛奇认为在现实主义小说中,语言并非也不应隐去自身的存在,相反每个作家的语言都具有其鲜明的色彩和个体印记。在《小说的语言》(“Language of Fic-tion: A Reply”)一文中,洛奇进一步指出“现代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提供了很多例子,表明所有的语言都会对我们本来以为的先于语言存在的现实进行塑造。这点在小说作品中尤为突出”②。在小说家的作品中,不管这些作品声称它们多么的“现实”,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经验仍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作家深刻的语言印记。
除此之外,洛奇在他的《小说的语言》(Language of Fiction)中甚至尝试探索一种建立于语言分析之上的小说诗学。洛奇认为,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语言其瑰丽的程度不亚于诗歌中的语言。小说中的情节或叙事策略如果没有附着于艺术化的语言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那便是毫无生命的东西。小说家语言的艺术体现在小说家能通过对语言的精妙把握将读者带到小说家所预设的地方,或者在读者心中唤起小说家所要刻划的生活景象。在《小说的语言》发表三十年之后,洛奇在《意识与小说》一文中再次谈到语言在表现人们情感和感受方面不可取代的强大作用。洛奇认为对人们意识中的感质进行刻划,没有什么其他的媒介能够比语言更为高效完美地完成这项任务。同时,语言的魅力还在于尽管有时候感质是无法言表的,但是语言总能唤起与此感质相关联的感受,并通过这种关联让人在意识中重新再现这种感质的特质③。正因为如此,虽然其他媒介比起语言来说可能能更好地记录客观的声音或者影像,但只有语言才能更好地捕捉再现隐性的主观的感受。
2. 洛奇的现实主义宣言。洛奇的现实主义宣言最早出现在他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一文中。对于他而言,这样的宣言是他对现实主义小说将来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这种信念谦卑的宣誓④。洛奇说他喜欢现实主义小说,他自己也写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各种独特的创作规范可能对很多其他作家来说是一种束缚,但是对于洛奇来说却是一种宝贵的原则和力量的源泉。洛奇承认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写现实主义作品,但是现实主义却可以说是所有小说的基石。洛奇甚至认为,如果读者无法在他的小说中找到一种现实的感受或发现一丝现实的印记,那么说明他在他的小说中所做出的努力还未成功。
洛奇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力和形式充满自信。当有些作家和批评家纷纷觉得现实主义小说的规则对于小说家的创作是一种束缚时,洛奇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洛奇认为正是这些看似严格的规则,使得现实主义小说能成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形式。洛奇拿诗歌的创作同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打了个比方。诗歌中的音律和诗节的规范使得诗人不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们总得费一番周折找到一个声音和语义最为恰当的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从而达到诗歌独特的形式和内容之美。同样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使得小说家不能只是简单地复述他脑中的故事,而是要更多地挖掘他脑中叙事的潜能,找到一种更为恰当的方式和策略,将故事艺术地展现开来。只有这样,小说才能脱离简单的叙事,成为更加浓烈和纯正的一种艺术表现。
洛奇之所以与现代很多的小说家不一样,执着地追求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于他对人文主义的坚强扞卫。他曾说:“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是独特的历史的个体,我们因为一些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沟通方式,在社会中生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所感到的幸福或者不幸都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情决定的;不管是从个人的层面上还是从群体的层面上,我们都在调整我们的生活以适应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价值秩序和体系。现实主义模仿的就是这样的现实,而且现实主义应该会和它所模仿的现实同在。”
结 语
洛奇的小说诗学主要由其对小说的辩护和对现实主义的辩护构成,贯穿于这两部分之中的一条重要的线索便是洛奇对于人文主义传统极力的扞卫。对于洛奇来说,现代的小说家不但“没死”,在现代媒体的作用下,他们在现代小说的创作和接受中甚至要比之前的小说家来得更为活跃。小说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具有真切的意义和功能,它们仍然还反映着生活、刻划着生活,并且体念着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喜怒哀乐。小说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对话的,所有的个体、所有的因素均在小说这个对话的整体中得到民主的尊重,而作为人文主义价值所建立之基础的“自我”概念亦在这样的对话体系中才得以体现和保证。洛奇坚信现实主义小说能够继续发扬光大,因为不管是现代人们对于时间、历史客观性的质疑还是对于小说语言本身的质疑,都无足以动摇现实主义小说这一现代人文主义艺术堡垒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