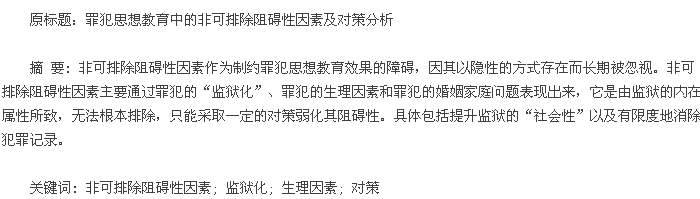
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在长期的改造实践中形成的以思想教育为核心、文化教育和生产技能教育为辅助的“三课”教育模式,有力地改善了狱中的思想教育环境,提升了罪犯的人生觉悟。在肯定这种积极效果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罪犯思想教育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阻碍性因素。其中一些比较明显的诸如监狱干警自身的素质问题以及教育改造的内容和形式等已获得较多的关注,且相应的措施也较完备; 而另一些比较隐蔽的,基于监狱内在惩罚性所致的具有寄生性特征的因素却未获得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足够关注,在事实上仍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这种因素以隐性的方式抵消着罪犯思想教育的效果,它就如同寄生在“监狱”身上的慢性病一样,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且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身处其中的罪犯,成为萦绕在罪犯心中的一团无法消除的阴影。笔者称这种因素为阻却罪犯思想教育效果的非可排除阻碍性因素。本文将对这种因素的内涵作深入分析,并尝试对缓解此因素的对策作初步探讨。
一、罪犯思想教育中的非可排除阻碍性因素分析
所谓非可排除阻碍性因素,是指由监狱自身定位而生,因监狱的特殊环境必然产生的阻碍罪犯思想教育实效性的不可排除性障碍。非可排除阻碍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 一) 罪犯的“监狱化”问题
监狱对罪犯的教育是在绝对安全稳定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必须使罪犯养成一种对监狱管理的服从习惯,这种服从带有某种意义的强制性和无条件性( 当然,监狱不能以此为由侵犯罪犯人权) 。在不损害罪犯最基本人权( 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等) 的情况下,监狱有权要求罪犯履行各种义务,甚至有权通过军事化的管理来规范罪犯的日常行为。通俗地讲,监狱中的罪犯走路、上厕所等基本行为都是要讲求规则的。监狱对罪犯的思想教育则是偏重于罪犯对其罪刑的忏悔,令其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自己是个有罪的人。罪犯身处这样的思想环境中,内心必然感到压抑,毕竟他们在被关押前享受过相对自由的社会生活,而监狱的隔离化、封闭化环境与其先前的自由社会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好比后天失明的人比先天失明的人更痛苦一样,心理落差普遍较大。与世隔绝的监狱环境和军事化的严格管理以及漫长的刑期,不断消磨着罪犯的心智,使其对外界的感知越来越麻木,以致最后丧失了适应外界生活的技能。
这就是“监狱化”所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它使罪犯因长期关押而逐渐被制度化,一旦刑满释放,脱离了这种制度,就好比失去了日常行为指南,生活便无法正常进行。在“监狱化”的影响下,罪犯在监狱中的思想教育成果与出狱后的社会现实生活很可能会形成零和博弈,使先前一切成果丧失殆尽。社会相较监狱显然并不“纯粹”①( 虽然监狱也并非真正意义的净土,但社会环境显然比监狱复杂很多) ,监狱的发展速度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速度。罪犯在经历了“纯粹”的监狱生活后,对社会生活很可能不适应。社会生活中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会使罪犯变得脆弱和敏感,一旦怯于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就很容易沉沦下去,甚至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为再犯罪率的分母。当然,再犯罪率的产生,一方面由罪犯的思维惯性所致,另一方面可能与罪犯试图重回监狱而因此采取的极端行为有关。
由此可见,“监狱化”对罪犯思想教育成效构成的阻碍本身就表现为不可排除性。因为“监狱化”的形成是由监狱的特殊环境所致,只要监狱存在,监狱的职能不变,“监狱化”问题就无法根除。
( 二) 罪犯的生理因素
罪犯的生理因素( 在此单指性的问题) 是罪犯服刑期间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然而,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持久影响,生理问题依旧作为个人隐私而难以寻求外界表达,加之我国监狱法中未涉及这一敏感因素,故而生理需求因素成为罪犯教育改造过程中一种易被忽略的隐性因素。
性的问题在男子监狱与女子监狱都会出现,其中男子监狱尤为突出。一方面男性罪犯在罪犯构成中比重较大,另一方面男性的生理需求往往比女性更强。在性犯罪中男性的主犯地位,女性一般成为从犯②就可见一斑。生理问题本身是一种正常现象,它基于人的自然属性而产生,从概率上说每一常态罪犯都会遭遇到生理上的需求。然而在监狱中,这种自然性的释放却受到严格的限制,罪犯的生理需求不可能如同在自由社会中那样易于满足,故而显得更加尴尬和反逆。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持续的性压抑一般会导致两种趋向: 一种是自然属性完全丢失,社会理想一并葬送,随之思想波动加大、情绪不稳定现象明显突出,对生活的乐趣和向往更是无从谈起,进而难以积极配合相关改造,严重影响到刑罚目的的顺利实现; 而另一种是个别罪犯更加极端,即将其对异性的渴望发泄在同性罪犯的身上,产生监狱同性恋问题。相比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对教育改造负面的影响可能更大。按照人的自然属性,同性恋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即使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在事实上承认同性婚姻,同性恋的权利已经上升至法律层面,但从生理学角度说,同性恋毕竟不是一种常态的恋情,社会对同性恋依旧持有批判性的态度,监狱对此现象更是严令禁止。因为监狱的同性恋情相比社会中出现的情况,其反社会性更强,有时就是纯粹动物性的表现,它是对监狱环境的一种丑化。但笔者认为,这种阻碍性因素确实是无法排除的,无论在我国的监狱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监狱,都会出现同性恋问题。从另一思路来看,监狱对罪犯进行规则性或无意性的生理限制,实属一种精神惩罚,这种惩罚,从客观上构成了罪犯教育改造的不可排除性障碍。
( 三) 罪犯的婚姻、家庭问题
罪犯的婚姻家庭问题是指未婚罪犯对未来婚姻问题和已婚罪犯对离婚问题以及二者对无法承担家庭责任而产生的担忧、悔恨、绝望等心理问题。首先是未婚罪犯的婚姻问题。随着罪犯低龄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未婚罪犯进入监狱服刑。罪犯在漫长的服刑生涯中,个人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尤为担忧出狱后自身婚姻能否解决。
婚姻问题本就是适龄男女青年考虑的重点,监狱中服刑的单身男女罪犯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顾虑。正常情况下并不严重的问题在罪犯这一特殊身份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乃至成为一块心病。这一方面缘于罪犯自身因犯罪而遭受刑罚的事实,作为有“污点”的人,在缔结婚约时是其一个严重的瑕疵,能否为社会认可尚存怀疑; 另一方面是对出狱后年龄的担忧,虽然通过减刑、假释,其中一些罪犯出狱后的绝对年龄可能不会很大,但相当一部分罪犯已过了结婚的最佳年龄。这在重刑犯和女性罪犯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对女性罪犯而言,因其适婚年龄范围较窄,且又曾被“贴”有罪犯的标签,使得女性罪犯在出狱后婚姻前景更加渺茫。而男性罪犯出狱后虽年龄不是最主要因素,但却因将青春年华耗在了监狱而导致自己碌碌无为,难以获得女性的青睐。久而久之,这种对婚姻的忧虑便会成为罪犯思想教育中一种不稳定的隐性因素,从而对罪犯教育改造的实际效果形成一定的潜在性阻碍。罪犯一旦将这种对前景的忧虑演变为对前景的绝望,则有可能以一种显性的方式( 如罪犯自暴自弃的行为) 表现出来,对监狱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此外,这部分罪犯无法适时尽孝所导致的亲情、温情缺失问题,虽不如婚姻问题表现得明显,但和婚姻问题一样,都是在监狱环境下无法排除的。从客观上讲,两者都是罪犯教育改造过程中的非可排除阻碍性因素。
其次是已婚罪犯面临的婚姻家庭问题。已婚罪犯群体所面临的是家庭责任的承担以及夫妻关系的维持问题。一般情况下,已婚罪犯从进入监狱那一刻起,就很难再谈家庭责任的承担问题。他们在无法直接履行赡养老人和照顾子女义务的情况下,且不说心中有无懊悔之意,家庭责任的不能承担已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若配偶不离不弃,罪犯会较好地接受服刑期间的各种改造; 一旦配偶选择离婚,对于那些难以维持家庭完整的罪犯来说,出狱或许成了一种心理负担,在教育改造期间明显会表现出些许的无所谓态度,这种心理表现于外的行为不仅会感染其他罪犯,而且也会进一步催化其自身的恶劣情绪。对于这部分罪犯来说,即便是重新获得社会自由,也会潜藏着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婚姻自由当然也包括离婚自由,社会所能做到的仅仅是说服罪犯的配偶为了不妨碍罪犯的改造尽量维系婚姻,但无法完全阻止狱中罪犯的离异问题。由此,罪犯的狱中离异必然会对思想教育的效果构成相当程度的制约。
二、非可排除阻碍性因素的缓解对策探析
非可排除阻碍性因素对罪犯教育改造效果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贯穿于罪犯服刑的过程中,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抵消罪犯思想教育的效果。从根本上讲,监狱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本来就不可能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其中的缺陷大多是由监狱的内在属性造成的。这就好比物理学中的误差问题,误差只能减少,但不可能绝对消除。所以,在上文中提到的非可排除阻碍性因素,只能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教育改造过程中不可抗拒的阻力,以弱化阻碍性因素对罪犯教育改造效果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如下对策。
( 一) 提升监狱的“社会性”,降低制度化对人的禁锢作用
罪犯的“监狱化”是缘于监狱相较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和人身自由的受限性所带来的制度化生活方式和机械化生活理念。罪犯以极端行为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理所应当受到惩罚。罪犯在监狱的服刑本身就是刑罚对罪犯惩罚的表现形式。但监狱的滞后性和人身自由的受限性所带来的制度化生活方式和机械化生活理念所产生的效果,无疑放大了监狱对罪犯的惩罚。从人道主义视角出发,考虑绝大多数罪犯最终都会出狱的事实,基于对罪犯长远利益的关切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等因素情况,笔者主张降低现存的“监狱化”影响,提升监狱的“社会性”。
按照人们的一贯思维,监狱是一个特殊社会,与正常状态下的大社会分处两个系统,两者各自独立运行,且对于大社会来讲,监狱这个特殊社会的运行对整个社会几乎不会产生丝毫影响,而社会对监狱罪犯的影响则非常大。因此,监狱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效果的要求不能高于社会对一般守法公民的要求,否则,罪犯在出狱后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等诸多不适应情况。目前社会呈现出的对罪犯的思想教育形成无形的抵销状况,就是由于监狱对罪犯的思想教育要求已经超越了社会对守法公民的一般要求所致。这对罪犯来说是不利于重返社会的。因而笔者所谈的提升监狱的“社会性”,是指监狱对罪犯的思想教育应当按照社会对一般守法公民的评价标准进行,而不是培养超社会性的理想化模范公民。
其实,监狱的教育环境也不可能实现这种愿景,监狱的教育改造对象是罪犯,因罪犯思想觉悟普遍低于社会公认的道德水准,所以矫枉不能过正,否则会由于脱离实际而将罪犯改造成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特殊群体”。由此,监狱应当以实用性的改造取代理想化的改造,与社会现实相结合,重在培养罪犯的法律意识、竞争意识和公民意识。从实用性的角度讲,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只要能使罪犯由“行为犯”至少转变为“思想犯”即可,而无需要求更多。另外,应当针对不同的罪犯结合其犯罪动机和具体的犯罪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甚至“一对一”的改造。监狱“社会性”的提升还依赖于监狱环境的“社会性”,以柔性制度取代刚性制度,减少制度化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效力,要把罪犯塑造成思想正向、遇事理性、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将其变成僵化的服从者。
( 二) 有限度地消除罪犯的犯罪记录
犯罪记录是对曾经犯罪受刑罚处罚的人所犯罪行、刑罚处罚类型等信息的记载。罪犯出狱后,档案式的记录会伴随其终生,并被视为一个无法摆脱的污点。犯罪记录对罪犯在出狱后的就业、生活都有不利影响,特别是罪犯的婚姻问题,“曾经犯”很容易遭受婚姻的失败。目前,我国刑法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免除未成年人的轻罪前科报告义务③( 但相应的犯罪记录是否被消除还存有争议) 。
相比之下,其他罪犯则没有享受到这种优待。笔者认为,罪犯出狱后,意味着其刑罚执行的完毕,而在其人事档案等个人信息中附加犯罪记录,则颇耐人寻味。从犯罪记录的设置初衷讲,可能只是对行为人人生经历的如实记载,本质上与工作经历、学业经历的记录属性一致。但由于社会公众对罪犯始终持有负面评价,对曾经犯罪的人也存有深深的疑虑和蔑视,这使犯罪记录一定程度上成了“曾经犯”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梦魇,让他们无法从容地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讲,犯罪记录在事实上成了刑罚的继续,以一种无形的方式让曾经的罪犯接受着非人道的待遇。由此,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笔者认为应当考虑在消除罪犯犯罪记录的政策上加大支持力度,使更多的罪犯能够真正重新开始生活,并对其工作、婚姻、家庭的影响降至最低。
当然,犯罪记录的消除应该是有限度的,即应采取区别对待原则,在消除记录方面避免出现“人人平等”的实质不公现象,使严重犯侥幸逃劫。比如,对于性犯罪和其他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暴力性犯罪者,其犯罪记录应适当保留。美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 对实施过性犯罪的人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其出狱后要向居住的社区和警察局报告,并接受前两者的监督。社区会向居民通报相关信息,并在性犯罪罪犯居住的房屋前做出特殊标记,提醒女性注意安全。
对曾经对儿童实施性犯罪的行为人,其居住的房屋要远离周边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甚至会专门为他们建立生活社区[1]。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性犯罪行为人采取的是一种社会隔离措施,意在防患于未然。笔者认为,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通过对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所犯罪行、改造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后,来决定是否消除罪犯的犯罪记录。具体来讲,除《刑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的八种行为以外,未成年人在出狱后,应确保其犯罪记录的消除; 对成年人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犯罪记录不得消除; 而对较轻的财产性非暴力犯罪、过失犯罪以及被害人存有明显过失的暴力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可消除犯罪记录。这样就可以在惩罚与改造间实现平衡。
上述对策出于笔者为缓解非可排除阻碍性因素在罪犯教育改造中的负面影响所作出的构想,虽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正是考虑到非可排除阻碍性因素不同于一般的阻碍因素,需以非常规的思路来设计相应的对策。这些对策的实现,还依赖于思想教育改造理念的革新,以及社会转型期整体价值理念的人性化。
参考文献:
[1]刘军. 性犯罪记录之社区公告制度评析———以美国“梅根法”为线索[J]. 法学论坛,2014(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