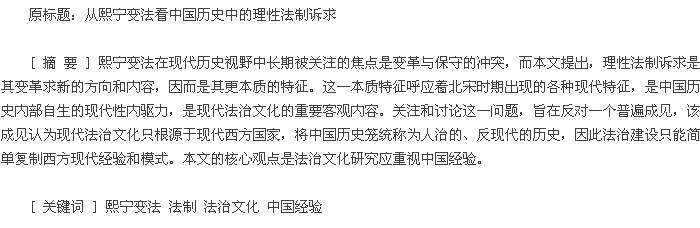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文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其权威认同和行为准则并非建立在社会政治结构的现实需要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祖先、圣人经典的传承认同之上,这决定了其保守主义立场;二是其权威认同和行为准则不是以法律、制度形式存在的客观行为规范,而是以文化、道德认同方式存在的主观文化认同,这决定了主观化、随意化的人治模式。
北宋熙宁变法与这两个特征都有本质分歧。其一,“变风俗”。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三不足”说,倡导从现实需要出发大胆变革,反对保守主义立场。这是现代历史阐释熙宁变法的基本立足点,王安石也因此主要被称为“改革家”。其二,“立法度”。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试图建立法律、制度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取代士大夫集团通过文化权力垄断获得的特权地位。
相较于“变风俗”,“立法度”更为本质和核心。因为它规定了变革的根本方向和性质。熙宁变法在随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主流叙述中,被称为“不合道德”,正因为它以理性法制诉求挑战文化道德认同。
但是,中国现代历史从晚清以降,始终将注意力放在移植西方的现代模式和标准上,因此产生两个相互关联的主流价值判断:其一,接受西方现代历史观,以求新求变为进步,以传统历史为保守;其二,在同一历史时间中,确立空间上的西方为现代标准,相应将中国与西方的空间差异认定为“现代与传统”的时间落差。在这两个价值判断主导的现代历史视野中,中国传统历史失去了从内部进行理性辨析的可能性,而是被简单化为现代历史的对立物。似乎现代中国只需要完整地克服传统中国、简单地复制现代西方,就能成功进入现代世界。
在这一视野中,人们更关注熙宁变法“变风俗”意义,因为“变风俗”最直接呼应了克服传统、求新求变的现代价值立场;而“立法度”所体现的理性法制诉求,则往往淹没在“中国传统历史是人治、反现代的”笼统判断中。最早是梁启超,从戊戌变法的立场和情怀出发,写作《王安石传》,这是现代文化以肯定新变、反对保守的价值观重新评价熙宁变法的开端。随后,熙宁变法及其主导者王安石在现代历史视野中日益受到重视和肯定:列宁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邓广铭以毕生精力四写王安石,文革期间“儒法斗争”将王安石纳入法家脉络,改革开放后,很多经济学家从“改革”的视野重新研究王安石,为20世纪的中国改革寻找历史资源。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各异,但在基本价值取向上,都集中于熙宁变法的变革精神和王安石的“改革家”意义,而忽视其“向何处变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这一更核心问题。
事实上,熙宁变法体现出遵循理性原则、建立法律制度,并以此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这是现代法治文化的重要客观内容和制度基础,也是充满现代精神的历史诉求。本文从这个被现代历史视野忽视的问题切入,分析正史对熙宁变法主流评价中的矛盾,解读熙宁变法提出的理性法制诉求,并论述这一诉求在中国历史转折中的意义,提出现代法治建设的“中国经验”问题。
一、 “品行出众”与“不合道德”
在具有正史话语权的史书中,都否定熙宁变法及其主导者王安石,而其否定的标准,是“不合道德”。通观这些史书,贯穿着两个根本逻辑:第一,文化道德标准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根本准则。在这一价值标准之下,对熙宁变法这样国家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其关注点并不在于国家社会的现实需要、变法内容对现实社会的适用性和变法引发的现实后果,而在于变法是否合乎道德,甚至对变法的评价转化为对变法主导者王安石是君子还是小人的辨析。第二,是否“合乎道德”的裁判权力掌握在士大夫集团手中,而非国家社会生活中占人数最多的百姓。士大夫通过对先祖、圣贤经典的学习和恪守获得天然的文化道德权力,一切有悖于他们认同的行为都会被指认为“不合道德”。在这一格局之下,熙宁变法是否合乎道德的评价就不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民生,而是是否合乎士大夫们对圣贤经典的理解。
《宋史》中,王安石首先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其当政后对自己的恩师挚友莫不翻脸无情:“于是吕公着、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1〕同时,王安石是一个表面善于伪装而实际上私心自用、党同伐异的奸臣:“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辩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卢杞合为一人。”;“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庭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则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
〔2〕《邵氏闻见录》不仅证明王安石是奸臣,而且把熙宁变法作为王安石刻毒奸险、挟私报复宋仁宗的后果,王安石的“不合道德”由此转化为熙宁变法的“不合道德”:“仁宗皇帝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碟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后安石自着《日录》,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以汉文帝恭俭为无足取者,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时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而下,皆为其毁诋云。”
〔3〕但是正史在这里遭遇到了一个尴尬问题:从其所举的例子来看,并不能证明王安石个人道德有亏。相反,用儒家道德标准衡量,即使是在这些充满偏见的史书记载中,王安石毕生行为表现出的个人品德都堪称楷模。首先,他谋国以忠,执政用人不以私恩为出发点,这恰恰是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不仅如此,《宋史》说他少年时“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乃是出于伪装,然而《宋史》又不得不承认他毕生清廉俭朴、位至首辅而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求任何私利。其次,他立身以孝,《邵氏闻见录》记载王安石“天资孝友,俸禄入门,诸弟辄取以尽”。
〔4〕最后,他处世以仁,《邵氏闻见录》还记载了这样一个足以证明王安石仁义品格的事件:他听到一个素昧平生、被买回家作妾的女子诉说丈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时,为之“愀然”,将其还给原来的丈夫,并赠金相助。〔5〕
仔细考察正史叙事,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一方面,史家的求实精神使他们不得不记载了大量足以证明王安石个人品德高尚的事实,并且不得不承认王安石以其出众的德性在当时受到士大夫集团领袖人物的称道;另一方面,士大夫的价值立场又使他们必须把王安石定格为“小人”、“奸臣”。
于是,正史只好动用了最强大的武器:“诛心”。其实质,是对人和事的评价脱离历史现实,由掌握道德话语权力的裁判者进行主观阐释和判决。于是,王安石之诚,只能是大伪若诚;之信,则只能是大诈若信;之名,也只能解释为欺世盗名。这一历史叙事方式不仅贯穿于宋代范冲所修《神宗实录》、李焘等人所修《四朝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史,也贯穿于《邵氏闻见录》等后来被称为“私史”的文人笔记,它们的立场、思路成为元人修《宋史》的渊源。
这种实际上背离了历史事实的诛心之论,在传统历史中也不断遭到质疑。质疑的标准仍然是传统文化道德认同,即证明王安石的“合道德性”。史传,作为王安石变法重要资料的《神宗实录》曾历经五修——今天能有定论和成书的是“三修说”——如此反复修改一本号称“实录”的史书,本身就反映了这一历史讲述过程的艰难和尴尬。这些史书的历史真实性也不断遭到质疑:与范冲同时,也因反对新法而受到排挤的黄庭坚,就曾当面指责范冲所修《神宗实录》曰:“如公言,盖佞史也”;虽从学于王安石然而政治立场不同于新党的陆佃,也曾批评《神宗实录》“岂非谤书乎?”至明,有陆九渊为王安石正名:“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业必为伊周,公之志也。”清人蒋士铨有诗:“后来十九尊新法,功罪如何请思量。”蔡上翔亦称“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
〔6〕这些散见于诗文杂评中的文字,其意义,不仅在于对这些史书在史实真伪层面提出考据学上的质疑,更重要的是揭示出正史讲述王安石变法故事的内在矛盾:既然王安石的本质问题不在于其本人私德“不合道德”,那么,他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合道德”?
二、 以理性法律制度取代文化道德认同
熙宁变法真正“不合道德”之处,不在于王安石本人人品的忠奸问题,而在于熙宁变法致力于从现实出发,建立理性法律制度,并且,试图以理性法制超越并取代传统文化道德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成为新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根本规则。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变法新政,每一次新政都是对当时利益格局的调整,但并非所有变法新政提出的诉求都与传统文化政治的根本原则产生本质分歧。有的是致力于修正现实中不合道德原则的现状,其实质是扞卫和重建道德;有的则是提出新的政治社会规则,并试图以此重建社会秩序,其实质是挑战和取代道德。这一差异在现代历史视野中长期被掩盖在笼统的“改革与保守”的冲突中,但忽视它就很难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虽然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会因为触动当时的利益阶层而在现实中遭受挫折,但当面对中国传统历史叙述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否“合乎道德”时,它们的命运却会产生天壤之别?
北宋有两次重要改革: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二者在今天的历史视野中都被同质化为“失败的改革”,但究其本质,前者致力于修复传统文化道德规则,后者则致力于以理性法制诉求取代文化道德法则。这一根本差异决定:庆历新政虽然在实践意义上和熙宁变法一样最终归于失败,在历史话语中却获得了和熙宁变法完全不同的命运,其领袖范仲淹虽然身前潦倒,死后却作为道德楷模享誉千载;熙宁变法的领袖王安石则身前身后都备受攻讦,被指称为“不合道德”的“奸臣”、“小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熙宁变法中作为“旧党”代表人物出现的韩琦、富弼等人,在庆历新政时期,却是新政的有力支持者。
比较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具体差异,能从本质上解释这一点。
1043年,范仲淹提出他的十项改革事目,而其中五项,是针对当时的官僚人事而提出,包括:
抑侥幸、精贡举、明黜陟、择官长、均公田。换言之,范仲淹的改革思路,重点在于人事,方式在于通过削减高级官僚特权、加强对官员的教化考核,来选择更加优秀的人才进入政权,并通过增加官员收入以促成廉政、勤政和善政。这样的改革所遵循的是儒家文化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教化以养德、厚禄以养身、升迁以励志。更重要的是,在范仲淹的改革中,他的出发点、立足点、关注点均站在士大夫的角度上,这场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让优秀的士大夫更方便地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获得更多政治上也包括经济上的利益。
而相比之下,熙宁变法的着力点却不在人事整顿或官员教化,而是首先放在建立理性法制。从当时的新法反对者与王安石之间发生的争论看,核心问题正是这一带有本质性的规则之争,具体集中在三个角度:
一是国家合法性标准。王安石提出了理性治国的诉求,即从社会现实生活和国家现实需要出发制定法令制度,并以其现实效果为评价标准,这是建立法制的理论前提。而反对者将道德当做国家存在的全部合法性基础。在这一视角下,国家不应该追求富强,而只应该追求道德,不合乎道德的富强是没有意义的。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说:“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7〕而王安石则提出,国家只有在现实中拥有强大的国力以保证其存在、有充足的财富以保证其发展,才谈得上合法性。他曾有诗论仁政典范汉文帝:“轻刑死人众,丧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谋。”指出这样的仁政是“浅恩施一时,长患被九州。”
〔8〕二是国家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王安石明确提出以建立施行客观法令制度为国家社会生活最重要问题,而反对者则将建立和维系文化道德认同作为核心问题。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开篇即明确提出:“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9〕这是苏轼为反对新法,向神宗皇帝提出的国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三件事,一言以蔽之,国家首要任务是维系文化道德认同。
而据《宋史》载,熙宁元年,王安石“始造朝,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10〕至熙宁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神宗又问‘然则卿之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11〕从这两次对答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王安石关注的重点不在文化教化与道德认同,而在“术”和“法度”这样的制度层面上。他不仅提出了迫切的为国家建立法令制度的诉求(“择术”、“立法度”),而且,他把这一诉求放置在最根本的位置上(“为先”、“最方今之所急也”)。
三是国家权力主体。王安石致力于建构由社会各阶层构成的、在理性法制逻辑下分担权利义务的社会共同体,这是建立理性法制的现实基础,而反对者坚决维护士大夫集团通过占有文化权力对国家政治生活权力的垄断。熙宁四年(1091年)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2〕这就是宋代关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场着名对话,这段争论典型地反映出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推行的这场变法的立场倾向,正是这种以便百姓为宗旨的立场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而引起了他们的“诚多不悦”。所谓“祖宗法度”、“道德人心”、“重义轻利”,这些浸透着士大夫价值标准的表述方式,在这场争论中统统指向对士大夫“治天下”这一根本利益的扞卫立场。而宋神宗作为熙宁变法的支持者,他提出的疑问是“于百姓何所不便”,体现出熙宁变法对国家权力主体的不同理解。正如包弼德所看到的:“王安石信奉地方政府的态度使他构想出一个‘包括民众在内’的政府,而司马光加入‘官僚贵族’的渴望使他将政府视为由士大夫掌握并为其服务的。”〔13〕变法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围绕这三个角度进行的反复论争,一言以蔽之,可以称为法制与道德之争。从这个角度,就能理解为什么正史叙事中,无论王安石本人品德多么出众,他和他所主导的变法都必须“不合道德”。
三、 理性法制诉求与北宋的现代性转折
熙宁变法发生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呼应着“唐宋之变”,致力于通过建立理性法制以重建国家政治社会结构。这是从中国历史内部自生的现代性内驱力,是今天研究法治文化的重要经验。
北宋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现代性的关系,已经为很多学者关注。1914年,日本京都史学派鼻祖内藤湖南发表《支那论》,提出“唐宋时代观”,此后亦有学者称其为“宋代近世说”。内藤依据西方现代历史标准,把中国近世历史的开端定在11世纪的北宋。不仅由此打破了传统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王朝史体系,更质疑了西方盛行的“中国历史停滞论”,提出中国历史进程自生的现代性内驱力。概括地说,内藤湖南提出北宋的现代性特征主要有二:一是制度上体现出理性主义实用色彩,尤其在官吏选拔录用中体现出来;二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上平民地位上升,即贵族没落后,平民直接面对君主,君权强化的同时民权也得到提升。
〔14〕流风所及,一些西方学者把宋代所呈现的新气象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新世界”。
〔15〕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如陈寅恪、钱穆、余英时,美国学者如包弼德、陈荣捷、狄百瑞等,也纷纷注意到中国历史自晚唐入宋所出现的巨大转型。
〔16〕虽然切入的角度、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但一般来讲,他们均看到安史之乱以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从整体上开始走向式微,一方面,是汉唐以来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思想体系经历了漫长的繁荣之后,开始显现出沉沉暮气,另一方面,则是新的制度和思潮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生长,直至西方现代思想传入中国,与中国内部自身积淀的变革因素相谋和,最终冲决整个封建社会而致其崩溃。上个世纪50年代,则有晚内藤湖南小半个世纪的另一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甚至将日本的现代政治,溯源到中国11世纪的北宋,从中国朱子学中找到了日本现代性的起源。
〔17〕熙宁变法发生在这样一个中国历史的本质转折点,体现出对整体历史进程的呼应和推动。
首先,理性法制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标志。现代启蒙很大程度上是重新发现罗马法精神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理性精神的核心地位。因此,当康德的理性启蒙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法治精神也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理性管理的核心精神。而遵循理性原则,以社会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建立法制并以此重建社会秩序,是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客观内容。
熙宁变法在北宋时期提出在中国建立理性法制、并以理性法制取代文化道德认同作为国家社会生活根本准则的诉求,根源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祖先和圣贤的经典在贵族政治彻底终结以后,已经无力解释新的社会结构,更无力解决由这一新结构所产生的新问题。有宋一代,多宽容忠厚之仁君,儒雅方正之贤臣,以“不杀士大夫”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训立朝,施行仁政的成就为历代史家所称道,其对传统文化政治理想的推崇和践行可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宋恰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贫弱的一个王朝。王夫之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是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18〕所谓“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说明依靠单纯文化认同维护大一统天下的文化政治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王安石是士大夫中较早正视这一问题的人物,而他思考和探索的方向,就是借助理性法制来建立和维持一个有序社会,这是中国历史在传统模式的困境中自生的现代诉求。
其次,熙宁变法建立理性法制的努力同时催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平民阶层上升,这是现代民主诉求的萌芽;二是国家观念改变,这是现代国家认同的萌芽。
先说平民问题,理性法制本身必然带有规则制定和执行的客观性(即不因个人主观原因而改变规则及规则发生效力的方式、范围)和平等性(即不因个体身份差异而在规则执行过程中产生标准和程度的差异)特征。这决定了熙宁变法的一个客观后果是平民阶层的上升和士大夫阶层的下降,体现出现代民主诉求的萌芽。比如免役法,让士大夫和平民一样出纳役钱,典型地体现出法制的客观性和平等性。在此之前,士大夫和平民在文化身份上的差异也扩展到对税收、徭役等非文化生活中,而免疫法抹平了这一差异,使他们变成法制客观范围内的平等义务主体。而熙宁变法所体现出来的这一平民化特征,正好呼应了前述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北宋整体平民化转型的时代特征。
再看国家观念问题。熙宁变法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制,从法的层面重新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在唐以前,主流国家观念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国家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文化道德功能,组织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职能主要依靠乡社族群自发承担,没有主权概念,领土有边疆而无边界。而熙宁变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是通过国家所掌握的货币来调节民间货币的供需,这里面必然包含着对政府职能的一种迥异于传统的理解,即政府不仅是一个围绕君主而存在的政治、道德、信仰的中心,它还必须直接承担经济功能。又比如,熙宁变法中的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在与西夏边境交界处广泛种植树林的做法,根本原因就在于北宋边患,王安石在这里已经具备了“边境”概念,并通过法制规定了国家保卫边界的职能。
总而言之,熙宁变法整体上致力于主要依靠理性法制来实现国家的秩序化,关注平民阶层在法制中的权利义务主体地位,重视国家组织和管理经济与社会的职能,这些都体现出“现代社会”追求理性、效率和民主政治文化的萌芽。
四、结 语
立足现实社会结构需要,遵循理性原则,建立客观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精神,是当下法治文化的重要客观内容。而这一诉求早在中国北宋年间的熙宁变法中就被提出,却直至今日尚未引起充分重视。讨论熙宁变法的理性法制诉求及其意义,实质就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内部的复杂性,尤其是发现这一复杂性中蕴含的中国文化自生的现代法治文化基因。这一点,是现代法治文化研究应该重视的中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