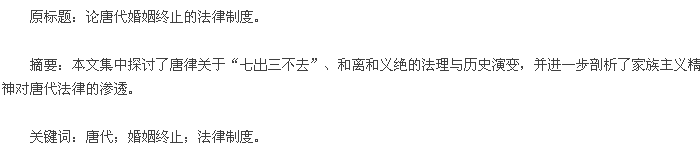
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婚姻的终止是指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因一定的法律事实的产生而归于消灭[1].导致婚姻关系终止的法律事实为配偶一方死亡(包括宣告死亡)和离婚。前者是婚姻主体的一方消失而使婚姻关系在客观上不复存在,是自然的结束;后者则是配偶于生存期间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除婚姻关系,是人为的结束。但古代世界婚姻关系的终止,从理念到制度较之现代要丰富多彩得多,这也许要归结于古代民族、国家及其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
就配偶一方死亡而导致婚姻关系终止而言,古今中外皆然。但唐代法律所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更具特色:(l)妻为夫服丧期间不得再婚。按照《唐律疏议》的解释,这一期间为27个月。(2)寡妻与夫的直系尊亲属的亲属关系依然存在。寡妻改嫁后,与亡夫的祖父母、父母相犯,依律仍须承担不同于凡人的刑事责任[2].并且寡妻改嫁后,与其寡媳相犯,唐律仍按亲婆婆身份的法条处断[3].从上列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唐代,因配偶一方的死亡而导致婚姻关系自然消亡,是就夫妻而言的,就婚姻所产生的家族、亲属关系而言,并不因一方死亡而完全消亡。事实上,法律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规定欲达到稳定现存家庭和族际关系的目的,而民间也常常自觉地保留这种族际亲属和姻亲的交往,以维持即有的家族社交圈不致变化和缩小。
就婚姻的解除--离婚而言,古代中国的离婚制度贯彻了浓厚的家族主义精神,无论是“七出三不去”的规定,还是义绝,都体现了统治者对家族社会的关切。虽然立法者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离婚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礼教还是法律乃至人们的观念,都以“白头偕老”为婚姻的最高境界,并不轻言解除。这首先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婚姻被视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因此,婚姻是两个家族的盛事。解除婚姻不仅意味着双方个人关系的破裂,更意味着男女双方家族关系的破裂和结怨,尤其是在通婚圈并不宽广的古代中国,这涉及到双方家族的声誉、利益和地位,因此人们并不会轻易就出此下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普通民众而言,婚姻的成立与解除还意味着经济成本的付出。婚姻的隆重背后往往是不轻的经济负担。不难想象,对承担这种经济负担的顾虑会影响人们的迟疑和退却。但是,在古代中国,婚姻从未脱离人事范畴而成为圣事,不曾出现西方中世纪的禁止离婚主义。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唐律从规定男子单方休妻到官府强制离异再到允许双方合意解除婚姻,为婚姻关系的解除创设了一个从个人、家族到官府主宰的法律制度体系,为离婚这一社会现象构建了一个宽宏的法律适用空间。
1、出妻。
出妻的涵义是指妻有七种法定过错之一种时,夫可以单方解除婚姻关系。最初,它只是礼制的一项内容,后人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颇具特色的一项离婚制度。
唐律的七出之法源于礼制自不待言,但在内容上有所变动,在顺序上也有较大的调整。《大戴礼记·本命篇》:“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妬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而依唐代律令,七出的顺序为: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妬忌,七恶疾“.从内容上看,礼称”不顺父母去“,而律称”不事舅姑“,虽然二者内容大致相同,但关注的重点大不相同,表现出礼与律两种社会规范的区别。依礼,言”顺“不言”事“,则舅姑的主观好恶是评判顺与不顺的标准。依法,言”事“不言”顺“,”事“的中心是侍奉,在恭从之外更偏重”顺“的客观表现形式--行为。这一变动更符合法律作为制度化创设的本质,它使得法律较之礼制道德规范更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使得人们的行为可以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
与礼制的顺序不同,七出的顺序在唐律中有较大调整,这主要表现在:
(1)无子出妻由礼制中的第二位取代”不顺父母去“而跃居第一位,”不顺父母出妻“这一项却被后置于第三位。
(2)淫去由礼制的第三项上升为法律的第二项。
(3)妬忌由礼制上的第四位下降为法律上的第六位。
(4)恶疾由礼制上的第五位退居法律顺序的末位。
(5)多言一项由礼制上的第六位,上升为法律上的第四位口舌。
(6)盗窃由礼制上的末位上升为法律上的第五位。
由上面这些变动可以概括出这样的结论:在唐代,无子、淫佚、口舌、盗窃的位次有所上升,而妬忌、恶疾的位次相对后置,这实际表明法律对继嗣、财产和家庭伦常的重视较礼制有所上升,位次的前置与后置,本身就是唐代社会根本特征在法律上的反映。
同时也表明唐代立法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引礼入律在唐代已经成熟,这一时期多的是对礼制的合理吸收,少的是对礼制的盲从;同时,立法者注意到了礼制与法律不同的适用范围和不同的功能,这种合理的区分有助于法律趋向合理化和世俗化,更能反映和适应社会的本质特征和需要。
七出是法律赋予男子单方面出妻的权利。这一权利,男子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是一种选择性法律规范,它既无强制性,又无须经过官府判决。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置子女于卑幼的地位,因而出妻的特权往往操之于男方父母,有时并不完全出于夫本人的意愿。
按照唐代法律的规定,出妻的法定条件有七,分别是:
(1)无子: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夫可以出妻。
(2)淫佚:纵欲放荡。[4]
(3)不事舅姑(公婆):缺少对舅姑无微不至的照料和违背无条件遵从的原则。
(4)口舌:说闲话、搬弄是非。
(5)盗窃:妻以秘密手段非法取得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这类财产包括他人的财产和妻私自取自家中的财产。
(6)妒忌:对男子性自由以及对与男子有染的其他女性的忌恨。
(7)恶疾。指妻患有不能与夫一同祭祀宗庙的疾病。
从上述七出法的各项内容来看,属于女子主观过错的有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妬忌五项,而无子、恶疾则是女子根本无法把握的客观事由,与女子主观无丝毫联系。以今人之观点看,其荒谬至极。
但是,在古代世界的法律中,因为通奸、不生育、仇恨、疾患甚至无原因的男子单方面的休妻带有普遍性,并非唐律独有。所不同的是,古代中国长达几千年均是一个家国一体的社会,这种家国同构的特征并未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削弱,相反,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家是国的基础,国则是家的扩大,由家族伦理推及国家政治,由家内秩序衍绎出政治秩序,家族利益和家族的稳定是礼制和法律关注的重点,七出法实际是礼律从宗庙继嗣、家族伦理、家族等级秩序和财产所有权等方面为着家族利益而设置的一项制度,其七项内容无一不与家族相关,无一不是为了家族利益。尽管明清以来不少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其中的不合理,但作为法律制度,其家族精神在传统社会始终未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唐律在七出之外,还规定了”三不去“来对七出加以限制。这一定制也源于礼的规定,但礼制与法律在”三不去“的顺序上有所不同:
(1)律将礼制上位居第二位的”与更三年丧不去“上升为”三不去“的首项,取代礼制第一项的”有所取,无所归,不去“,强调子妇为舅姑服过三年之丧可以成为对抗七出的法定理由。
(2)将礼制上位居末位的”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上升为法律上的第二位。这一顺序调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律在婚姻家庭领域对社会地位和财富变化的干涉。
(3)将礼制中位列首位的”有所取,无所归,不去“降为律的末位,表明唐律较礼制漠视对妻族所予财产和妻的现状,也表明了相对于礼,律更为漠视妻的利益和现实困难。
当然,以上调整都是在”三不去“的总框架内进行的,就”三不去“的精神而言,是对男子自由出妻的一种限制,自有其积极意义,对于稳定婚姻关系,也具一定的效果;体现了儒家仁义的精神,[5]也反映了礼制与法律对人伦的重视。但从根本上讲,七出三不去所构建的法律秩序体现了古代中国血缘家庭社会的要求,贯串着稳定家族社会的精神。
就违反”三不去“的处罚来看,唐律规定,凡是妻有七出之状,但存在”三不去“的情形而出妻,杖一百,并且出妻行为无效,原婚姻仍存续。但是,”三不去“并不具有完全排除七出适用的效力,妻犯恶疾及奸,虽有”三不去“的条件,夫仍可以出妻。由此可见唐律重奸非、畏恶疾的法律精神。
2、和离。
和离作为离婚形式的一种,是指男女双方不能安宁、和谐相处而自愿离婚,类似于今日之协议离婚。它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在这一离婚形式下,法律将男女双方置于同等的法律地位,双方共同决定婚姻归于消灭。
比起七出和义绝来,和离这种离婚形式要平和得多,它尤其顾及到了女方的声誉和地位,不致给两个家族带来难堪和尴尬。这在家族社会以及古代狭小的通婚区域内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从和离的法定条件看,表面是”不相安谐“(律),实质是彼此”情不相投“(疏议),前者是夫妻感情失和的外在表现,后者则是失和的内在实质。因此,较七出和义绝这种因过错而离婚的形式而言,它关注的是夫妻双方的感情状态。对这一立法,言其达到了古代离婚制度的高峰并不为过,即使在今天,也有其合理的价值。
但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和离这一离婚制度,仅仅是唐代离婚制度体系中的一项制度,并不具有对抗七出和义绝的效力,这说明和离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无限的,相反,义绝具有排除其适用的效力。当男方行使七出权利时,和离便不可能成立,由此观之,和离的主动权又是掌握在男方手中的。
3、义绝。
这是中国古代颇具特色的一种离婚制度。其意是指夫对妻、妻对夫的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犯有殴、杀、奸罪,经官府认定双方义绝而强制其离婚。
按照古人的理解,夫妻关系是由”义“来连结的,这种”义“可以理解为夫妻基于基本的人伦对对方及对方家族所应承担的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无”义“,夫妻关系就失去了连结点,婚姻的解除便成定局。这种婚姻观念渗透到法律中,便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的官府强制离婚制度--义绝。至于义绝之说何时入律,今已难考。但在礼法,大致只是确定了义绝的原则和精神,而法律则是将义绝之说具体化、制度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从唐律的规定来看,法律设立义绝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伦常和防范亲属相犯,这可以从唐律所规定的义绝条件看出:
(1)夫殴打妻之祖父母、父母;(2)夫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3)夫妻双方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互相杀害;(4)妻打骂夫的祖父母、父母;(5)妻杀伤夫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6)妻与夫的缌麻以上亲奸,夫与妻母奸;(7)妻欲害夫。
上述七项条件中,除第二项外,其余各项中妻所负的责任都重于夫。夫对妻方亲属,有殴、杀行为才构成义绝,而妻对夫方亲属,仅有骂、伤行为,就构成义绝。妻与夫缌麻以上亲属相奸,构成义绝,而夫只有在与妻母通奸时才构成义绝。同时,夫妻相害,只确认妻欲害夫为义绝条件之),而将夫欲害妻排除在义绝条件之外,足见唐律对夫族伦常的重视和唐代社会男权为本、男性为贵的特征。第二项关于夫妻双方的亲属相犯而构成义绝的规定,则是以夫妻之外的因素来决定婚姻的终结,这种在今天看来似乎荒谬的规定在当时却是极为合理的,因为在古代家族社会,家族具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特权。
上述七种行为同时被法律确认为犯罪行为,在承担刑事责任之外,法律还规定虽逢会赦,夫妻之间仍然义绝,官府仍应强制解除其婚姻关系。义绝自妻入门前起生效,[6]但从程序上言,是否存在义绝的情形,要由官府来判决。一旦官府判决义绝成立,夫妻就必须离异,否则,对不肯离异的一方,处徒刑一年。若夫妻双方都不愿离异,则按造意为首,随从者为从的原则处罚。
在古代社会,离婚生效后,不仅夫妻关系归于消灭,而且男女两家的姻亲关系也随之消灭,由此在身份、财产等方面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
1、身份方面的效力。
离婚生效后,夫妻身份关系即归于消灭,基于夫妻身份所产生的权利义务随之消失,双方享有再婚的权利。对妻而言,离婚意味着失去夫姓,恢复婚前的姓氏和身份,脱离夫家而回归本宗。其住所从夫家转为本家。同时,妻与母家的服制恢复如昔,不再降等。
而父母子女之间的自然血亲关系,并不因父母的离异而消亡。在古代家族社会,人们尤其重视血缘的延续。无论是礼制还是法律,都确认自然血亲不能人为地改变。这一观念以《仪礼·丧服》为典型,其疏言:”母子至亲,无绝道也“.这一原则为唐律所确认,律文多次引用这一表述。[7]反映在法律上,离婚后,母亲与子女仍具有如下法律关系:(1)子女为母服丧。按照礼制,子女为出母服期年之丧。[8]但唐代法律对离婚后,子女为母服丧并无明确的规定,我们只能从唐律反复强调虽与夫家义绝,母子终无绝道的法理念推知,既然母子的自然血亲关系为律所承认,则子女为其母服丧则在情理之中。(2)离异后,母亲犯刑事责任,仍可因子之恩荫而享受减赎特权,这明确规定于《唐律疏议·名例》”以理去官“条中:”其妇人犯夫及义绝者,得以子荫。“注云:”虽出,亦同“.[9](3)与旧夫的其他亲属仍保持法律上一定的身份效力。就刑事责任而言,姑改嫁或被出,虽与子之父无夫妻关系,但子媳与姑相犯,唐律仍规定按照母子关系类推适用法律,视为子媳与亲姑相犯。
对此,疏议有详细的规定和解释:”一问曰:子孙之妇,夫亡守志,其姑少寡,改醮他人,或被弃放,此姑妇相犯者,合得何罪?答曰:子孙身亡,妻妾改嫁,舅姑见在,此为-旧舅姑今者,姑虽被弃,或已改醮他人,子孙之妻,孀居守志,虽于夫家义绝;母子终无绝道,子既如母,其妇理亦如姑,姑虽适人,妇仍在室,理依亲姑之法,不得同于旧姑。“[1”]就婚姻的禁止条件看,任何男子不得娶袒免亲已离异的妻妾为妻。按照疏议的解释,属于袒免亲的亲属有高祖父的兄弟、曾祖的伯叔兄弟、祖父的隔二代的堂兄弟、父亲的隔三代的堂兄弟、本人的隔四代的堂兄弟。
针对亲等的不同,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定罪和处罚标准:凡嫁娶曾经是袒免亲的妻子,各杖一百;嫁娶曾经是缌麻亲及舅父、外甥的妻子,嫁娶各方处一年徒刑;嫁娶小功以上亲的妻子,则以奸论。如果嫁娶的是以上各种亲属的妾,则各比照上述规定减二等处罚。此外,以上婚姻都须解除。[11]
2、财产方面的效力。
唐代社会,家庭财产属于同居亲属共有,其使用和处分权属于家长,妇女并无所有权,因此也无离异而分割财产之说。妇女能否从夫家得到一部分资财,全由男方决定,律无定制。但妻带至夫家的妆奁,礼制承认妻有所有权,妻被出,夫应送还其妆奁。[12]汉时,律有“弃妻界所齑之文,据程树德先生考,汉时女嫁携妆奁而来,被出,则携妆奁归本宗。”[13]唐律虽无相关规定,但妻之妆枢,均作“当房”、“私产”,其归属实践中当依礼制。[14]
注:
[1]《婚姻法学》,杨大文等主编,法律出版社198》年版,第1《》页。
[2]《唐律疏议·斗讼》“妻妾殴詈故夫父母”条:“诸妻妾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各减殴、詈舅姑二等;折伤者,加役流;死者,斩;过失杀伤者,依凡论。”
[3]《唐律疏议·斗讼》“妻妾殴詈故夫父母”条疏议:“(姑)已改蘸他人,子孙之妻,孀居守志,虽于夫家义绝,母子终无绝道,子既如母,其妇理亦如姑。姑虽适人,妇仍在室,理依亲姑之法,不得同于旧姑。”
[4]《左传·隐公三年》:“骄奢淫失,所自邪也。”孔颖达疏:“淫,谓嗜欲过度;佚指放恣无艺。”
[5]《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取,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
[6]《唐律疏议·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条疏:“义绝,,妻虽未入门,亦从此令。”
[7]《唐律疏议·名例“以理去官”条疏议:“妇人犯夫,及与夫家义绝,并夫在被出,并得以子荫者,为-母子无绝道。故也。”《唐律疏议·斗讼》“妻妾殴詈故夫父母”条疏议:“虽于夫家义绝,母子终无绝道。”
[8]《仪礼·丧服》:“出妻之子为母期”.疏曰:“母子至亲,无绝道也。”
[9]《唐律疏议·名例》“以理去官”条疏议:“妇犯夫及与夫家义绝,并夫在被出,并得以子荫者,为母子无绝道故也。”
[10]《唐律疏议·斗讼》”妻妾殴詈故夫父母“条。
[11]《唐律疏议·户婚》”尝为袒免妻而嫁娶“条。
[12]《礼记·杂记》:”诸侯出夫人,有司官陈器皿,主人有司亦官陈之。“注云:”器皿,其本所齑物也。“疏云:”,,有司官陈器皿者,使者既得主人答命,故使从已来有司之官,陈夫人嫁时所赍器皿之属,以还主国也。“
[13]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三·律文考》”按急就篇,妻妇聘嫁齑媵僮。颜注,齑者,将持而遣之也。言妇人初嫁,其父母以仆妾财物将送之也,所齑盖即指仆妾物而言“.
[14]《中国婚姻史稿》,陈鹏着,第5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