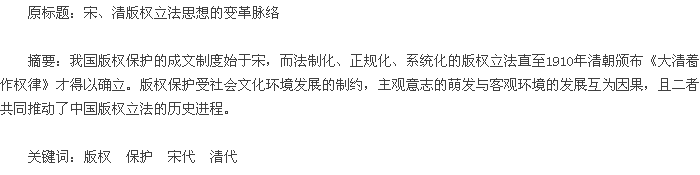
版权保护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在中国版权发展史中再次确证,即中国版权发展史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同时也彰显了不同时代的保护特点。宋朝与清朝作为中国版权的萌芽与建制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一、封建集权与列强入侵:宋清版权保护的社会差异
任何事情的存在与延续都与历史、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国人版权保护意识的萌动与版权法制的建立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宋帝赵匡胤强化皇权弱化相权,中央集权的程度得以扩大,对社会控制的力量得以强化。宋代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出版业的繁盛,为维护自身统治,在文化思想的管控方面,宋廷直接制定多条出版管制法令,一切对皇上不敬、对皇朝统治不利的书籍纷纷得以查禁。同时,宋朝属于典型的文人治国,民间流传的“杯酒释兵权”暗含了弱兵强文的旨意,复兴理学的思潮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中兴。故而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与繁荣中,也刺激了版权意识的觉醒。宋朝将典籍作为承载治国、教化的根本,两宋三百年间,官府推行访书推赏制,大量在民间访求先朝、前人的遗书遗训,对主动自愿献书者加以封官和重金奖赏。此举一方面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另一方面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单就搜访遗书而言,附加的推赏制度刺激了社会对书籍的需求,促进了出版业的繁荣。
但不法行为也开始出现,如一些献书者巧换名目、近作伪古、一卷多分等现象时有发生。迫于形势,宋廷出台了出版发行的事前审查制度,“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
法律一般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宋代版权意识的萌芽与商业发展也息息相关。宋代的商品交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商人地位逐渐提高。汴梁主要街道两侧全是商店,由原来的政治行政中心开始变成贸易活动中心。书籍在国内与国外贸易中成为主要内容,“像朝鲜和日本这些文化较高的地区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书籍、绘画和艺术品”。
尽管自宋代以后便有了对文字作品加以保护的成例,但作为一种制度,作为国家的正式法律系统,中国的版权保护法规却是在清后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完成的,且受制于西方列强的驱使和牵制。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纷纷抢占中国市场,在日益深入的商业贸易往来中,出于保护本国商业利益的目的,强烈要求清廷出台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体制。如在《辛丑条约》谈判中,美、英、日等国巧妙地将版权保护与近代化联系起来,承诺倘使清廷开始保护版权,可与清海关衙门重新订立进出口货物的关税比例,可禁止向中国贩卖鸦片。更为甚者,列强承诺若清廷的立法与执法均按法律规定加以保障与落实,其愿意放弃治外法权。而在中美两国之间始于1902年的商贸谈判中,版权保护也得到极大重视,先后举行了12次之多的有关保护版权的条款会议。迫于外商的压力,1903年“版权”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随之《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在北京签订。尽管带有被动成分与迫于形势的压力,但这些版权保护条款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开始以法律形式对版权保护予以确认。
与之相呼应,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之风日盛,“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国人的权利意识、利益意识增强。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等人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立法,修订清朝各项法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中国翻译了大量西方国家的法律,并参考日、德、法、美等国的法律体系,对《大清律例》的许多内容进行了修订。学者严复第一个提出着作者的版权保护问题,开始推动版权保护的对象化、实体化,主张国家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来保护着作者的权利。
19世纪80年代初期,新型的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开始在中国出现,民族资本向出版业大量注资,国民思想为之变化更新,着作者开始不唯名誉而兼顾利益。随着现代印刷术的流传,国内新式出版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速度,大量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作品得以翻译、推介。特别是随着“西学东渐”运动的深入,知识界译介西方书籍成为一种时尚。西方版权保护的做法与相关法律成为中国效仿的范本,如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参加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工作,1问题提出意见。而在致香港各日报的书文中,林乐知还介绍了西方国家在录用他刊着论时需注明出处的定例,以此对原作者权利得以保护。译着市场的繁荣助长了出版商、着作者、译者等人数的增加,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形成了清末对着作权进行立法的社会空间。知识传播的同时也带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法治思想,有关版权保护的法律条文、法治观念也大量传入中国,出版市场中各类人员的版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出版市场的繁荣导致的商贸摩擦也日益增多,版权纠纷案件与日俱增。典型的如1902年由廉泉(南湖)、俞复(仲还)、丁宝书等在上海集股创办的文明书局与1901年由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官报局之间的版权纠纷案。尽管版权纠纷日益增多,但大多各执一词,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诉讼程序可遵循。在矛盾、利益、竞争的共同作用下,“众多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奔走相告,要求实行版权立法”。
二、出版商与着作者:宋清版权保护的范围差别
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版权制度与印刷出版业有着密切联系。一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既加快了文化的传播速度,使作者的知识成果、思想观念得以及时传播,又催生了以书籍印制为生的出版商的壮大,书籍的批量化、低廉化出版发行同时给作者和印刷商带来巨大收益。二是印刷术中大量刻版、印制的产品不可能保留原作者、原着作的底稿特色,使以往基于手抄本而形成的无形财产权难以为继,从而公开的、强制性的法律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商人对财产权最为敏感,于是印刷出版商先于作者提出要求保护印刷出版财产权。南宋光熙年间(1190—1194),四川眉州程舍人刻印了同1权益,该书在初刻本目录页附着一方醒目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与现代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如出一辙,此牌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版权声明”或“专有出版权声明”。这标志着南宋时书肆书坊为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已公开声明对自己刻印的书籍具有专有出版权,提出了最初的版权要求,并已得到官府的认可。
与此同时,一些私人出资编辑、出版书籍的人也提出了保护其版权的要求。如南宋嘉熙二年(1238),祝穆刻印了自编的《四六宝苑》《事文类聚》等书,为防“嗜利之徒”翻印出售,祝穆向两浙“转运司”请求保护。官府批准了祝穆的版权保护请求,并出示榜文,张挂于衢婺州雕版印刷书籍的地方,令各方知悉。如发现“嗜利之徒”翻印销售,则允许祝家陈告,惩以“追人毁版,断治施行”,以此约束、禁绝盗版行为。此时的官府榜文可认为是世界上保护版权的第一份官方性质的“法律性”文件。作为中国古代版权史上的一份珍贵文献,它比欧洲发放的第一份印刷出版“许可证”早了200年。
祝穆提出对《方舆胜览》等书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不仅保护了其着作人的所有权,且保护了其着作财产权。印刷出版者主动要求政府保护其私人的出版经济权益,确认其私有财产权,这在“重农抑商”“见义忘利”的中国古代社会环境中可谓是一个历史性进步,是版权制度的非正式约束向正式约束过渡的开端。
现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主要是指国家出台明确的法律,且着重指明某一单位或个人对某项着作享有印刷出版和销售的权利,任何人要复制、翻译、改编或演出等均需要得到版权所有人的许可,否则就是对他人权利的侵权行为。从内容上看,我国正式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着作权立法始于清末。1903年,学者严复上疏学部大臣张百熙,要求也制定类似日本《着作权法》的法律,以保护“编”“纂”“译”“着”等作者的权利。1910年,商务印书馆的陶保霖撰写了《论着作权法急宜编订颁行》一文,阐明了制定着作权法和出版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敦促清政府尽快颁行两法。清廷当时派出观察员,参加了1908年在柏林召开的修改《伯尔尼公约》的会议。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在主持修订法律中,也重视着作权法的立法工作,还邀请了三位日本专家参与帮助。基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推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着作权法《大清着作权律》终于在1910年得以颁布、实施。
从内容上看,《大清着作权律》分为“通例、权利期限、呈报义务、权利限制、附则” 5章,共55条。该法规定:“凡称着作物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曰着作权。称着作物者,文艺、图画、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等是。”由此而知,此时的版权主要包括出版权和复制权,书面作品和雕刻、模型等立体作品都包含在作品范围内。该法确认版权为作者的专有权利,并通过6条禁例予以保障。这与宋朝版权保护重心在出版商的做法相区别,又向现代版权保护迈进一大步。具体为:(1)凡经呈报注册取得版权的作品,其他人不得翻印复制,及用各种假冒方法进行剽窃;(2)接受作者的作品出版或复制,不得割裂、篡改原作,不得变匿作者姓名或更改作品名称发行该作品;(3)对于版权保护期满的作品,亦不得加以割裂、窜改,或变匿作者姓名或更改作品名称发行;(4)不得使用他人姓名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5)不得擅自编写他人编着教材的习题解答;(6)未发表的作品,未经版权所有者同意,他人不得强行取来抵偿债务。就立法特点而言,《大清着作权律》基本上采用了英美法系原则,亦吸收了中国法系的原则,如规定不能更改或隐匿作者的姓名,以及不许对作品的内容进行歪曲、篡改。保护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30年。取得保护的条件是必须到当时的民政部进行注册登记。不注册登记就不发给着作权执照,没有着作权执照就不给予着作权保护。
三、政府意志与民权兴起:宋清版权立法的效果各异
如前文所言,尽管宋朝版权制度的非正式约束中已孕育着正式约束的萌芽,但封建君主和官府颁布特许授权仍是个别、零散的行为,并没有升格到正规化、强制化、法条化的国家成文法高度。由于缺乏系统化、明确化的版权法律保护制度,且不具有普遍性与强制性的约束力,近现代法学中以私人权利、个体着作者为保护对象的法律条款并未出现在宋代的版权法律法规之中。于是,在中国古代“德治高于法治”的传统下,尽管有很多着作者、出版商在作品中刊印了“不许复版,翻印必究”的权利主张,但更多流于形式,成为着作者、出版商的一厢情愿之举。正如晚清版本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所说:“当时一二私家刻书,陈乞地方有司禁约书坊翻版,并非载在令甲,人人之所必遵。特有力之家,声气广通,可以得行其志耳。”“从保护效果看,并没有产生由侵权行为人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以及向古书作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后果”。
从出版、发行管制的目的上看,宋代制定的一系列出版发行方面的规章制度,还是为统治者的政治目的而考虑的,还是在于维护社会政治秩序,还是力争谋求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更为严重的是,禁止民间随意翻刻、出版有关王朝统治的书籍,无论是假借防止泄密还是误导后人之口,严令之下对于宋代乃至之后历代王朝的版权发展都产生极大消极影响”。
但面对政府的政治统治,诸如出版商出版类似通俗文学读物、儿童启蒙书籍、日用万宝全书、医用书籍等作品,又会失去向政府寻求保护的正当性依据。悖论性的出版选择实质反映了维护政府的政治统治与保护着作者、出版商的版权利益并未实现有效衔接。仅当出版商主动将出版物的内容与宋朝政府的统治利益相关联时,才有希望受到政府的重视与保护。个体的版权利益诉求臣服于国家政治统治的状况,导致宋代民间萌生的版权观念与利益主张无法推动国家层面的版权立法,民意中的版权保护观念无法转化为国家层面的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同时,政府权力、国家意志的导向是公共领域,与排他性、独占性的现代版权法甚至整个知识产权法大相径庭。于是取得政府对自身出版物、出版利益的关注成为宋代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商的主要途径,出版物上禁止“私人翻印”的警告之语,沦为宣示性文字,“尤其是在盗版横行的环境中版权保护更是力不从心”。
到了晚清,这一局面大为改观。清末《大清着作权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版权保护法制的正式确立。不可否认,《大清着作权律》未尽成熟,如吸收了大量欧美法律观念,律条杂抄众国。加之封建官僚体制、文官政治的局面没有改变,《大清着作权律》在着作权注册呈式、继续呈式,以及着作权立案、侵权处罚等方面的规定中凸显了封建王朝的统治特点。但瑕不掩瑜,《大清着作权律》吸收了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知识,借鉴了西方权利保护理念,自觉融入着作权立法的世界潮流之中,开辟了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层面的着作权立法新纪元。政府以政治强权来维护着作者、出版商的私人利益,这标志着中国现代版权制度的确立,改写了我国版权发展的历史分期,我国现代版权保护的历史得以开始。《大清着作权律》颁布后随即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为方便国外传播与遵循,外国政府曾函致中国公使将此项法律译成德文或法文。自此以后,从清末到民初的出版物上都开始标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等字样。
《大清着作权律》的颁布既使着作者和出版商的权利得以维护,深层次上也给清朝末年迂腐僵化的知识界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版权保护意识更是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加之清末大多翻译者、着作者多为留洋之士,他们既翻译介绍外文书籍,同时也吸纳了西方现代的法治观念、人权观念。第一,从《大清着作权律》开始,政府角色由文化传播的钳制者转为版权利益相关人的保护者,“官本位”开始向“民权”倾斜。第二,版权保护主体开始由以出版商为主转到以着作者为主。《大清着作权律》具体规定了着作权保护中的权利主体、权利期间、侵权救济等,这些内容体现了以着作者权利为重心的现代版权保护制度。第三,私有财产由忽视转为重视。在“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传统国情下,个人的财产私利并未得以公开化、明确化的法律保障。但《大清着作权律》直接肯定了着作者的财产权益,并针对各种侵权行为制定了补救措施。
四、多元互动:中国古代版权保护的发展逻辑
通过宋清两代版权保护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效果影响等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版权保护的历史呈现出以下发展逻辑:
1. 作者及出版者权利意识的萌动和维护
前文已述,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其根源为中国传统“重义轻利”的处世之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视书籍为传承文明、思想宣教的载体,而不视其为可流通、可增值的商品。在义与利的选取中,“君子谋道不谋食”一直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加之封建社会中强权主义、专制主义的推广,长期以来版权意识并不突出,创作、发表、刊印文化作品更多是传播道义。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社会民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广大文人对于财产利益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转变,愈加重视稿酬及有关版权财产利益的获取。
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理路,现代版权保护法也有其萌生的经济基础,其旨在维护着作者的财产权益,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二者都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经济利益。清末民初之际,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利益观已经逐渐在发生质变,爱财求财、逐钱言利等难以启齿之举逐渐变得公开化、世俗化。“正是由此,他们第一次背离了文人不言利的传统,而理直气壮地主张对自己的劳动给予报酬,这些观念潜伏在西方思想的背后静悄悄地展开,构成了影响中国版权法的一种内生性力量”。
2. 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从技术层面加速版权保护的制度化、系统化
“版权史向来是一部对技术发展作出立法反应的历史”。平民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推广使图书的大规模复制成为可能,着作权问题也开始凸显起来。从世界印刷术的发展趋势看,西方石印术经由日本人改制成的白铅印刷术,也在清末传入,经过改制的白铅印刷术印制效果更精良更高效,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后,得以大面积推广。同时,装订图书的方法除刊版书籍仍须用线装外,精装、胶装书籍也大量出现。技术的革新使得书籍开始变得物美价廉、便于携带、易于流通。“科技是把双刃剑”,印刷出版的日趋简易快捷精良诱发盗版现象频出,而盗版必然引起原作者及原雕印者(出版者)的不满并使其采取防范措施。
书籍出版者一方面请求官府准许其独家经营,另一方面为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制止他人轻易复制,一些刻印者便在自己的出版物上标明自己有独家出版的权利。
3. 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导
“对于知识产权来讲,个人救济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当知识产权客观上需要成为权利时,客观上和逻辑上唯一能借助的外壳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支持。只有国家公共权力的干预,才能使权利人对于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再现予以控制成为可能”。
当然,行政力量只有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更加长久、稳定、客观。清廷于1904年由商部牵头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翻译国外各种版权保护法令,之后分别于1906年、1907年制订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和《大清报律》,奠定了版权立法的框架基础。之后,1910年中国近代第一部版权法——《大清着作权律》终于出台。
4. 外来力量的推动
中国的现代版权法体系具有舶来性质,这与西方外来势力的入侵息息相关。单就印刷技术而言,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为扩大在华的宣传和出版中文书报的需要,积极将铅活字印刷术和印刷机引入中国,并利用这些技术及设备传播西方思想。如1819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铸成了中文铅字并译印了第一部汉字铅印书《新旧约圣经》。受外来传播业影响,中国的民间书肆、书坊纷纷开始引进现代化的机械印刷设备来刊印书籍,雕版印刷术逐渐被机械印刷技术所取代。随着资本、业务、技术、厂房、人员规模的扩大,国内众多民间印刷出版机构逐步发展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群学社等现代出版机构陆续建立。
参考文献:
[1] 马泓波点校. 宋会要辑稿·刑法[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204.
[2] 费正清. 传统与变迁[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33.
[3] 语和.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着作权法——《大清着作权律》简论[J]. 历史教学,1995(6):16-19.
[4] 姚怡昕. 中国版权制度变迁研究[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65.
[5] 潘文娣,张凤杰. 关于中国版权史溯源的几点思考[J]. 出版发行研究,2010(12):6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