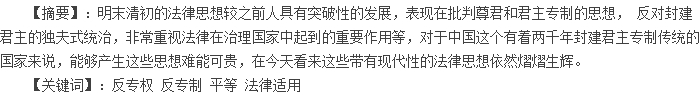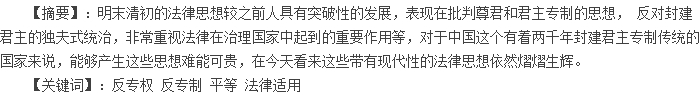
一、现代性法律思想在明末清初的产生与表现
(一)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君主专权的批判和“分权”思想的产生
明朝法律思想发展首先表现在批判尊君和君主专制的思想,对于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能够产生这种思想难能可贵。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表现的最为激烈的就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他们以满腔的怒火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存在的正当性:比如,黄宗羲认为:君主独夫式的专制并不是上古仁君的统治方式,因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现世的君主专制只是后世君主贪婪成性,为谋一己私利而造成的,他们“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因而“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他进一步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此外,黄宗羲还反对君主把百姓视为自己的囊中私物,认为正是君主对民众百般的剥削才导致人民生活困苦,他愤慨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唐甄对君主专权的批判更甚于黄宗羲。首先,他从平等的观念出发,否认君主的神性,所谓“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这就意味着君民之间至少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即“抑君”.
其次,他将封建帝王视作“贼”,并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的论证理由是:“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再次,唐甄将明末清初的世事动乱、人民凄惨的生活归咎为帝王之过并毫不掩饰其对封建君主的憎恶。
唐甄在《潜书》中对君王质问说:“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贼盗之乱者谁也?……毒药杀人,不能杀不饮者。……良药生人,不能生不饮者。……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抚之则安居,置之则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进而,唐甄认为那些荼毒百姓的帝王“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
黄、唐二人的反专制思想都是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封建纲常思想的反抗,带有近代启蒙思想的深刻内涵。相比之下,王夫之对君主专制的认识就没有黄、唐二人深刻激进:王夫之的总体思想还是尊君,忠君的。他认为君臣纲常是不应该被废除的,否则就会“庶人可凌跳乎天子,而盗贼起”,因为这种纲常的存在是“原于天之仁,则不可无父子;原于天之义,则不可无君臣”.
但是,与一般的士大夫盲目愚忠所不同,王夫之也提出了限制君主专制的思想,即为了约制君主的至高大权不被滥用,应该设计一套由天子、宰相、谏官“环相为治”的独特的制衡机制。
“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而言乃为功。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者也。”这种以皇帝为中心的制约机制的出现与明清之际朝中无相的事实有很大关系,因为包括王夫之在内的许多士大夫都认为正是明朝无相致君权无所约束最终招致国家的灭亡。
为了限制君主专权,总结有明一朝国中无相,宦官专权的亡国教训。黄宗羲也提出了“分权”这一具有现代宪法意义的概念,具体措施包括:第一,恢复设置宰相,防止因君主集权的过度膨胀给国家带来灾难,黄宗羲论述说:“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尤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即通过设立宰相之位抑制了君主的恣意妄为。第二,赋予学校以议政之权力,预防国家政策决绝于一人而致失误。因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学校的功能不仅在于“所以养士也”,还可以“……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学校既立,则“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也就可以达到“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这种理想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分权思想虽然是在明清两朝取消丞相这一官职的前提下而产生的,但是绝不仅仅限于对丞相这一官职的废立与否的讨论中,它更多的表达了明末清初先进士大夫阶层对封建君主集权的否定,带有一种与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分权思想相似的内涵。
(二)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现代性的产生及其表现
1.黄宗羲的“天下之法”论证了现代意义上一部真正的法律存在的正当性,即立法为民。黄宗羲认为:明末清初的法律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即这种法律既不利于百姓的生产生活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是君主专权的工具,“所谓非法之法也”.
真正的法律因该是君主为天下公利所立之法,因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意即君王是为了天下百姓而治理国家的,因而其所指定的法律必须要能够为百姓谋福祉除祸患,只有符合这一目指定的法律才是真正的为天下所共同尊奉的法律。他在《原法》中指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
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与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未尝为一己而立也“.但是现在,君王们所立的法律却仅仅是为了一己一姓的私利所服务,即”后之人王,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黄宗羲指出,这种以”一家之法“
的身份存在的法律丧失了作为”天下法“而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因此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律法,意即这种法律成为了”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种求诸于法律本身的价值而非法律的工具性价值来论证法律存在的正当性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法工具论的突破。
2.唐甄的法律理念。唐甄反对封建君主的独夫式统治,但非常重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首先,他提倡依照法律治理国家,法律应该与时俱进。唐甄在他的《潜书》中描述了法律存在的重要性,即”国中无法,虽众不一,其主可虏;军中无法,虽勇不齐,其将可禽“,”凡为国之道,善后有定制,乱制有定刑。明法不置丞相,其后孰敢言置之!“且”盖法所不及,则不可禁,法之所及,则易禁也。也就是说,法律关乎着一个国家的存亡,因此君主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并制定一部通行全国的律法,还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治理国家,不可以仅依个人的好恶来随便的役使百姓。
此外,法律还必须因时制宜,因为“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商周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盖礼之既坏,如美木积久而有蠹朽,不可以为宫室。是故圣人之兴也,随时制法,因情制礼,岂有不宜者!”唐甄进一步指出,法律并非是万世不易,它的制定必须符合百姓的需求,对于不符合百姓需求的法要懂得及时变更,即“君子行法,为从为更,何常之有!行之而民悦,则行之,从其所欲也;行之而民不悦,则不行,更其所不欲也。”其次,唐甄还认为法律应该具有普遍适用性。这就要求法律适用时不仅要消灭权贵特权的存在,还应该先拿封建官吏和富豪权贵开刀,对他们先刑、重刑、严刑。即“夫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刑乃威,威而民畏。刑于命狱,于鬻狱,于奸狱,刑乃清,清则民服。”因为“有些亲贵大臣手握权柄,执掌法政,只知‘营田园,计子孙’而‘心不在民';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狐假虎威,凌驾于法律之上,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荼毒天下;他们结成朋党,打击执法守法的贤才,横行无度。”,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君王必定会“刑先于贵,后于贱;重于贵,轻于贱;密于贵,疏于贱;决于贵,假于贱,则刑约而能威。反是,则贵必市贱,贱必附贵。是刑者,交相为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泽乎?”
二、明末清初现代性法律思想产生的原因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可知:明末清初的现代性法律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经济的发展有着内在的根本的联系。
明末清初之际我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从土地的流转关系来看,明末清初战乱不断,16世纪开始推行的永佃制将经营权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土地的高度集中又使许多农民沦为佃户,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集释》卷l0中说,明末“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所有的这些都促使农民逐步脱离土地的束缚走进手工业工厂成为雇工。
从商业的发展看,大的商帮也逐步出现。徽商、晋商、陕商三个最大商帮均形成于16世纪早期,广东、福建两个海外贸易商帮形成于16世纪中期,其余最晚不出17世纪前叶。从商人的地位来看,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商人的地位,传统的“士农工商”就业结构中商人数量不断增加。明后期弃农就商、弃儒就商、致仕就商记载屡见。
但是,由于我国长达二千年的传统封建帝制根深蒂固,资本主义萌芽的力量尚不足以摧毁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即封建君主专制。因此,摩擦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要求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明末清初的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商人横征暴敛,多加限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曾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这种平等性的,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矛盾或许就是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现代性产生的根本原因。
其次,明末清初的战乱动摇了封建专制君主的统治基础。
虽然明末众多的农民起义为清王朝的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但是清王朝以“蛮夷”的身份一统天下还是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深深思考。他们还将明朝的灭亡与明太祖废除丞相、改革官制、加强集权导致明末以锦衣卫、东、西厂为首的特务组织荼毒人民危害社稷的行为相联系,黄宗羲曾把明太祖废相看作是明代政治的首要弊端,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这些有识之士认真思考君权与民本之间的关系,使得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在批判君主专制统治的基础上超越了此前“尊君”的民本思想,主张维护‘天下公利’的法律代替维护君主个人私利的‘一家之法'.
三、对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明末清初的法律思想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这一时期产生的法律思想无疑是具有巨大的进步性的。它们反对君主专政提倡“天下公利”,反对“一家之法”提倡“天下之法”;它们还努力将皇帝拉下神坛,提倡平等。
其次,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具有无法摆脱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黄宗羲也好,唐甄也罢,他们都只是反对极端的君主政治而不是想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君主。因而,他们的法律主张从根本上来讲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维护既定的封建秩序。这与以“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为理论基础的西方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相比,具有不彻底性。
当然,考虑到中国二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和儒家纲常伦理思想的控制,结合这一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来分析,我们依然认为明末清初的法律思想较之前人具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些带有现代性的法律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吴光万斌着。《天下为主:黄宗羲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2011年版。
[3]唐甄。《潜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4]顾炎武着。《日知录集释》,(清)黄汝成集释。(清)岳麓书社版,1994版。
[5]吴承明。《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来源于网络。
[6]《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的现代性分析》苏凤格《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1期。
[7]毛泽东选集(卷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