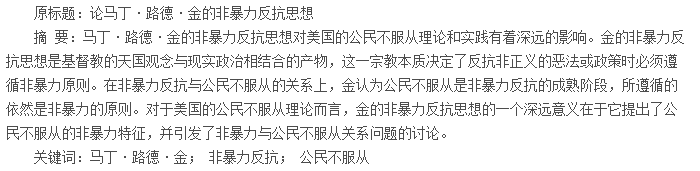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他出色的领导能力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对于美国"1964 年民权法案"的颁布功不可没,其非暴力反抗思想作为民权运动的一种主导思想在人类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特别是对美国公民不服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非暴力反抗的宗教起点。
金在《非暴力的朝圣之旅》一文中曾详细地讲述其非暴力反抗思想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梭罗是他"同非暴力反抗理论的第一次思想接触"[1]78,其后金在大量神学、哲学和政治学经典文献中辗转,直到后来接触到甘地和尼布尔( ReinholdNiebuhr) ,这一思想经历直接促成了他的非暴力反抗思想。从金的非暴力思想本身来看,他的这一朝圣之旅的主题实际上只有一个,即将基督教的天国观念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他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原因就是唯物史观不承认神的存在,尽管马克思主义使他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1]79 -83.金对甘地的赞许也是因为甘地很好地实现了这种结合。他认为"甘地是历史上第一个将耶稣爱的伦理提升为超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上而成为大规模的强大而有效的社会力量的人"[1]84.而神学家在金的朝圣之旅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芭芭拉·阿伦( Barbara Allen) 指出,沃尔特·饶申布士使金意识到"基督教的天国观念反映的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绝对命令",而尼布尔则使金不仅摆脱了"天真的乐观主义",而且偏离了"和平主义".最终,金找到了一种个人主义作为将上述两者综合起来的方法。阿伦认为,这也注定了金整个思想的宗教语境,因此,"'自我净化'就成为金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第一步"[2]97 -100.金曾经明确地指出过非暴力运动的四个阶段,即"收集事实以判定非正义是否存在; 谈判; 自我净化; 以及直接行动"[3]290.其中自我净化似乎并不是非暴力运动的出发点,但收集事实以对非正义是否存在的问题进行判定所依据的基点一定是自我净化。因为自我净化所要求的是经常性的自我评估,正如阿伦所言,"代表了自我净化观念的经常性自我评估强调了通过用卓越的道德要求调和政治正义的方式来修正非正义的个人责任。"[2]101从根本上讲,对一种既定事实的判定取决于个人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观念,自我净化要求与非正义的决裂,这构成了整个非暴力反抗的逻辑起点。因此,阿伦的观点无疑是切中肯綮的。
二、非暴力反抗的现实逻辑
首先,金的非暴力反抗思想的宗教起点决定了对善的向往和与恶的决裂是一项基本的个人义务。
正如金指出的那样,"拒绝与罪为伍正如要与善同行一样也是一种道德义务。"[4]215这就导致人们实际上处于一种服从与不服从的困境当中,服从善与反对恶同时都是一种个人义务。这种困境在现实当中可以集中地表现为服从良法与反对恶法的义务,或者说服从正义的法律与反对非正义的法律的义务。
从现实角度而言,一种非正义的现实存在无疑是不服从行为的根本动因,因此,如何区别正义与非正义的法律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金从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两方面进行了回答。金对法律的实质正义的认识依然是从宗教层面出发的,他认为良法是与道德法和上帝之法相一致的法律,反之则是恶法[4]215.种族隔离的政策或法律无疑就是一种违背上帝之法与道德法的恶法。在程序正义的意义上,一种恶法反映了多数与少数之间的不平等,因为排斥了少数的立法程序并不是真正民主的立法程序,因而恶法是多数滥用权力压迫少数的一种工具。
对于无论是违反上帝之法或道德法的法律,还是违背民主程序而制定的法律,二者都是非正义的法律,人们都不应当去服从它。
其次,如果非正义的存在是不服从的根本动因,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应对。金认为,受压迫的人们对于他们所受的压迫有三种回应,"一种方式是默许: 被压迫者屈从于命运。"[1]206默许的人们面对自身所受的压迫时往往表现得非常消极,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没有反抗的理想和能力,对于一切非正义总是逆来顺受,安于现状。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枯竭的自由",并认为这并非出路。"消极地接受一种非正义的体制就是与它合作,因而受压迫者变得与压迫者同样邪恶。"[1]207第二种方式是"诉诸身体的暴力和腐蚀的仇恨"[1]208.反抗的暴力方式遵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目的在于毁灭而不是修正,它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有害的,因为暴力会激发仇恨,瓦解友爱,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被对抗所取代,最终导致的只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因此金认为,暴力也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介于默许与暴力之间,还有第三种通往自由的方式,这便是非暴力反抗。非暴力反抗方式是对默许与暴力的调和与修正。"非暴力反抗者认同主张默许的人们而认为不应当对其对手造成身体侵犯,而作为平衡,他认同主张暴力的人们而认为罪恶必须予以反抗。他避免了前者的不反抗和后者的暴力反抗。有了非暴力反抗,任何个人与群体都不必屈从于任何非正义,也不必以暴易暴。"[1]208 -209再次,既然非暴力反抗是人们反对非正义的最佳方式,那么这种反抗方式具有哪些内容? 金指出了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必须强调非暴力反抗不是懦夫的方式,它一定要反抗。"第二,"它并不试图战胜或羞辱对手,而是赢得其友谊和理解。"第三,"攻击直接指向邪恶力量,而非碰巧为恶的人。"第四,"自愿遭受痛苦而不报复,自愿接受对手的打击而不还手。"第五,"它所要避免的不仅是外在的身体暴力,还有内在的精神暴力。"第六,"它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宇宙站在正义一边。"[1]90 -95非暴力反抗的第一点内容表明,这是介于怯懦与暴力之间的第三种选择,既不是对罪恶或非正义的屈从,也不是用暴力手段来达到根除它的目的。
非暴力反抗是一种消极反抗,之所以是消极的是因为它不诉诸身体上的暴力,其精神和热情却具有生命力。因此,这种看似消极的反抗带来的却是积极的和平。金认为,对于积极和平的追求不能满足于局部融合,如仅仅在一些学校为一些黑人学生开放,他称这种满足为象征主义或表面文章。他认为,积极和平的目的是在任何地方黑人都拥有机会,是完全融入美国生活,而且不仅满足于融合,而且要争取民主。此外,金还认为积极和平的追求应反对所谓"时间的神话",即那种认为只有时间才能解决问题的想法,因为时间并不是中立的,时间也能够成为"叛乱的和原始的社会停滞力量的同盟"[4]218 -219.
非暴力的第二点内容表明,非暴力反抗的真正目的在于唤醒人们的道德情感,而表面上的或身体上的胜利甚至是羞辱只会引起或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无法形成对非正义的共识。基于此,非暴力的第三点内容要求人们真正要反抗的不是为恶的人而是罪恶本身。金认为善与恶同时存在于人的本质当中,"人们有能力为善,也有能力做恶。……因此,非暴力反抗者从未放弃这一想法,即人类本性中有一些事情能够与善良相呼应。……所以深信这一运动以及深信非暴力和我们在南部的斗争的个人无论如何都会相信,即使是最糟糕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也能够成为一个取消隔离者。"[4]214因此,非暴力的目的并不是让一种社会力量战胜另一种社会力量,这样只会撕裂社会。而非暴力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社会团结,人们只有在共同的道德情感上形成一种具有共识的凝聚力,才会真正消除非正义的存在。
非暴力的第四点和第五点内容指出的是反抗行为所应采取的策略。遭受痛苦旨在通过一种自我牺牲而增强其道德说服的力度。在金看来,遭受痛苦本身能够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比如自愿接受牢狱之灾能够使人们相信非暴力反抗者反抗非正义和追求正义的决心,从而唤醒和赢得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同时,金指出暴力也会导致遭受痛苦,但不同的是,"暴力认为遭受痛苦能够通过造成他人的痛苦来成为一种有力的社会力量; 所以这便是我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这便是我们在暴力推动暴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暴力相信人们能够通过造成他人的痛苦而实现一些目的。非暴力认为,当人们自愿接受施予自身的暴力时遭受痛苦才变成一种有力的社会力量,以至于自我遭受痛苦处于非暴力运动的中心,以及相关个人能够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来遭受痛苦,并感到不应得的痛苦是救赎的,而且遭受痛苦可以有助于改变社会形势。"[4]214由此可见,非暴力与暴力的根本分歧便是反抗是否造成了他人的痛苦。暴力通过造成他人的痛苦而成为一种有力的社会力量,但这种社会力量造成的只是伤害和仇恨。
金曾经指出过三种不同的暴力观: 一种暴力观主张纯粹的非暴力,这种非暴力要求极严格的纪律和极大的勇气,从而在实践上更加难得。另一种暴力观主张一种合乎道德和法律的暴力,即在危险和伤害面前的自卫原则。还有一种暴力观主张把暴力视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这种暴力需要深思熟虑地组织。金指出,最后一种暴力观更加吸引人,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使反抗者最终陷入一种错误的信仰,认为暴力是唯一的出路。尽管有时这些暴力具有正当的或正义的目的,但仍不免受到谴责[5]32 -34.
金认为这种暴力观实际上建立在一种"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哲学观念之上,而他认为非暴力反抗应当"建立在目的与手段必须一致的哲学之上"[4]212.
因此,在金看来,不论目的是多么的正义,它都无法证明非正义的暴力手段的正当性。目的和手段一样纯洁的哲学所要求的必然是非暴力反抗。非暴力反抗不仅不能造成对他人的身体伤害,也应当避免精神上的暴力。金认为,要想满足这一要求,反抗者只能诉诸"爱的伦理"[4]212.人们诉诸一种宗教关怀基础上的爱的伦理,并非意味着鼓励或说服人们以一种感伤的心情去接受施予他的压迫,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和无力的屈从哲学。非暴力诉诸的是一种积极的爱,金将其称为阿迦披( agape) .金指出: "阿迦披是指对所有人的理解和救赎的善意。"[1]93
阿迦披是公平无私的,它要求人们不困囿于自身的好处,而扩展为全人类的幸福。阿迦披旨在维持和创造社会,它使人们认识到作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对任何一方的伤害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伤害。"当人们在这一层次唤起爱的时候,他爱人们不是因为他喜欢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方式呼吁他们这样,他爱人们是因为上帝爱他。"[4]213非暴力的第六点内容事实上是上述五点最终必然导致的一种信念,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讲,对于正义的信念也是前五点内容的基础。一方面,如果没有对前五点的领会和理解,正义观念很难真正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对正义的信念,人们能够坚定地选择非暴力反抗的方式就变得非常可疑。
三、非暴力反抗的激进化
尽管很多人都将马丁·路德·金视为公民不服从的样本,但金本人在概念上并没有使用公民不服从这一术语来描述或概括其思想和实践。在金的着述中可以看到,他本人并不认为公民不服从与非暴力反抗是同一回事。金认为公民不服从与非暴力反抗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涉及对基本的国家法律的蔑视。他说: "两种方式并非同义。公民不服从在其真实意义上并未被黑人用于他们的斗争。在其真实的历史形式上运用公民不服从涉及对基本的国家法律的蔑视。"[6]220与公民不服从不同,非暴力反抗并不挑战国家的根本法律和法律体系,它可能只是反抗地方的法律或政策。他说: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黑人当他在大街上游行时并不是在实践公民不服从,因为他并不挑战宪法、最高法院或国会的法令。相反,他们试图支持它们。他可能是在违反地方市政法令或州法,但这些法律与基本的国家法律相违背。"[6]221那种无视法律秩序的反抗者其出发点是个人利益,他们并没有看到自己与社会的联系,而非暴力反抗者即使在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也不会忘记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他说: "真正非社会的违法者无视法律,因为他是寻求个人好处的人。
黑人从未忘记,甚至在非正义的千斤重担下也不曾忘记,他们与大型社会相关联,他们可能阻碍的道路和他们所围困的公共建筑都为所有公民共同使用。"[6]221由此可以看出,在金看来,公民不服从与非暴力反抗的不同之处在于: 首先,二者对于基本的国家法律和法律体系的态度不同; 其次,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前者只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后者则同时强调二者,甚至偏重于义务。
更为具体的区分也可以从金所指出的非暴力反抗的个人反思过程中演绎出来。金曾经指出一个详细的非暴力反抗的主体反思程序[6]221,这一反思程序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可以理解为金对于非暴力反抗的正当性证明。从中可知,非暴力反抗所具有的一个正当理由,是一种非正义的存在,而不是个人报复与制造混乱。非暴力反抗应当首先穷尽所有的合法途径来就非正义向当局进行呼吁,而当这些合法途径无效时,非暴力反抗才会选择采取违法手段,并自愿接受惩罚,以遭受痛苦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的团结。最后,非暴力反抗的所有构思和预期都不应当脱离社会的伦理与传统,这意味着非暴力反抗不应当太过激进,其对非正义的补救之道应限制在社会大众的承受范围之内。在此,非暴力反抗的正当性证明也可以从反面成为观察公民不服从的切入点。
但是,有趣的是,金对公民不服从的态度似乎并非前后一致。在金早期的文献中,他对公民不服从的态度是相对消极的和否定的,认为公民不服从太过激进。而在后期的论述中,金又主张公民不服从是非暴力反抗的成熟阶段,认为公民不服从更符合当时的抗议活动[7]222.这个时期金的思想表现出早期所不具有的激进内容,原先所批评的公民不服从对基本法律的蔑视,此时却成为金进行抗议的得力武器。不过,金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并未使其放弃非暴力的原则。非暴力反抗可以扩大其反抗目标的范围或提升其反抗对象的层次,但反抗的手段必须仍是非暴力,这一点是不变的。
因而,发展到大众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反抗也与暴乱有着鲜明的区别[7]222.因此,公民不服从就成为非暴力从蒙哥马利这样的县域上升至国家规模时的必然结果。这也是解释金前后观念变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一方面,"蒙哥马利和阿拉巴马的公交车斗争现在已经成为历史"[1]182,经济大萧条和汽车的普及使得地方性的斗争迈向全国规模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肯尼迪的 1964 年民权法案的颁布以及《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可以作为金思想变化的一个节点。1964 年的民权法案使得种族隔离成为历史,蒙哥马利式的非暴力反抗已经收到成效,非暴力反抗的目标从种族平等开始转向更为普遍的非正义,这种非正义不再是黑人的个别现象,而是包括白人在内的所有人都面临的困境,这种非正义就是贫困问题。此时金指出,黑人对种族隔离的反抗就变成了穷人对于政府的要求[7]224 -225.
在此基础上,金指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出路是依靠"大众的非暴力行动"和"投票"[8]137.
当非暴力反抗从种族平等的目标转向更高层次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或自由时,金所依靠的非暴力反抗就需要更为激进的抗议形式,因为他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和单一种族的问题,而是更具包容性和更为复杂的全国性问题。因此,金的非暴力反抗也具备了他所指责的蔑视基本法律的公民不服从的特征,甚至金后来更多地使用革命一词而不是公民不服从或非暴力反抗。
四、余论
如果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把良心问题带入公民不服从理论的话,那么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反抗思想给公民不服从理论提出的基本问题是,非暴力是否是公民不服从的一个基本内容或特征? 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将公民不服从与非暴力联系起来。尽管他们仍然为暴力留有余地,但没有人会在暴力与公民不服从之间划上等号。关于非暴力或暴力与公民不服从的关系问题,公民不服从理论中大概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民不服从与非暴力是同义的,这一点与金的观点完全一致,同样遵循的是一种目的与手段一样纯粹的哲学立场。暴力在这种观点中没有任何的正当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公民不服从与非暴力没有直接的关系,暴力也可以是公民不服从的一种手段。这种观点遵循的是一种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哲学立场。公民不服从与非暴力或暴力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虽然暴力手段会给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证明带来伤害,因而公民不服从并不鼓励采取暴力,但在一些特殊的具体情况下,暴力可能更有助于实现目标。
公民不服从理论对于非暴力和暴力大体上是一种暧昧态度。一方面用非暴力来彰显公民不服从与革命和犯罪的区别,急于向世人表达其目的与手段的道德一致性。这派观点实际上赋予了非暴力一种价值特征,认为非暴力代表了秩序、和平和道德; 而暴力则象征着混乱、无序和伤害。另一方面,公民不服从理论又含蓄地暗示暴力与公民不服从的相容性,同时给予暴力一种工具特征,努力摒弃暴力的道德色彩而证明其有限的正当性。绝对主义的道德哲学与相对主义的实用哲学势必会带给公民不服从理论家们一种精神上的分裂和对抗,理想是纯粹的,而现实是残酷的,这样一种心理困境成为这些理论家们的一贯特征。
事实上,这种困境不能归结为公民不服从理论的不确定,而是因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向来是一件不太容易说清楚的事情。暴力可以为善,非暴力也可以做恶,哪一个更能被证明为正当呢? 一旦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角度来看,这种暧昧的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意料之外的悖谬。主张道德一致性的观点认为目的的正当性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手段的正当性应当从其内部寻找证据,在这一意义上,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导致的却是目的和手段分离。而暧昧的另一面展现的无非是手段与道德的分离,手段的正当性取决于目的的正当性,在这一点上,被指责为手段与目的不一致的态度导致的却是手段与目的的不可分割。无论如何,需要注意的是,就算是甘地和金这两位如此强调和鼓吹非暴力反抗的人物,想要将他们与革命或暴力区别开来也绝非易事。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对于英国统治的既有权威体系而言更像是革命者的准则,而金在后期也更多地使用了革命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