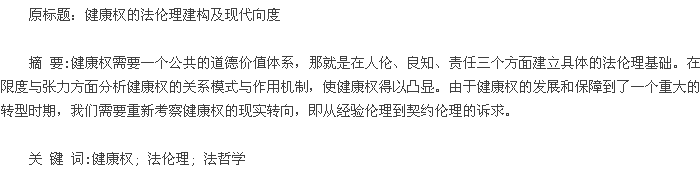
健康权是国际人权法规定的重要人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保持身体机能正常和维护健康利益的权利。《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规定: 享受最高而能获之健康标准,为人人基本权利之一,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情境各异,而分轩轾。
很明显,身心健康是公民生存和进行正常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也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对健康权的法伦理内涵进行梳理和界定,明确国家是其重要的契约主体,这对于研究健康权的现代向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健康权的法伦理基础
健康权约束了可能侵害健康的行为,这些约束被人们称为真正的道德法。公民对于健康权的要求实质上已经变成一种道德上的权利文化,这种权利文化通过世俗需求的推动而创造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追求与价值追求的和谐统一。“因为在他们所共有的道德规则、戒律概念和他们共同的人性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一致。”[1]因此,受道德影响的权利文化,倾向于将健康权稳固地植根于自然状态之中,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任何人都应享有健康权而不受限制。
同时,享有和保障健康权被视为所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个体与生俱来的一种公民美德。当然,关于公民美德,不同的理论家所想象的真实性内容各有不同。霍布斯将人的真实性等同于为了肉体生存而进行的竞争性斗争; 洛克将人的真实性等同于为了积聚财富而进行的勤勉劳动; 卢梭将人的真实性等同于原始的天真无邪和动物性的生活的自发性。
问题的关键是不论健康权表现形式如何,伦理是人们在共同的权利文化下需要彰显的本性。在这个本性中,健康权有一个公共的道德价值体系,那就是在人伦、良知、责任三个方面建立本质的、具体的正当性基础。健康权失去了其基础的位置,任何美德的源头就会显得暧昧不清。
( 一) 人伦
“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在整个世界智慧中,对人类影响最重大的是人伦。由此可见,健康权的法伦理基础在本质上必然寓于“人伦”之中。从一些表述能够看出,健康权开始构筑自身哲学大厦的根基,把人伦纳入到思考的领域。但是,健康权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作为理智的法律和真实生活道德之间的矛盾,“人伦”一时还解决不了。
可见,对健康权的研究不能完全从经验中抽象出法伦理。相反,健康权“人伦”问题的主要倾向有两个: 一是确立探究“人伦”问题的理论图景和模式; 二是自觉寻找法伦理问题形式的论证根据。这显示了健康权研究对“人伦”问题考虑的路径: 不是单独从个体的角度来思考,而是从关系的角度判断人以及自然的特性,从而为正确处理健康权的法伦理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基础。
( 二) 良知
良知指的是天赋的道德观念,孟子曰: “所不虑而知也,良知也。”以良知作为健康权的法伦理基础之一是由健康权的意义所决定的。健康权的实施和保障在意义世界上就是为了追求善的价值,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善的价值包含个体的善与社会的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来自于生活的良知。“自然理性及其形式律令一旦遇到生活的道德两难处境,就窘相毕露; 道德主体性人格的建立以此为基础,根本是极脆弱的。”[2]需要明确的是,必须弄清良知与健康权的意义联系,在逻辑关联中推进问题的深入,以求最终获得若干具有确定性的结论。
毋庸讳言,国内主导的健康权的分析框架,其实是由西方启蒙哲学发展出来的一套思想方法,这套思想方法把健康权仅仅作为法理意义的解释而忽视了伦理学的特殊属性,这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即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样的习惯去判断健康权研究的严谨与否。相反,把良知作为健康权的法伦理基础之一依循的是道德哲学的逻辑,即保持对良知的尊重,也是在理性占强势的思想背景下保持的一种自觉。
( 三) 责任
健康权的研究对于社会伦理实体的设计在于: 以它为基础的“后现代研究范式”建立的科学哲学理论,最后落实为一种能够有效地维护发展权的伦理观,当然包括有效地规范实施和保障健康权的行为,从而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那么,与责任相对立的“权利研究范式”能够建立一种科学的理论吗?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责任这种伦理实体具有根源的意义。一方面,任何个体的现实存在总是以责任为中心的; 另一方面,脱离责任的社会实践缺乏内在动力。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权利研究范式”,而在于建立责任和权利偏好基础上的共同体。
当我们进入健康权的实践环节时,也就同时进入了与社会上其他人的相互关系中,这种关系的维持以及维持的责任决定着健康权的发展和发展的快慢。人们只有拥有责任的美德,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健康权的实践活动才能持续达至完美与卓越。在此意义上,我们必须把责任作为健康权法伦理基础的必要组成部分。
二、作为经验伦理与契约伦理的健康权
经验伦理将经验从人类道德活动中区分开来,探讨经验的道德本质、起源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与经验的关系问题。经验伦理学将经验作为道德现象加以研究,着重研究经验中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从中揭示道德的发展规律。所谓契约伦理就是人们在订立、执行契约以及毁约中所表现出来的伦理性质。契约的形式必须以一定的伦理品质为基础才能实现,如诚实守信原则、责任感等。
当代法伦理学的发展,已经把关注点由经验伦理转向了契约伦理。这一转向不仅仅是研究视角的转移,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及所运用的核心范畴发生了变化,并在此变化中蕴含着健康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调整。
在现代社会,健康权作为人们要求、生活的基本保证,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性的伦理要求,是人们处理好与他人、家庭、社会等各种关系的基本保障,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具有强大的伦理功能。实施与保障健康权的主体,在敬人律己中会获得一种极大的伦理优势,这种优势会敦促其有效地把握“人性”,表现在经验伦理与契约伦理两个方面的不同。
( 一) 德性起点的不同
健康权在经验伦理方面的德性起点在于自觉不自觉地以“感性”的方法建构一切、评判一切,其目的在于实现感性对于真理的垄断。可以看出,一方面,健康权的主体毕竟是人,如果为政者缺少德性的意识,没有仁德之心,没有对个体的关爱之心,仅仅依靠制度等技术并不能保证健康权的实施。另一方面,经验伦理学对健康权的认识又并不停留在衣食温饱的生存层次,而是有着人性完善、风俗纯美的道义要求,此在孔子即所谓“教之”,在孟子即所谓“申之以孝悌之养”,在董子即所谓“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
这种要求对经验伦理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人性的社会教育固然是一端,但为政者的德性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为政者自身缺少德性,不能依据德性来研究人性,那么,健康权的保障与实施也必然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健康权的经验伦理在根本上是一种以德性的教育、完善为理想归依的教化伦理。
理性作为一种指向“优良的生活”的德性,是人们必须坚信和保持的,是契约共同体得以持续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理性意味着确定社会上所有健康活动的道德边界,规定着健康权的道德义务。契约共同体必须遵循人类社会追求“优良的生活”的合目的性,依据社会大部分成员共同选择的价值取向或共同持有的理性,其契合度越强,健康权的伦理性就表现得愈加显着。
( 二) 实践智慧的不同
健康权在经验伦理方面的表现是个体的实践智慧,而在契约伦理方面的表现是社会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就是关于对人的善与恶的真正理性的实践品质”[3]。经验伦理不仅决定了健康权会形成“好生活”的观点,而且也会使个体来审视、选择并确立最适用于“好生活”的“共同善”。如果说经验伦理的核心范畴是“好生活”的话,那么契约伦理的核心范畴就是“公正”。当我们从契约伦理学角度来研究健康权实践智慧的时候,公正范畴就不是泛指一般,而是特指公正的美德。
然而,个体的趋善性并不意味着健康实践活动一定表现为“善果”: 因为社会是健康生活中最活跃的因素,个体的经验有可能偏离“共同善”,导致偏离契约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从而远离“优良的生活”的本真。就此而言,伦理个体如何对“好生活”和“公正”达成一个平衡点,自然成为考察健康权的有效形式。
因此,“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能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前地自由”[4]。
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经验伦理的健康权,还是作为契约伦理的健康权都需要道德理论的相应指导。
正如西方德性伦理学所希望的那样,理论在实践教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道德理论对健康权的引导,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概念结构,而是需要一种理想的状态,同时在实践中使理想转化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信念、行为。
三、在法伦理建构方面的限度与张力
对健康权在法伦理方面的分析往往引导人类判别健康权的存在与非存在、善与恶,从而提出限度与张力方面的问题。显然,健康权的实现,必然涉及行为的规范与调节,许多小问题变成了社会秩序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我们需要在限度与张力方面分析健康权的关系模式与作用机制,使得健康权得以凸显。
事实上,健康权本身是伦理生态的存在,身、家、国、天下本来就是一体,而且“身”作为这一体的基础,需要不断超越现有存在状态而面向未来。在一定时空中的限度使健康权既在自身之内又在自身之外,当把这种“身”抛向“家、国、天下”的目标要求时,才完成健康权发展前途的确立。具体说来,健康权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限度。
首先,健康权“重情”的主张与情感主义虽有某种区别,特别是“情感”中本身就蕴涵了道德的先天规定,但是“重情”与情感主义也有共通之处。不可否认的是,健康权由于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特性,更多地强调“情感”的无滞碍而呈露良知,因而导致以“情”而非“理”为主体的结构。在健康权中,对情的重视超过了健康权的权利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说,对自然情感的过分放任的确会导致理性的湮灭。在健康权确立的传统中,“理”是“里子”,“情”则是“面子”,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这构成了健康权的主要内容。从“里子”“面子”互动的方面看,健康权实施保障的终极目的指向人的健康,为了更好地完成健康权利的诉求,必须自觉构建不同文化中健康权的互动机制。
其次,健康权存在功利与价值的限度。功利与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健康权确立的变革。同样,在健康权的实施与保障领域中还存在着功利与价值的界分,并且对功利与价值的范围和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限定。从个体本位上看来,健康权只是功利与价值中一个并不显眼的组成部分,由生命健康权、心理健康权、发展健康权所构成,其核心是这些权利的相互联系,其主要作用是使功利与价值的平衡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虽然健康权对功利与价值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但把个人看待健康权的选择作为重要依据,忽视了个体感受健康权自主性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健康权得以确立的历史可以看作规则的历史。“它意味着每一种具体权力或者基于具体同意或者基于每一个权能组织全体成员的契约,只服从同意契约基础上产生的规则。”[5]而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 是什么导致了对规则的辩护呢? 即使保障健康权的规则已经成为人们日常道德生活的一个基本范畴,也并不意味着规则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健康权所依据的原型。因此,健康权的背后必然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规则伦理原因。在这个原因的具体回答上,我们需要在作为法律的规则与作为伦理的规则之间的“相似”中寻求连接的张力。
( 一) 规则的意义
自《世界卫生组织宪章》首次倡导对健康权保障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对健康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对健康权的促进和保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对于如何做好保障健康权,其方法各异。作为规则的意义,关注道德底线,不希望看到法律规则出现“例外”,也是保障健康权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任何权利的运转无法凭借一个或几个人就能实现,而是需要一个规则,由此就意味着必然存在规则的意义。
对于健康权的保障来说,规则的意义表现在国家与个体相互遵守各自的规范,按照契约精神调节各自的行为。对于作为健康权保障的主体———国家来说,规则一旦确立,便成为一种价值标准,不仅成为对个体行为,更是对国家行为进行评价的尺度。
( 二) 伦理精神
目前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地把健康权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虽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但这里所规定的显然不能涵盖健康权的所有内容。“精神显现为映现在它们中的客观普遍性,显现为必然性中的理性东西的力量。”[6]因此,作为健康权的保障来说,伦理精神同其他所有合理性问题、合法性问题迥异,是健康权在伦理世界中得到实现、得到具体贯彻的基石。每一个权利都有它的伦理精神,不同权利有不同的伦理精神。伦理精神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道德风范,展示了人类道德发展的趋势。健康权也有着特定的伦理精神,即契约是健康权中各要素主体的连接方式和纽带,契约是健康权中最独特的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
四、健康权的现代向度: 从经验到契约的过渡
今天,健康权的发展和保障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各种困难,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断档”现象,这表明健康权的发展和保障进展到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作为目前我国权利领域中备受关注的“法伦理”现象,不仅仅只是一个纯粹的权利“保障”的问题,对健康权而言,它实际上更关涉到影响更为深远的“发展”问题,即国家、社会、家庭,尤其是国家如何诠释健康权的核心伦理条件———发展的价值。我们认为,健康权作为在我国现有权利结构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形态,到了必须认真看待和处理其法伦理现代向度的时候了,这将有助于厘清我国健康权尤其是弱势群体健康权的发展问题。
由于经验只是对人们道德层面上的约束,当人们的情感越过理性的时候,健康权的发展就成了问题。
同时,由于经验本身缺乏一个公共的权威使人们去自觉遵从,因此当人们的情感战胜理性的时候,契约便变成了一张空文。实际上,当人们用经验来发展健康权的时候,那只能是权利的互相转让,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次契约行为。
但是,一次的契约行为并没有形成强大的人文力,因此健康权的发展并不会得到真正保证,人们并未从根本上摆脱经验状态。所以,便需要一种使大家敬畏并指导其行动以谋求健康权发展的契约,于是生活在经验状态下的人们把权力和力量托付给国家并予以认同和维护。也就是说,经验状态下的每一个主体都相互订立契约并放弃管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把它授予代表理性精神的实体———国家,每一个人都使自由意志服从于理性意志,使自己的判断服从于契约的人文力。这样,健康权的发展就统一在契约背景下的主体———国家。
虽然契约是从一个虚构的自然状态出发而建构的内容,但是契约开启了道德哲学对健康权的反思。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契约极力强调理性,因为只有理性才是最重要的,在理性的基础上确立健康权安身立命的基础。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健康水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依然要立足于契约,并对这些在人类发展中不断追求的价值和理念进行维护,当然这种认同和维护是建立在契约认同的基础之上的。
健康权的实现不是自发的,为此个体与国家的契约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没有国家主动地协助和积极地干预,健康权要获得真正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定程度上,公民健康权的实现水平取决于国家契约的实践。为实现公民的健康权,国家须承担契约伦理,即尊重的契约和实现的契约。
正是通过“尊重的契约”的社会镜像,给现代人一种道德哲学的启迪: 契约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是解决健康权现实性矛盾的最好契机,也是铸造新的制度范式的智慧。可以断言,就健康权的发展而言,契约伦理意味着人类的生活智慧进入现代性的特殊时期。“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息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行为选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尊重的契约,对传统经验伦理的结构有着震荡和颠覆作用。对于健康权的现代性而言,从经验向契约的转向,关涉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性价值、人的权利等方面,因而它既是一个尊重的契约转换过程,也是围绕人的问题而萌发的现代性。
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实现的契约”是国家个体的合理性互动。如果说,尊重的契约受到解决道德问题的努力所直接驱动,那么我们可以说,实现的契约凸显一定的秩序背景和某种伦理预设,或者说是特定的伦理状态下所产生的,不能脱离道德空间和秩序状态的框架去谈论纯粹的健康权发展。因此,对健康权现代向度的探讨实际上就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域: 在社会转型期,我们所要面对的健康权的“实现的契约”是怎样的? 如何进行国家的道德意识或心态调适,以达至个体与国家、特殊性与普遍性同一的伦理精神建构? 因而,现阶段的真实困境不是所谓对于健康权的漠视,而是缺乏一种从根本上可以整合各种伦理元素和伦理资源的“实现的契约”。
在法伦理学的研究中,健康权的现代向度是应然命题,不是实然命题。“在多元化社会中,各种同一的世界观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早已分崩离析。”[8]当然,契约同样不可被生硬地理解成“产生”“创生”,而与国家的选择息息相关。这意味着契约呈现时,不仅为健康权的发展培养和准备了一批具有伦理精神的经营者,同时也为他们努力提供永不满足的内在驱动力,在较大程度上超越了个体的经验需求,超越了国家的实用性、功利性目的,他们所要满足的是人的长期的精神性需求。
在我国现阶段,国家对健康权的实施与保障常常局限在微观层面的展开,需要国家行使权力干预公民健康权的实现过程,或采取措施鼓励、支持甚至直接参与对国民健康权的保护,以具体行动发展健康权。契约是道德上的应然,或者说是一种价值上的赋予。国家若能够尽其性,超越经验,健康权的发展就选择了一种高尚的德性———契约。
结语
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考察健康权的现实转向。在法治文明的现代社会,健康权的表现如此之多,而健康权的正当性取决于其与契约伦理的紧密联系程度。
这其中,弘扬伦理精神、信奉契约伦理是构建当代中国健康权的法制观念、立法形式、法律模式、动力权衡和资源配置等道德哲学的最佳选择。健康权以伦理为基础,从而获得了正当性,社会对健康权的重视,从而推动了从经验伦理观转向契约伦理观的诉求。健康权的伦理基础发生了变迁,健康权也必然要发生变化。无论是从道德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探求契约与健康权的正当性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就是健康权现代向度论证之真谛。
参考文献:
[1][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德性之后[M]. 龚群,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7.
[2]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绪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88: 169.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20.
[4][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23.
[5][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 迈向回应型法[M]. 张志铭,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8—69.
[6][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 264.
[7][美]罗纳德·H·科斯. 制度、契约与组织[M]. 刘刚,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5.
[8][德]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M].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