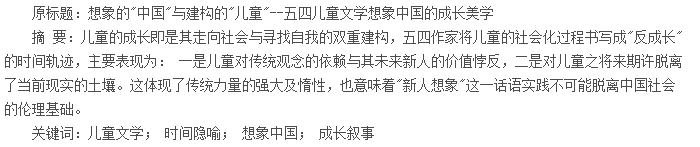
一直以来,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天地,没有很好地予以区别、辩证与融通。"成长"母题恰恰具有缝合两种文化板块的功能,它架起了一个贯通期间的文化纽带。曹文轩将"成长小说"与"少年小说"混用,他认为"成长小说"的命名将会给儿童文学带来一个新的天地,并且它的存在,会使其他门类更加明确自己,因为自己永远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而看到自己的[1].
在这里,曹文轩肯定成长之于儿童的变化,在时间的变动中审视和认识自己。通过时间视角审视儿童的成长轨迹,可以图示儿童与社会文化整体的关联,进而开掘儿童反成长的中国根源,由此实现与时代话语、国家话语的对接。
一 社会化演进与"反成长"的儿童文化心理
儿童主体的命运关联着国家的走向,也表征了中国形象的生命状态。通过观照儿童的成长轨迹,五四知识分子呈示了"儿童形象"与"中国形象"的深刻关联,以及儿童向国家认同融合的话语实践,体现了他们想象中国的独特眼光,反映了儿童文学研究中一种不无策略性而又关乎其本体的学术意识。首先,儿童作为"人"成长的起始阶段,这一阶段潜在地表征了人的基本生命形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用"成长"的视野来关注,能在一个时间进程体系中探究人的发生、发展脉络。其次,"成长"命题还是检视"儿童-成人"的社会角色与社会文化之间不可或缺的思想方法,它呈现出成人与儿童主体认同的社会根源,亦提示着社会文化建构主体造就代际间角色分工的事实。再者,儿童的成长关联着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以成长的角度去探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主体构成及文化形态是中国想象的核心要义。
对于儿童而言,其成长的过程是人身心得以完善的体现,是其自然性与社会性由原初的析离状态逐步走向融合的阶段。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与互动是儿童成长的常态,两者的此消彼长表征了儿童成长的一般轨迹。然而,在儿童文学界的诸多研究者过分强调儿童的"自然性",而盲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化"特征。确实,在儿童文学的"儿童化"或"成人化"的优劣取舍问题上,学界多有分歧,这也影响了儿童文学"想象中国"问题的思考。1980 年代班马提出了"儿童反儿童化"这一看似充满了悖论的观点,在他看来,过分强调儿童情趣,实际是忽略儿童"极欲摆脱童年而向往成年的心情"[2]113,忽略他们"暗暗准备着走向未来的社会实践,从而渴求认识现实生活的那种强烈愿望"[2]114.这一观点深刻地契合儿童成长的必然规律,那些试图将儿童与成人社会隔离开来的观点势必会造成儿童的自我封闭。
"成长"是儿童由"儿童世界"向"成人世界"的转变过程,那么成长主体、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就是成长的 3 个要素,其中"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构成了"成长叙事"的两极,儿童就是在这两极的互动中完成自己的社会化过程。因而,研究儿童的成长问题,我们可以作如下两方面的梳理与考察: 一是通过时间阶段的比较,纵向梳理儿童伴随历史发展变化而呈现出的嬗变历程; 二是在考察儿童嬗变轨迹的基础上,横向考究生成这种变化的内外根由。毋庸置疑,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父权思想和成人声音,儿童的地位受到了长期的压制,对于儿童的成长关注非常薄弱,这也成为五四儿童文学先驱极力批判的地方。
皮亚杰指出,社会化是儿童由自然人转换成社会人的过程。成长既是一个社会化的历史,也是一个个人化的过程,并在这一互动中平衡发展,儿童的成长即为其走向社会与寻找自我的双重建构。冰心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的主人公意识到儿童社会化的成长蜕变,在儿童自足阶段,"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3]124,但当他融入成人社会的时候,"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成了问题,满了问题"[3]124,前后两个阶段的情形大相径庭。从现在与过去的对照可以窥见儿童社会化所滋生的诸多问题,这些社会化的成长冲击着儿童相对稚嫩的精神王国,也给他们带来不少困惑,"不想问题便罢,不提出问题便罢,一旦觉悟过来,便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3]124.
对于儿童而言,"烦恼"是其成长中的必然现象。
生活于自足世界之中的儿童是很难想见的,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遭遇社会。社会会让儿童脱离其原有的精神世界,逐渐认识自我及与他人的复杂关系。
解读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不难发现: 上述成长的烦恼较为缺乏,儿童成长缺失其作为"人"而存在的主体价值。换言之,儿童人格的内在成长和自我主体意识较为薄弱,呈现出一种"反成长"的精神轨迹。所谓"反成长"是指儿童的主体意识无法在时间发展中贯彻,或中断、或倒退,在压制中呈现出一种错位的成长态势。以冰心的小说《庄鸿的姊姊》为例,庄鸿和姊姊很小就失去了父母,跟随祖母和叔叔一起生活,两人都在一所高等小学读书。尤其是姊姊,"她们学校里的教员,没有一个不夸她的,都说像她这样的材质,这样的志气,前途是不可限量的"[4]76.而且姊姊也自命不凡,私下里对"我"说: "我们两个人将来必要做点事业,替社会谋幸福,替祖国争光荣。你不要看我是个女子,我想我将来的成就,未必在你之下。"[4]76应该说,冰心刻画的这个儿童有着现代意识,与其他儿童也拉开了距离,是一个独异的儿童形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眼中的叛逆者,却以死亡的方式终结了其成长历程。深究其因,她依然无法摆脱来自社会与家庭所施加的重压。由于"中交票"大跌,叔叔的薪水无力支撑整个家庭,尽管庄鸿的姊姊是块读书料,但祖母却说: "一个姑娘家,要那么大的学问做什么? 又不像你们男孩子,将来可以做官,自然必须念书的。"[4]76姊姊辍学后,她非常失落和无助,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庄鸿身上。就在庄鸿到外地求学时,姊姊心无所依,在无所寄托的压抑、绝望中死去。"死"与"生"既是时间段中的两极,同时又对立统一、密不可分。探讨死亡问题虽名为谈死,实则论生,或毋宁说它是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的一种深化、延续和扩展。这其中明显地渗透了现世的生命关怀,同时不放弃对现世人终极意识的叩问。因而"知死"实为"知生",由生与死生成的文化意义及生死之间的转化关联是时间意识重要的哲学内涵。在这里,冰心绝不是简单的悲剧人生体验,而是在"死"的"临界处境"中反观"生"的存在困境,这种"临界处境"是人面对痛苦、绝境和死亡时的一种意识状况。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存在处境才使人们有体己的震惊,因为"在我们的实存的边缘上被感受到、被体验到、被思维了的处境,把实存的内在矛盾、二律背反统统展现出来了"[5].可以说,这种"临界处境"就是时间的重要中介点,处于这一关节点上的主体面临着重大的生命转折,其思维意识在这一特殊瞬间、场景中被释放和播撒。庄鸿的姊姊在弥留之际陷入虚无,她没有任何的反抗,默默地接受了一切的安排。
"在死亡的感知中,个人逃脱了单调而平均化的生命,实现了自我发现; 在死亡缓慢和半隐半现的逼近过程中,沉闷的共性生命变成了某种个体性生命。"[6]换言之,主体在逼近自己死亡之际,能对生有相对深刻的思考。然而,这种死亡临界点上"生"的发现对于庄鸿的姊姊来说没有太多意义,最多不过是本能的反应或是加快其死亡到来的心理要素罢了。尽管在小说的最后,冰心借庄鸿之口质问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 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 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7]
但是,这种质问并非主体自觉的体现,而是作家跳出文本而阐发的观念。
二 时间思维与盲视现在的成长模态
对于儿童而言,成长意味着与过去告别。在自我意识的寻找中,儿童启悟了新的认知,其身心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成人眼中的"异常"和"叛逆"恰是儿童成长中的自然表现。除了书写儿童过早夭亡的身体死亡之外,五四儿童文学中还大量出现儿童精神死亡的现象,这是"反成长"的重要表现。精神死亡的一个共同点是虚无,它是肉体存活精神却已死亡的本质表现。由于成人文化和儿童根性的合谋,很多五四儿童陷入了精神危机或精神死亡的状态之中。反抗思想的倒退、现代思想的退场、意义的虚无等均是其精神死亡的主要表现。这种反成长的时间轨迹背后潜藏着诸多文化奥秘: 五四儿童用"折回"或"远眺"的方式切断了他们"直面"现实的路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中,"过去"的时间是属于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是"现在"的人辉煌的"过去"和"现在"既得地位的根源,是他们"现在"和"将来"应沿袭的思想基石; 而"将来"的时间则是"神"许诺的未来前路,为消弭痛苦和不幸,可以进行超脱现实的廉价想象。强调过去时间的"圣贤之治"和将来时间的"黄金世界"都是对"现在"时间中人生困境的精神逃逸,因为"过去"时间和"将来"时间的不在场性,被方便地为怯懦者提供时间归所。于是,我们可以沿此理路来洞悉五四儿童文学时间意识的内涵。
一是通过描摹儿童持存的"过去"心理来探究其内在的精神困境。由于历史的惯性,儿童无法排斥传统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思维态势,牵引着他们理性的价值判定和行为意向。
我们可以在二儿( 《白旗子》) 、阿凤( 《阿凤》) 、国枢( 《两个小学生》) 、义儿( 《义儿》) 、小小( 《寂寞》) 、阿美( 《阿美》) 、小全( 《红肿的手》) 等儿童身上发现他们依然持存着过去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这是他们永劫不复的思想桎梏。由于无法辨析和区别"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他们误将过去的强势话语等同于现在的认同和判定。换言之,当他们难以找到现实行动的依据时,过去观念中的"通行"话语就被援用,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儿童会不约而同地将自我的救赎意识投向过去呢? 对此,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的一番话也许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过去的记忆源于现在的社会压力和痛苦境遇,对"过去"的回忆是通过"现在"而得以重构的。"过去"和"现在"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是确定的,而"现在"是处于一个正在运作的不确定当中。"因为约束只有运作才能被感觉到,而根据约束的定义,过去的约束已不再发挥效力,所以,昨日社会里最痛苦的方面已然被忘却了。"[8]
无疑,一个没有约束力和消解了痛苦的"过去"必定被人们长久记忆,而在"过去"的温情记忆中,个人现时所遭受的困境却被忘却。这也能很好地解释国人"好古"、"信古"、"尊古"的心理倾向。在这里,儿童对于"过去"的依赖心理有自愿和被迫之别,但不管哪种,都凸显了作为国家未来主体的儿童在面对现实的困境时的精神状态。应该说,要使儿童摆脱做奴隶的命运,就必须切断他们对"过去"太依赖的心理,站在"现在"的时间点上思考人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五四儿童文学先驱的启蒙工程的起点问题之一。
二是通过叙述儿童的"将来"向往来透析其虚空的精神质素。儿童对于"将来"的期许应建构在现实的土壤里,否则有可能会陷入虚幻的梦想之中。五四儿童作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曲终奏雅"和"大团圆"的"将来神话"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们看来,这种"瞒"和"骗"的时间神话只能造成让人逃避现实境域的恶果。在《除夕的梦》一文中,冰心阐释了这一实质。在篇首,冰心写道: "我和一个活泼勇敢的女儿,在梦中建立了一个未来的世界。"[9]131这个未来的世界给予人一种庄严的光明,然而,"一阵罡风吹了来,一切镜像都消灭了,人声近了,似乎无路可走,无家可归"[9]131.于是,"我"和女儿用自杀的方式彰明对于"未来黄金世界"的不信任,"将来的黄金世界在哪里? 创造的精神在哪里? 奋斗的手腕在哪里,牺牲的勇气又在哪里"[9]166,破除"未来黄金世界"的梦幻体现了冰心执着现在的时间意识。锦明的《小岔儿的世界》也是一例。小岔儿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有着超越现实苦痛的童心,他的心灵世界纯净无尘。当处于生活底层的成人惧怕寒冬时,他却渴望寒冬的到来,因为寒冬是其枯燥无味生活的亮色; 他不懂得世俗社会的交换规则,用洋糖换了自己喜欢的卡片; 路上学堂同龄人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无法理解他们的冷眼和悲悯; 当爷爷不允许他再出门做买卖时,他却用将来"我可是还得进城上学"[10]予以回驳。小岔儿的这句童言无忌的话中隐藏着他所不能预料的遐想。当儿童在现实中无法找到他们的期待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将其视野撤离现在的时域,期待在将来的梦幻中寻找自己的栖息之所,以此来慰藉现实的痛苦。于是,当现实的重压一步步朝向这些儿童时,翠儿( 《最后的安息》) 、小顺( 《湖畔儿语》) 、六一姊( 《六一姊》) 、霍君素( 《纪梦》) 、陆方( 《陆方的梦》) 等借助"将来"这一"心造的幻影"来作短暂的疗伤。然而,这种廉价的想象并非永久的避难所,最终他们还是难以逃脱现实的重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