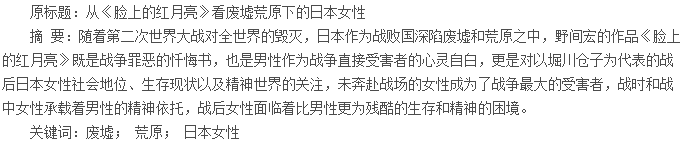
野间宏是日本"战后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征入伍,辗转于中国和东南亚,由于自身的战争经历,他的创作题材主要是战争和战后日本社会。《脸上的红月亮》是野间宏初期创作的一部具有浓重反战意味的作品,战后的男主人公北山年夫和女主人公堀川仓子从相识到暧昧再到无法正视战争带来的阴影,最终分道扬镳,战争不仅仅给作为战争直接参与者的男性带来了伤害,同样也让的未奔赴战场的广大日本女性承担着沉重的伤害。
一、废墟下,女性成为男性的精神依托
由于战争是力量的较量、身体的对抗,因此奔赴战场的都是以年富力强的男性为主的群体,女性由于生理上的局限性,未能直接参与战争,除了在后方为前线战士提供必要的物资等支持,未奔赴战场的女性还以臆想的"他者"姿态来到了战场,成为了男性的精神依托,当男性在战争中精神无处安放,北山年夫在战场上做出这样的感慨:"除了母亲和他死去的恋人,没有一个是真心爱他的。"[1](P4)废墟之下,女性无疑成为了男性情感的支撑,这种精神寄托主要表现在对母亲的原始依恋以及对恋人的温暖需要。
1.对母亲的原始依恋
"入伍当兵,始知娘亲。"[1](P4)北山年夫曾这样表达战争中对母亲的思念,战争所带给男性的不安全感以及战争中的残忍场面,使得男性萌发了对母亲女性的原始依恋,如同回到襁褓之中,只有在母亲的怀抱中才有十足的安全感和被保护的感觉,"在战场上,肯把自己的口粮分给别人的,除了母亲,又有谁能做到呢?"[1](P12)母爱的无私和强大,使得北山年夫在残酷的战场上对母亲格外的思念。
同时,"从传统观念来看,作为母亲的妇女对男人代表着一种归属地……此外,男人还把母亲妇女作为一种包装物,以便帮助他对事物进行限定。"[2](P377)不安和居无定所的战争生活使男性对"归属地"有着热切的向往,由此转嫁为对母亲的原始依恋,同时,也代表着在战争中战士们对自己归属地祖国的一种向往和思念。"他挨过皮靴底的打,用冰冷的手,摸着又紫又肿的脸颊,不禁想起母亲轻柔的手",[1](P4)母亲的手此刻是轻柔的,寓意着北山对母亲和以"母亲"为象征的祖国的温暖思念,是一种停留在记忆中的原始的美好的依恋,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遐想。
2.对恋人的温暖需要
除去战争中对母亲的原始依恋以外,男性更多的是将精神寄托于对恋人的思念上。战场上的北山年夫对已故的恋人"明知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还需要她的爱。"[1](P12)战后的北山"他觉得需要堀川仓子。"[1](P17)北山对已故的恋人和堀川仓子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身体以及情感依附的需求,是一种后悔莫及和同病相怜的感性认知,并非真正的平等爱恋,"仓子的那种美,和北山苦痛的内心十分合拍".[1](P2)因为这种合拍,使得误认为两者的精神保持一致性,这就是爱恋,事实上并非如此,北山仅仅从仓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战后遍体鳞伤的影子形象,是对自己镜像的一种重新认知,所以北山对仓子的感情不是真实的爱恋,更多的是对女性恋人精神慰藉的一种需要。
"北山年夫有过一个恋人,但从没打心眼里爱过她。或者说她是北山从前失去的另一个恋人的替身罢了。"[1](P2)起初赴战场之前对自己的恋人,北山的态度是"拿她权且充当自己的意中人,跟她不过是虚应故事".[1](P4)后来入伍之后,"当了新兵整日价吃苦受难,日久天长终于懂得了爱情的可贵".[1](P4)北山真的在战争中顿悟了爱情吗?事实上,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北山以为自己真正懂得了爱情是有前提的,是在自己当新兵时候的"吃苦受难"使得他明白了爱情的可贵,北山所谓的爱情的可贵只是战争中男性对女性恋人的精神依赖,女性恋人在此刻是一个避风港,是一种"天使"的形象,是一个可以带领男性脱离战争苦难的理想女神的化身。所以,北山曾描述"死去的情人"的手是一双湿软的手。"他意念中紧紧搂抱着她的身影,一面忍受战斗的痛苦。"[1](P4)此刻的爱恋,是一种对女性的温暖港湾的需求,是一种对安静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意念。
由此来看,以母亲和恋人形象出现的女性,尽管成为了战争中以及战后男性的精神支撑,却仍然消磨不掉女性"他者"的地位,女性无法摆脱自身的生理以及心理的特殊性,在战争的废墟上女性仅仅成为了"被需要".
二、荒原中,女性自我的无处安放
战时的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的精神依托,同时,作为女性本身,战争也给女性带来了不可修复的伤痛,依附于男性生存的日本女性,当面对战争带来的灾难,女性表现出了自我的无处安放、所依附对象的消失以及面临着生存和精神的困境,再一次将女性推到了寂寞的荒原之中。
1.生存的绝境
《日本女性史》中曾这样描述战争时期的日本女性:"家里做了多年的买卖,却被迫歇业和强制'转业'.丈夫和儿子大多被征用或拉入部队。而且粮食的情形从一九三九年起显然恶化。几百人拿着锅子在平民食堂排队领粮,不久连平民食堂都没有了。"[3](P260)这是对日本战时社会的真实再现,这也是野间宏笔下主人公们所生活的时期,面对生存的困境,堀川仓子走上了一条"靠卖家当来糊口"的道路,[1](P9)这条道路不被社会、法律所允许,却也是女性为了生存无可奈何的选择,因此堀川仓子"脸上总好似有些愁眉不展的样子".[1](P1)在日本战后全国上下严峻的生存环境下,女性生存空间较之男性的生存空间则会显得更加狭窄,日本男性大多都被征兵,男性作为复员的战士,日本社会虽然无法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蚊帐""军用枕头套""儿童鞋"这些物品的发放,也为战后男性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的微弱保障。女性的生存状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过不了多久,就该糊不上口了",[1](P21)战后男性的复员,工作岗位的归还和再分配,使得"北山意识到,在战败的艰难时世里,仓子终究会生活不下去的".[1](P21)因此,"在她宽阔而白皙的前额和富有表情的薄嘴唇上,不时流露出一种痛苦的神情。"[1](P1)这种痛苦是战争带来的,是战争这个主导因素将女性推向了生存的绝境之地。
2.精神的困境
日本女性不仅陷入到战争所带来的生存的绝境中,同时还要面临精神的困境。井上清在《日本女性史》的序言中针对日本女性的社会认知时说:"'女人也是人',这是简单明了的事实,可是至今还有不少日本人不甚理解……他们说什么'女人到底是女人'和'女人只是管家婆';换句话说,就是把妇女看成男人的附属品,并且是那样对待她们。""仓子把自己的心情完全摆在脸上,这在日本女人中也是很少见的。"[3](P2)可见,女性在日本的社会连表达自己心情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仅仅以男性的附属品的身份存在着。
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给予了男性情感上的慰藉,"仓子的面孔,对北山那颗破碎的心来说,既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同时又给他带来了苦恼".[1](P2)再来看看男性对待附属品的态度,面对战争带来的女性的生存困境,"而我对于她的痛苦,也是爱莫能助".[1](P20)男性在此刻表现出来的是无可奈何;面对女性的精神无处安放,"北山先生,你看,我该结婚么?""当然,我看还是结婚好。""是吗?"[1](P20)男性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责任的逃避,最终女性所想要依附的对象无情地将自己推向寂寞的荒原之中,女性情感最终无处依附,日本战后的女性终将会像堀川仓子一样"身子愈来愈小,终于失去生命力,像粉屑尘埃一般,不知飘到何处……"[1](P21)故事的最后,女性以落寞的姿态渐行渐远,堀川仓子望着北川,回复的只是"再见吧!""他看见仓子在窗外朝车厢里找他,她留在月台上,离自己越来越远".[1](P23)女性最终被抛弃在月台上,这一情节的细致的表述表现出战争所带给女性的伤害将被遗忘在历史当中,无奈只好"脸上浮出一丝痛苦的微笑".[1](P23)这种笑是对社会的一种控诉,更是对战争的一种沉重的反抗。
使堀川仓子为代表的日本女性陷入精神困境的还有日本的传统观念,堀川仓子与汤上由子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但是堀川仓子的神情痛苦、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和汤上由子的性格开朗、心胸坦荡、无拘无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去个人与生俱来的性格,更多的差异性来自于汤上由子的丈夫死于殉国,然而堀川仓子的丈夫则是"病死在战场上的".[1](P13)众所周知,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所谓的"英灵"都是阵亡的日本军人,病死的堀川仓子的丈夫未居其列,同样作为战士的妻子,不同的死亡模式却也带来了不同层次的精神折磨,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对战争的一种责备,更是对日本传统观念的一种质疑。
日本作为侵略者,同时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带给日本女性的不一样的伤害和更加沉重的负担,堀川仓子脸上的小斑点既是女性岁月的象征,也是战争消磨了女性青春的鉴证,同时也代表着战争所带给女性的精神伤害,不仅要以女性的姿态抚慰男性的创伤,同时还要自舔伤口,最终女性不得不存活在战后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中和死气沉沉寂寥冷漠的荒原之上。
参考文献:
[1]王向远,亓华。脸上的红月亮:废墟荒原小说[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法〕露丝·依利格瑞。性别差异[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日〕井上清。周锡卿。日本女性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8.
[4]〔日〕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