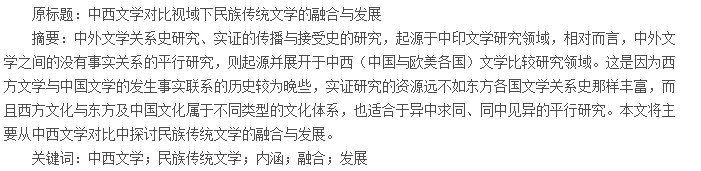
原标题:赵树理文学与东方化文体初探
从人类社会活动角度来看,文学确实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中国文学在历代都起着重要的教化功能,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学除了与政治历史有关,还有着地域性,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要说随着历史“进步”和“发展”,东方最终会变成西方,中国会完全成为美国,那是无稽之谈。中国文学不被完全西方化,中国文学的核心精神也一直存在。这就是东方文学研究的价值,即背后的东方文明,那个深远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的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中国的东方化文学的根本。不容乐观的是,当代大部分作家即使在写乡村和农民,其目标也是达到西方的“文明”标准,甚至要求完全抛弃东方传统,只要感觉到非西方的东西,就不假思索地否定,或者千方百计找到其“反动”的痕迹,加上否定性的标记,给接受者负面的导向。这些标志都能在文本中发现,那或者是明显的情绪表达,或者是隐蔽的情感流露。在此全面“向西”的时代,中国文学的东方化能不能实现? 或者能不能发现?
本文重点分析赵树理文学的传统特征之下的现代意识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赵树理的叙事具有鲜明的传统特征,又有着隐含的现代意识,他有意识地吸收了很多中国传统文艺的手法,包括话本、评书和戏曲等,叙事角度也类似中国古典全知叙事,与意义层面的中国乡村伦理内核、现代特色的整体教育意识等相结合,都意味着赵树理所有叙事创新的努力都以东方化的现代新农村为目标。
一、话语模式:由作者到说书人 由读者到听众
从话语模式来看,“五四”以来在文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直是欧化语言,1930 年前后的赵树理也深受影响。后来赵树理之所以从早期的欧化式创作转向非常传统化的形式,是因为农民与新文学的隔膜和疏离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农民的识字能力决定了他们没有阅读能力,只有听的兴趣。
所以赵树理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可说性的具象式的语言,而非抽象性的抒情化语言。读其小说,就像是农民闲话家常,他不是在“写”给农民,而是要“说”给农民。这种可说性的语言却又不是原生态的山西农村的方言,而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把知识分子的话语“翻译”成农民的话,“把不必要的字、词、句尽量删去,不连贯的地方补起来。以说话为基础,把它修理得比说话更准确、鲜明、生动”.[1]到了晌午,饼也烙成了,人也都来了,有个社首叫小毛的,先给大家派烙饼---修德堂东家李如珍是村长又是社首,李春喜是教员又是事主,照例是两份,其余凡是顶两个名目的也都照例是两份,只有一个名目的照例是一份。[2]不过也有不同,像老宋,他虽然也是村警兼庙管,却照例又只能得一份。[3]小毛自己虽是一份,可是村长照例只吃一碗鸡蛋炒过的,其余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4]照例还得余三两份,因为怕半路来了什么照例该吃空份子的人。
( 小句标号为笔者所加,下同)这是《李家庄的变迁》开始时地主为了抢夺铁锁的财产,在庙里开会时分派烙饼的描写,把繁琐的议事分派烙饼的事情写得清晰明朗,句子不长,而且大都是主谓式的结构,每一句话都有直接陈述事实,[1]句中关于李如珍和李春喜的介绍采用“是……又是……”的结构,既简洁清晰又口语化,不同于书面语“既是……又是……”或“是……的同时,还是……”等,赵树理在这里只用了一个关联词“又”,清楚易懂。而且不到两百字的叙事片断居然连续八次使用“照例”这个词语,这在文学创作中是极力避免的,因为从“五四”式欧化创作来看,词语的重复意味着文采的贫乏; 但在农村的口头说话中却不避讳重复啰嗦,只求意思清楚,而且一再的重复达到实用目的的同时,也使读者在听的时候对分派烙饼这个“例”印象深刻,隐含着嘲讽的修辞效果。这当然不是纯粹的农民语言,农民无法用如此简短的语言把一件复杂的事交代得如此清楚,赵树理在农民语言的基础上进行了删削剪裁,使其通俗化的同时更加简洁干净、清晰易懂,同时又根据农民说话的特征及习惯对书面语进行修正: “‘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 ’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
《李有才板话》在传统化方面相当有典型特色,除了像《小二黑结婚》从地方戏曲中吸收塑造人物和讲故事的方法,还大量采取了民间的快板。
先看全篇的开始:[1]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2]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3]他只是一身一口,没有家眷。[4]他常好说两句开心话,说是“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5]村东头的老槐树底有一孔土窑还有三亩地,是他爹给留下的,后来把地押给阎恒元,土窑就成了他的全部产业。
这个片断是赵村理一贯的直入主题,不会像西化小说先来段风景描写,很有话本小说的特色。
此段[1]到[3]句交待了李有才的基本情况,[1]中的“气不死”与[4]句类似,特别能体现他的比较有韧性的性格。接着文本又交待了李有才的性格和另一种价值: “在老槐树底,李有才是大家欢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饭时候,没有他就不热闹。
他会说开心话,虽是几句平常话,从他口里说出来就能引得大家笑个不休。他还有个特别本领是编歌子,不论村里发生件什么事,有个什么特别人,他都能编一大套,念起来特别顺口。这种歌,在阎家山一带叫’圪溜嘴‘,官话叫’快板‘.”就是说,李有才的板话加速了事件的传播。下面看段李有才的“板话”是如何达到这一效果的: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版,刻个大名片,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这是描述地主阎恒元的快板,极其快捷地说出了这个地方的主要特点和劣迹。这是最有亲和力的民间话语,最易在缺乏文化教育的民间流传,因为它类似行吟诗人的口头文学,适合农民记忆和传诵。而且它的功能与戏曲中的介绍性的唱腔非常相像,都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告诉接受者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来龙去脉。而且在接受效果上确实取得了这样的作用。不管是作为听众的农民还是一个现代读者,都能获得最有效的信息。再看另一段: “刘广聚,假大头: 一心要当人物头,抱粗腿,借势头,拜认恒元干老头。大小事,抢出头,说起话来歪着头。从西头,到东头,放不下广聚这颗头。”这段全部直接押单一的“头”字韵,不讲文人化的平仄韵部,这更符合农民的欣赏水平。每个人物一出场就来一段快板,用高度民间化的语言说明了此人的特点,且以最少的文字提供给接受者最关键的信息。从现代读者看来也是极其形象的描述。如对刘广聚这个反面形象,用七言的打油诗就非常经济,前两句说出他对权力的渴望,接着的两句说出他如何获得权力,原来是认干爹,做地主的奴才和帮凶,后四句则说出他狗仗人势的丑态。交待得非常清楚,连标点也仅 65 字,如果用叙述,即使是概述性的话语恐怕也要几百字能说清楚这人的性格特点及来龙去脉。
二、叙事视点:从散点透视到散点叙事
从叙事视点/叙事角度来看,《小二黑结婚之后的赵树理文学较多地借鉴了地方戏曲中的表现方式,让人物的行动带动叙事的发展,类似于穿针引线,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全知全能的叙事。作为叙述人的作者站在与农民同一的立场,虽然对于故事是全知全能的,但是并不站在农民视角之外说话,而是透过故事中人物的眼睛来叙述,而且只讲述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并不做主观的分析和评价,这也就是赵树理所说的: “写风景往往要从故事中人物眼中看出,描写一个人物的细部往往要从另一些人物眼中看。”
中国画与西方画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于西方的景物画之类通常有一个固定的视点,表现出明显的主次,中国景物特别是山水画则没有,从任何角度看可能都是中心,被称为散点透视。赵树理的叙事视点就类似中国古典传统中的散点透视,形成“散点叙事”,类似从多个角度表现事物特征和塑造人物,整体上看无中心人物,从而建构出整个东方色彩叙事世界。
散点叙事下的叙述人更像话本小说或民间书场的说书人,全知全能地引导着读者去经历所有的人和事。《三里湾》中没有固定的人物视角,不断变换的人物既是事件的一部分,同时又带动事情的发展和情节的展开,引出其他的人物,叙述人就跟着这个人物的所见所听来叙述。叙述人和小说中的人物是同一的,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叙述人的全知与小说中人物的限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但是无论是全知叙事还是限知叙事,作者都没有赋予其作品人物以一种主动观察的意识,而叙述人的主动意识则隐藏于小说人物的自在状态中。
就以王玉梅为例,她穿针引线的作用并不具备主动性,只是作者呈现在读者眼中的农村年轻姑娘,但她是王家的女儿、合作社的社员、夜校的学员、青年团员、三对青年恋情中的一方,所以她参与的所有事件,既是她日常生活的普通行为,同时又使与她有关的人与事情自然地呈现。其他人物也是如此,他们生活在三里湾这个地理空间中,共享着三里湾不言自明的伦理和行为规范,同时也在推动着三里湾的变动与重组。而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并不存在一种旁观的或外来的视角,作者化身于每一个人物,与他们融为一体。
尽管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是跟着故事人物的眼睛走的,但是叙述声音却是叙述者的,这个叙述者又是全知全能的,就使赵树理的作品既不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也不是限知视角,因为在其作品中,“谁说”和“谁看”并不总是统一的,即使他们在同一立场上。[1]灵芝一走进去,觉得黑咕隆咚连人都看不见,稍停了一下才看见有翼躺在靠南墙的一张床上。[2]这间小屋子只有朝北开着的一个门和一个窗户,还都是面对着东房的山墙---原来在有翼的床后还有两个向野外开的窗户,糊涂涂因为怕有人从外边打开窗格钻进来偷她,所以早就用木板钉了又用砖垒了。[3]满屋子东西,黑得看不出都是什么---有翼的床头仿佛靠着个谷仓,仓前边有几口缸,缸上面有几口箱,箱上面有几只筐,其余的小东西便看不见了。[4]当灵芝走进去的时候,可以坐的地方差不多都被别人占了。[5]她见一条长凳还剩个头,往下一坐,觉得有个东西狠狠垫了自己一下; 又猛一下站起来,肩膀上又被一个东西碰了一下,她仔细一审查,下面垫她的是玉生当刨床用的板凳上有个木橛---她进来以前,已经有好几个人吃了亏了,所以才空下来没人坐; 上面碰她的原是挂在墙上的一个小锯,已被她碰得落到地上---因为窑顶是圆的,挂得高一点的东西靠不了墙。[6]有个青年说: “你小心一点! 玉生这房子里到处都是机关! ”灵芝一看,墙上、桌上、角落里、窗台上到处是各种工具、模型、材料……不简单。
这两个叙事片段是灵芝对马有翼、王玉生的房间的观察,[1]-[3]为中农家庭的青年马有翼的房间,[4]-[6]为贫农家庭的青年王玉生的房间,从叙事视点来看,都是随着灵芝的眼光写的,透过灵芝的眼睛可看到截然不同的房间,也反映了有翼和玉生截然不同的性格及家庭环境,从而为后文灵芝选择玉生放弃有翼作了铺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分属第 22 和 24 节,故事中的时间距离不短,叙事距离也不算短,但对两个房间的描述隐含作者采取几乎完全相同的叙述方式,甚至连使用标点符号都是一样的。两个叙事片断都是三大句,中间的第二句都出现了破折号,第二个片1话语的功能也完全一致,即[2]和[5]中叙述人和灵芝分离,是以全知的视角进行补充说明,前者写出了糊涂涂的精明,而后者在灵芝的视角之外对玉生的房子作了更具体的补充,[6]句的最后三个字“不简单”既是灵芝所想,也是叙述者的评价话语,等于隐含作者的声音,同时还可以是满屋子里人的想法。从接受上看,对两个房间的描述产生的修辞效果却是完全相反的,马有翼是阴暗的封闭的,没有生气的,而王玉生的房间却是明亮的、科技化且充满生机的。但隐含作者的叙述干涉却是很隐蔽且简洁的,他的干涉仅在于对描述对象的选择,即叙述人虽然会不时地以全知的视角作补充说明,但其补充说明的只是人物看不见的部分,或是看到的事实背后的原因,叙述人的立场、想法和故事中的人物依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虽然他是全知的,但是叙述却又始终没有离开故事中人物的眼睛,其叙述的部分也没有超出故事人物的理解和接受范围。
其叙事视点既没有源自他者“凝视”的目光,同时也不存在一个内视的目光。叙述者或是作者虽是全知的,但是他们附身于故事中的人物,借着故事中人物的限知视角,平静地看着或者说着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由于故事中的人物是自然而然地生活于乡村中的,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性和独立精神,所以消隐了全知视角叙述者的同时也没有就农村的变化作任何评述。根本的推动力在于隐含作者的故事语法,他选择了素材,并加上隐蔽的因果关系,非常巧妙地实现了他的最终修辞。对农村内部的关注是核心。所以事情的发生与解决、农村的改变和重组是由各种力量的集体作用推动的,同时也使得事情的发生与解决摆脱了外部( 包括国家) 的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点也决定着小说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暧昧关系,从而将其作品中的乡村呈现为某种自足、自在的意义空间,当然这种自足自在性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暂时的,三里湾并没有完全摆脱外部的干扰,赵树理定位于内部的同时也隐藏了一种危险的破坏力。如《三里湾》中何科长的外来者身份,只是赵树理尽力弱化其外来者的行为特征,而使他成为第 12 至 15 章的线索,作为三里湾变化进步的一个佐证。虽然他的外视角被弱化,但并不代表不存在,不过这种弱化外部的人物线索式的叙事,使得三里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暂时的自足性,内与外呈现一种互动式的和谐,其中蕴含的则是作者对于理想乡村生存形态的一种想象。
三、东方化叙事:传统形式下的现代乡村伦理
赵树理文学在民间化上非常成功,是迄今为止在接受方面最成功的“大众化”文学,不但如此,赵树理文学在形式层面的传统化之下隐含着相当强烈且自觉的现代意识。如《李有才板话》不仅仅是民间化的极具乡土特色的“快板”,意义层面上也有着非常现代的观察农民的视点,这些是由赵树理化身的隐含作者赋予文本的。他不会把作者的声音直接加入到叙述之中,他的高明在于,他的倾向非常巧妙地隐藏在叙事对象的选择之中。即赵树理选择一些特定的场景、人物和事件,以隐含的现代意识进行编码组接,建构出表面上非常传统的乡村叙事,在农民的自觉接受中得到现代意识的熏染,从而潜移默化地真正实现了梁启超和鲁迅竭力想达到的教育民众的效果。下面看《李有才板话》中的另一个片段:[1]像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编,一方面是他编惯了觉着口顺,另一方面是老槐树底的年轻人吃饭时候常要他念些新的,因此他就越编越多。[2]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轻人不用一天就都传遍了,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3]西头的人不论老少,没事总不到老槐树底来闲坐,小孩们偶尔去老槐树底玩一玩,大人知道了往往骂道: “下流东西! 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树底去住啦! ”[4]有这层隔阂,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传到西头。
这个叙事片段用概述的方式交待了李有才的快板在村中的接受和传播情况。第[1]句说明了快板很受穷人欢迎,第[2]句就有了大的转折: 这些快板很少传到富户所在的村西。第[3]和[4]句交待了原因,即富人不屑与穷人来往,孩子们偶尔来往也被骂丢脸。就此,隐含作者以非常简单的语言揭示了农村的等级差别,说明阶级的分野在中国农村确实是存在的。整个文本都用口语化的短句,少用欧化和过于文人化的词语,其意义指向隐隐与党的阶级论相合,但没有刻意强调,而是基于真实的自然显现,从而在无形中达到民间的传统话语与现代国家要求的结合,也从侧面证明党在当时的政策是符合农民需要的,解放区的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农民利益的双赢,就此大巧若拙地把现代意识隐含在完全农民化的话语实践之中。
再者,赵树理文学采取了中国古典化的散点叙事,这种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交替的叙事视点使得隐含作者的叙事始终围绕着农民展开,党代表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来到村庄,首先接受的便是农民视点的检验,在农民视点的观照下,其与村庄的融合程度恰恰是其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李有才板话》中章工作员的失败和老杨的成功,就是说外来的思想虽然会对农村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前提是必须要和农村内部固有传统伦理道德相契合。
散点叙事也使赵树理的叙事世界与西方化的叙事明显不同,赵树理文学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个体化的人物,个体的成长就很不明显,即使有“成长”,最终也会融入集体之中,如《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在后半部分的背景化,因为赵树理叙事的中心始终是乡村和集体。他的叙事世界中的人物既有现代特色,同时又是群体化的。这点正与社会主义对个体的要求相合,即个体要服从集体。
其实在这点上,赵树理坚持的是乡村伦理中的集体,即梁漱溟所说的中国乡村的“公中有私,公私不分”,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也持同样观点,但由于赵树理的成名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过于密切,所以不少评论者出于 1980 年代的新启蒙思路而直接否定赵树理文学的价值,而且 1980 年代知识分子倾向于把社会主义封建化,造成对社会主义的各种误解,赵树理文学也因此被归入左倾幼稚化创作之列。由于新启蒙思路重回西方崇拜,所以也不可能注意到赵树理其实更多地从中国乡村伦理出发讨论个体的成长问题。于是,中国乡村又一直被“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归于前现代的“封建”,在急于实现欧美式现代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传统一无是处,执着于传统就反动。因此,赵树理文学面临的是双重否定: 对封建的否定与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赵树理的乡村关怀一直被忽视,同情赵树理的也多是从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入手,但必然要“一分为二”地批判赵树理“境界”不高、缺乏现代意识及囿于小农的狭隘等。
当前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自我他者化思路是限制对赵树理进行全面评价的根本原因之一。
实际赵树理坚持的一直是东方传统,而不是革命第一,他之所以赞同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那时的革命确实维护了乡村伦理,给了农民切实的从奴隶到主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赵树理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模式中吸取有利的因素也是为了保证中国新乡村的经济和伦理建构,其乡村伦理的核心没有变化。后来“大跃进”被错误地发动,摧毁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实际意味着革命对底层和乡村的抛弃。赵树理在 1950 年代之后的叙事危机一直被解释为跟不上时代,这是多年来的盲目解读,叙事危机实际上是赵树理拒绝再与抛弃了底层的政治权力合作,表现出一个东方文明坚守者的强大人格。认识赵树理文学的东方化特色及价值有着非凡的意义。竹内好对鲁迅和赵树理的同时肯定就已经是对中国学术界一个启示,竹内好对赵树理的肯定需要不断进行正面重读,赵树理文学对古典、现代和社会主义的三重超越在今天仍然无人可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赵树理文学的出现,预示了一个东方化文学时代崛起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