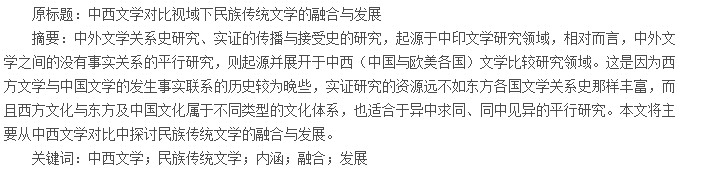
就民族性说,中国人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伦理信条最发达,而有系统的玄学则寂然无闻;表现在文学上,关于人事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最发达,而凭虚结构的作品则寥若晨星。中国民族性是最“实用的”,最“人道的”.它的长处在此,它的短处也在此。长处就是重视人际关系,使涣散的社会居然能享到二干余年的稳定,短处在它过重人本主义和现世主义,不能向较高远的地方发空想,所以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求。社会既稳定之后,始则不能前进,继则因其不能前进而失其固有的稳定。朱光潜认为,诗人对于自然的爱好有三种[1].第一种,也是最粗浅的是“感官主义”,第二种起于情趣的默契欣合,第三种是泛神主义,即把大自然全体看作神灵的表现,感受到其神秘超人的力量,自然的崇拜于是成为一种宗教。这是多数西方诗人对于自然的态度,中国诗人很少有达到这种境界的。在哲学与宗教方面,朱光潜认为,“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
一、民族传统文学的内涵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土壤与文化积淀之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吸收、融汇域外其他民族文学的活性养料与有益范式,但这并不能完全更换其牢固的生命根须。越是有生存活力的文学,越不会消褪其民族生活与民族精神的纹章徽记,不会割断其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天然联系。
无论中国文学还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历史,均提供了此种昭示。很难设想,某个国度、某个民族能够在一片文化废墟上矗立起自己巍峨的文学殿堂。
然而,在近几年的文学领域里,却滋长了一股令人惊诧的所谓“新思潮”,以怀疑主义和民族xuwuzhuyi粗暴地对待我们的文学传统。一段时间里,主张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文学传统的科学态度,被贬斥为陈腐、过时观念,而怀疑和否定文学的民族传统,力主以西方现代派艺术法规全面取代文学的民族传统,甚至要将所谓“黄色文化”变种为“蓝色文化”的论调,竟成为理论时尚和引领文学创作实践的思维导向。这股思潮也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徽记出台的,因而,就增添了明辨是非的复杂性[2].
二、中西民族传统文学对比
1925 年,沈雁冰(本名沈德鸿,笔名茅盾,1896-1981)的第一篇神话研究论文《中国神话研究》发表于《小说月报》第 16 卷第 1 号。他尝试运用欧洲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来阐释中国神话问题。他在论述中国神话之前,先援引了安德鲁·兰(Andrew Lang,1844~1912)和麦根西(A.Mackenzie,通译麦肯齐)的主要观点,作为他论述中国神话的理论根据,说:“我们根据了这一点基本观念,然后来讨论中国神话,便有了一个范围,立了一个标准”.他根据兰氏的原则,理出来研究中国神话的“三层手续”(即三条原则):
第一,区别哪些是原始神话,哪些是神仙故事。
第二,区别哪些是外来的神话,哪些是本土神话。
第三,区别哪些神话受了佛教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按照这三条原则来研究中国神话资料,则表现中华民族的原始信仰与生活状况的神话就会凸现出来。这三条原则,特别是后两条,实际上是强调中国神话与外国神话的比较研究的原则。与朱光潜、梁宗岱一样有着留洋经历,一样有着扎实的国学与西学修养的钱钟书(1910~1997),也以他自己的方式踏入了比较文学园地。
与朱光潜、梁宗岱一样,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在中西诗歌领域,但与朱光潜的逻辑化、体系化的研究不同,钱钟书更倾向于以 SU.g 随笔的方式,信手拈来地做中西比较,在这一点上有点近似梁宗岱。但他是个极重文献的研究家,对文献的引用不厌其烦,这与梁宗岱的径直爽快的评论风格又形成对照。这一时期,钱钟书除了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几篇文章,如《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1 卷 4 期,1937)之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作品是以品评中国古典诗歌为中心的随笔札记集《谈艺录》[3].
《谈艺录》写于 1939 年至 1942 年间,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全文用文言文写成,文字较为古奥,其间有夹杂一些英文引文,引述资料显得堆砌、繁复、琐屑,非专业读者读通不易。《谈艺录》有九十一则札记,后又增补十八则“补遗”.
以唐代以降的中国诗为话题,对诗人、诗派、风格、轶闻趣事等加以品评,都是一些片断性的文字,篇与篇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没有多少术语概念,没有理论命题,更没有体系的构建,结构比较松散,内容比较驳杂,行文比较自由散漫,这些都使得《谈艺录》颇似中国传统的诗话。
进入现代之后,这种传统诗话式的写作与研究方式几乎无人为之了。但这种写法似乎很适合钱钟书那种不赶时髦不从众,自由洒脱的学术个性,因而用起来显得得心应手。更重要的,《谈艺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诗话,因为其中夹杂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旁证材料,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为传统诗话所不及。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研究比较文学的人,有理由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钱钟书在谈论菜一中国话题的时候,必以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对的材料作为佐证或旁证,以强调他在序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世界文学整体观。
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首推朱光潜(1897~1986)。朱光潜在 1934 年发表《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原载《申报月刊》第 3 卷第 2 号)一文,试图解释中国的长篇叙事诗缺乏的原因。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饮冰室诗话》中就已提起,他说:“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然长篇之诗,最传诵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古诗《孔雀东南飞》一篇,干七百余字,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诗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在这里,梁启超较早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学长篇叙事诗的不发达,为中西比较文学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朱光潜则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探讨和回答[4].
三、民族传统文学的融合与发展
在整体世界史观的指导下,明确了民族文学处于向世界文学前进的过程中,这就给了文艺家和批评家一个重要启示:民族风格不可能有某种具体的样板,民族风格应该是植根于民族土壤中的活生生的东西,是从内容到形式的结合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丰富多样的具体风格中民族精神的印记。这种民族精神,包括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习惯,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表情达意的方式和价值观,但也要在外来文化冲击和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微妙的有时是深刻的变化。从前人们以女人缠小脚为美,以少年老成为难得,现在正好相反,便是观念变化的证据。因而提倡民族化,决不是强迫文艺家遵循现有的某种规范,而是要他们从世界文明大潮中广泛吸收有益的养料,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只要文艺家生动地表现了生活中所蕴藏的民族的精神素质,艺术上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较为完美的结合,不论他采用什么风格手段来组织题材,刻画人物,其作品必定具有民族气派。这正如鲁迅评陶元庆的画时所说的:“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彩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对于这种“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桔亡中国的民族性”的风格,鲁迅认为“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俪尺或清朝的营造尺”,而“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需要指出的是,向“世界的文学”靠拢,并不是要抹杀文学的民族特性。世界的有机统一本有一个多样性的前提。人类一方面越来越接近自由的共同本质,另一方面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各民族在奔向自由的道路上总是采取了带有自己历史特点的方式[5].
一个民族的诗人不仅必须对本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他的出现还必须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环顾西方作家,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并不罕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等,无不以其独特的艺术天才,贴近人类的创作意识,塑造了无数与全人类紧密相连的艺术形象。因为他们既是本民族火热生活的参与者,也是“人类一般生活的参与者”托尔斯泰语)。在这方面做得更自觉的是莎士比亚。他总是把戏剧冲突提高到“人类矛盾的高度”,“让人类的要旨产生于它时代的历史斗争之中,并赋予它以一种如此集中、如此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高度”.
但是,我们不能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割断历史、脱离国情的类比。一般来讲,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闭关锁国的封建经济生活,使得无数文人缺少西方世界乃至莎翁那种自觉。但是,谈艺的第一原则是要看对象是否符合艺术规律。众所周知,“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使我国许多古代作家赢得了生前不曾料想过的殊荣。这是艺术形象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超过了作家主观认识的有力的证明[6].
总之,求同论证可以视为辐合思维,它能在提供的根据中得出有方向、有范围的结论。求异论证又叫辐射思维,它能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不同的途径去开拓,以探求多种答案。它不受固定方向、范围的制约,能求答案于未知,更易有所发现。
参考文献:
[1]闫培培。 浅析传统文学在移动阅读下的生存状况及优化路径[J]. 东南传播,2014,(2):119-120.
[2]林木阳。 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形象描述赏析[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4,(1):87-88.
[3]王琳。 中西文学思想哲学场域的契合与分野[J]. 湖南社会科学,2013,(5):239-241.
[4]纪海龙。 1950-1960 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08-113.
[5]廖可斌。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非古典传统--读《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06-110.
[6]张冠夫。 梁启超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重新认识[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32-37,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