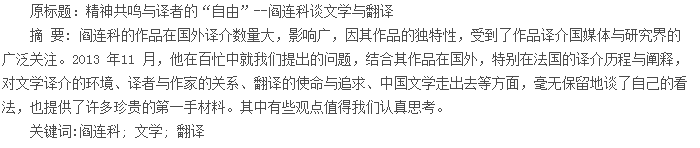
高方: 阎连科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抽出时间与我们探讨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话题。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您的作品不仅享誉国内,而且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瑞典、挪威、以色列、西班牙、葡萄牙、塞尔维亚、蒙古等 20 几种语言,在 20 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受到海外各界读者的追捧与热评。能否请您向我们谈一谈您的作品目前在海外的译介情况,您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时候被翻译出去的?
阎连科: 谢谢你准备了这么具体详尽的问题。关于我的小说翻译,其实没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介绍和讨论。在中国,我不是最好的作家,有许多前辈、同辈和更年轻的人,他们的作品都比我写得好。看他们写的小说,我常常有种自卑感。常常会在看完之后,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在国外,我也不是中国作家在海外影响最大的人,无非是比起一些朋友,更有些翻译的特殊命运。不用回避,《为人民服务》是我较早翻译出去的一部小说,而《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的“特殊性”,也是它得以广泛翻译的一个窗口和契机。
其实,在法国最先签了合同要翻译的作品是《受活》,而非《为人民服务》。因为《受活》方言翻译的难度,使它的翻译一波三折,没那么顺利。这中间,《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出来了,出版社就决定暂时搁置《受活》,首先翻译《为人民服务》。到今天,因为《为人民服务》的特殊性,因为这部作品短,不到十万字,翻译起来更便利,也因为这部小说故事更集中、更好看,所以它有近 20 种语言翻译和出版。必须要承认,对我来说,那扇翻译的大门是借助《为人民服务》推开的。但就《为人民服务》这部小说本身而言,在我一生的创作中,远不是我最理想的作品,甚至不具有多大代表性,更具有偶然性、事件性。我常说,喜欢《为人民服务》了,你就去看看《坚硬如水》。看了《坚硬如水》,你们就明白《为人民服务》的优劣来了。可惜的是,《坚硬如水》直到今天的译本还很少。法国一直在翻译计划中,但又一直有别的新作品,总是排不上它。因为我亚洲之外的翻译,都首先是从法语开始的,法语没有译,别的翻译就难以推开和介绍。
高方: 文学作品的译介,译者至关重要。您的作品的翻译质量上乘,《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年月日》、《受活》、《四书》等一经翻译即刻在海外引发了广泛好评,甚至还入围了“曼氏亚洲文学奖”( Man Asia Literary Prize) 、“独立报外国小说奖”( 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Award) 、“费米娜文学奖”( Prix Femina) 、“布克国际文学奖”( Man Booker Prize) 等一系列重量级的文学奖项,这其中译者的功劳不言自明。我统计了一下,翻译您作品的译者大致包括英国著名汉学家蓝诗玲( JuliaLovell) 、美国的中国文学翻译家辛迪·卡特( Cindy Carter) 、美国汉学家罗鹏( Carlos Rojas) 、法国翻译家克劳德·巴彦( Claude Payen) 、金卉( Brigitte Guilbaud) 和林雅翎( Sylvie Gentil) 等,您和这些译者熟悉吗? 能否请您谈谈和他们之间就翻译问题的交流情况?
阎连科: 你是专家,掌握的情况比我多。关于你谈到这些英语、法语的翻译家,我都比较熟。几乎都是朋友吧。都是因为翻译,由陌生而熟悉,再由熟悉而朋友。至于翻译问题的交流,已经成为我写作中的一部分。几乎每部小说在翻译过程中,都有一些有趣难忘的事。《丁庄梦》的英语译者辛迪·卡特,她在中国住了十几年,最早认识她是因为她看了《年月日》和《受活》。她真正想翻译的是这两本书。但后来,英语的《丁庄梦》出版社决定由她译,是因为她首先翻译了一段《丁庄梦》,把这段翻译放在网上,被出版社读到以后才选由她来翻译的。但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她太忙,因为别的事,迟迟没有按日期交稿,和出版社之间有了一些不愉快。但必须要承认,当她开始动手翻译后,她的认真令我感动和感慨。大约是在 2009 年,有半年时间,几乎每周或者半个月,辛迪都和我相约见面,或我家,或者咖啡馆,一块讨论小说中她不甚明白、有些模糊的字、词和句子; 尤其那些模糊但又有某种隐含和韵味的地方,她都用红、黄、绿在那本中文书中画下来。这本中文的《丁庄梦》,几乎就是她画的文学翻译的线路图,或者叫翻译地图吧。中文、英文的蝇头小字,在书中密密麻麻。我曾经想要辛迪把这本“翻译标本”的中文小说作为纪念送给我,但最终没把这话说出口。
我是从辛迪翻译《丁庄梦》感受到译者劳苦的。在我看来,很多时候翻译比写作更辛苦,更值得尊敬和理解。事实证明,辛苦和认真,终是会有好的结果和回报。无论如何,《丁庄梦》的英译是个好译本。只不过这个好,都被作者得到了,而译者,辛苦之后就像做出好菜供客人品尝的厨师一样。
客人记住了哪道菜好吃,并记住了那家餐馆名,于厨师,他可能就不去刻意过问了。菜馆就是一部书的原作者,客人是读者,中间环节是译者( 厨师) ,客人吃到好菜时,是会记住那家菜馆的,可厨师是谁,一般情况下,客人就不太去记了。但菜馆是最知道哪个厨师辛苦、手艺高巧的。
与辛迪情况截然相反的,是《受活》的著名法语译者林雅翎( Sylvie Genti1) 。《受活》遇到她,是《受活》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受活》是 2004 年年初在中国出版的,一经出版在法国比基埃出版社工作的陈丰女士就慧眼独到,很快签了法语翻译合同,但因为《受活》的方言和结构之复杂,先后找了两个译者,他们都没有接手。甚至有位翻译家翻译了一部分,又把作品退回到了比基埃。就是信。但去年彼此在北京见了面。第一次见面没谈太多话,那种彼此的信任就在我们中间建立了。
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翻译家。这正如我们找朋友,有的人看一眼就“萍水相逢”了,有的人朝夕相处也难以成为好朋友。我和罗鹏属于那种萍水相逢而胜过朝夕相处的人。他在翻译英语《受活》时,和林雅翎一样,是没有问过我小说问题的人。可译本出版之后,从读者和媒体反映的热情看,是可以知道他翻译之成功的。《四书》他也已经翻译结束了,计划今年秋天出来。从这些过程和角度讲,我说在海外和中国其他作家比,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不是因为我在中国比别的作家小说写得好,而是在海外我总能碰到好的策划人和翻译家。在和这些翻译家的交流中,我以为交流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交流彼此对文学的认识和对某一部书的感知和体悟。
我以为,作家和翻译家,对文学共有的大理解,远比字、词、句子、段落的意见统一或分歧更重要。
高方: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您在法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到目前为止,已有 7 部作品在法国翻译、出版,并且反响热烈。不过,尽管译者付出了卓越的努力,但是就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译介的普遍情况而言,却往往出现译本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完全忠实于原作的现象,您对这一问题有何见解? 您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讲到,“一部成功的译作不是在于逐字逐句的机械翻译是否完美,而是在于译者是否与作品的精神具有内心深处的共鸣”,您提到的“共鸣”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译者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学与社会规范,如何才能达到这一“共鸣”? 除了“共鸣”,您对译者还有哪些方面的要求?
阎连科: 谈到我在法国的被接受和知名度,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陈丰女士。几乎可以这样说,没有陈丰的努力,就没有我小说在法国和欧美其他地方的今天。法国比基埃出版社是专门翻译出版亚洲文学作品的。而陈丰多年来一直是这家出版社中国文学的策划人。我知道,如老作家陆文夫和当代作家王安忆、毕飞宇、迟子建、王刚、张宇、曹文轩等,有些作家的作品一部部地连续出版,都是陈丰推介、定夺的。我感觉,陈丰在介绍中国文学中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她认为好的作品,翻译多难也要介绍。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和《受活》。这两本书在语言层面上,很多人认为不可译,但她坚持要翻译,最后都在法国有了很好的译本和销售。二是她一直主张介绍作家,而非某本书。主张持续地推介作家一生的写作,而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哪本小说热闹就哪本。比如毕飞宇、王安忆,还有我,都属于她的“持续”对象吧。第三点,她在做一个作家而非某一本小说时,她有她的安排和节奏。比如小说的长短、接受的难度和容易度。以我自己为例,《为人民服务》是容易推广的,好看的,之后她就安排出版有一定长度并在阅读上会让法国读者苦痛的《丁庄梦》。《丁庄梦》之后她又安排翻译完全不一样阅读口味、而且篇幅更短的《我与父辈》和《年月日》。等你有了较为稳定的读者群,再接着出版大部头的《受活》。而《四书》和《日光流年》是充满疼感的两本书。这接下来,她又安排翻译充满奇异“神实”和幽默、欢乐的《炸裂志》。这种长短、口味的调整和搭配,如同厨师请客时要做哪些菜,先上哪些菜和后上哪些菜的调整和安排。所以说,我在法国的景况,一半缘于我的写作,另一半缘于陈丰和比基埃持续而有节奏的计划翻译和出版,甚至哪本书适合哪个翻译家,都在陈丰的计划中。比如,翻译家金卉女士有很好的文学功力,自己也不断地进行散文写作,语言中有强烈的韵味和诗意,陈丰和出版社就安排她翻译《年月日》、《我与父辈》、《日光流年》等,而请林雅翎来翻译《受活》、《四书》和《炸裂志》。甚至,陈丰和出版社还和我英国的经纪人不断商量在其它语种中先翻译哪一本,后推介哪一本,把法国的出版节奏和经验带到别的语种中间去。
陈丰和比基埃是我小说外译的发动机。如果说在中国作家中,我的外译是幸运的话,他们就是我的幸运之神吧。
这时候,几乎很多中国人和法国汉学家都认为《受活》“不可译”时,林雅翎女士出现了。她说没人翻译时我来翻译吧,唯一的翻译条件就是出版社不要给我时间限制。就这样,《受活》的翻译再现曙光了。林雅翎用了二、三年的时间来翻译《受活》这部 30 多万字的书。在这二、三年的时间里,她大多时间,人都在北京。我们同在一个城市,却很少见面。偶尔见面喝茶,她也从来没有问过小说中有哪些模糊和疑问,直到两年多后的某一天,她给我写了一个邮件,说小说最后结尾处“花嫂坡”的一节里,有很多花草、植物的名字,她遍查植物词典都不知道那些植物花草为何物。我回她一封信: “那些植物花草的名字都是我编的。”她又回信说,“那就没有什么问你了。”
《受活》在法国出版是2009 年,更名为 Bons Baisers de Lenine( 《列宁之吻》) ,后来其它语种的翻译都沿用这个名。它在法国的成功,实在令人意外。我完全没有想到读者会那么喜欢它。当年好像就卖了三、四千册书,这个数字在中国是个小数字,但却是中国文学在法国很大的数字了。之后它每年都再卖两千册或不到两千册。说今年法国的图书市场不景气,可这本让中国人看着都费劲的《受活》,竟又意外卖了 2800 册。而且因为它的销售,也在带动着此前出版的《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年月日》和《我与父辈》等的慢热与长销。因此,我经常说,它在法国的好运,是因为它首先遇到了伯乐陈丰,接着遇到了林雅翎。诚实地讲,没有陈丰,就没有我今天整个翻译的结果; 没有汉学家林雅翎的翻译,就没有《受活》的各种外语的青睐。我问过林雅翎,《受活》中那些广泛的方言在翻译中是怎么处理的? 她说当她找到了她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法国南部的乡村方言时,《受活》的方言翻译就没有那么大的难度了,加之她对德语的一些借鉴,把中国的河南方言转化成让法国读者意外着迷的法语,也就水到渠成了。
《受活》使译者在法国得到了国家翻译奖。但在《受活》出版的前一年,金卉( Brigitte Guilbaud)女士也因翻译出版《年月日》获得了这个奖。法国是个文学翻译大国,一个作家两部作品的不同译者,连续获得这一奖项,除了小说风格和语言有较大差别外,我想这两个译家的内在不同,大约也都在翻译中最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还有《四书》,它的语言也是最难翻译的,译者也是林雅翎,除了小说开篇的第一句“大地和脚,回来了”,我们两个用了一个多小时去讨论这句叙述外,其它的翻译她也未曾问过我。而之所以第一句“大地和脚”要讨论这么久,是因为这句话最准确的意蕴我也说不清。从语法和字面上说,“大地和脚,回来了”,这是不合乎中国语法、文法的,但它其中的意蕴确实丰富到无法用别的句子去替代。现在,林雅翎马上着手翻译《炸裂志》,这也是一部难以捉摸的书,但我知道,她在翻译中不会来和我讨论什么了。因为她太了解我和我的写作了,我们彼此间有了一种很难得的理解和信任。
像我这样连中国的普通话都讲不好的人,不要说懂一门外语,其实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
我连一天的外语都没学过。在我作品的外译过程中,我和翻译家大多都有那种彼此理解和信任的关系。所谓理解,是我希望他们充分理解我的整个小说,理解字、词、句子的某种意蕴和节奏; 而我也必须明白和理解,每个翻译家的母语对我都是神秘的盲区。在这盲区中,我一定要相信和尊重那些心灵慧智的翻译家。
美国杜克大学的教授罗鹏( Cgrlos Rojas) 是我英译本的第三个译者。最早翻译出版的英文版《为人民服务》的译者是蓝诗玲( Julia Lovell) 。其实她最先向英国出版社介绍推荐的,也同样是《受活》,可后来《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捷足先登了。我说我在翻译中的命运好,就是说我总是能遇到好译者。蓝诗玲是帮我带来英语读者的第一人,是因为她的译本和《为人民服务》的特殊性,让英语读者注意到中国有个奇怪的作家叫阎连科。而让英语读者进一步接受的,是辛迪·卡特翻译的《丁庄梦》,而在英语中确立我一个作家地位的,是罗鹏翻译的《受活》。罗鹏是王德威和刘剑梅推荐的,直到《受活》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个版本先后出版,我和罗鹏都没有通过几封20对于一些译本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忠实原著的看法,我个人以为没有那么忠实就没有那么忠实吧。要给译者那种“自由度”。我曾经极其认真地把多年前翻译到中国的印度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的小说《卑微的神灵》和几年前这本小说的另外一个更名为《微小的神》的译本放在一块比较着看,让我惊异的是,这两个译本的译者不同,我一字一句对比着看这两个译本的前几页时,发现他们每句话翻译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没有一句话使用的字词是完全相同的。这让我震惊和害怕———从此我就不太相信翻译的“忠实”那种说法了。一部书,在一个翻译家那儿是“忠实”的,到了另一个手里,可能那种“忠实”就发生变化了。哈金和我说过一件事,说托尔斯泰的小说最初翻译到美国没有那么受欢迎,几个译本都反响平平,到后来,换了译者又有了新译本。新译本的文字有些“粗”,但却大受欢迎了。而前者的译本太“细”,甚至太“诗”了。当然,这是当笑话去说的,不可太在意。然而,果真是这样,是哪个译本对托尔斯泰更忠实? 更尊重? 又是哪个译本对托尔斯泰更好呢?
我是北方人,生活糙,性格也粗,所以对译作于原著的“十分忠实”和“八分忠实”,没有那么在意。忠实就忠实,没那么忠实就没那么忠实吧。我不是昆德拉,没那么在意这些。也没有语言能力去在意这些。我的主要任务是写好小说,管不了翻译也要好的事。所以说,我是愿意把翻译中的某些“自由”留给译者的。于我言,我宁要翻译中韵律的完美,而不要机械翻译的字词之完整。译者和原作精神的共鸣,远比译者单纯喜欢原作所谓语言的字、词、句子更重要。
这种精神的共鸣,表现为译者必须喜欢和爱他( 她) 所要翻译的那个作家和那本书。只有喜欢和爱,在翻译中才会有译者的情感走进去,才会把作家作品中的情感和灵魂带给新语种的读者们。
而现在的很多情况是,译者并不喜欢这个作家和这本书,只是为了翻译而翻译。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翻译。比如你翻译和研究昆德拉,这其中是有你对昆德拉的喜与爱,是有你对文学与世界的认识和昆德拉的相似、相同存于其中的,这就是共鸣,而不简单是为了翻译和出版。
第二,我说的共鸣,是译者和原作者应该有相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他们应该是文学的同道和同仁,而不仅仅是搭档和朋友。
第三,是译者和原作者要“心有灵犀”。某种文学中的只可意会而无法表达的东西,译者应该可以感受和把握,而且可以同样用“意会”的方法转化和传递。我说的共鸣,就是指这些,一是译者要更喜欢和爱他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二是译者和他( 她) 的对象要有相似、相近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三是译者要能译出作家叙述中的韵律和节奏。
说到对译者的要求,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很“弱势”,很“低层”。总体来说,往往是出版社和有能力的译者在挑作家,而非作家去选出版社和译者。如此,中国作家大体是对译者没有太多要求的。就我个人言,我除了上述的“共鸣”外,是希望译者有极好的母语,而不是他有多好的中文。尤其还希望,译者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创作经验,能是个作家就最好了。
高方: 您的作品能够在海外被接受与被传播,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读者。近年来,您不断出现在海外的各种文学讲坛之上,因此一定有机会直接接触到海外的读者。那么,您如何看待海外读者? 他们与中国读者有哪些共通之处,有哪些不同? 请您谈谈您在这方面的见闻。
阎连科: 这一说起来,就又落入“西方月亮比中国圆”的圈套了。我们每每谈起外国读者,也多是指西方读者。其实,在亚洲,韩国、越南的读者都对中国文学充满着情感和热爱。余华在韩国有很大的读者群。在其他地方书也卖得好。莫言的《丰乳肥臀》,在越南连印十几版。当然,莫言是今天中国作家在海外最有知名度和销路的作家了。而亚洲的日本,也翻译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相对于越南和韩国,日本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态度就冷一点,不像中国读者对日本文学那么温情有热度。究其原因,这里有文化的因素,也有政治的缘由。
社对作家不感兴趣,但对书很感兴趣,对书的故事很感兴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有些书的介绍就专门拿‘被禁’说事儿。……一看一部作品被禁止,法国出版社就马上来了兴趣,尤其是记者。既然这本书被禁,那一定是本值得译介的书”,而您的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则恰恰印证了这一观点。《为人民服务》法译本的封面内页上介绍“这本书在中国一出版就成为了禁书”,《丁庄梦》的介绍中也提到“他的书在中国被禁”,《受活》也有类似的介绍性文字“在他的国家,他的言论和出版物都被禁止”,《四书》的推介文字中则称“我们明白这部小说毫无疑问永远不会在中国大陆出版”。对于出版社与翻译家的上述推介,您如何看待? 您对自己作品的外译过程有何看法? 能否谈谈您作品的外译途径?
阎连科: 我不熟悉何碧玉教授。我想她这样说是有她的道理的。的确很多出版社更感兴趣的是“书”,而非作家这个人。而“禁”,也的确成为国外媒体向读者“说事儿”的最好噱头。但就我和比基埃出版社的出版关系言,恰恰是同何碧玉教授说的不同的。只有我自己明白,比基埃为了我终生的写作和出版,有着怎样长远的出版计划和安排。我说过,他们最先计划翻译我的作品是《受活》,而《受活》翻译受阻时,《为人民服务》出来了,只好首先翻译《为人民服务》了。而《丁庄梦》外人完全不知道,是在我小说还没有写完时,比基埃的老板菲利普到北京通过陈丰问我在写什么,我简单讲了故事,他就当场决定,让我尽快写作,完稿后即刻翻译的。那时小说才写了一半,谁能知道会被禁? 《四书》是我在法国时,一字未写,只讲了故事的大致轮廓,出版社就决定要我写完初稿就交由他们安排翻译事宜的。如此,谁能料到它的不能出版呢? 别忘了,在我七、八本的法语作品中,还有《我与父辈》和《年月日》等那样和挣钱完全无关的散文和小说。而《受活》卖得好,是出版社也有些“意外”的。
说实在的,我不在意出版社在推介一本书上说什么,我更在意我在写什么和怎么写。《四书》、《受活》、《年月日》和刚刚出版的《日光流年》等,在法国更被人关注的是“怎么写”,而非“写什么”。一个作家对自己的写作自信了,别人怎么推介都没什么重要的。《洛丽塔》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作为“黄书”、“禁书”走进中国的,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今天的经典地位。《古拉格群岛》和《日瓦格医生》也是被禁而更受关注的,但那不是让我们更加地尊敬作家吗? 不在于书的封面上写什么,更在于封面以内写什么。今年《四书》在捷克出版,我不认识捷克文,但能猜想那封面上会写什么话。然而到年底,捷克媒体在盘点一年中大的文化事件时,称2013 年最大的文化事件是“中国作家阎连科的《四书》在捷克的出版”———由此,我就更不在意“封面文字”了。拉什迪的《午夜之子》和《撒旦诗篇》,全世界的翻译出版,都会在封面上写着“追杀”那样的介绍。可那两本伟大的小说,封面怎样的介绍,其实都无关紧要了。《日光流年》出版了,《炸裂志》正在翻译中,这两本书出版社怎样在封面上介绍那是他们的事,而这两本小说本身好不好,怎样写,写什么,这是我最要关心的。
高方: 我最近整理了一些关于您作品在法国的评论资料,注意到其中的三个关键词: “反传统”、“魔幻现实主义”与“政治批判”。例如,《为人民服务》被描述成为“表现出最‘反革命’的性欲,狂乱的情爱以及对官方正史无所顾忌的改写”,它“蔑视军队、革命、性欲和政治礼教最神圣的禁忌……无视传统”,而《受活》则被认为是“用闪光的语言写出的一本充满想象力、富有创意、荒诞幽默的小说”,这本“无视礼教的小说满载着生活与写作的乐趣,令读者赞叹不已”等等。您如何看待西方文学界对您所持有的这种文学印象? 事实上,成功译入西方国家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被标记上了某种文学印象,而在文学印象诱导下的西方读者,或许很难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拥有一种完整的认知。能否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阎连科: “文学印象”似乎是一个必然。俄罗斯文学、拉美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在中国也而西方国家的读者群,对我来说,法国的读者最为理想和成熟。我们有个误会,以为西方对中国作家的喜爱不是因为电影就是因为禁书,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电影和禁书,会帮助你开始翻译,但不能保证你长久地被接受。莫言、余华、苏童等,之所以有很多外译,能说都是张艺谋的努力吗? 禁书中谁都没有卫慧卖得好,可《上海宝贝》之后,读者就对卫慧的作品没有那么持续暖热了。
把话题转回到法国来,陈丰在法国 20 多年,她在台湾介绍中国文学在法国的情况时,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出版社会因为政治的原因,对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保持热情和支持。没有一个读者会因为对禁书的好奇而对一个作家的每本小说都要购买和阅读。”以《四书》为例,它是在中国没能出版的书,是因为某种所谓的敏感和犯忌。但去年《四书》在法国出版后,我到法国,所有的媒体大多问的都是这本小说为什么这样写,而非写什么。比如小说的语言、结构、小说中“孩子”形象的神奇与《圣经》和神话的运用等,他们并不怎么关心小说中的“大饥荒”和“大跃进”。还有《受活》,法国读者更关心的是你的想象力和讲故事的方法,而非别的。最难忘的事情是,《受活》出版后,在法国文学节上签售时,有一位 70 几岁的老太太,她把我那时出版过的 5 本法文作品每本都买两册,共是十本书,待签名时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她告诉我说,她的丈夫半年前去世了,说她丈夫是我忠实的读者,每本必看,有的书还会看两遍,可惜他不能活着见到我,所以她买两套十本签名书,一套送到墓地她先生的碑前边,一套留给自己慢慢地读。还有《年月日》,因为被法国教育中心选推为法国中学生的课外读物了,你就经常可以收到法国读者的来信和孩子们自制的圣诞贺卡。
类似的事情,只要出去,总是可以碰到。在英国、在美国、意大利、挪威、捷克等,都有这样美好的记忆和情节。对于读者,总体、大致的印象是,西方读者,关心你小说写什么,同时也关心你怎么写,有时甚至更加关心怎么写。但中国读者,更关心写什么,而疏淡怎么写。
高方: 中国当代文学是否能够在海外成功传播,出版社也是当中一个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环节。
就您的译作而言,英语世界为美国著名的格罗夫出版社( Grove Press) ,法国则是以出版亚洲图书著称的比基埃出版社( Philippe Picquier) 。您对上述两家出版社对于您作品的选择与翻译感到满意吗? 您对这两家出版社是否有所了解? 与他们是否有过交流与沟通?阎连科: 一般说来,决定翻译你作品的是出版社,而不是译者。当然,译者有他的推荐理由和推荐权,不过只是推荐而已。对于法国的比基埃和美国的格罗夫,还有别国的出版和翻译,我都非常满意。在我心中,出版社没有大小,能出好书就是“大”。比基埃和格罗夫对我的好,让我终生难忘和感谢。为了我的书,我去过法国四、五次。每次去,出版社的老总菲利普和他们公司的人,都对我和家人一样。四年前,美国格罗夫出版社安排我去参加纽约文学节,到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出版社是那么了不得。是备受争议的法国荒诞派大师贝克特和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以及《北回归线》作者亨利·米勒等一大批受“争论、压抑”作家所在的出版社。才知道当年他们创业时,为了让这些受争论、压抑的作家能够好好生活,安心写作,创始人 Barney Rosset 先生偷偷地变卖房产,把这些钱作为作家们的生活费,提前汇给这些作家,让他们安心写作,而不被争论、批判和生活所困而搁笔。大江健三郎先生当年听到这些故事后,决定就是不要版税也要把作品交到格罗夫。2012 年Barney Rosset 先生已经谢世了。但在四年前,我见到 Barney Rosset 先生是现任社长引荐的。彼此见面后,老人坐在轮椅上,对现任社长说的第一句话是,“他( 我) 在中国出版困难影响他的生活吗?如果他的生活困难了,出版社一定要照顾好他和他的家,让他别因为生活困难而写作受影响。”
当时我听了这样的话,眼泪差点掉下来。还有陈丰和她所在的比基埃,对我个人的写作和家庭生活之关心,都让人难忘和感慨。我知道,我这一生遇到他们,是我写作的好运,是我遇到了最好、最好的出版社。
高方: 就法国的出版社而言,法国著名汉学家何碧玉教授( Isabelle Rabut) 曾经指出,“仿佛出版23都有这种集体印象。有时候,一种文学被另一种语言所接受,正是以这种印象为桥梁、为标识。似乎没有印象,对方就无法辨别你,认识你。就如一个人必须有个名字一样,没有名字别人就无法把你和他人、人群区分开。而文学,有时是靠作家名字在另一国度存在的,有时是靠“文学印象”替代名字存在的。总之,你的作品决定着你的文学印象,文学印象又左右着你的接受和被接受,如我们一说魔幻就谈《百年孤独》一样。集体意识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为人民服务》在法国被“印象”和“标识”,我开始也有些不顺畅,后来就算了,随他们“印象”标识吧。反正我知道,那不是我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自《年月日》和《受活》后,这种标识的印象就慢慢改变了。还是那句话,怎样“印象”和“标识”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你作品本身达到的艺术高度。中国文学确实在海外是和“中国印象”分不开,这影响着中国文学整体的被接受。但要改变这种“印象”不能靠别人,还是要靠我们写出好的作品来。
我以为,一部翻译作品被异地的读者简单接受还不算有影响、被接受,而是改变或丰富了那儿读者的文学认识并影响了那儿作家的写作,那才叫真的“文学印象”和被接受。达不到这一步,都还是仅仅停留在翻译、出版和阅读的层面上。就此而言,我以为中国文学真正的“文学印象”在海外并没有形成,而形成的是“文学社会”印象。所以,中国文学对人家要有真正的“文学印象”,还有很远的路。别怕文学印象,就怕没有文学印象。
高方: 当今社会,随着各种传播媒介的急速发展,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载体,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也往往会变得更加迅速与广泛。比如由莫言《红高粱家族》诞生的电影《红高粱》,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蓝本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通过电影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又反过来带动了其译本的推出与认可。您是如何看待电影等新媒体对于文学作品译介与传播的作用的? 您是否考虑过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
阎连科: 我没有想过把小说改为电影而使自己的作品得到更为宽展的翻译那样的事。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和接受,最终还是要靠内力,靠作家和作品之本身,任何外力的推动都是暂时的。
高方: 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在西方国家的出版物中,翻译作品所占的份额非常之小,法国10% ,美国只有 3% 。而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的作品,或者说中国从西方国家翻译过来的作品达到了出版总量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中国文学输出与西方文学输入之间存在有巨大的逆差,中国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当中,仍然处于十分明显的边缘地位。您如何看待这种“边缘性”? 中国文学的弱势地位将长期存在,或是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 根据您对于西方市场与读者的了解,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改善这一边缘地位?
阎连科: 谈到文学,我们也总是会用经济的输出和输入来谈论,来比较。我不认为中国输入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是坏事,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吸纳性和包容性。要相信中国文化的强大和包容。以我们天下第一的中国菜为例,中国菜中的各种原料如味精、菠菜、芥菜、红薯、南瓜、佛手、辣椒、胡萝卜、青花菜,等等等等,不都是外来的物品吗? 最后不都被吸纳、同化、改变成了中国菜?
不怕输入多,就怕没输入。要相信中国文化、中国作家的吸收能力和创造性。但对于中国文学的输出,我说关键是我们要写出好作品,写出值得输出的作品来。如果以为这一步我们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了,那就把我们急于输出的态度和方法变一变。不是很想输出吗? 不是有很多资本钱财吗?
那就敞开门扉,让国外的出版社到中国来选文学作品,凡是他们选上的———不是我们选上、评上的,都给一定的资助让人家出。据说,现在,与写作和出版相关的很多机构都在花大价钱和大力气要把中国文学推出去,那就敞开大门,让外国出版社到中国来选人家喜爱的作品,不要我们选好后低三下四往人家手里塞。
我们要有一颗文学的大度心,文化的大国心。既然中国所有的出版物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那就让人家想出版什么就予以资助什么,别再进行那种权力机构的再审查和再评选。如此,中国文学的输出与输入,就会有较大的改变了,就不会那么“边缘”了。要尊重人家的读者和市场的需要,人家需要什么书,就配合人家资助什么书。说到底,我们对他国的市场与读者,都是隔着一层的。
高方: 近年来,包括您在内的众多中国当代作家以及翻译研究学者,都在为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做着许多踏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根据您个人的经历,您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主要面临着哪些方面的障碍? 同时,在中国文学不断“向外”的过程中,应当如何摆脱西方社会与文学范式的桎梏,从而书写出真实、完整、丰富的中国文学形象?
阎连科: 我没有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过什么。如果说做过什么,也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我以为,今天中国作家的作品,比起别国他地作家的写作,艺术上并不逊色和低矮。而桎梏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原因,除了文化、语言本身的因素外,就是太干预文学和文学的走出去。
我们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我们为推广中国文化花了那么多的钱,有专门的机构筛选、评议把哪些作家和作品向外推,为什么要筛选和评议? 就是要干预。中国的许多事情是,权力愈重视,结果愈糟糕。文学走出去,可能就是这结果。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这种恶习正在看似推动、实在阻碍着文学走出去。政府用大国和发展的态度面对文学,希望三朝两日,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就如中国经济样崛起和瞩目。这怎么可能? “文学要发展,他人不要管”。作家想写什么,就让他们写去。想怎么写,就怎么去写。就文学而言,谁都没有作家更懂文学应该写什么,应该怎么写。如此,当文学获得了真正自由想象、创造的天空,中国文学像中国菜一样,完成了吸纳后的创造,写出了作家个人的、丰富的、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故事”,完成中国文学的东方的现代性叙述,那时候,就不愁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了。而现在,是过分急切了。组织、花钱、评选、推动,甚至让中国人来翻译中国作品,然后自己印刷、自己发行、自己上报外译数目,这实则是一场闹剧和笑话。不是说中国人就不能翻译中国文学,而是说,无论怎样,你的母语不是外文,而是中文,不可能人人都有外语如母语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国外有不少专吃“中国饭”的出版公司和书店,你给我钱我就翻译,叫我翻译什么我就翻译什么,翻译完了,低廉印刷几百本,堆在某一家书店的书架上,如此而已,和读者、市场是没有关系的。翻译出版者,是为了一笔中国资助; 那些掌握资助的人,是为了年底上报一个数字; 而被翻译作品的作家,是为了一些虚荣心。文学输出,就是这样成为文学“发展式输出”的一个链环,从而也败落着中国文学的形象,阻碍着中国文学长远的翻译和出版。真的不知道中国文学应该怎样走出去,但一定不该这样“走出去”。
高方: 最后,非常感谢您能够与我们交流探讨中国当代文学译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您的许多意见与建议,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思考。最后,能否请您对海内外的翻译工作者们讲几句话?阎连科: 谢谢,谢谢,再谢谢! 深知你们对我们文学、文化的爱,甚至超越了对本土文学、文化的爱。翻译是富于爱而穷于利的事业,而你们,是这种爱的高尚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