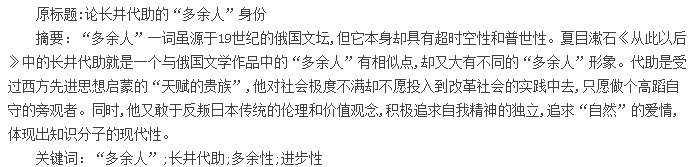
“多余人”一词源于19世纪初期的俄国文坛,最早见于屠格涅夫的小说《多余人日记》。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率先使用这个词语评价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多余人”成为当时典型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他们受西方启蒙思想熏陶,却又不能摆脱旧有的贵族习气;怀有重建社会的理想,却不能付诸行动,他们的性格呈现二重性冲突,即“文化的冲突、先进意识与阶级地位的冲突、历史使命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这是造成他们成为“多余人”的根本原因。虽然“多余人”产生于俄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它又是个具有超时空性和普世性的名词。任何时代里,只要有社会变革就会有“多余人”。尤其是变革伊始,神经敏锐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弊病积习有着清醒认识,当外来的先进思想传到本国,他们能最先嗅到变革气息,但由于种种因素他们没能参与到变革的实践中去,不能为社会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只能“无为”地生存着。被称为“国民大作家”的夏目漱石钟爱描写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知识分子也是漱石本人的真实写照。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双重局限,漱石在现实的压迫下既愤慨又无能为力,所以他的笔下就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多余人”气质的人物形象。《从此以后》中的主人公长井代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明治后期出身富贵的知识分子,受过现代化的教育和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以敏锐的神经感知到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但没有尝试改变社会,而选择了逃避,终日无所事事生活在自己的公寓里,以旁观者身份打量整个国家,满足于做一个“多余人”。
一、多余性
长井代助被称为“天赋的贵族”,他的父亲是明治维新时期新兴的资本家30岁的他没有工作只是依靠家里的资助生活。虽然代助自己表示“决不想过游手好闲的日子”,但他的确是在无所事事地活着。他的座右铭是“我什么都不想干”,或者“我的想法就是对什么都无所用心”。代助安然享受身体的寄生,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客观的冷静,”始终是保持“nil admirari”(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的冷淡心理)。代助对自己的寄生丝毫不感到难为情,而且面对要为生活打拼的朋友平冈,他还产生一种优越感,说“我今天悠然自得,何必自卑地去为尝试那些经验而折磨自己呢!”
他认为工作是对自身的折磨,并且以高傲的姿态俯视为面包而工作的芸芸众生。他每天的主要事情就是思考,然后得出形而上的结论,如“关系到面包的经验,也许是切实有用的,但这是卑俗的。人类如果不抛开面包和水去追求更高级的经验,就会失去做人的标准。”
他不愿意工作,不愿与世俗打交道,所以也看不起为了生存而劳动的人民大众,认为那样的劳动是“堕落的劳动”。代助既不愿与上层资本家为伍,又不愿意融入到底层民众中去,只能处于悬浮状态,成为无所作为的“多余人”。正如八住利雄所说,“其实他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谁的命令他也不会百分之百地去服从,另一方面,谁的意见他都不想认真地加以抵制。
其结果便成为一个无所作为的人。”
代助追求超脱世俗的生活方式,耽溺于在精神世界里思索和玩味,凭着这种思索他把头脑里的世界同现实的世界分割开来。但显然人不可能永远活在这样的世界。追求自由独立的代助,反对父亲为攫取经济利益而操办的政治联姻。而当他与三千代的结合受到家庭极力反对时,他的寄生性使他一度动摇对爱情的决心。选择爱情意味着与家庭决裂,这对没有自立过的代助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不想吃苦,考虑到要外出找工作的辛酸他甚至想过退缩。如果不是三千代发出“一死了之”的绝望呼喊,恐怕代助就会丧失反抗的勇气。
1907年3月,夏目漱石辞去东京大学教授的职务,转入朝日新闻社,由学者变成了专职作家。
1909年6月27日至10月14日连载在《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的《从此以后》是漱石进入朝日新闻社后创作的第四部作品。小说中的代助不想去工作其实是漱石对“工作”的社会功用产生怀疑。转职成为新闻记者后,漱石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保障,但在精神上远不如作学者自由,经济关系的羁绊又使他内心充满忧虑。夏目漱石对经济是极为敏感的,他在辞去大学教授职位之前曾常为经济苦恼,所以在虚构的文学世界里设定代助为一个不用为金钱忧愁的知识分子。可代助在享受身体寄生的同时必然会失去真正的精神自由。李光贞在《夏目漱石小说研究》中对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进行了分析,“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是从资本家、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后,要求独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同他们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不休的关系。”
这种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二律背反是代助的苦恼,是漱石的苦恼,也是长久以来知识分子的苦恼。“代助可以说是漱石的分身,在他验证无法进行纯粹知性生活的同时,平冈无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平冈是当时敢于行动的一类人,“我要将自己的意志付诸于现实的社会之中,要使现实社会按照我的意愿行事,哪怕一点也好。没有这样的保证,我就难以生活下去了,从这里,我才发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他们比“多余人”更进步。虽然实业行动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但这些人迈出了改变社会的第一步。他们的失败受到以代助为代表的“多余人”的嘲笑,这是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和凄凉。可夏木漱石也明白,知识分子在当时背景下注定要淹没在世俗的潮流中。平冈实业之战失败后,为了生活不得不投入找工作的滚滚红尘中,最后也被丑恶的社会同化,变得委曲求全、见利忘义。代助把自己不想作为的原因归结于社会黑暗。他认为,“向灭亡发展”是日本最典型的象征。在全盘西化的日本近代社会,西洋压迫下的国民被驱使着不息劳作,人人“精神困惫、身体羸弱、道德沦丧”,整个社会的精神、道义和肌体崩溃破裂,知识分子在这样国家里看不到光明和希望。
然而,代助却没看到自身的缺点:消极、怀疑。他是一个世纪病患者,对国家前途怀有悲观恐惧心理,整个人呈现一种颓废厌世状态。代助的多余感与他的怀疑主义有很密切的关系。他“生来就是对万物抱有怀疑的直率而敏锐的人。”他在学生时代就有理智上怀疑事物而产生的不安,“他的脑袋里充满了从古到今一些思索家常常反复考虑的毫无意义的疑念。”这些使他丧失了生活的热情,陷入“孤独的悲哀”和“怀疑的地狱”。
“多余人”的概念由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赫尔岑提出,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有觉醒意识却不能勇敢发动民众起义的贵族青年。叶甫盖尼·奥涅金、别林托夫、毕巧林、罗亭、奥勃洛摩夫等成为“多余人”的典型。在当时背景下,判定“多余人”的标准带有阶级意识,但随着时代发展,“多余人”一词有了新内涵。代助厌恶黑暗的社会,对一切现存秩序感到不满,可他并没有提出新的社会构想;他看到底层民众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困苦不堪,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试图拯救;他厌恶黑暗的社会,却没有让这个社会听到他的哪怕是一声抗议的呼喊。从某种意义上说,代助是个自私的人,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关怀天下、救国救民的意识。他一味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对整个社会冷眼旁观,在追求安逸生活的同时表示对他人的同情。他对社会不抱幻想,没有客观实在作为,只是置身事外做看客。代助的这种“自我”状态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西方人本主义精神与日本传统的专制主义相碰撞,造成日本近代自我的封闭性,“自我局限在追求‘内部生命’中的自我主体的真实,即集中在追求自我内部———个人的感觉、感情、情绪上的自由,以及在空想中的自我的充实”。
代助一味沉浸在自己营造的高级趣味的世界里,在空想中自我满足,他的“自我”缺乏社会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多余人”。
二、进步性
长井代助作为“多余人”的同时还是“超越旧时代的日本的人物”。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使他具有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首先,他反对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
30岁的代助整天蜗居在公寓里,父亲极力鼓动他去干实业去为国民尽点义务,但他总是阳奉阴违。因为他看到了传统的“利他主义”美德在当下社会中已经变质,过去的人总是“固守自己的利己主义立场,坚信是为了别人”。代助的父亲是脱胎于旧官僚的新兴资本家,他始终认为诚实是成功的充分条件。而代助却认为,传统的价值观念如“胆量”“诚实”“热情”等都需要重新建构,旧观念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像诚信和热情“都不是装在肚子里的现成的东西,它应该是当事者两人很好合作、互相信任的产物”,“与其说是自己固有的品性,毋宁说是精神交换的结果。”
这是一种辩证、多元的先进观念。其次,他批判现存的社会秩序。明治维新盲目西化,造成日本传统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激烈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经济迅速强大的同时,也使“金钱至上”的观念蔓延,从而导致信仰缺失,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日趋没落,民众变得麻木混沌,国民精神逐渐沦丧,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脱节严重。代助对这样的社会感到厌倦,当外部世界让人找不到精神寄托,他就将探索目光转向“自我”。一方面,代助对自己的身体引以为豪,他常对镜孤芳自赏,听到别人夸赞他的肉体丝毫不觉得难为情;另一方面,他常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习惯以手抚心感知心脏的跳动,这种对待生命的谨慎态度,使他反感“以死为荣”的传统价值观。他渴望饱享生之欢乐。虽然父亲企图像支配私有财产一样支配他,但他拒绝把自己纳入别人的生活轨道。他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索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像心理学家那样对人性进行深入剖析。长井代助的内向化表现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再次,代助追求自然的爱情。大学时期的代助出于“哥们儿义气”把心爱的女子让给好友,可数年之后重逢时,他发现三千代过得非常不好:幼子夭折、夫妻关系紧张、身体和精神都经受巨大压力。他意识到平冈与三千代的结合是个错误,而此时他对三千代的感情更加浓厚。可是与三千代在一起会面临着社会、家庭和友情三方面的压力。如果服从父亲的安排,他就可以继续悠然自得地活在纯粹知性的趣味世界中,并且能保留与平冈之间的友情,可是“代助认为,以非自主性为核心的伪善是一种大罪,这种伪善是杀害自己真性情的元凶”,他不愿违背自己的内心。摒弃伪善、追求自然的爱,反叛和批判意识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了一个“多余人”不多余的一面,即知识分子的现代性。
同为贵族知识分子,长井代助与俄国第一个“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有很大不同。奥涅金是地位稳固的封建贵族,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蒙,但其封建性根深蒂固;代助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贵族,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滋养,更具独立性。代助可被称为“新贵族”。“新贵族”一词鲜明地展现了代助的先进性与滞后性,反抗性与妥协性。许多学者着重研究《我是猫》的主人公苦沙弥,认为他是“多余人”的典型。《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第一部小说,主人公苦沙弥可以看作是漱石文学中“多余人”的雏形;而《从此以后》的主人公长井代助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多余人”。创造“多余人”形象的俄国作家们对其笔下的“多余人”评价说,他们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而且缺点除了与他们自己思想、阶级上的局限性有关外,更多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苦沙弥作为“多余人”,其悲剧性更多是因为自身局限:懒惰颓唐、迂腐懦弱。从某种程度来说,苦沙弥只是个“伪知识分子”,他不具备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在这方面长井代助要进步许多。
他看透社会状况,有着哲学家的思辨和心理学家的敏锐。他的缺陷是颓废怠惰,可他曾经也是热血青年,是黑暗现实社会浇灭了他的实业梦。苦沙弥的悲剧让人感到可怜,而代助的悲剧则让人感到可悲。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悲剧,这种悲剧融入了更多的社会因素。“多余人”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主导的社会因素和次之的个人因素,所以与苦沙弥相比,代助作为“多余人”更有启发性。
长井代助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多余人”,但他在小说结尾敢于争取三千代,并毅然决然地与家庭决裂,这是他将思想上的反抗化为行动的第一步。刘立善在《论夏目漱石<其后>中的爱与金钱》中说“漱石让代助外出谋职,旨在让他能保住以惨重代价换来的与三千代的爱情。面临物质力量强烈地支配着的社会,客观地认识现状,不为物质的压力所屈服,作一个有健全精神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是漱石在《其后》中对代助寄予的期望。”
参考文献:
[1]郭秀媛.再论“多余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108.
[2]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M].陈德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韩贞全.从“三部曲”看夏目漱石的精神世界[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99.
[4]八住利雄.读《从那以后》[J].陈笃忱,译.世界电影,1986(4):151.
[5]李光贞.夏目漱石小说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6]高西峰.解析《从此以后》中的新闻记者形象[J].日本文学研究,2013(3):126.
[7]李光贞.试析夏目漱石小说中的“明治精神”[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5):106.
[8]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9]刘立善.论夏目漱石《其后》的爱与“自然”[J].日本研究,1999(1):64.
[10]刘立善.论夏目漱石《其后》中的爱与金钱[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