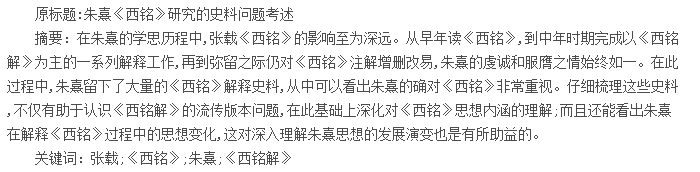
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早年读《西铭》,到中年时期完成以《西铭解》为主的一系列解释工作,再到弥留之际仍对《西铭》注解增删改易,朱熹的虔诚和服膺之情始终如一。从朱熹留下的大量《西铭》解释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对张载《西铭》是非常重视的。
仔细梳理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看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本文即拟对朱熹研究《西铭》的相关史料问题进行考述,以期进一步推动对朱熹《西铭》解义的研究。
一、《西铭解》的版本
《西铭解》是朱熹解释《西铭》的专篇文字。乾道六年(1170),朱熹草成《西铭解》。他追忆说:“向要到云谷,自下上山,半涂大雨,通身皆湿,得到地头,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时季通及某人同在那里。某因各人解此两句,自亦作两句解。后来看,也自说得着,所以迤逦便作《西铭》等解。”
云谷在芦山之上,乃崇安五夫至寒泉所经之地。朱熹此年夏天游芦山,故有云谷之行。从这时起,朱熹便开始着手草拟《西铭解》,直至此年秋天完成初稿。乾道八年(1172),朱熹序定《西铭解》,这标志着朱熹《西铭》解义工作的基本完成。
从传世文献来看,《西铭解》的流传版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所收的《西铭解义》。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不知何人编刻,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据昌彼得考证,此本编辑虽系按文体分类,但分前后集却又颇无章法,当属淳熙十六年朱子无职住于临安时,闽间书坊所搜得而随时付刻者。此本虽然非朱子手定,亦仅二十九卷,其文字与后来浙、闽刻本颇有异同,但不乏传世全集“足本”所未收之文,《西铭解义》即其一。
由此可见,《西铭解义》是朱熹《西铭解》的最初流传版本,即第一个版本。《朱子全书·西铭解》的校点者曾说:“淳熙本《文集》所载《西铭解义》因系朱熹初稿,文字异处太多,今不取。”
从朱熹《西铭》研究史的角度来说,正因为《西铭解义》是朱熹研究《西铭》的初稿,所以它才更能够代表朱熹最初对《西铭》的理解;“文字异处太多”,这恰恰说明朱熹研究《西铭》的思想变化。因此,从“朱子全书”之“全书”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取”的作法是否合适,还值得商榷。二、《朱子全书》本《西铭解》。尽管我们对《全书》本《西铭解》不取《西铭解义》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但《全书》本《西铭解》的价值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全书》本《西铭解》是以黄瑞节《朱子成书》元刻本为底本,校以《性理大全》永乐十三年刻本,并以《张子全书》万历三十四年徐必达刻本、万历四十六年刊本参校。
因此,从《西铭解》定本的流传来看,《全书》本应该说是目前所见最好的一个版本,是我们考察朱熹《西铭》解义工作最重要的文献依据。
二、《朱子语类》、《朱子文集》所见《西铭》解释史料
在《西铭解》之外,朱熹对张载《西铭》还有大量的散论性解释文字,这主要保存在《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之中。因此,这两部书中有关《西铭》的解释和评论文字,同样是我们考察朱熹《西铭》解义工作的重要史料。我们知道,《朱子文集》是朱熹亲笔撰写的文字,这可以说是了解朱熹学思历程的第一手材料。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即使是作者亲笔撰写的文字也不一定就能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实想法,因为在作者写下这些文字时,由于受到各种外在制约因素的影响,作者的思想可能会有所保留,用语也更为谨慎。例如:在天体运行问题上,朱熹对张载“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之说非常推崇,但由于他顾虑到时人对此不易理解,因此在作《诗集传》时仍然采用了较为传统的“右旋说”。
黎靖德编订的《朱子语类》也保存了朱熹解释《西铭》的大量史料。与《朱子文集》相比,《语类》作为老师与弟子之间直接对话的原始记录,它或许更能代表老师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作为师生之间的直接交流,语言表达的顾忌性就会大大减少,在著述中不能或不便于表达的思想,在师生问答之际,就会以口语的形式零散而直接地表达出来,显得更为真切。值得注意的是,“语录体”在彰显其优越性的同时,实际上也已暗示了其自身的劣势和不足。也就是说,语录固然能反映出师生在问答之际的真实想法,但是由于它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再加上记录者在理解和表达能力上的参差不齐,这就很容易造成思想表达的歧义性,有些甚至是自相矛盾。但是不管怎么说,《朱子语类》的确是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材料,它不仅能够弥补撰著文字表意的有限性,而且还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答问者的思想进展情况,甚至可以从答问过程的记录中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
通过比较《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的优缺点,我们认为,要想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朱熹的《西铭》解义工作,我们就必须在《西铭解》的基础上,采取扬长避短的策略,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文集》和《语类》所保存的朱熹解释《西铭》的史料。
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三、《西铭解》释义之演变
从历史上看,《西铭解》一直被认为是朱熹解释《西铭》的最重要著作。但是,通过梳理朱熹的所有著述,我们发现,朱熹对《西铭解》中的具体解释并未因该书的完成而止步,而是处于不断地修改中。从早年草拟《西铭解义》到《西铭解》的定稿,再到晚年的讲论,在此期间释义用词的变化,都反映出朱熹对《西铭》认识的不断深化。试举三例,以说明《西铭解》释义之演变。
第一,《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朱熹《西铭解》曰:天,阳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阴也,以至顺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禀气於天,赋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无间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体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无息之谓,万物之所资以始者也;坤者,顺而有常之谓,万物之所资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而父母乎万物者,故指而言之。
在《朱子语类》中,程端蒙记录了朱熹对《西铭》首句的解释。其云:《西铭解义》云:“乾者,健而无息之谓;坤者,顺而有常之谓。”问:“此便是阳动阴静否?”曰:“此是阳动阴静之理。”暂且不论“乾健坤顺”与“阳动阴静”的关系,只要对以上两条引文略加比较,我们就很容易能看出,《西铭解》对“乾健”、“坤顺”的解释要比《西铭解义》更为完整、准确。
第二,《西铭》“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西铭解》曰:孝子之身存,则其事亲也,不违其志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亲也。仁人之身存,则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天也。盖所谓“朝闻夕死”、“吾得正而毙焉”者。故张子之铭,以是终焉。
我们知道,朱熹曾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围绕《西铭》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对于朱熹而言,这些往复论辩是推动他更为深入地阐释《西铭》思想的重要力量。朱熹对此句解释的前后变化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朱熹后来对此解释感到不满,他在《答郑子上四》中就表达过这种疑虑。朱熹说:“《西铭》卒章两句,所释颇未安。试更思之,如何?向来诸书,近来整顿愈精密矣,只是近处难得学者肯用心耳。”
在《答吴伯丰》的信中,朱熹不仅承认“旧说误矣”,而且还作出了修正。朱熹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二句所论甚当,旧说误矣。然以上句“富贵”、“贫贱”之云例之,则亦不可太相连说。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则其事亲也,不违其志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亲也。仁人之身存,则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天也。盖所谓‘夭寿不贰’,而‘修身以俟之’者。故张子之铭,以是终焉。”似得张子之本意。
此处朱熹所改,与《朱子全书》本《西铭解》的主要差别在于倒数第二句。《西铭解》“盖所谓朝闻夕死,吾得正而毙焉者”,源自于《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及《礼记·檀弓上》“曾子易箦”之事。答书中“盖所谓‘夭寿不贰’,而‘修身以俟之’者”,则直接承自《孟子·尽心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之说。那么,朱熹为何会以旧说“未安”、“误矣”,而认为后来所改“似得张子之本意”?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不同呢?
先来看朱熹对《孟子》“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的解释。朱子说:夭寿,命之短长也。贰,疑也;不贰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张子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愚谓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
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则亦无以有诸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寿贰其心,智之尽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他在解释《西铭》“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时也说: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
故事天者尽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则亦天之舜也。申生无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寿不贰,而修身以俟之,则亦天之申生也。”张载曾说:“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
在张载看来,人之气质不可改变的只有死生修夭,即自然生命的长短。因此,在人面对生死存亡之事时,应该顺应自然,不可强求,并以此批评道家追求长生乃是“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人能够做的就是遵循孟子所说的“修身以俟之”,但此“俟之”并非只是单纯地等待,而是通过“修身”将人的自然生命提升至道德生命的高度,因为只有“道德性命”才是“长在不死之物”,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孟子所谓的“立命”。
再来看“朝闻夕死”与“吾得正而毙焉”。“朝闻道,夕死可矣”,朱熹解释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
朱熹所谓“生顺死安”,应当是受《西铭》“存顺没宁”之说的启发。如果这一判断不误,那么,朱熹以“朝闻夕死”解之,尚不算为误。“吾得正而毙焉”,曾子所谓“正”,当即孟子所谓“正命”之“正”。合而观之,朱熹《西铭解》之说,从义理解析的角度看,均是符合先秦儒学的古义。这样一来,朱熹所谓的“未安”、“误矣”必有其他原因,此即是朱熹所凸显的“事亲—事天”逻辑架构,这也是朱熹解释《西铭》的一个突出特点。
朱熹之所以坚持以“事亲—事天”逻辑架构解释《西铭》,笔者认为这与张载对《西铭》的定位有关。张载曾说:“《订顽》之作,只为学者而言,是所以‘订顽’。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学者心于天道,若语道则不须如是言。”
陈来先生认为,《西铭》要解决的是如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宇宙,其“民胞吾与”等等的说法,其真实的用意并不在于要用一种血缘宗法网络编织起宇宙的关系网,而是表明,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人就可以对自己的道德义务有一种更高的了解,而对一切个人的利害穷达有一种超越的态度。
由此看来,朱熹之“事亲—事天”的解释逻辑是符合张子本意的。其弟子徐子融也评价说:“先生谓‘事亲是事天底样子’,只此一句,说尽《西铭》之意矣!”
再由前引文亦可看出,朱熹不管是解释《孟子》“夭寿不贰”章,还是解释《西铭》“不弛劳而底豫”章,始终贯穿着“事亲—事天”的解释逻辑,而“事亲”与“事天”的结合,不仅在语意表达上比“朝闻夕死”、“吾得正而毙焉”更为具体和丰富,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朱熹在这一框架下特别强调了“修身”的重要性,正所谓“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综合来看,朱熹以孟子“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解释《西铭》末章,这不仅是朱熹坚持“事亲—事天”解释逻辑的结果,而且与张载自身对《西铭》“只欲学者心于天道”的定位也是相符合的。朱熹在修改后所谓“似得张子之本意”,可见其对旧说的不满,对新说的自信。
第三,“论曰”一段与“某既为此解”一段与《西铭解》的关系。《朱子全书》本《西铭解》将“论曰”一段与“某既为此解”一段相连,而与《西铭解》正文相分。束景南先生在《朱熹年谱长编》中将此两段文字合称为“《西铭后记》”。
笔者认为,束先生此说尚缺乏足够的证据。理由有二:
其一,“论曰”一段与“某既为此解”一段,虽然均提到杨时对《西铭》的评论,但朱熹立说的重点显然不同。前一段中,朱熹说:“龟山第二书盖欲发明此意,然言不尽而理有余也,故愚得因其说而遂言之如此。”由此可见,朱熹虽然批评杨时有“言不尽意”之嫌,但仍然肯定了其“理有余”,并且表明自己的解释是根据杨时之说推阐而来。
后一段中,朱熹说:“此论所疑第二书之说,先生盖亦未之许也。”
很显然,“此论”指的是“论曰”一段;“所疑第二书之说”,指的是前段朱熹评论杨时之语。也就是说,朱熹从伊川对杨时“未之许”的态度中,看到了自己对杨时的怀疑与伊川之论杨时有“暗合”之妙。在这段文字中,朱熹充分表露出对杨时晚年论“理一分殊”之说的赞同,从而也表明了他写下这段文字的初衷:“因复表而出之,以明答书之说诚有‘未释然’者,而龟山所见,盖不终于此而已也。”
一方面,朱熹证明了自己对杨时《答书》质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杨时对“理一分殊”的理解确实是不断深入,朱熹所谓“年高德盛而所见始益精”,即可见此意。
其二,“某既为此解”云云,指的是朱熹在完成包括“论曰”一段在内的《西铭》解释文字之后所发的议论。也就是说,“某既为此解”一段与朱熹《西铭解》并非作于同时。那么,它与“论曰”一段是否作于同时呢?显然不是。《朱子语类》为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朱熹曾说:《西铭》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为父,坤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兹藐焉,混然中处,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于篇末亦尝发此意。
此处所谓“篇末”即指“论曰”一段文字。因其系于《西铭解》正文之后,故朱熹有“篇末”之称。
这就说明,朱熹在《西铭解》正文之末,曾对“理一分殊”之意有所阐发,而“论曰”一段又恰恰证实了朱熹此说。其云: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会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蔽;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
从《西铭解》所谓的“一统而万殊”、“万殊而一贯”,到《朱子语类》朱子所说的“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一”,这体现了朱熹对“理一分殊”理解的深入和表达的完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论曰”一段与“某既为此解”一段并非作于同时,前者属于《西铭解》的内容,应该是在乾道壬辰(1172)秋完成,后者作于此年冬天。
束景南先生将二者统称为“《西铭后记》”,显然不符合事实,但束先生之说却提示我们可以把“某既为此解”一段称为“《西铭后记》”。
《朱子全书》本《西铭解》将此二段相连,而与《西铭解》正文相分,亦欠妥当。既然“论曰”一段属《西铭解》正文,当然应该与正文相连;“某既为此解”一段属《西铭解》完成之后的追记,故可以将其与“论曰”一段相分,以示追记与正文之区分。
四、朱熹《西铭》解义的前后变化
通过上节对《西铭解》所涉史料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历史上,《西铭解》虽然是朱熹解释《西铭》的最权威文本,但却并非是朱熹的最后定本,或是朱熹最满意的版本。朱熹虽然也非常看重《西铭解》,但其释义之演变却反映出朱熹对《西铭》理解的不断深化。本节将关注点由《西铭解》扩及到朱熹所有的《西铭》解义工作,通过疏解文献,进一步展现朱熹《西铭》研究的丰富面向和前后变化。兹举二例:
第一,“承当”之说。朱熹《答吴伯丰五》记载:“‘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近见南康一士人,云顷岁曾闻之于先生,‘其’字有‘我去承当’之意,今考经中,初无是说。”
“《西铭》‘承当’之说,不记有无此语。然实下‘承当’字不得,恐当时只是说‘禀受’之意,渠记得不子细也。”此段引文中,前者乃吴伯丰之问,后者乃朱熹答语。“南康士人”即周谟,《朱子语类》中即存有周谟记朱子之语:“‘吾其体’、‘吾其性’,有‘我去承当’之意。”
尽管朱熹在《答吴伯丰五》中否定了“其”字有“我去承当”之意,但这并不代表朱熹早年就没有此意。余英时先生认为,道学家继承了孟子“大有为”的承当精神,朱熹提出《西铭》“吾其体”、“吾其性”有“我去承当”之意,大概是很可信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朱熹始终会以“承当”精神去解读《西铭》,只是想指出,朱熹早年读《西铭》可能真的体悟出了“我去承当”的精神价值。也就是说,《语类》中周谟所记并非出于虚构,也并非朱熹所谓的“渠记得不子细”。事实可能是,朱熹确曾这样讲过,其“不记有无此语”的含糊表达,也暗示着这一可能性的存在。
第二,“塞”之义。《朱子语类》记载:问:“先生解《西铭》‘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后来改了,只作‘充塞’。横渠不妄下字,各有来历。其曰‘天地之塞’,是用《孟子》‘塞乎天地’;其曰‘天地之帅’,是用‘志,气之帅也’。”
朱熹最先认为“天地之塞吾其体”之“塞”是“窒塞”之义,但通过对《西铭》用语的通盘考察,朱子最终还是以“充塞”替代了“窒塞”。朱熹的根据有二:一是“充塞”之义更符合孟子“塞乎天地”之说;二是认为“横渠不妄下字”,字字“各有来历”,正如他晚年所说的:“张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
由此分析不难看出,朱熹对《西铭》的研究,即使是一字一词,也不轻易放过,更不囫囵迁就,而是孜孜以求,锱铢必较,“横渠不妄下字”的印象,也是他解释《西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当然,朱熹的严谨态度和依从经典的立场,大多时候都使得他对《西铭》的解释细致而妥帖,但有时也可能使得《西铭》的诠释视域变得狭窄,如朱熹对“我去承当”精神的否定,对“理一分殊”思想的特别表彰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张载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
五、结语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对前辈学者的继承,张载即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位。朱熹一生虽然对张载的《正蒙》颇多微词,但却终生服膺《西铭》之教。他不仅有《西铭解》的专篇注解,留下了大量解释和评论《西铭》的文字,而且还与同时代的诸多学者展开论战。这些工作,无疑极大地扩大了《西铭》的历史影响。
通过细读朱熹解释《西铭》的文献,我们认为:要准确把握朱熹的《西铭》解义工作,就必须把淳熙本及《朱子全书》本两种版本的《西铭解》进行综合研究,还需要对《全书》本《西铭解》中“论曰”一段及“某既为此解”一段与《西铭解》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当然,还需要对《西铭解》释义之变化以及朱熹其他《西铭》解释之变化均有细致的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朱熹在《西铭》解释中的思想变化,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