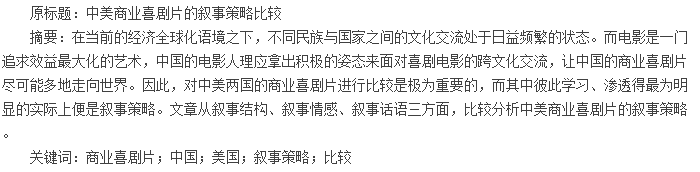
喜剧是一种自电影诞生以来就一直兴盛、始终吸引着各个年龄段和阶层观众的类型电影。早在默片时代,美国好莱坞就涌现出了诸多优秀的喜剧电影,以卓别林为代表的喜剧明星享誉世界,为喜剧电影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于欢乐的追求是具有普适意义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拍摄了带有滑稽戏意味的"李阿毛"等系列电影。[1]
到现在为止,中国喜剧电影不仅在内涵和美学意蕴上更为丰富,在商业运作方面也更为成熟。
但是,与美国的商业喜剧片已经形成风格迥异、题材多样化的现状不同,我国的商业喜剧电影从发展上而言目前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之下,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处于日益频繁的状态,而电影是一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艺术,中国的电影人理应拿出积极的姿态来面对喜剧电影的跨文化交流,让中国的商业喜剧片能够尽可能地走向世界,占领更多的市场。因此,对中美两国的商业喜剧片进行比较是极为重要的,而其中彼此学习、渗透得最为明显的实际上便是叙事策略。一部电影在叙事结构、情感以及话语上的选择直接决定了电影的品位以及喜剧性的构建。
一、中美商业喜剧片的叙事结构
一部电影的叙事方法可以是千奇百怪的,而电影的匠心所在往往在于其叙事结构上,电影的叙事结构主要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其内在的逻辑、思路,另一个层次则是它外在的开头、发展、高潮和结尾。换言之,叙事结构就是导演如何"讲故事"的大致框架,脱离了叙事结构,电影所要承载的信息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喜剧电影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部分喜剧电影的喜剧效果恰恰是要通过特殊的表达方式才体现出来。中美两国的商业喜剧片在叙事结构上都经过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这实际上也是电影艺术发展潮流的一个缩影。
早期美国的喜剧电影往往都采用单线叙事,这一方面是电影的技术限制(如默片时代电影的表现力有限,观众往往只能看到演员夸张的肢体动作与表情等,难以接受过于复杂的剧情),另一方面也与观众的思维习惯有关。以卓别林自导自演的《城市之光》(CityLights,1931)为例,全片讲述的是一名流浪汉爱上了双眼失明的卖花女的故事,采用按照时间顺序的线性叙事方式。先是介绍了流浪汉对卖花女的一见钟情,并在艰难度日之时依然想着帮助对方复明。接下来讲述的是流浪汉意外地拯救了一名想要自杀的富翁,翻脸不认人的富翁打碎了流浪汉的希望,流浪汉只好凭借着羸弱的身躯去打拳攒钱,之后又经历了被强盗抢劫、入狱两年的坎坷经历,最终流浪汉还是帮助卖花女重见光明。观众尽管为流浪汉的命运纠结,但是并不怀疑最后的大团圆结局。而随着观众欣赏旨趣的提高,单线叙事的电影已经不能满足部分观众的需要,尤其是新世纪电影经过了诸多叙事大师的实验与改造以后,多线的、环环相扣却又繁而不乱的叙事结构深受观众推崇。
这一时期出现的商业喜剧电影如《情人节》(Val-entinesDay,2010)、《新年前夜》(NewYearsEve,2011)、《爱在罗马》(ToRomewithLove,2012)等都是多线叙事的喜剧作品。而其中最为精妙的莫过于以非凡的控线能力著称的盖·里奇执导的《偷抢拐骗》(Snatch,2000)。电影采取的是环形结构,[2]一个大事件中又可以分为多个小事件,而每个小事件的叙述顺序并不严格遵守发生的顺序,而是不断打断叙述。电影实际上一开始就已经介绍了故事的结果,随后再步步跳回,当A事件叙述到一半时,跳回B和D事件,当C故事叙述到一半时,又回到A事件。这样的叙事手法能让导演通过剪辑更好地控制叙事节奏和给观众留下悬念的时机,同时让观众为导演设置的诸多紧凑的"巧合"而大呼过瘾。
相比之下,中国喜剧电影则往往更倾向于单线叙事与线性叙事。但是这种叙事方式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故事较为单一的,以周星驰系列喜剧为代表的电影;一种则是拼贴式、碎片化的,以冯小刚贺岁片系列为代表的电影。以带有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特色的,李力持执导的《唐伯虎点秋香》(1993)为例,电影讲述的是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与华府侍女、貌若天仙的秋香之间的爱情纠葛。唐伯虎为了追求秋香,先是进入华府成为家丁华安,随后又帮助华府摆脱了宁王的刁难,最后在多次破解了华夫人设置的障碍后迎娶秋香。可以说电影在这条主线之外没有任何支线,观众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唐伯虎的身上。
而冯小刚则在电影中创造了一种"小品拼贴"式的叙述方式,受编剧王朔的影响,他的《甲方乙方》《私人订制》等电影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个小故事,甚至是一个个来自网络和相声艺术的小"包袱"在一条主线(圆梦公司)之上的拼凑。在宁浩出现以后,中国商业喜剧出现了明显的模仿盖·里奇的多线索、多巧合、小片段的叙事方式。[3]
以《疯狂的赛车》为例,电影中艰难谋生的前自行车车手耿浩与奸商李法拉,李法拉与妻子以及两个业余杀手,来自台湾的黑帮以及泰国的毒贩,连同厦门当地的警察几路人马因为种种意外而互相扯上关系,又因为涉及扣人心弦的犯罪题材,宁浩在叙事上毫不拖泥带水。小人物的闯荡、大佬们的心怀鬼胎等,都在迅速推动的剧情之间展示,而人物因为种种巧合造成的倒霉也让观众捧腹大笑。这样的叙事结构与传统的叙事方式相悖,在时间与空间的安排上都对导演要求极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宁浩在后来的《黄金大劫案》与《无人区》中放弃这种太过复杂花哨的叙事方法的原因。
二、中美商业喜剧片的叙事情感
电影作为艺术作品,传达给人们审美享受固然是其首要目的,但是它还要带给接受者一种来自思想、伦理和道德上的教化性,以达到如贺拉斯在《诗艺》中强调的"符合众望"[4].尤其是中国的戏剧理论之中,"寓教于乐"始终是一个重要内容。这就要求电影在叙事中一定要具有某种情感,以让观众能够被这种情感打动,与剧中人物产生一种同理心,将艺术品的审美性和功利性、娱乐性和教育性结合起来。可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商业喜剧电影都具有传达各种情感与教化的"微言大义"功能,但是由于面对的观众不同,因此在选择的情感倾向、表达的具体方式上,中美双方仍有一定的差异。
美国喜剧电影在叙事情感上比较倾向于表现小人物的种种霉运、无能,让观众感到亲切,同时内心中的某些欲望得到释放。早期的美国喜剧强调一种"笑中带泪"的情感,在电影表面上的逗乐下却是让观众掬一把辛酸泪的沉重。如《城市之光》背后是荒谬的、贫富差异极大的社会现实,主人公所代表的是面临饥饿与贫困的穷人们。
而到了商业性更强的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鞭挞丑恶的任务已经渐渐从喜剧电影中淡化了,谋求休闲与愉悦成为电影至高无上的目标。这一时期尽管电影仍然会表现社会的阴暗面,但往往通过主人公迫使"坏人"们倒霉来制造笑料,同时,小人物出身的主人公们也往往因为命运的捉弄而措手不及。如《宿醉》(TheHangover,2009)中的道格、菲尔、西德和阿兰,四个男人都是极为普通的美国中年男人,四人在拉斯维加斯的派对中因为嗑药醉酒而惹出了一系列鸡毛蒜皮的倒霉事,甚至还招惹了当地黑社会成员。就价值立场而言,电影并不针对什么社会问题,也不蕴含什么批判力量,电影的主人公们所犯的错误尽管略微出格,但完全符合人之常情。
国产喜剧电影同样追求一种亦庄亦谐的叙事情感,也同样会表现小人物们的无奈和性格弱点,但是国产喜剧更讲究一种对道德感和价值观的体现。如在《黄金大劫案》中,主人公小东北的爱情是表,而他以及他的父亲、东北救国会等人的爱国之情才是叙事情感的里。正是这蓬勃的爱国之情才迫使他们与关东军对抗,夺取日本人准备购买军火的黄金。类似这样的爱国情感在《举起手来》(HandsUp!2003)等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喜剧电影中更是层出不穷。
三、中美商业喜剧片的叙事话语
如果说叙事情感体现的是电影的"道",那么叙事话语体现的就是电影的"技".在西方叙事学的研究之中,无论是早期叙事学还是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叙事话语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层面。[5]无论导演希望传达怎样的教化作用,希望得到观众怎样的心理认同,最终都要依靠具体的叙事话语来实现。表现在电影中则是导演所运用的各种连接故事情节的剪接手法,突出人物特点或心理活动的标志设计,增加电影艺术感染力的声画结合运用等,都可以视作电影的叙事话语。
良好的叙事话语的运用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有效地调动观众的情绪。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商业喜剧电影的表现手段还远不如美国同类电影丰富多样,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导演也大有奋起直追之势。
早期的中国喜剧电影往往只以让人忍俊不禁的台词来增加喜剧效果,如周星驰的"无厘头"台词和冯小刚的"京味儿"调侃。然而到宁浩充满游戏感的电影剪辑后,就出现了对美国喜剧电影极具想象力的叙事话语的多种再现,如快速剪接、镜头的变格、巧妙的转场、奇怪的摄影机位等。如《偷抢拐骗》中将画面切割为几个部分,给观众呈现不同空间下不同人物的表现,宁浩在《疯狂的石头》中对这一手法进行了极为到位的模仿。如麦克与房地产商进行最后的决斗时,画面分成了三个部分,剑拔弩张的两人在左右两边,中间则是房地产商办公室的一幅巨大的"忍"字,制造出了一触即发的喜剧效果。音乐也是美国喜剧电影惯用的叙事话语之一。而在中国喜剧电影中,在汲取对音乐的利用这一点时,又改变了具体的音乐选择,如《夏洛特烦恼》(GoodbyeMr.Loser,2015》中,就大量运用了极具时代感的20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一方面是契合电影的"穿越"主题,另一方面则也是为了喜剧效果的制造。如袁华一出现时背景音乐往往就自动切换为费玉清的《一剪梅》,这种怪诞、反复、公式化的手法,实际上恰好是符合伯格森在《笑---论滑稽的意义》中强调的笑与机械、重复之间的关系的。
事实上,喜剧艺术绝不仅仅意味着丑化、夸张和搞怪,商业电影也不意味着浅薄和低俗,当商业与喜剧相结合时,除了能够给观众带来数不尽的欢乐以外,同样可以产生极具感染力的思想内蕴和艺术效果。要想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商业喜剧电影注重各方面的艺术突破,尤其是在叙事艺术上。目前中美两国在商业喜剧片的叙事策略上仍有一定差别,总体来说,美国喜剧电影的历史更为悠久,商业化更为成熟,无论是"外显"的技术层面还是"内化"后的精神内核,都为中国喜剧电影提供了众多可以借鉴的理论和素材。
就当前中国导演大胆探索的结果来看,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趋同趋势越来越明显,两国的艺术差距和市场品位之间的距离正在缩小。人类追求愉悦、渴望欢乐的情感是普遍且永恒的,商业喜剧电影作为一种满足大众休闲的文化产品,它的发展也势必不会停止,而中美两国商业喜剧片在叙事上的手法、内涵等各方面的开掘也不会止步。
可以预见到的是,在未来,不仅中国观众能够充分欣赏美国喜剧电影,美国观众也将普遍地从中国喜剧电影中获取欢笑。
参考文献:
[1]饶曙光。旧中国喜剧电影扫描[J].电影艺术,2005(06)。
[2]王璐璐。盖·里奇电影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3]陈捷。宁浩的类型与意义[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02)。
[4]薛永武。试论贺拉斯《诗艺》的理论体系[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2)。
[5]南帆。叙事话语的颠覆:历史和文学[J].当代作家评论,199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