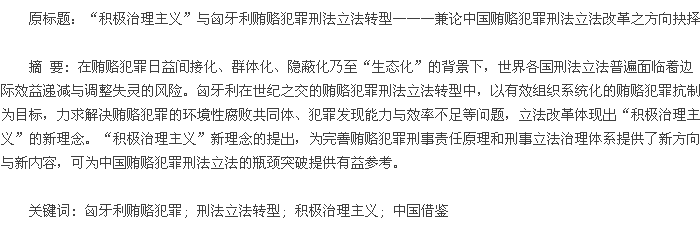
腐败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贿赂是腐败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从古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十二表法》,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员治罪条例《尹训》,再到 2003 年高度整合国际反腐经验与智慧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人类与腐败的角力已历经 21 个世纪,如何提高国家腐败治理能力、建构有效立法体系,正为全球所共同关注。匈牙利地处东、西欧交汇处,法律文化谱系上的大陆法系基因、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的制度基础,造就了其贿赂犯罪立法的特色。然而,其因循的立法理念、固有的立法机制,也造成了以新型犯罪为驱动的跟踪型、被动性立法格局,刑法无法面对社会转型中贿赂犯罪爆发的尖锐矛盾。世纪之交,匈牙利探索创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将瓦解贿赂犯罪“共犯结构”、重构“囚徒困境”作为立法转型关键,以“监督责任理论”、“对称治理理论”、“组织结构责任理论”、“权力属性理论”为基础,重构立法体系,提升了犯罪治理能力。中国正步入社会转型深化期,腐败问题久治难愈,立法更新缺乏新理念指导,立法“活性化”与犯罪膨胀化矛盾突出,贿赂犯罪立法向何处去,成为国家法治大厦之基石问题。全面解构匈牙利贿赂犯罪立法演进中的理念转变,分析“积极治理主义”在摆脱立法困境中的作用,再造中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体系的理论基础,是贿赂犯罪立法“从困境中突围”的关键。
一、匈牙利贿赂犯罪刑法立法的生成与完善
( 一) 匈牙利现代贿赂犯罪刑法立法的生成
1878 年,匈牙利颁布了以该国着名刑事辩护律师 Codex-Csemegi 之名命名的首部刑法典,“二战”后,以社会主义价值与政治原理为指导,匈牙利分别于 1951 年和 1961 年修正刑法典总则与分则,削弱德国刑法教义主义的影响,构建起社会主义“一元化”的刑法典体系( 第二部刑法典) 。
20 世纪 40 至 70 年代,是世界格局的重构期与各国现代法制的转型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匈牙利贿赂犯罪立法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同一时代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大陆法系贿赂犯罪立法的发展相类似,匈牙利贿赂犯罪立法围绕对公权力的规制展开,但又有其鲜明特色:
一是区分公权力属性的“二元”立法体系。尽管受到前苏联及大陆法系立法模式的影响,但匈牙利贿赂犯罪立法在罪名体系上,基于对不同属性的权力权钱交易危害性的认识,采取了区分化的政策,刑法典分别在第 11 章“违反政府行政、司法管理犯罪”和第 13 章“危害国家经济犯罪”,就公职人员( public official) 与国有经济组织( stateowned enterprise,other state owned economic body)人员贿赂犯罪做出规定,前者的刑罚高于后者。
二是犯罪行为模式多元。大陆法系国家通常仅将索取与收受贿赂行为规定为犯罪,匈牙利则在公职贿赂罪中将“索取或收受非法利益”( 即,受贿罪,第 149 条) 、“行政贿赂”( 即行贿罪,第 151条) 及“利用影响力交易受贿”( 第 153 条) 犯罪化[1],该规定为匈牙利刑法所独有。三是权责制配刑原则。在明确身份的犯罪构成意义的同时,赋予身份对刑罚配置的决定机能,明确提高高职位身份者实施贿赂犯罪的刑罚,刑法典第 149 条对高职位公职人员受贿的刑罚幅度为 2 年以上 8 年以下,而普通受贿罪则为 6 个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四是不对称配刑原则。刑法典对受贿罪与行贿罪配置不同的刑罚幅度,对贿赂犯罪的双方实行差别化的处遇政策。其中,公职受贿罪的刑罚为 6 个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公职行贿罪的刑罚则为 3 个月以下。
( 二) 匈牙利现代贿赂犯罪刑法立法的发展
在前社会主义阵营中,匈牙利较早认识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在 1968 年开始了“新经济机制改革”,在苏联与南斯拉夫模式之外创建了第三种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将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承认企业利益的独立存在,确立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改革的核心。[2]多元经济成分合法化、企业利益独立化,动摇了经济运行中公权力原有的平衡,激发了权钱交易的内在动因,原有的、局限于公权力范围内的贿赂犯罪立法体系已无法满足犯罪治理的需要,1978 年匈牙利修正贿赂犯罪立法: 一是法益属性上采“不可收买性说”,只要公职人员索取、收受或做出收受非法利益的允诺即构成犯罪,将违反职责设定为受贿罪的加重情节; 对行贿罪做对应区分,加重处罚诱使公职人员违反职责的行贿行为。二是立法模式上变分散立法为集中立法。所有贿赂犯罪被集中规定于第15 章第7 节“危害公共职务廉洁罪”中,提高刑法威慑力。三是罪名体系上区分公职 人 员 ( public officials ) 与 非 公 职 人 员( employee or member of a budgetary agency,economic operator or 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 ,创立新“二元”体系。经济改革后,为区别化、细致化不同类型贿赂犯罪的危害性,匈牙利在公职领域设贿赂罪、利用影响力交易受贿罪和打击披露贿赂信息人员罪,同时建构非政府组织成员贿赂犯罪罪名体系,并对非政府组织人员受贿罪主体做非政府组织成员与代表人的区分,设立不同罪名。四是治理重点上专设司法受贿罪,重视维护司法清廉。这一立法模式,即使在现行欧洲国家的立法中亦属独有。经过立法修正,匈牙利构建起跨越公职与非公职领域、重点突出、法网较为严密的规制体系,现代贿赂犯罪立法体系正式成型。
值得提出的是,匈牙利 1978 年刑法典对贿赂犯罪立法的修正仅具局部完善意义,表现为: 在立法修正动因上,仍是以犯罪的新领域、新模式为导向的“跟踪型”、“回应性”立法,仅是将发生于新领域的新型危害行为纳入刑法调整; 在立法理念与罪名体系设计上,仍是以受贿罪为核心的“权力型”体系,忽视行贿罪在贿赂犯罪场中的源头作用。究其原因,贿赂犯罪刑法立法与国家经济体制模式相关。尽管匈牙利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即开始了价格体系、财政、投资、物质分配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是在国家计划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非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型。“1970 - 1980 年代的中央计划收缩和企业日益扩大的自主权并不意味着出现了通常的竞争性的市场关系。相反,中央计划被市场型的控制所取代,部分被企业与财政当局特定的讨价还价所取代。从名义上看,企业受价格、利率、税率而不是实物分配的调节,但在实际上,价格、利率、税收仍是持续的讨价还价的对象。”[3]经济改革的实质,不过是由直接的行政控制变为了间接行政控制,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尚未有效发挥作用。经过改革的经济体制仍是一种修正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由此决定,贿赂犯罪并不具备充分爆发的条件,犯罪规模相对较小,①1978 年刑法典只是对传统贿赂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
二、匈牙利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转型
在 1950 - 1990 年,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度统一,匈牙利几乎很少有腐败案件发生。
[4]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平衡,为 1978 年刑法典贿赂犯罪立法保持较长时期的稳定提供了条件。然而,在东欧剧变、制度急剧转型中,贿赂犯罪开始由公职领域向经济乃至社会领域大幅蔓延,既有刑法的规制漏洞暴露出来,立法转型迫在眉睫。
( 一) 匈牙利贿赂犯罪立法转型的时代根据
1990 年匈牙利迎来了第一次全国自由大选,联合政府确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私有化、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回归欧洲的国家发展战略。在政治、经济转型初期,既往行为控制规则已经失效,新的规则尚在建立,导致行为失范现象大量出现,贿赂现象从公共领域直接向社会领域迅速蔓延。
根据联合国相关统计,1990 年匈牙利检察机关起诉的贿赂犯罪案件数量是 335 件,而从 1991 年至1997 年每年案件总数分别为 344 件、782 件、464件、796 件、509 件、967 件和 865 件,案件总量在90 年代呈现波动性上涨趋势。[5]这些数字仅是已知的犯罪,犯罪黑数的存在,只是大量贿赂犯罪的“冰山一角”。根据以公众主观腐败感受为评价标准的“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腐败指数(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 的统计,匈牙利 90 年代 CPI 指数整体平均较低,而1998 年 CPI 指数仅为 4. 3,为历史最低。[6]根据世界银行 1999 年的一项调查,有超过 1/3 的匈牙利公司报告“每年要向公职人员支付相当于年收入 1% -25%不等的黑色费用”。[7]引发转型初期匈牙利贿赂犯罪爆发性增长的原因在于: 一是“渐进性”经济转轨模式。在经济转型方面,匈牙利采取了不同于以波兰为代表的激进休克疗法,转轨战略偏重于渐进改革,实行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补贴削减开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取消税收优惠,逐步实行价格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等措施来推动经济转轨。渐进转轨过程中,国家在一定期间内仍对市场资源保留控制与分配权,在相关权力监督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寻租型”贿赂犯罪激增。二是彻底的私有化政策。匈牙利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化的基础上,私有化的重点是土地和国有企业。1990 年匈牙利共有国家和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公司1858 个,到 1998 年国家保留所有权的公司和企业仅 93 个。[8]经过 10 多年的转轨,私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1989 年私有经济成分占 GDP的比重仅为 18%,2000 年私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占 85%。[9]私有化过程中,“影子经济”( 国家无法监控管理的地下经济) 的主导者利用其信息优势占尽先机,通过贿赂等腐败方式改变私有化进程的方向,为个人谋取大量利益。[10]( p. 111)
三是国家治理重点的偏向。最早两届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转型政治体制与加快经济转型,而未将腐败治理纳入国家治理战略的重要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贿赂犯罪的积极治理。
贿赂犯罪的严重态势不仅直接侵害了匈牙利政治、经济转型的平稳,更成为匈牙利回归欧洲的主要障碍。匈牙利于 1993 年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1998 年启动入盟谈判进程,欧盟对候选国入盟制定了严苛的标准,要求候选国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人权方面向欧洲靠拢。然而,1999 年欧盟委员会常规评价认为,匈牙利当年腐败案件数量比之前增长了 4%,腐败问题是阻碍匈牙利符合欧盟政治标准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11]
面对贿赂犯罪的严重影响,1998 年欧尔班政府首次将加强监督防止腐败作为国内政策的六项重点任务之一。[12]同年,匈牙利签署了 OECD《国际商务交易活动中禁止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次年签署了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并根据国际反腐公约的要求修正刑法,迅速实现了贿赂犯罪刑法立法的转型。
( 二) 匈牙利贿赂犯罪体系的重构
国家治理模式变化所产生的贿赂犯罪形势是促使立法修正的根本原因。1989 年匈牙利在东欧剧变、制度转型期间,基于政治构架的变化于1993 年颁布 XVII 法案对第 137 条“定义”中的公职人员范围进行修正,增加总统、国会议员、宪法法院法官等,及根据法律规定受托行使公共权力或行政管理职能的主体。但是,单纯扩大主体范围的方法,无法满足犯罪治理的需要。在反思既有立法犯罪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借重于立法理念的优化,2001 年匈牙利颁布第 CXXI 法案,大幅修正贿赂犯罪立法。CXXI 法案是匈牙利刑事反腐史上最重要的法案之一,标志着全新的贿赂犯罪治理理念———积极治理主义的正式形成。2012年匈牙利颁布新刑法典,①以积极治理主义为导向,在第 27 章设“腐败犯罪”一章,共 11 个条文,除“解释规定”外,具体规定了经济组织贿赂犯罪( 第 290、291 条) 、公务人员贿赂犯罪( 第 293、294条) 、在司法或管理程序中贿赂犯罪( 第 295、296条) ,以及对贿赂的玩忽职守( 第 297 条) 、间接腐败( 第 298 条) 、滥用职权( 第 299 条) ,贿赂犯罪立法体系得以重构。
( 三) “积极治理主义”与匈牙利贿赂犯罪刑法立法创新
1. 贿赂犯罪积极治理主义的理论缘起
“积极防御主义”是军事学上的一个概念,意指为了反攻或进攻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挫败进攻之敌的防御。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将“积极防御”解释为: 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地打击组成的盾牌。[13]军事学上的“积极防御主义”对贿赂犯罪治理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由此形成的犯罪治理理念可称为“积极治理主义”。
重视刑法在贿赂犯罪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长期的立法发展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传统。如严惩贿赂犯罪的基本立场、以新型犯罪为驱动的立法理念、行为犯的立法模式、仅谴责权力滥用者而忽视监督者的立法路径、重刑化的刑罚策略,等等。传统的贿赂犯罪应对与治理策略可归为“消极治理主义”,由此形成的立法因“法据恶生”而存在被动性问题,在贿赂犯罪日益间接化、群体化、隐蔽化乃至“生态化”的背景下,刑法立法时刻面临边际效益递减与调整“失灵”的风险。在反思与批判既往贿赂犯罪立法理念基础上生成的“积极治理主义”,着力使贿赂犯罪立法摆脱困境,以有效组织系统化的贿赂犯罪抗制措施体系为目标,通过引入监督责任理论、对称治理理论、权力结构组织理论,重构“囚徒困境”,力求解决贿赂犯罪“环境性腐败共同体”、犯罪发现能力与效率的问题。
2. 贿赂犯罪“积极治理主义”的核心内容
1998 年欧尔班政府执政后,面对国内严重的贿赂问题,率先提出将有效预防公职人员贿赂和更为严厉地惩治特定类型的贿赂犯罪作为国家反腐策略[14],成为匈牙利贿赂犯罪立法向积极治理主义转型的号角,2001 年 CXXI 法案和 2012 年新刑法典标志着积极治理主义理念的全面生成。
积极治理主义的基本表现是:
( 1) 破解贿赂犯罪的“共犯结构”
随着国家乃至世界性贿赂犯罪治理战略的整体推进,贿赂犯罪不断衍生出新的行为类型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在交易日益隐蔽并间接化的同时,贿赂犯罪“共犯结构”的出现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贿赂犯罪的“共犯结构”是基于各国官员任用体制而形成的贿赂犯罪主体层级化、梯队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态化”现象,“环境性腐败共同体”的形成削弱了立法对贿赂犯罪的控制作用,并对同一贿赂犯罪生态体内的公职人员,乃至不同生态体内公职人员实施受贿行为产生极大暗示作用,直接造成国家贿赂犯罪立法的“治标不治本”现象。提高既有贿赂犯罪立法的治理能力,单纯依靠犯罪新行为的跟踪性立法已难达治理要求,在既有的行为模式型立法已近终极化的情况下,调整贿赂犯罪立法的治理模式与结构显得尤为关键,而这一调整必须依赖于对贿赂行为犯罪化的根据进行理论基础的更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在危害行为的基本模式上通常做作为与不作为的类型划分,前者为犯罪的基本模式,通常仅对国家法益、公共法益以及重大人身法益设置有不作为犯的规定,以期在对重大法益进行刑法保护的同时,不过分干预公民的权利自由,因而,刑法并不全面干涉怠于举报犯罪的行为。然而,面对公共权力滥用严重化的趋势,积极治理主义通过引入刑法的保证人责任原理,将特定公职者设定为维护权力廉洁运行的保证人,突破了传统贿赂犯罪立法所框定的作为犯立罪模式,其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开始对贿赂犯罪设置不作为犯的类型,匈牙利刑法典对此进行了最早的尝试。2001年匈牙利 CXXI 法案新增“怠于报告贿赂犯罪活动罪”,根据法案第 255 条 B 款,“任何公务员通过可靠的来源知悉某一尚未被发现的贿赂行为( 第 250 条至第 255 条) ,但未及时向有权机关报告的,构成轻罪,处 2 年以下监禁、公益劳动或者罚金。”
①2012 年新刑法典第 297 条( 对贿赂的玩忽职守) 规定: “公务人员应当知晓未被发觉的贿赂行为,却没有立刻向权力机关报告的,构成重罪,判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从立法规定的内容来看,尽管存在适用中的界限与范围界定问题,但是,匈牙利刑法明确将举报所发现的贿赂犯罪线索设定为公职人员的法定义务,规定违反者不履行义务的刑事责任,表明了严密贿赂犯罪法网的基本立场,切实提高了刑法实现贿赂犯罪预防性治理目标的能力。
( 2) 调整“偏向型”的犯罪治理结构
贿赂犯罪属刑法理论中的对向性犯罪,对实施亵渎公职的行为人双方采取区别化的刑事处遇政策,是消极治理主义贿赂犯罪立法的又一基本立场,由此形成“偏向型”的犯罪治理结构。消极治理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通常对行贿罪配置轻于受贿罪的刑罚,或为行贿者设置专属的特殊出罪规定,如,匈牙利 1961 年刑法典第 152 条第 2 款规定,“在公职人员要求下给予或者允诺给予利益的人,不受起诉,如其有合理理由担忧其会因拒绝要求招致非法侵害。”这种规定显然是要突出对受贿行为在权力滥用中较重危害性的否定性态度,本无可厚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规定若在权力驱动的国家主义时代有其合理性的话,在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时代,则无疑弱化乃至低估了行贿者在贿赂犯罪发生中的触发作用,欠缺其存在的社会根据与合理性价值。消极治理主义导向下的行贿者轻罚化制度,以对行贿者与受贿者在贿赂犯罪中的地位不平等为其立法基础。这一认识存在着在对贿赂犯罪社会危害性评价根据上将贿赂犯罪行为人关系不当“私法化”的问题,贿赂作为对公权力非法处置或交易的行为,无论是贿赂双方积极达成的交易,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结构不平衡的交易,只要贿赂行为现实地发生,公权力的不可收买性即已受到严重侵害,权力的廉洁性才是贿赂行为最直接的受损对象。不仅如此,消极的、区别化的刑事政策,在贿赂犯罪的发现与揭发中并未产生立法者所预想的积极效果,行贿者并不会因刑法的宽赦而放弃其利益追求,从而扼止贿赂行为。积极治理主义力求冲出消极治理主义所设定的犯罪治理困境,而其突破口则在于重新评价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根据与犯罪发生的机理,将贿赂的犯罪“过程性”治理策略调整为“源头性”治理策略,惟此才能适应贿赂犯罪治理的需要。始于 2001年 CXXI 法案,匈牙利刑法根据积极治理主义的要求开始重视行贿犯罪的刑法治理,CXXI 法案做出了两项重要修正: 一是将原第 253 条行贿罪第3 款被勒索情形下不处罚的规定,调整为轻罪; 二是删除第 258 条向国外公职人员行贿罪 B 款第 3段中行贿人因担心不愿行贿而导致不利后果的责任阻却事由。
①以之为基础,2012 年新刑法典进一步强化行贿犯罪的治理: 一是在立法编排体系上将行贿罪置于受贿罪前,更符合犯罪的发生机理,明确行贿行为的犯罪触发作用。二是将行贿罪基本法定刑从 2 年以下提升至 3 年以下,犯罪性质从轻罪转为重罪; 三是删除行贿罪中对于被勒索情形下的减轻处罚规定; 四是增设“利用影响力交易行贿罪”; 五是统一公共领域行贿与私营领域行贿的认定标准。通过修正,行贿罪成为与受贿罪性质一样的重罪,贿赂犯罪治理结构实现了向对称性治理的转向。
( 3) 重构贿赂犯罪“囚徒困境”模式
对行贿者设置“特别自首制度”,是消极治理主义贿赂犯罪立法的又一基本立场,也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贿赂犯罪的立法传统之一,②匈牙利于2001 年通过 CXXI 法案将之引入刑法行贿罪处罚规定之中。刑法立法理论认为,“特别自首制度”的设立借鉴了博弈论最着名的“囚徒困境”模型:两个罪犯由于相互不信任并且不敢相互信任,都不愿意冒险选择抵赖罪行; 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抵赖,则坦白方被释放,而抵赖方会被判处重刑,结果几乎都选择坦白而被从轻处罚。所谓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就是采取立法与司法措施,使行贿者、贿赂介绍者选择主动交待贿赂事实,使受贿者选择拒绝贿赂,从而减少贿赂犯罪。[15]根据“囚徒困境”原理设置的特别自首制度涉及“单边型”与“双边型”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仅对行贿人设置特别自首处遇政策,其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满足了从严惩治公职人员的特殊需要; 另一方面是为了打破行贿者与受贿者的平衡,调动行贿者的积极作用,以强化其在揭发受贿犯罪中的作用。而后者则是指同时对行贿人与受贿人设置特别自首处遇政策。虽然二者均具有积极的犯罪治理功能,然而,从积极治理主义角度看来,“单边型”的“囚徒困境”设计,尽管有利于发现权力者的受贿行为,但并不符合对贿赂犯罪源头性治理的需要,且在彻底瓦解贿赂双方的信任关系上存在功能欠缺,而积极治理主义在强化源头治理、减少犯罪机会上更显优势。为此,匈牙利刑法典通过调整“囚徒困境”的设计思路,“人为”制造出受贿者与行贿者内在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内在信任关系,实现了彻底打破贿赂犯罪相对方沉默平衡的目标。在 2012 年匈牙利新刑法典所规定的三组贿赂犯罪中,①均明确设置了“双边型”的特别自首制度,并根据犯罪性质的不同,设置了差异性的自首成立条件。即,对于行贿行为而言,只要“行为人亲自向权力机关坦白犯罪行为,揭发犯罪情况的”,均“可以无限制减刑或者经特别考虑撤销案件。”对于受贿行为而言,只要“行为人亲自向权力机关坦白、上缴所得的所有形式的非法利益并且揭发犯罪情况的”,均“可以无限制减刑,特殊情况下,可以撤销案件。”显然,立法对受贿者设置了严于行贿者的条件,但二者的刑法处置原则则是相同的。
( 4) 调整贿赂犯罪责任根据
以贿赂行为为本体展开的贿赂犯罪治理,在贿赂犯罪责任根据选择上,实行权力结构个体性责任理论,是消极治理主义的又一基本立场。在积极治理主义看来,贿赂犯罪的发生是特定公共权力组织体内部权力运行与监督不均衡的突出表现,单独的权力者如果受到来自权力组织体的有效监督,是能够有效避免贿赂犯罪发生的。鉴于此,有必要将权力结构个体责任原理调整为权力组织结构原理,实现贿赂犯罪立法防卫基点由行为环节向监管环节的转型。根据权力结构组织体理论,行为监管者应当承担对权力组织体中公职人员的监督责任,怠于行使这一责任者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匈牙利属于传统的欧陆法系国家,仍然沿用传统的法人刑事责任否定观,不承认法人犯罪,②较大程度上限制了贿赂犯罪的治理效果。为解决这一问题,2001 年第 CXXI 法案根据 1995 年欧盟委员会《保护欧洲共同体经济利益》第 3 条、1997 年欧盟委员会《基于 < 欧盟打击涉及欧洲共同体以及欧盟成员国的官员腐败协议> 第 K3( 2) ( C) 之公约》第 6 条“商业组织首脑刑事责任”之要求,③在刑法典第 253 条和第 258 条B 款之后增加第 3、4 两段,另辟蹊径地将法人管理者怠于行使预防行贿的行为犯罪化,即,法人负责人或有决定权、控制权的法人内部主体可以为在其授权下的法人行贿行为承担责任,但其能证明已经履行了控制与监督义务的除外。[16]该规定被 2012 年新刑法典所吸收,成为行贿罪下的一种特殊类型。
④立法前移防卫基点,通过构建对法人管理者的刑事处罚,反向激励管理者积极履行内控职责,构建严密的企业内控机制,预防、减少行贿机会,最终达到预防性治理之目的。
( 5) 完善“权责制”刑罚结构
刑法立法仅将公职人员身份规定为定罪身份,而非量刑身份,即在法定情节设置上采用不区分公职人员职务高低的“无差别主义”,是消极治理主义贿赂犯罪立法的又一基本立场。然而,在积极治理主义看来,贿赂犯罪中公职人员所实际滥用的权力属性,决定了其行为社会性程度的不同。在通常情况下,滥用宏观性权力实施的贿赂行为,其危害重于微观性权力滥用的行为,如,滥用国家经济配置权而进行的贿赂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程度重于微观权力者的行为。高级权力滥用的危害性程度,普遍恶劣于低级权力的滥用,如,滥用国家中央公共权力的危害重于低层级权力组织的滥用行为。不仅如此,高层级公共权力组织的贿赂犯罪还对低层级组织具有示范效应。鉴于此,对于掌握国家高级、宏观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应当给予更为严厉的惩治,在法定情节上应当充分考虑身份的差异性而规定不同的处罚机制。匈牙利刑法对此进行了积极的立法尝试,早在 1978年刑法典中,立法不仅将司法人员受贿行为独立成罪,同时,还将高级公务员实施受贿规定为受贿罪的法定加重情节。2001 年 CXXI 法案继续强化了刑罚配置差别化的做法,在将普通公职人员受贿法定基本刑从 3 年以下提升至 1 - 5 年监禁刑的同时,将高级公职人员受贿的法定刑区间从 1- 5 年提升至 2 - 8 年监禁刑,将高级公职人员受贿并违反职责的法定刑区间从 2 - 8 年提升至 5- 10 年监禁刑。2012 年新刑法典对此进行了立法确认,进一步突出了对高级官员重点惩治的策略,体现了“严中从严”的积极刑事惩治立场。
三、匈牙利贿赂犯罪积极治理主义之评价与借鉴
以经济转型及加入欧盟为契机,匈牙利贿赂犯罪刑法立法逐步摆脱了对传统贿赂犯罪治理的路径依赖,实现了由消极治理主义向积极治理主义的转型,构建了既符合国际反腐标准,又具本国特色的贿赂犯罪刑法体系,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欧洲国家反腐败委员会( GRECO) 2012 年第三回合评价认为,新立法与其推荐意见相符合。
[17]2013 年联合国在检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中对匈牙利贿赂犯罪实体立法改革部分给予了赞许。[18]匈牙利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转型所奉行的积极治理主义,代表了国际贿赂犯罪治理发展的最新趋势,对同样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 一) 匈牙利贿赂犯罪积极治理主义之评价
1. 为更新贿赂犯罪刑事政策内容指明了新方向
一般而言,各国贿赂犯罪的刑事治理均会奉行严厉的刑事政策。消极治理主义的具体机制设计,主要依靠扩大受贿罪的规制范围、增加刑罚供应量来完成,刑事立法呈现出压制性特点。然而,具有事后堵截性质的单纯刑事打压,难以对犯罪源头给予有效控制,不能真正缓解犯罪压力,过度打压甚至会出现立法不断修正而犯罪总量不断上升的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故而,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反腐公约均强调疏导治理机制、加强源头治理。积极治理主义通过调整行贿罪与受贿罪“偏向型”治理结构,实行对称性治理,严密了行贿罪法网,降低了行贿的脱逃可能性,提高行贿的犯罪成本。不仅如此,积极治理主义还深化了源头治理的理念,特别强调对犯罪机会的有效遏制。加强企业管理者监管责任或公职人员举报责任的立法意图并不在于打击这些不作为犯罪,而是期望通过立法激发特定主体的反腐意识,在贿赂犯罪衍生的关键环节构建廉洁文化的环境屏障。此外,积极治理主义从未放弃严厉惩治的基本立场,但更具方向性和目标性,如对普通公职人员与高级公职人员在刑事责任承担程度上的区分,立法锋芒明确,体现了“严中从严”的严厉政策。综上所述,积极治理主义从贿赂犯罪衍生规律角度重新阐释了严厉打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之内涵,形成了以“机会遏制”及“严中从严”为并行主线的犯罪治理思路,为现代贿赂犯罪刑事政策更新提供了有益参考。
2. 为丰富贿赂犯罪刑事责任原理注入了新内容
消极治理主义将贿赂犯罪限定为违反禁止性规范的积极行为,其犯罪化根据较为局限,积极治理主义则打破这一立法传统,创制出“法人管理者预防行贿失职型”行贿罪和怠于报告贿赂犯罪活动罪的真正不作为犯模式。真正不作为犯,是刑法分则明文规定了保证人与作为内容的犯罪。
[19]( p. 151) 所谓保证人,是指具有作为义务的主体。在贿赂犯罪中设置真正不作为犯,更新了贿赂犯罪可责性原理,将违反特定预防义务和举报义务的不作为视为对公职廉洁性的侵害行为。就怠于报告贿赂犯罪活动罪而言,公务员基于特定的职务及法定身份要求,被赋予了确保公职人员群体廉洁性的“保证人”地位,对贿赂犯罪具有特别监督义务,不履行监督义务等同于纵容犯罪,侵害到公职行为的廉洁性。就法人管理者预防行贿失职型行贿罪而言,法人管理者对于预防企业成员为企业利益行贿具有保证人地位。预防贿赂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2004 年《联合国全球契约》提出了“企业应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将预防行贿责任法定化和犯罪化,使企业管理者充分认识到预防责任所在,对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加强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英国 2010 年《贿赂法》( Bribery Act 2010) 也规定了类似的“商业组织预防 贿 赂 失 职 罪 ” ( Failure of CommercialOrganization to Prevent Bribery) ,对商业组织疏于构建内部行贿预防制度而导致行贿行为发生的行为设定了刑事责任。[20]( p.78) 有所区别的是,英国立法规定的是法人犯罪,而匈牙利立法规定的是自然人犯罪,但无论如何,市场经济下行贿犯罪的实施主体多为经济组织,企业内部控制薄弱而导致行贿行为的发生,无异于在犯罪预防前置关口上放纵贿赂犯罪,管理者负有不可推卸的保证人责任,从积极预防角度,刑法有干预的必要性,这已经成为国际贿赂犯罪治理的新方向。综上,积极治理主义主张对贿赂犯罪衍生环节上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主体施加更为严厉的作为义务,积极拓展并丰富了贿赂犯罪刑事责任原理,创建了现代贿赂犯罪刑法立法新的理论依据。
3. 为创建一体化贿赂治理模式提供了新注释
“刑事一体化”理论认为,犯罪产生于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原因错综复杂,因此,犯罪问题的惩罚与矫正不单单是刑法自身的问题,必须着力于社会综合治理,加强“犯罪场”的控制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1]( p. 1) 实际上,在贿赂犯罪治理的刑法本体规范内也应当提倡“一体化”概念。除了行贿人逐利动机及受贿人贪欲因素之外,行为监控制度的缺乏、腐败文化环境的影响等都是推动贿赂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尽管对于贿赂犯罪的刑事治理应当遵守刑法的谦抑性,严格控制犯罪化的范围,但若仅依靠对贿赂本体行为的刑法治理不能取得明显效果时,刑法就有必要积极介入“犯罪场域”,将事前治理、事中监控责任犯罪化,通过严控犯罪衍生环节的方式,提升对贿赂犯罪的治理效果。就此而言,积极治理主义本身吻合了“一体化”治理的理念,其所主张的“机会遏制”,合理延伸了前端预防空间与后端监控空间,形成源头治理、事中监控与事后严惩紧密集合的一体化“场域”,使得刑法治理具有了立体化、层次化与整体化的特征,最大限度地提升刑罚威慑效果及治理效益。
( 二) 匈牙利贿赂犯罪积极治理主义之借鉴
中国自 1978 年启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以来,贿赂犯罪开始走出单纯的公共权力领域,开始向市场经济领域加速蔓延,促使中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进入调整与变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从 1979 年刑法典颁布至今,贿赂犯罪刑法立法一直处于扩张状态,但经历了近十次的立法修正,犯罪治理效果并不理想,1997 年后贿赂犯罪立案数量在总体上仍呈上升趋势,[22]( p.124) 中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正站到改革与完善的十字路口。合理参考匈牙利贿赂犯罪的治理经验,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是实现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转型与突围的重要契机。对此,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加以借鉴:
1. 加强行贿犯罪刑法治理,构建“对称性”治理结构
目前中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存在着严重的“非对称性”问题,如构成要件要素并非处于同等对向的关系、更重视对受贿罪的刑事追诉,等等。
[23]( p. 17) 非对称性治理模式不符合源头治理之要求,难以实现对贿赂犯罪的长效治理,应在积极治理主义引导下及时修正。具体包括: 一是基于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向关系,对两罪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对应性调整,在删除受贿犯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前提下,删除行贿犯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素; 二是在刑法典第 388 条之下增设“影响力行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对应。
2. 合理借鉴“囚徒困境”理论,设置“双边型”自首制度
扩大“囚徒困境”原理在贿赂犯罪立法设计中的积极作用,建构“双边型”特别自首制度,纠正“偏向型”治理结构,对此,一是取消行贿罪中“因被勒索给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之规定,将此种情况作为行贿罪的法定减轻情节; 二是设置受贿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规定适当严于行贿罪特别自首的成立条件,通过法律“制造”贿赂者之间的冲突,同时,根据贿赂犯罪所侵害权力属性的具体情况,对贿赂犯罪特别自首人设置多梯级的宽赦类型。
3. 拓展刑法干预的犯罪场域,构建“一体化”的治理模式
中国历次贿赂犯罪立法修正均限于贿赂行为类型完善,缺乏对贿赂犯罪场域刑事控制的深入认识。尽管中国刑法第 393 条规定“单位行贿罪”,但该罪仅是针对行贿行为,未涉及对行贿行为预防、监控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积极治理主义的指导下,以有效遏制犯罪机会为目标,将防卫基点从行为环节向监管环节前移,破解“环境性腐败共同体”,构建一体化的刑事治理模式。具体包括: 一是适时增设预防行贿失职罪。
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市场主体对于预防贿赂犯罪、创建廉洁的企业文化、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特别义务,在对《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前置法已规定市场主体反贿赂义务的前提下,应在行贿罪下增设预防行贿失职罪,将故意或过失未构建单位行贿预防机制而导致单位成员为单位利益实施行贿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根据罪过的不同,设置轻重有别的梯级刑罚处罚标准,同时规定单位也可以构成该罪。二是适时增设怠于报告贿赂罪。在《公务员法》增加国家工作人员对于贿赂犯罪的法定报告义务的前提下,应在受贿罪之下增设“怠于报告贿赂罪”,将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获知他人贿赂犯罪事实而不报告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规定为犯罪。
4. 采取“严中从严”之策略,加重高级公职人员的刑事责任
近年来,贿赂犯罪大案、要案的增长速率与贿赂犯罪案件总量增长成正比,尤其是 2013 年以来,在中央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高级别官员落马频繁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反腐机构侦查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也说明既有刑罚对于高级公职人员缺乏一般预防效果。基于此,可借鉴匈牙利经验,采取“严中从严”之策略,将高级公职人员身份增加规定为量刑身份,即将“高级公职人员受贿”及“向高级公职人员行贿”分别规定为受贿罪与行贿罪的法定加重情节。
参考文献:
[1]Ezer év trvényei( 千年法律) [DB/OL]. [2014 - 7 - 10].
[2][匈]雷热·涅尔什.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J]. 经济研究,1984,( 03) .
[3]孔田平. 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J]. 社会经济体制比较,1992,( 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