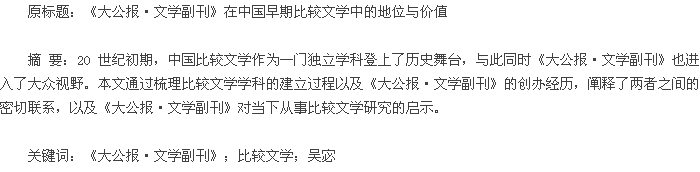
20 世纪初期,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创办于此时的 《大公报·文学副刊》(以下简称 《文学副刊》) 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这门新生学科在中国的传播。按照学界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①,《文学副刊》 创办的 6 年 (1928年 ~1934 年) 属于比较文学的初兴期②,并且处于初兴期前后 15 年的衔接阶段 (以 1934 年为限),“这两个时期的区别是:前期,比较文学学科开始建立,高等学府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一些学者发表了一批比较文学论文和比较文学方面的著作;后期,学者队伍扩大,研究层面与领域拓宽、加深,比较文学的论著质量与数量均有提高。”[1]
在这段时间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走进高等院校,应归功吴宓。随后,吴宓创办的 《文学副刊》 作为该时期介绍西洋文学最全面、最系统的文学刊物,也走进了比较文学的视野③。
总体来说,从 20 世纪初期的比较文学状况来看,《文学副刊》 构筑了完整的欧美文学知识谱系,强调全面地介绍欧洲文学;从我国当下的比较文学发展来看,针对 《文学副刊》 的研究将有助于整合我国比较文学初期的学术资源,进一步规范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促进我国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发展。
一、 《文学副刊》与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
要界定 《文学副刊》 在我国比较文学初兴期的历史地位,我们首先必须梳理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过程,以及 《文学副刊》 的创办经历。
首先,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研究者的要求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良好的外语基础;二是坚实的国学基础;三是丰富的学科知识。[2]这三点主要针对学习比较文学知识,初涉比较文学门槛之人而言。如果要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20 世纪初期的中国高校,那我们不妨在以上三个要求的基础上加以延伸:一是必备深厚的外国文学功底,具有欧美留学背景;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认识,具有文化认同感;三是自身接受过比较文学的正式教育,对比较文学学科有系统的认识。令人遗憾的是,这几点为比较文学学科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比较文学的传播与发展。因此,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某几座高等学府和一些知名教授之中[3],其影响力并没有扩大到全国范围。
究其原因,一方面比较文学是一门相当强调文学连续性的学科,因此钱钟书才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一个强调文学的连续性,并且呼吁中国的比较文学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把我国的“旧文学”也包括进来,这一点和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并没有完全契合。另一方面中国 20 世纪初期是一个文学上门户大开的年代,基本上欧洲所有的文学思潮都被介绍到中国。
当然,其中也有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区别,其中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就没有像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那样,受到新文化运动诸君的认可,而当时以吴宓为首的一批学院派人士所推重的正是具有古典主义倾向的新人文主义,“由于‘五四’后蔓延中国的进化论思潮,使文学研究者倾向于‘向前看',而不能对古典主义进行客观的关照。”[4]故在这一时期内,比较文学的思想并没有通过高校的讲堂直接扩散到国内的知识界,而是通过接受了比较文学思想的学者,从其个体思想、言论以及著作中得以传播。
然而,《文学副刊》 的出现是一个特例,它成为沟通学术界与社会舆论的媒介平台,对扩大比较文学的影响力而言功不可没。当然,这也归功于主编吴宓的自身经历与学术倾向。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从直观上看,创办一个比较文学刊物非吴宓莫属。吴宓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专攻欧洲文学和比较文学课程,回国后又与陈寅恪、梅光迪等人联手打造了 《学衡》 杂志,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具认同感,也因此被贴上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吴宓当时的代表性文学批评作品是 《论新文化运动》,在文中他专门阐述了法国学派的观点,认为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白话新诗实际上是受美国自由诗的影响,而美国自由诗又是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的产物,这属于典型的影响研究。在 《希腊文学史》 一书中,吴宓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评论了荷马史诗和中国弹词作品,认为二者无论是表演方式还是文学体裁,都具有相似性。
1924 年吴宓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中西诗之比较”.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吴宓进入清华外文系,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外语系教授,连续开设“中西诗之比较”、“古希腊罗马文学”等讲座,他提倡中西合璧,将中文与外语打通,要求学生文、史、哲兼修,聘请了一批比较文学学者来清华授课⑤。1929 年,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主任、语义派创始人瑞恰慈在清华开设了比较文学课,并将讲义编辑成了《比较文学》 一书。⑥至此,比较文学学科在清华正式确立,在这种学风的熏陶下,清华培养了一大批比较文学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陈铨、张荫麟等人,这些人在 《文学副刊》 创刊后,大多成为编辑为其撰稿。“于是,对中西文化进行折中调和的比较研究就成为清华的传统,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开始,这一学统就形成了。因此,尽管吴宓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已经把比较文学搬上大学课堂,讲授’中西诗之比较‘的课程,但是,只是他在清华的时候,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才真正建立。”[5]
而 《文学副刊》 恰恰也是在这一时期走入大众视野。在研究文学、艺术与道德等问题时,《文学副刊》并没有使用“比较文学研究”这个词汇,毕竟这是一本 20 世纪初期,比较文学学科刚刚在中国建立时创办的副刊。《文学副刊》 所使用的是“综合研究”一词,在第 3 期刊载的 《欧洲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与吾国人应有之觉悟》 一文中,《文学副刊》 对“综合研究”的定义有二:一是采集各派之特长,以此解决宇宙人生之矛盾,如进化论、相对论等。二是明晰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直至新系统的构成。在《文学副刊》眼中,斯宾格勒的 《西方的没落》 即是“综合研究”的代表作品,并称斯宾格勒知识渊博,能洞见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政治、经济、风俗等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见,《文学副刊》 已经发现了比较研究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斯宾格勒给予 《文学副刊》 的启示,正是如何探寻人文科学之间普遍存在的原理与相互关系,不能局限于各学科之间的壁垒,而导致文学、文化研究的一成不变。
因此,《文学副刊》 在进行文学和文化研究时,也尝试着使用综合研究方法,当然, 《文学副刊》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学科内部,相对于自然学科和技术学科而言,文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紧密。作为一份 20 世纪初期的文学批评类刊物,我们不能强求 《文学副刊》 将研究视域延伸至三大学科体系的各个独立学科,毕竟这是一本诞生于百余年前的刊物,它依然立足于文学批评而非后世流行的文化研究。
二、 《文学副刊》与中国比较文学的联系
按照我国学术界的通行观点,“中国比较文学兴起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此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有四大特点:一是国外比较文学理论的译介;二是高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与讲座;三是一批学贯中西的学院派学者参与;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从西方文学中吸取大量营养。其中,吴宓无疑是这个动荡时代中开拓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他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开设了一系列比较文学性质的讲座,并正式建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与此同时,吴宓还与 《大公报》 合作创办 《文学副刊》,尝试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在大众媒介上传播文学、文化批评研究知识。毫无疑问,《文学副刊》 是中国比较文学兴起时期的重要刊物。
第一,《文学副刊》 建立了一个以欧美文学评论为主体的研究领域。 《文学副刊》 出版之时,正值中国政治上较为衰败,而文学上较为繁盛的一个时期。西欧两个多世纪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都在此时的中国杂乱而凌厉地爆发出来。
因此,必须设立一个立体的参照系,梳理脉络,理清渊源影响。《文学副刊》 实现了此目的,从 1928 年 1月第 1 期开始,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在 313 期中相继介绍了数十个国家的几十位作家。其中包括法国的韦拉里、马莱伯 (马勒尔白)、伏尔泰 (福禄特尔)、柏格森、司汤达等;英国的哈代、罗塞蒂、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约翰·班扬、罗素、托马斯·霍布斯、劳伦斯、柯南道尔、阿诺德·贝内特;美国的约翰·沃森、白壁德、辛克莱·路易斯、华盛顿·欧文等;德国的赫尔曼·苏德曼、莱辛 (雷兴)、施莱格尔兄弟、托马斯·曼、黑格尔、歌德、马克思、叔本华、马丁·维兰德、白瑞蒙、费希德以及欧美其他诸国的托尔斯泰、易卜生、易班乃士、卡斯底格朗、斯宾诺莎、圣·奥古斯丁等人。 《文学副刊》 对这些欧美诸贤的推介并没有局限于生平简历,作品介绍,而是以文化批评的方式对其所属流派,思想脉络,写作风格进行了系统的评论。这也是以吴宓为首的编辑群体对国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时,倾向性过于明显的一种反思。“盖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尽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绝少,故梅君与宓等,在此三数年间,谈说西洋文学,乃甚合时机者也。”[6]
第二,《文学副刊》 的编辑大多为中国早期比较文学人士。当日之中国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有志国人皆从西方引进改造中国的方法,《文学副刊》 在第 1 期的 《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 中明白阐述,希望在文化层面上找到一条中西文化调和之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主编吴宓笼络了一批青年才俊,纵观 《文学副刊》 的编辑名单,才华横溢者比比皆是:和钱钟书并称为“北秀南能”的清华文科才子张荫麟 (笔名素痴),17 岁时即指正梁启超的考据失误,被梁引为忘年交;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赵万里 (笔名蠡舟);精通多国外语,研习梵文,和朱自清并称“清华双清”的浦江清 (笔名微言);有活词典之称,英文甚佳的毕树棠 (笔名民犹) 等人。
当时的编辑部就设在清华校园之内,除编辑群体之外,《文学副刊》 还以其文化品位与知名度,将众多学术大家汇聚一堂,“章太炎、陈寅恪、吴芳吉等等,这些学者在这里高谈阔论,旁征博引,一时间形成了’满座皆鸿儒,出入无白丁‘的景象。”
1929 年,《文学副刊》 评论朱希祖发表在 《清华学报》 上的 《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於南方考》 一文,引得朱希祖接连发表 《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书》、《再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书》 等文,这场笔战的结局以 《文学副刊》 发表一则启事告终,而类似的逸闻趣事在 《文学副刊》 上多有发生,这说明了 《文学副刊》 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当时学界对 《文学副刊》 的关注与重视。
第三,《文学副刊》 具备一种包容的研究态度与办刊宗旨。《文学副刊》 中对于文学的定义并非局限于纯文学作品,它的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学术思想批评,包括:哲学、艺术、社会生活以及国民思想感情。主旨在于---欲提高思想之境界,必须先用文学来固本清源。在 《文学副刊》 的创刊号上,吴宓阐述了 《文学副刊》 所涵盖的范围,包括文学人物通论及其作品评论,中西新书推介,纯文学作品,读者学术争鸣。
“对于中西文学,新旧道理,文言白话之体,浪漫写实各派,以及其他凡百分别。亦一例平视,毫无畛域之见,偏袒之私,唯美为归,为真是求。而专重批评之精神。”[9]
这恰是比较文学学者应该保持的立场,虽然主编吴宓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有着自身的看法,也在 《文学副刊》 上发表了诸多质疑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但从整体上看上,整个编辑团队依然保持着相对公允的立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朱自清也是编辑部成员之一。毕树棠在回忆录中也说到,“吴宓先生自己不写白话诗与白话文,但从不拒绝投稿书写白话文。”
同时,《文学副刊》 成为了中西文化会通之园地。这一思想在第二期 《支那客谈欧洲事》 中表露无遗,对物质进步而导致的精神文化衰竭的忧虑,必须保持东方式道德与智慧才能使今日中国不重复欧洲物质文化衰败的覆辙。
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对待传统文化有着摧毁与解释两种观点,《文学副刊》 并没有站在某一学术流派的立场上来进行文学探讨与文学批评,而是采用了一种会通的方式将摧毁与解释两种学术理论融合起来,以文学领域为起点,进而探讨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也是比较文学学者在一个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时代的一种探索与努力。
三、 《文学副刊》对当下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启示
“20 世纪初期,特别是五四时期,中国进入了一个国门开放的时代,世界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如潮水般涌了进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流派纷呈的繁荣景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12]
诞生于这种环境的 《文学副刊》,一方面拥有发展比较文学学科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拥有促进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才队伍,为我们比较文学研究留下了丰硕的果实。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文学副刊》 所取得的成绩,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首先,研究 《文学副刊》 可以促进人文精神与思想研究的发展。从前文可以得知, 《文学副刊》 具有古典主义倾向,在其对欧洲古典主义研究文章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 《文学副刊》 视野中的古典主义直接继承了古希腊文化精神,强调人的解放和人性自由,但其认可的古典主义精神又是理性的,一方面反对浪漫主义的散漫与放纵,另一方面又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绝对理性与刻板。从这个角度来说, 《文学副刊》 所崇尚的人文精神更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且这种对儒家文化的继承直接来源于孔子,《文学副刊》 第 199 期刊载了 《新孔学运动》 一文,⑦文中提出儒家学说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具有普遍性与永久性的成分,应该成为中国一切改革的核心所在。第 247 期的 《孔诞小言》 更是直接指出:“吾国之文化精神,寄托于孔子一身,今虽时移世易,然孔子仍为中华民族之楷模代表人物,非任何人所能否认。”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副刊》 对儒家思想和孔子的推崇并没有导致其陷入道学与说教的误区,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文学要追求精神层面的目标,这种追求使得文学一般是循着超越即时、超越当下的层次进行发掘,探求精神层面具有恒久价值的范围和对象。”
所以,《文学副刊》 通过两大源泉来吸取人文精神的养料:
一是来源于欧洲的古希腊文化思想;二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情理和谐思想。在将近百年之后,对 《文学副刊》 这部分思想的梳理与阐发必然会促进我国的人文思想研究。
其次,梳理比较文学研究的早期学术资源。比较文学是一门包容性极强的学科,诸多新的研究方法与方式最终都会被比较文学容纳,成为其内在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比较文学学科是一门常变常新的学科,但由此带来的弊端就是,我们学科的研究者很难“往回看”,我们往往热衷于追逐学术前沿,而忽视了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由此可能导致某些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从事学术研究时走弯路或做重复性的研究,为了防止这一现象,整理我国比较文学早期的研究资料与学术资源,规范我们学科的研究方式就显得非常必要,而研究 20 世纪初期的 《文学副刊》 就是我们应该迈出的一步。然而,当下不少针对外国文学作家的研究,无意识地回避了 20 世纪初期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做的工作,或者对该时期的研究成果轻描淡写。的确,由于比较文学初兴期的研究论文或资料大多散落在各种期刊、副刊之中,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前辈学者在出版个人文集时会有意识进行整理收录,但由于各种原因,依然有诸多内容“遗落”在旧报刊中,如 《文学副刊》 的编辑浦江清就针对外国文学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由于 《文学副刊》 坚持不署名政策,浦江清的后人在为其出版文集时,有许多文章无法确认作者而不能收录。该时期的大多数文学报刊将文学创作、翻译、评论融为一体,即使涉及外国文学也以翻译为主,文学批评为辅,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者较为忽视这一方面资料收集的原因。不过,像 《文学副刊》 这样集中评论外国文学,带有明显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的副刊很罕见,这也成为我们学科研究者应该对其产生重视的原因。
《文学副刊》 是一个比较文学初兴期的特例,它通过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位一体的模式来进行文学批评研究,在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初建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文学副刊》 重点论述的英、法、德三国文学,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充分的论证,这是其他同时期媒体所忽略的地方。在我国 20 世纪初期,英、法、德三国文学相对而言并不是我国文学界吸收的重点, 《文学副刊》 在当时虽然很好地填补了这一块空白,但由于不符合该时期我国的文学主流,其历史功绩遭到了忽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中国比较文学学科逐渐发展,并将研究目光转移至欧美主流文学时,《文学副刊》 的研究成果又大都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因此,还原 《文学副刊》 的文学批评研究成果,通过将其放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大环境中进行比较,将有利于我们当下的研究。另一方面, 《文学副刊》 非常重视外国文学译介,它对译者与翻译理论的探讨是我国以往译介学研究中少有涉及的方面。我国 20 世纪初期是译介外国文学的高潮时期,《文学副刊》 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涉及翻译方式与方法、翻译方向及内容,对译者的基本素质,译作的选择倾向,文学翻译的标准等问题都有论述,《文学副刊》 的翻译研究对我们当下从事译介学研究依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此外,以前的研究者涉及 《文学副刊》 时,多为材料摘取,且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这一现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 《文学副刊》 对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意义。
因此,对其进行价值重估,是我们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以及回顾与展望我们学科时应该走的一步。
参考文献:
[1] 徐志啸。中国比较文学简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2] 张铁夫,季水河。新编比较文学教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3] 杨义,陈圣生。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4] 武新军。现代性与古典传统[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5] 高旭东。比较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6]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7] 吴宓。吴宓日记(第 3 册)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8] 杜素娟。沈从文与《大公报》[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9] 吴宓。 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 [N]. 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1-2.
[10] 毕树棠。琐忆吴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 吴宓。支那客谈欧洲事[N].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01-09.
[12] 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3] 孔诞小言[N].大公报·文学副刊(247 期),1932-09-26(。未署名文章)
[14] 张荣翼。在消费与时尚语境中的文学问题[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