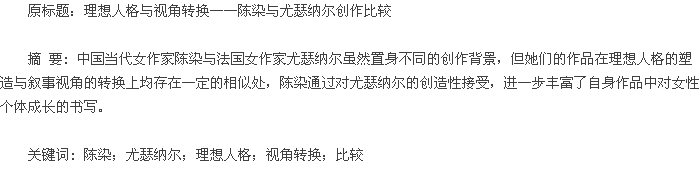
在陈染看来,“法国的尤赛纳尔是女作家中较有力度、有厚重感的一个”。[1](P92-97)在尤瑟纳尔近 70 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她往往将笔触伸向久远的历史深处,在古老的历史背景之下展现个人的生命历程,致力于理想人格的诗意建构,同时在叙事视角的转换上也不断创新。陈染在对尤瑟纳尔的接受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创造性,尝试将女性个体的成长作为叙事主旨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框架中,同人格建构与视角转换结合起来,令作品呈现出全新的艺术效果。
一、理想人格: 战斗与逃亡
理想人格的塑造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作者常常会将心中理想化的道德品质贯注在某个主角人物身上,通过刻画其生活遭遇反映出个人与社会或时代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并通过人物的选择将正确的人生和文化观念树立起来,这样一种写作模式的产生实质上是与作家内心自我认同的需要有着紧密联系的。
法国哲学家拉康在“镜像”理论中认为,“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属于己,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2](P90)这里所指的“镜中影像”其实就是一个被发现的他者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他者是自我成长的参照系,个人只有通过和他者进行全方面的比较,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对自我的找寻。同时,自我主体和镜中我之间假设要产生某种认同感,这就必然要求想象的介入,个体的理想化虚构使得“我”和“他者”之间拥有了相似性,而由作家在自己笔下所描述出的理想人物形象正是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他者。
“总的来说,对真理的探索是我的主题,我认为,要通过人、通过有生命的东西来寻求真理,这是我主要的见解”。[3](P127-133)在尤瑟纳尔的作品中,这种观念直接表现为通过叙述家族史以审视家族的优缺点,并在历史叙事中建构具有典型性的优秀人物形象,这两类人物共同作为他者形象完成了她对于自我的构建,面对现实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战斗精神成为他们共同的特点。
《世界迷宫》三部曲是尤瑟纳尔自传式写作的最主要作品,以其父亲、母亲为代表的家族前辈成为作品的主角,在作者以冷静的态度回望自己曾经辉煌的家族历史之后,她清楚地发现,尽管先辈们的身上有着太多的缺点和不足,但他们中的年轻者在自己的一生中仍然执着地追寻真理,虽然他们无力去改变生活,但却始终坚守着对自由的渴望。如果说先辈形象身上的优秀品质主要只是表现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社会及时代的对抗尚不够激烈的话,那么,在尤瑟纳尔的历史小说中,强健的人格力量就成为带有普遍性的存在。以哈德良、泽农、索菲等人物为代表,这些杰出人物对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均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并竭尽全部力量尝试改变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当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强权之时,这些人物甚至会以死亡的方式作出自己最后的抗争。“可能有人陷入了当前普遍存在的偏见之中,不肯承认贵族血统的典型人物不管有多矫揉造作,有时还是有一种独立不羁的精神或是自尊心的,有一种忠贞不贰或大公无私的精神,就定义而言,这些品质都是高贵的”。[4](P310)客观的说,无论身处哪个时代,这样的人物终究只是少数,但正是这些孤独的精神守卫者令漫长的历史长河不时地闪现些许微光,带给人们某种希望。
与尤瑟纳尔塑造的人物相似,陈染的作品中也有着大量的理想人物形象,在她笔下建构出来的女性人物谱系中,人物逐步确证自身的存在,进而完成作为独立个体的成长过程。在对待现实社会的态度之上,她们选择的也是孤独的坚守,绝不向外部势力妥协,应该说,两位作家内在的精神实质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当尤瑟纳尔作品中的人物采取了积极的战斗姿态时,陈染却让自己的小说人物走向了逃亡之路。“不断地寻找与逃离,是陈染小说人物面对世界的姿态”。[5](P45-48)这种景象同陈染在生活中表现出的个人气质有着惊人的相似。“很长一个时期,‘向后转’,逃跑,一直是我在现实对抗中的姿势,而这些矛盾的、抵触的关系又是那么地源源不断,扯也扯不完”。[6](P248)正像前文所言,作家对于小说人物的塑造其实是源于内心自我认同的迫切需要,而在陈染的身上,“自我认同的渴望来源于人物自身具有的深层的不真实感与漂泊感”。[7](P80-86)由于现实环境中这种无所依傍的情境,因此,选择逃亡便成为陈染笔下的人物保存自身独立性的唯一良方。
陈染作品中理想人物建构的完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其早期创作的《小镇的一段传说》《空的窗》等作品中,人物完全沉迷于自我内心的孤独,对世俗生活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在《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等作品中,人物开始具有了明显的自我意识与反抗精神,不过,主人公的行动在此时仍表现为自在的形态,例如黛二和琼斯的结合纯粹只是因为惧怕孤独,所以,这里的逃亡之路表现得还过于情绪化,是茫然和困惑心态交织下的选择。
到了《空心人诞生》《时光与牢笼》中,主人公的反抗意识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并且开始寻求全新的生活伙伴。苗阿姨在注视父亲之时“眼里迸射出刀子一般的寒光”,水水大胆地写下“我不是一个小对钩而是一个人”的内心呼喊,她们最后的逃亡让读者感受到的不再只是简单的哀伤,而具有些许的悲壮色彩。直到《沉默的左乳》《破开》等作品中,人物开始拥有最为强烈的个体意识,更关键的是,其反抗对象得到了清晰的确认,她们学会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思考起之后的人生道路。由此,个人的逃亡升华为女性群体从男性和秩序的压迫下自发逃离的过程,人物的精神气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以表现出来。
理想人格的建构最终往往表现为自由意志的生成,“自由与意志相关,自由产生于意志决断和行为”。[8](P11/P80)在此基础之上,无数次的行为选择培养了人物各具特色的性格,最终完全内化为主人公自我人格的组成部分。“性格是个性坚强特性的总和,这种特性在抽象概念体系中表示:贪权、勇敢、坚定、残忍等性格,或者温存、胆怯、腼腆等性格。这些特性总和构成其人的本性……也可以称为他的经验性格”。[9](P11/P80)在尤瑟纳尔和陈染的作品里,主角人物的经验性格所导致的最重要结果便是他们对于死亡不约而同的选择,死亡叙事在两位作家的创作中均占有极大的比重。但是,在前者的叙述过程中,人物受到思想中生命永恒轮回观念的影响,死亡成为其主动选择的自我完成方式,在后者的笔下,死亡则是人物对于外在世界不得已而为之的拒绝方式,这也正符合他们不同的生存姿态。
谈及死亡,人们首先感知到的便是无尽的恐惧,躲避与死亡有关的话题成为一种下意识的选择。但在尤瑟纳尔这里,对死亡的恐惧完全被排解了,通观她的作品,绝大多数的理想人物最终都走向了死亡。“一位批评家指出,我在作品中特别喜欢表现将近死亡的人物形象,而死亡与一切生命的意义格格不入”。[9](P123)实际上,选择死亡并不意味着对生命价值的抛弃,如若个体生命和现存秩序完全不能相容,主动终止生命的行为正实现了对价值体系的维护。正如《苦炼》里的泽农所想的那样,尽管他在面对死亡之时同样产生了强烈的生理反应,但在长时间的呕吐之后他确信自己毁掉躯体的做法“是为了使他避免受到更坏的、不值得忍受的痛苦”。
同样的死亡景象也不断出现在陈染的作品里,对此,作者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态度。“去死,在某个层面上,起码是对平庸哲学的叛逆;死,是一种否定行为,这种否定于某一类人来讲,我以为正是对生命的渴望,尽管这样说是有悖逻辑的”。[10](P76)这种陈述清楚地反映出死亡书写在作者建构理想人格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人物区别于他人,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不过,与尤瑟纳尔的作品不同,陈染的小说所描述的主要是想象式的死亡,而并不涉及真正的肉体的消亡。例如《消失在野谷》中的“我”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后仍具有清醒的意识,死亡成为自我审美的对象,《麦穗女与守寡人》里“我”则用充满诗意的文字写下自己的死亡构想,对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做了详尽的交代。可以说,拥抱死亡完全是源自于孤独的生存处境,人物用退守代替前行以获取心灵的慰藉,维护人格的完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尤瑟纳尔始终强调人在面对困境时所应具有的无畏和勇敢精神,战斗到最后一刻成为不同人物身上表现出的共性。
“西方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11](P81)这种文化观念使得她将描写出生命的厚重感作为追求的目标,人成为同神与耶稣并列的一员而存在。
陈染则具有鲜明的内倾性个人言说特征,她将观照自我置于更为主要的层面,由此生成的理想人格主要是朝向内部的。“我对人群和世界都有一种逃避感。当然你可以将这种逃避升华为一种主动性,但对于我来说主要是被动的,也就是没有出路的一种选择。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就只好不断地寻找与逃跑”。[12](P38-44)这种区别的出现实际上源于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区别,“西方的自由追求面对束缚采取的是进攻方式,它以解除束缚来获得自由。……中国的自由追求也是基于束缚,但它获取自由的方向却是退却”。[13](P151)当外部社会将人们抛入无所凭借的虚无之中,陈染笔下的人物努力实现的是对于自我的把握,个性化的人格气质最终使得她的作品具有了和尤瑟纳尔并不全然相同的风格。
二、视角:个人声音的表达
文本的建构过程不仅仅是对人物及事件的罗列,它同样还涉及到叙述手法的问题,作家要将自己的内心思考充分表现在文本世界之中,这就必然要求他通过多样的叙事策略以实现对于外在经验世界的重建。在这其中,叙事视角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不同的叙事视角完全可以造成对作品的多样理解。“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14](P159)与传统小说主要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不同,尤瑟纳尔与陈染的作品里均存在多重叙事视角交替与转换的现象,极大地扩充了作品的张力。
尤瑟纳尔的小说首先大量采用了第一人称内视角的写作手法,叙述者作为小说文本中的人物真实地存在,并用“我”的眼光去感知和讲述所发生的一切。例如在描写历史人物哈德良时,作者别具一格地使用第一人称来写历史作品,哈德良自己成为述说生平往事的主体。而在她的自传性作品中,尤瑟纳尔又有意识地使用全知全能视角进行叙事,故事的全部发展过程、人物的言行、心理活动及最终结局全部在叙述者的把握之中。譬如在《世界迷宫》三部曲中,虽然“我”在表述自己的生活往事时完全走入了回忆之中,但在对家族情况的讲解中则仍不露痕迹地俯视着所有人的行动,整个家族的历史都在“我”的叙说中重现出来。另外,外视角也时而出现在故事的叙述之中,人物尽管也伴随着事件的发展过程,但却保持了一定的叙事距离。《默默无闻的人》的开头部分“,纳塔纳埃尔死在弗里斯兰的一个小岛上,他的死讯传到阿姆斯特丹,在亲人中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之所以使用这样的陈述作为小说的开始,重点并不在于告知读者主角人物的最终命运,其最主要的意义是揭示出纳塔纳埃尔孤苦无依的生命状态,为之后表现他在人世间体验到的万般滋味预先进行注解。
陈染对流动的叙事视角所带来的多元审美效果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无处告别》《空心人诞生》《空的窗》《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文本中,叙事视角均实现了自由转换,充分满足了作者的倾诉需求。《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是陈染在叙事视角的转换上最为成功的一个文本,多种叙事视角在文中交替出现,叙述者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每个人物都具有了独立言说的能力,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与角度上对同一事件展开多重叙述,使得整篇小说表现出丰富的叙事内涵。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外视角的方式简要描述出黛二的生活经历,在较远的距离上审视她在此时此刻的境况,如“现在,她只爱她的梦幻,爱某一些局部,除此以外,她一无所有”。在介绍黛二和母亲、伊堕人、“大树枝”之间的关系时,作者又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叙事,客观地揭示出黛二在混乱的人际关系之中复杂的心态。同时,陈染还使用第一人称内视角的方式将黛二、母亲、伊堕人和“大树枝”各自观察到的生活和内心所思所想交错呈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在小说的第四部分,叙述者的转换更是直接以【黛二独白】和【伊堕人独白】的方式不加遮掩地表示出来,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人物形象的认识。然而,陈染对叙事视角的把握并不仅限于此。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女性主义表达‘观念’的‘声音’实际上受到叙述‘形式’的制约和压迫;女性的叙述声音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技巧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社会权力、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15](P320)因此,女性作家不断尝试打破男权话语对文学写作的统治地位,以一个女人的眼光独立实现对个体自我的言说。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提出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和集体型声音三种概念,认为它们分别代表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15](P17)与传统的作者型声音相比,个人型叙述声音虽然会令女性作为叙述者的权威大打折扣,但这种区别并非绝对,尤其是在讲述个人经历之时它往往具有名正言顺的权威性。陈染正是希望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表达出一种不同于传统作者型声音的具有女性叙述权威的个人型声音,这突出表现在故事叙述过程中不同人称的使用情况上。
陈染在自己的小说中大量运用第一人称的“我”来讲述故事,作为对作者身份有清晰意识的叙述者,“我”完全独立地进行着女性个体的话语表达。《与往事干杯》在写到肖蒙和男邻居的过往经历时已经使用了第一人称参与叙述,只是当时的“我”还处于少女的茫然之中被动地接受耕作,到了和老巴交往时“,我”占据了支配地位,审视着这个孩子般的男人。“我把头埋在他的胸膛上不住地亲吻,并且要他也这样对我做。他就听话又急切地做起来。”由此,女性正逐渐走向叙述的中心,“我”从性爱过程中的简单参与者转变为引导者与指挥人,这种努力在此后的作品中有了更为强烈的表现。在同样描写尼姑庵岁月的作品《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里,为了明确地强调“我”作为叙述主体的权威性,作家本人在开篇之处便出现在作品之中,隐晦地向读者展示小说的阅读线索“,我”以敏锐的主观意识参与到叙事之中,并不断强调自己是以作家这一身份而存在。当故事进展到高潮部分时“,我”主动向那男人出卖自己,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我是那么地喜爱这声音,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一种对女性的呼唤比这声音更令人心情激荡,更纯洁尊贵。”叙述者在此处毫无顾忌地表达着对生命欲望的追寻,这实际上带有鲜明的挑战色彩,意味着女性要在第一人称的欲望呈现中宣告自己对于叙事权威的把控。
应该说,在陈染的作品序列里,第一人称叙述手法的使用并不鲜见,前面说到的文本中“我”的主动言说充分强化了叙述者个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在文本内部中不同人称的转换过程表现得还不够明显,而在长篇小说《私人生活》里,不同场景中的叙述人称出现了鲜明的变换,直接代表了叙述声音的转移。作为一部对倪拗拗个人生命成长史的回忆性叙述文本,《私人生活》的绝大多数叙述过程是由第一人称“我”来完成的,女性主体的个人型声音在此处占据了核心地位。然而,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在文本中的两个部分悄然出现,成为一种颇有意味的叙事现象。首先,在倪拗拗与 T 老师的交往过程中,尽管 T 一直处于主动的进攻位置,但叙述人仍旧是由“我”担任,这正是由于倪拗拗始终对其保持有强烈的敌对意识。可在“床的尖叫”和“阴阳洞”这两章中,当“我”在他的诱惑中放弃抵抗之后,叙述人称悄然过渡到了第三人称“,她”只是很机械地目睹这一切的发生,彻底走向了被动的接受。小说中的一处描述也许可以对此做出最准确的解释,“在这一刻,她的肉体和她的内心相互疏离,她是自己之外的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完全被魔鬼的快乐所支配的肉体。”正是由于“她”从这个男人身上获得的只是单纯的欲望满足,因此,失去女性主体地位的叙述者只能将叙述的权力拱手相让。相反,在同禾与尹楠的关系描述上,叙述者“我”主动地控制着整个过程的进展,其间也从未出现过叙述人称的转换。
假使说 T 对“我”而言是一个纯粹的肉体征服者,那么禾与尹楠便是陪伴我一天天长大成人的真诚伙伴,是他们给了“我”面对世界的勇气与信心,“我”既然成为自由行动的主体,当然也就是话语言说的主体。其次,在小说的最后两章里,这种叙述人称的转换也表现得格外醒目。当倪拗拗因为糟糕的精神状况而被送入医院时,医生祁骆给她开具了一份病历,使用的正是第三人称的记录手法,这里的“我”身处于孤独无依的外部世界里,内心状态也前所未有的虚弱,因此只能为他人的眼光所审视。而在长期的思考与回忆之后,倪拗拗用一封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信替代了去医院复查的报告,“我”对世界的看法与对生命的理解都更进一步,可以独立面对外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由此,“我”终于成长为完整的生命主体,这封信的寄出则成为“我”向世界发出完整的个人声音的标志性事件。
“妇女的小说以第一人称现实主义叙述作品的姿态复苏,这是一种在观念上契合女性主义的形式;作者视之为第一次以不掩饰的声音讲述妇女的故事的一种方式。……这样做,企图把妇女第一次展示为积极说话的主体”。[16](P227)对于陈染而言,由第一人称写作带来的情绪宣泄上的便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精神需求,但这种叙述方式中所隐含的个人型声音才代表了作家内心最本质的创作动机。与以往女性作家多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表现情感世界的感伤或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不同,陈染作品中叙述视角的转换显然具有更为明确的目标指向,“我”在公开展现自我隐秘经验的过程中最终建立起的是独立于男性世界之外的个人生活空间,这种主人意识的生成为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成长起到了内在精神的支撑作用,从这个意义而言,陈染的写作真正实现了表达具有女性叙述权威的个人型声音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林 舟,齐 红. 女性个体经验的书写与超越———陈染访谈录[J]. 花城,1996(02): 94-99.
[2](法)拉 康着,褚孝泉译. 拉康选集[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柳鸣九. 我所见到的“不朽者”[J]. 读书,1982(05):120-135.
[4]柳鸣九,罗新璋编选. 尤瑟纳尔研究[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5]杨 敏. 论陈染小说人物的心理困境[J]. 小说评论,2005(05):47-50.
[6]萧 钢,陈 染. 陈染对话录———另一扇开启的门[A]. 陈染文集(第四卷)[C].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