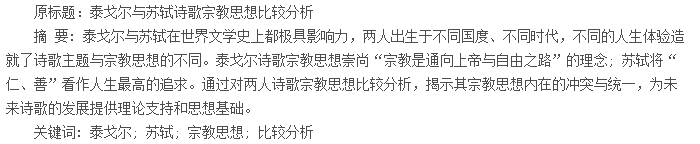
泰戈尔和苏轼不仅是诗人,在文学的平台上更代表了两个国家的文化潮流和宗教思想。中国和印度有着同样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两国的文学和诗歌作品都丰富了世界艺术的百花园。两者差异也非常明显,都拥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泰戈尔诗歌中的宗教思想侧重于“个体平等”和“梵我合一”; 苏轼诗歌中的宗教思想则强调“仁德慈悲”和“豁达自由”。两种宗教思想的对比也是文化的对比,诗歌中宗教思想生长的土地最终要归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化内涵。
1 泰戈尔与苏轼诗歌宗教思想解读
泰戈尔是着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诗人,以及社会活动家和民族主义者,也是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泰戈尔将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奉献给了世界文学,在教育、艺术、宗教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圣雄”甘地称赞泰戈尔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其诗歌作品最吸引人的魅力在于其宗教思想所传达出的哲学精神,诗歌中宗教思想价值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1]。印度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哲学与宗教的天堂,印度人民普遍信仰宗教。印度的宗教思想有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婆罗门教、印度教等,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众多印度宗教文化,养育了善良真诚的印度人民。泰戈尔在宗教思想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思想观念。泰戈尔出生的年代正是印度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其言行、思想、诗歌都被打上了宗教思想的烙印。其宗教思想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和连贯性的特点,在他的诗歌中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其宗教思想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格论”,强调“自我”和“灵魂”。泰戈尔倡导“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拥有同等权利”的理念,诗人在致力于提高女性地位、改善农民生活的运动中,用诗歌严厉地抨击社会的旧习俗和野蛮行为; 他在宗教观上坚持“人与自然合一”“梵我合一”[2]。泰戈尔看来,自然与生命是无限循环的,而要在无限循环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就要遵守和谐统一的原则。
诗人最着名的诗歌《吉檀迦利》就是献给神的礼物,充分表现了诗人渴望“人神结合”的人生态度和追求。
苏轼是宋代着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诗人,他才华横溢、不拘泥形式,创作手法洒脱大气,人生观念潇洒旷达。史书记载: “苏轼生性放达,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3]在苏轼 4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共留下了 2700 多首诗,其诗歌和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无不与禅、佛相关联,儒家思想是苏轼创作的基础。任何诗歌和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都是分不开的。苏轼的诗歌根植于北宋的社会土壤之中,建立在北宋文化环境和个人的生活历程之上。他将内心的情感融入诗歌,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宋代掀起了一场“儒学复兴”的浪潮,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苏轼在“儒学复兴”的运动中,将儒家、道家、佛家三种思想进行了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思想,为儒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和视角。正是这场文化运动,使得苏轼的宗教思想逐渐开始走向成熟。苏轼的一生,与宗教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首先,其思想以“仁”为核心。他一生为官,造福一方百姓,是儒家思想“勤政为民”和佛家思想“慈悲为怀”的体现。面对起伏坎坷的人生经历,能够做到洒脱旷达,与宗教思想密不可分。
其次,其宗教思想集三家之大成而融会贯通。苏轼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精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宗教思想修养,他是真正的宗教思想的实践者。
2 泰戈尔与苏轼诗歌宗教思想比较
2. 1 情感表达
“爱”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是宗教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人诗歌都离不开情感与爱的表达,情爱、母爱与泛爱构成了情感的整个世界。通过对这三种情感的比较,体会两种宗教思想的不同。
2. 1. 1 情爱表达
在印度宗教经典里有提及情爱的诗歌,基督教《圣经》里的《雅歌》,便是将男女的爱情比作人对于“神”的向往,耶稣也将自己比作生活中的新郎。我国着名学者郑振铎说: “泰戈尔是一个爱的诗人,爱情从他的心里、灵魂里泛溢出来,幻化了种种的式样。”泰戈尔的《爱者之贻》第 15 首说“她村里的邻居都说她黑,然而她在我的心上是朵百合花,是的,虽然并不白皙,真是朵百合花”[4],可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便是爱情,泰戈尔以其直白简练的语言诉说着内心的爱情。泰戈尔的爱情诗写给女人,也写给宗教里的“上帝”,是写给“上帝”的赞美诗。
苏轼与泰戈尔所表达的情爱观有很大区别: 泰戈尔将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与弗洛伊德的“性爱理论”进行了完美统一,苏轼通常在诗歌中为爱情营造一个纯美的虚幻的意境。《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中的“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
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通过美好意境来营造氛围。苏轼的爱情诗风格也是多变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为纪念去世十年的妻子而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情感朴素真挚,备感沉痛。
苏轼的诗歌在男女情欲的表达上更为含蓄内敛,诗词《双荷叶·双溪月》“红心未偶,绿衣偷结。背风迎雨流珠滑。轻舟短棹先秋折”,他“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影响下,将宗教意识和情欲观念融为一体,诗歌中情欲的表达也沾染了宗教色彩。
2. 1. 2 亲情表达
在泰戈尔的作品中,母爱是最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的,也是泰戈尔宗教思想与哲学思想的起点,拥有战胜一切的力量。诗人以饱满的激情赞美母爱、歌颂母爱,情感直接而热烈。在《金色花》中,诗人写道: “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走到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的香气,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5]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和谐生动的画面,孩子化身为花香,时刻追随着母亲的脚步,只有在母亲身边才是最幸福的,用细腻的文字刻画了一个温婉善良的母亲形象。“当母亲看书时,我便要将我小小的影子投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但是你会猜得出这就是你的小孩子的小影子么?”[6]泰戈尔以一个调皮的孩童的身份写这首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母亲的依赖之情,这也是宗教思想中最干净、最纯净的感情,孩子是上帝派来人间的天使,母亲是孩子的守护神。
苏轼诗歌中的亲情主要体现在对兄弟的感情上,这也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手足之情”,并开创了“夜雨对眠”的文化意象。苏轼兄弟从小在一起读书学习,其兴趣爱好相似,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苏轼的“夜雨对眠”诗将亲情作为了人生的最终归宿,不仅包含了情感对人生的慰藉,反映了诗人对时光逝去的焦虑感,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了儒家文化观念中对血亲人伦的重视。《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中,全诗以“悲”为基调,营造了一种忧郁感伤的氛围。“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这两句诗充满了与弟弟分别的痛苦,同时对弟弟厚重的牵挂之情也跃然纸上。最后四句“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在提醒弟弟也包括自己,不能忘记最初的志向。“夜雨”意象的运用也来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悲秋”的意识,这种悲秋的意识和儒家的“中和”思想是有所背离的,但是也体现了苏轼独立思考与人格的成熟。
2. 1. 3 泛爱表达
泰戈尔曾说过: “爱是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爱不仅是感情,也是真理,是根植于万物中的喜,是从梵中放射出来的纯洁意识的白光。”[7]泰戈尔的泛爱论,包含了印度传统宗教思想中的“泛神论”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国家的平等、自由、博爱的观念。诗人的泛爱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选》: “我能生在这一片土地上,因此我有运气去爱她,我是有福的。即使她不曾拥有王室的珍宝,但是她的爱的活财富对我就够宝贵的了。”诗人对祖国的情感毫不掩饰地表现在诗歌里,这是一种大爱。泰戈尔的泛爱与宗教是紧密相连的: “你把你的爱给了我,充满着世界因你的礼物。你的礼物聚于我身上,而我却不认识,因为我的心中正睡着夜,可是我虽然沉埋在睡之谷里,我早就快活的浑身打颤,而且我知道因为你的大宇宙的宝贵的报告,你将从我这里接受一朵小小的爱的花,在早上我心醒来的时间。”其中对宗教和神的爱与赞美也是泰戈尔情感的一种表达,这是一种崇拜和感激之情。
在苏轼当时生活的社会,泛爱主要体现在对人民和对国家两方面。当时社会正处于恢复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中,社会急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和法规。苏轼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之德”作为自身形式的准则,“圣人之德”是指儒家的“仁义孝悌忠信礼乐”,这是一种大爱,以“仁”为核心的思想追求在苏轼的诗歌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蜂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
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8]。在正月十五灯月交相辉映的时候,满城的仕女在游玩,忽然听到吹箫的声音,原来是农民在祈求来年的丰收,苏轼心系百姓,直到深夜才离去。这首诗里体现出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践行,同时也体现着对祖国深沉的爱。苏轼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儒学同样推崇的是“国破家何在”。
2. 2 生命诉求
生命是宗教永恒的主题,包含死亡、美学、人格等内容。由于受宗教思想影响,两人诗歌中都渗透了宗教元素,他们在诗歌中都提到了生命意象。
印度的宗教思想强调生命与宇宙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泰戈尔说,“人的灵魂意识和宇宙根本就是统一的”,是生命和神的统一。其诗歌是对宗教思想中“梵我合一”思想的继承[9]。在诗人看来,生命是宇宙的整体,是由“梵”主宰的。“梵”是宇宙中最高境界的自我,是人生命的最终追求。诗人怀着无限的敬意赞美“梵”,“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像七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诗中“神”在作者心中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抽象关系,而是成为了肉体的化身,无处不在,永恒地存在着,将无限的循环和有限的生命统一成了衍生万物的本源。其次,诗人认为生命是有灵魂的。
他在《什么是艺术》中讲道: “在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不是肉体的,而是人格的人,人格的人有自己的好恶,并且想要找到某种东西以满足自己爱的需求。”由此可见,诗人将所谓的人格看成了生命本质的一种体现,是人生命存在的本体。人格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是自我的人生观,另一方面是超我的价值观。自我的人生观是要受到社会规律的限制,也是这个世界上一切不平等、侵略、欺诈的根源。而超我的价值观则是生命最高的境界,宗教中的“神”或者“梵”是可以超越自然和现实的力量,是人格的最高的追求。
苏轼在看待生命和人生的问题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本的,他认为“天”的力量是无穷的,掌控着人间的一切,而皇权就是“天”的象征,因此自己的生命是归于皇帝的。“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儒家思想也是苏轼所尊崇的。苏轼认为君主的权利是“上天”给予的,正所谓“天命可畏”。苏轼说: “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他一直以儒家的“君权”思想作为束缚自己道德修养的准则,这种理论将皇权推向了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两人思想最大的不同。同时,苏轼对生命本质的感受也受到了佛家思想的影响。人生来是罪恶的,要在人世间洗净身上的罪恶,以求得来生的幸福。《安国寺浴》: “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诗人企图扫除尘世间的污染,同时摆脱身上功名利禄的束缚,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和清净,这也是这首诗的主题。这种思想的形成受到了佛学“大乘般若性空”思想境界的影响,是苏轼在安国寺里“默坐”之后对生命本质的一种感悟。
在泰戈尔的诗歌中,有着对生命归宿与生命本体之间关系的深深思考,泰戈尔将自己定义为“诗人的哲学家”,他在用诗歌展现独特的“生命”美学。
这种展现方式和东方所提倡的神韵美学是不尽相同的。他认为宇宙之间是和谐统一的,对立和矛盾会使世界的本质发生变化,生与死在本质上就是统一的,表面上的对立只是暂时的,生命的结束就是重生,这是一种轮回的生命美。这一理论和儒家的理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对死亡的肯定,体现了生命的美。美学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是一种升华的生命,宗教中的美学继承了对平静和谐的追求。泰戈尔的美学思想来源于宗教,对其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发展和超越。他的诗歌“莲花开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觉地在心魂飘荡,我的花篮空着,花儿我也没有去理睬。不时的,有一段的幽愁来袭击我,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的芳踪”,借助美学意象表达了对生命美的喜悦。同时,诗人认为所有的情感都是可以转化的,所有的罪恶都能够在朝着善良和美的方向发展。泰戈尔渴望见到上帝,在诗歌中表达“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永远用坚决的拒绝来拯救我,这刚强的慈悲已经紧密地交织在我的生命里。有时候我懈怠地捱延,有时候我急忙警觉寻找我的路向; 但是你却忍心地躲藏起来”,后期诗人明白这种欲望即是罪恶。尼采曾经说: “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把人生看作一件艺术品,这就是哲学思想上的审美意识。
苏轼的美学意识起源于儒家的宗教思想,经过道家和佛家的融合,实现了本质上的超越,其诗歌中美学意识的体现尤为明显。他在《定风波》中写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再次回望人生时,无论幸福还是痛苦貌似都不见了。此时审美意象的最终归宿为顺其自然和人合于天,克服了生命中的局限性,将磨难、富贵、荣辱都当作了人生的一种经历,这是对“人生如梦”思想的一种突破。悲剧只是人生中片面的一个体现,苏轼在后期的诗歌中构建并完善了美学体系,将乐观冷静的生活态度与激情抗争的悲剧精神进行了完美的结合。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所说“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正是对苏轼后期思想的高度概括。
3 结语
在近百年的时间长河里,泰戈尔和苏轼的诗歌作品以其独特的意蕴、优美的意境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熏陶了一批又一批热爱文学的人。两人的诗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形成,却拥有同样的价值和力量。泰戈尔和苏轼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宗教思想都带有时代和国家的烙印,是世界文学史上宝贵的财富,也是生命馈赠的礼物。
参考文献:
[1] 李金云. 泰戈尔文学作品中的宗教体验[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2005.
[2] 杨桦菱. 泰戈尔爱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在 20 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冲突与融合[D].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2013.
[3] 李明华. 苏轼诗歌与佛禅关系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2011.
[4] 李金云. 论泰戈尔思想和文学创作中的宗教元素[D]. 上海:复旦大学,2009.
[5] 李骞. 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分析[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2) : 100 -103.
[6] 苏蔓. 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宗教内涵[J].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 : 30 -32,36.
[7] 张德福. 熔诗情与哲理于一炉: 泰戈尔宗教诗歌评述[J]. 南亚研究季刊,1998(4) : 59 -61.
[8] 龙晦. 从《前赤壁赋》谈苏轼的宗教思想[J]. 中华文化论坛,1998(1) : 72 - 79.
[9] 武澄宇. 浅议泰戈尔的宗教观[J]. 青年文学家,2010(16) :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