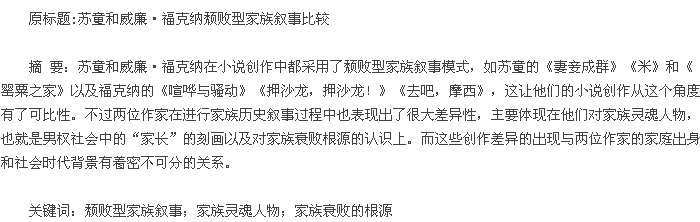
中国当代作家苏童在其小说中经常以中国南方大小家族为叙事背景来表现家族的衰败,可以说“他的家史演义小说暗藏了一则衰败的国族寓言”,[1](P408)如《罂粟之家》中以刘老侠为代表的刘姓家族、《妻妾成群》中以陈佐千为主的陈姓家族以及《米》中五龙一手创建的家族等。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其着名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界里更是详细地描述了美国旧南方几大家族——《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家族、《押沙龙,押沙龙!》中的塞得潘家族、《去吧,摩西》中的麦卡斯林家族——逐渐分崩解析的过程。关于颓败型家族叙事的这一共同主题让苏童与福克纳的小说创作有了可比性。本文将主要从家族灵魂人物、家族颓败根源两个方面对两位作家的颓败型家族叙事进行比较,并进而探讨出现差异的原因。
一、家族灵魂人物
两位作家所描述的都是男权化的家族关系,而典型男权化社会决定了男性家长在家族中的主宰地位,由此成为了家族中的灵魂人物。苏童小说中的刘老侠、陈佐千和五龙等人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的“灵魂人物”,也就是家族中具有权威地位的“家长”,应是整个家族的主心骨,具有男性的阳刚之气,承担着照顾妻小,扞卫家园的责任。但是在苏童小说中,作家对此却进行了解构,他解构了男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意义,突出表现了男性的心理缺陷和阴暗面,深层次展现了男性弱小的一面。而这一切,作家往往都是通过灵魂人物怪异的性行为或性心理和性能力的丧失来表现的。
《罂粟之家》中的刘老侠是解放前夕一个封建大财主,但是他在有了一子一女之后就丧失了生育能力,唯一的亲生儿子还是个“白痴”。为了继承家业,他让妻子与长工通奸生下了另一个“儿子”。没有生育能力、带着“绿帽子”的刘老侠已然完全丢失了所谓的“权威”。
《妻妾成群》中的陈佐千作为陈家一家之长,娶了几房姨太太,表面上风风光光,但内里已被掏空的他也逐渐丧失了性能力。为了寻求刺激,他竟向妻妾们提出怪异的性要求,结果不仅遭到颂莲的拒绝,还遭到妻妾们的嘲笑,其三姨太还给他带了一顶“绿帽子”。最终恼羞成怒的他杀死了三姨太,但也只能在谄媚的二姨太的房里靠着“刺激”过日子。
《米》中的五龙靠着忍辱负重、心狠手辣打下了一片天地,但由于内心的极度自卑在遭遇到残忍的压迫和欺凌之后转化为极端仇恨,心理的扭曲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他与女人发生关系时总喜欢将米塞进她们的体内。但后来因流连妓院染上性病而丧失了性能力,最后更是全身溃烂而死。除此之外,苏童在小说中还常通过表现家族灵魂人物无力或不愿承担家庭责任来解构他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意义。
刘老侠的家族曾遭遇两次危机,但两次他都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牺牲女儿来“扞卫家园”。他第一次将女儿嫁给一个驼背以换取三百亩地,第二次更是将女儿拱手送给土匪供其淫乐三天以解救能够继承家业的“儿子”。陈佐千虽然在陈家仍是一家之长,但凭借的只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规训制度给予他的特权,而非他承担家庭责任的能力,其实整个陈家都是靠他的儿子飞浦在支持,而他自己终日只回旋在几房姨太太中间,操心于床笫之事。五龙在黑道上发迹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之后很少回到米店——他的家,而是混迹于各个妓院之间直至染病,更谈不上承担家庭责任了。
总之,苏童笔下的这些家族灵魂人物“不断地逃避责任,自我放逐,或多或少迷失了男性自我,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心理弱化甚至病态”。[2](P20)苏童在小说中对这些男性家长的心理阴暗扭曲以及弱小一面的揭露体现了作家对男权主体地位的解构,表现出了作家对男权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在福克纳生活的美国旧南方,家庭是南方庄园经济的基本运作机制,“父亲”则是家庭的主宰者。
美国南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男权文化再加上加尔文教派对“父亲”位置的绝对认同,造成了“父亲”在家族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于是,“父亲”也成了福克纳家族叙事小说中的“灵魂人物”。不过,与苏童不同的是,福克纳的家族叙事却在“批判父亲”和“崇拜父亲”的矛盾中徘徊。
一方面,福克纳家族小说中的“父亲”大多是暴君式、家长专制的父权主义者。他们大多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是非人道的南方社会本质的反映,是其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清教思想的集中体现,如《押沙龙,押沙龙!》中专制冷酷的托马斯·塞得潘。
他为了建立心目中宏伟的纯白人血统的“家族王国”,抛妻弃子,甚至设计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去杀害另一个具有一点黑人血统的儿子。《去吧,摩西》中的老卡洛瑟斯·麦卡斯林更是灭绝人性,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他不仅强奸了自己的黑奴,还强奸了自己与黑奴生下的女儿。《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作为一家之长,虽然充满仁爱慈祥,但却软弱无能,整日靠酒精麻醉自己来逃避现实,根本无法承担作为父亲应承担的家庭责任。
这些南方旧家族的父辈们在南方的土地上犯下了罪孽,他们将黑奴视为私有财产进行买卖,仇视和迫害黑人。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不仅成为家族衰败的源头之祸,也让它们成了福克纳笔下批判的对象。
但是另一方面,作家在描述这些南方父辈们的罪恶时却也不时暗示他们不是天生的恶人。在作家的笔下,他们也不乏一些优秀的品质,是南方英雄主义和贵族精神的代表。塞得潘和麦卡斯林虽然满身罪孽,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在创建各自“家族王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美德,如塞得潘的勇猛刚烈、敢作敢为、吃苦耐劳、意志坚强,以及麦卡斯林的超群勇气、精明能干和富有威望。而这些都是作家所珍视的南方传统美德。这一切使得福克纳对这些家族灵魂人物抱着一种既批判又崇拜的矛盾心理。
除了对家族灵魂人物的刻画不同之外,苏童和福克纳在小说人物的侧重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两位作家的笔下,虽然具有权威地位的男性家长都是家族的“灵魂人物”,但在苏童笔下,女性似乎才是作家着墨最多的人物,才是故事的灵魂,如陈佐千的四个妻妾、《米》中的织云和绮云等。而在福克纳的小说,女性虽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但男性才是作家所要借以表达思想的重点。
二、家族衰败之根源
在苏童和福克纳的小说中,从表面上看,家族的衰败都多多少少与家族灵魂人物的无能、不负责任或罪孽有关。如苏童笔下毫无血性的刘老侠、终日回旋在女人间的陈佐千和作恶多端、对家庭漠不关心的五龙,以及福克纳笔下无力维持家庭的康普生、满身罪恶的塞得潘和麦卡斯林。但是,如果更深层挖掘的话会发现,这只是家族衰败之源的表象。家族的衰败其实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只不过苏童弱化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更加强调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新势力登场而旧势力退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比如,在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属于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刘老侠一家作为旧势力的代表必然走向消亡,“《罂粟之家》宣告了一个阶级的破产……。”[3](P231)《罂粟之家》讲述的就是“一个地主家庭在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逐渐走向衰亡的故事”。[4](87)陈佐千生活的时代要比刘老侠早一些,虽然没有赶上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业,但其所代表的封建大家族已明显在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日益感到力不从心,生意也比以前差了很多,可以说正走在一条退出历史舞台的路上。五龙时代的后期正赶上日军侵华,只着眼于“家仇”、“内斗”的五龙也必然被卷入时代的漩涡,成为“国仇”的另一受害者。
与苏童不同的是,福克纳在揭示美国旧南方家族衰败之根源时更强调滋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罪孽,即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清教思想,是它们扭曲了人性,导致了美好传统道德的丧失,最终只能换来罪有应得的惩罚。导致康普生家族衰败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凯蒂的失贞。这个事件之所以会导致这一严重后果就是源于旧南方将女性的“贞洁”置于至高地位的清教思想,而凯蒂的“失贞”让家族颜面尽失,最终导致康普生先生靠着酒精逃避现实,昆丁绝望自杀,而杰生自甘堕落、浑身充满铜臭。在麦卡斯林家族,老麦卡斯林霸占自己的女奴,甚至强奸自己的亲生女儿,罪行令人发指,使得后代子孙在得知这一罪孽之后主动放弃家业,做了一个自力更生的木匠,最终使得该家族归于沉寂。该片土地上的另一大家族的“家长”塞得潘抛妻弃子,让兄弟自相残杀,并最终导致家族毁于一旦。老麦卡斯林和塞得潘之所以会犯下如此恶行并最终导致家族的衰败则都源于根植于美国旧南方这片土地上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是它们扭曲了人性,让塞得潘一心只想建一个“纯白人血统”的家族,容不下哪怕一丁点的黑人血统,也是它们赋予了奴隶主权利,让他们可以完全占有奴隶,当然也包括黑人妇女。奴隶制不仅使黑人奴隶变成了“财产,牲畜”,也使奴隶主丧失了人性,使得老麦卡斯林做出如此令人发指之事。
三、家族叙事差异的原因
苏童和福克纳两位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选择了颓败型家族叙事模式,但在家族灵魂人物和家族衰败根源的刻画和理解上却各不相同,究其原因,这与两位作家的家庭出身和社会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苏童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苏州一个普通家庭,他在苏州度过了童年,后到北京读书四年,之后工作并定居在南京,也可称得上是一个“移民后代”。此外,他的祖辈,也就是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去世得都很早,让他对祖辈的生活所知不多。生活的漂泊不定和祖辈的早逝使他没有太过强烈的家族意识。所以,对苏童来说,颓败型家族叙事只是适合表现作家对历史、对人性体悟的独特视角。此外身处女性居多的生活环境之下,也多少影响了苏童的创作,使之对女性描写更加细腻动人。
福克纳生活的美国南方从传统上来说非常重视家庭的地位,可以说“家庭观念在南方比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更突出,家庭的价值在南方比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更得到珍惜”。[5](P102)出生在美国旧南方一个颇有声望的庄园主家庭的福克纳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庄园主后代,作为这个家族的长子长孙,他从小就意识到自己的家庭责任。而且在当地广为流传的关于他曾祖父的传奇故事也让他对自己的祖辈和家族充满自豪。南北战争中南方的失败使南方人痛惜过往美好岁月的一去不回,于是为了替奴隶制和南方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南方人制造了一系列“神话”来美化旧南方。作为南方之子的福克纳自然也不能例外,他也同样深深怀念被他视为美国南方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那部分。不过思想敏锐的福克纳也深刻认识到了美国旧南方土地上的罪恶的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清教传统对人性的腐蚀。这一切使得他在家族叙事小说中对那些庄园主的态度总是在“批判”和“崇拜”“同情”的矛盾中徘徊。
参考文献:
[1]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A].汪政,何平,苏童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张翼.苏童,莫言家族叙事比较论[D].湖南师范大学,2007.
[3]柯泽孔.苏童历史悲剧观评析[A].范今,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C].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4]张静芝.《罂粟之家》:颓败家族的生存世相[J].当代文坛,2011,(3):87-89.
[5]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