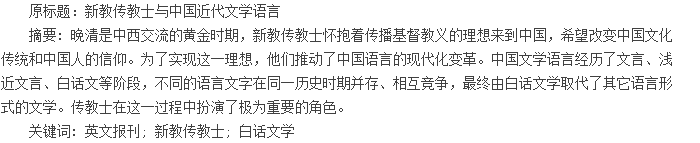
语言的多元共存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在晚清这个充满了革命气息的时代中,传教士、革命者、启蒙者们争先恐后地利用语言来传达各自的知识理念,建立新的文化秩序,中国的官方语言文字也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语言在这个时代中正酝酿着本身秩序的改变。正是在这种跨文化、跨传统、跨阶级的碰撞与竞争之中,汉语逐渐摆脱了文言文的陈腐、罗马字的偏激和方言的局限性,最终由最具现代性的白话文一统天下,结束了众声喧哗的多语时代。汉语与外国语言文化的交汇是出现这种多元语言现象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传教士在这个时代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一
文言与白话的争论由来已久,虽然两者长期并存,但是白话的影响力在晚清以前要远远小于文言。言文难于一致,文言阻碍了白话作品的成长,白话自然要起来反抗。不同语言形态的背后是不同阶层地位的碰撞和斗争。文言和白话的地位也会伴随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变动而发生变化。而近代特殊的时空土壤孕育了语言革命的条件,西方传教士的东来更是激化了这种矛盾。然而传教士对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贡献却长期被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丰功伟绩所掩盖。胡适甚至说:“这个‘白话文学工具’的主张,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论了一年多的新发明,是向来论文学的人不曾自觉的主张的。”然而,中国书面语经历的从文言到白话的现代转变并不是 20 世纪的产物,更不是胡适等几个留学生的新发明。胡适等人和传教士都提倡白话,其共同原因是他们都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中国语言应该照办。早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所编写的天主教中文书籍文献中就大量有意识地使用了白话文。晚清新教的传教士更是重视白话文,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选择白话文作为基督教中文文献的首选语言,积极地通过办报、教育、翻译等手段推广白话文,甚至有意识地创作白话小说,极大地提高了白话文作为书面语的地位。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白话启蒙运动也通过兴办白话报等方式推广白话文,白话文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前,白话文虽然还没有正式取代文言的地位,但它的地位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白话取代文言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过去人们常常把五四白话文运动看作是现代白话文的起点,这妨碍了我们对白话文发展的连续性观察。
传教士偏爱白话,很早就开始了白话的推广活动,这是由各种内外部原因所决定的。首先,明清时期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分离现象已经很严重。传教士们发现,“(中国)书面语采用深文言,而口语则是惨不忍睹的打油诗,很少有人能够说一口好白话。”虽然如此,当时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文人却依然沉浸在文言的精英主义之中,并没有自觉地去改变这一现状。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救亡图存的晚清启蒙运动才大力推广白话文为革命造势。第二,由于文言难学难懂,难以面向大众,因此中国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很少。而近代传教士面对的主要群体就是这些下层百姓,文言给传教士书面传教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第三,文言不适宜翻译外语,然而在近代这样一个极度需要开眼看世界的社会,文言已经成为了阻碍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大障碍。虽然严复、林纾等翻译家用文言翻译了许多西方书籍,然而这样的翻译家毕竟是凤毛麟角,文言翻译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语言是人类传递讯息的主要符号,如果不能完整有效地表达其所指涉的事物,那么它所传达的讯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就有待质疑了。文言的翻译常常令人不知所云,也不适合中下层读者阅读。
传教士们普遍偏爱白话,他们批评晦涩难懂的深文言,肯定有活力的浅文言,不遗余力地推崇白话文。传教士的活动对近现代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95 年,美国长老会牧师薛思培(John Alfred Sils-by,? - 1939) 曾预言:“中国文言文学即将终结,‘传统的’形式将被更为通俗易懂的浅近文言所取代,但是浅近文言也将被更通俗易懂的官话或方言所取代。”言文分离和文言的封闭性给传教带来众多困难,因此传教士表现出统一中国语言的意愿,这种统一主要表现为用白话取代文言。
二
在传统二元对立的观念中,汉语书面语被分为文言文与白话文,然而这种简单的划分忽略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其它层次。文言和白话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语言,而是一种语言的两种形式,因此它们的界限并不清晰。文言常常越界进入白话,使得白话和文言中间出现了一种调和体———浅文言。当我们跳出二元论的窠臼并重新审视中国语言变革的历史进程时,就不宜再用“白话”和“文言”来对其进行简单的划分了。
传教士发现中国语言有很多层次,文言中有特别深奥难懂的文言,有稍微简单一些的文言,还有浅近文言;文言和白话之间有文白夹杂的层次;白话文中有传统的中国白话,也有受到西方语法影响的欧化白话文。他们打破了二元论的思维,使用三分法对汉语进行分层,突出了语言的中间层次。
他们将文言分为深文言和浅文言。深文言主要指文人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浅文言主要是为初识文言的中下层群众准备的。传教士对于深文言的态度是否定多于肯定。
深文言的危害表现在八股文上,传教士对此表示否定和痛恨。梅威良(William Scott Ament,1850 - 1909) 牧师说:“我们都要和八股文作战,它是一条真正的八爪鱼,是几百年来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魔鬼。八股文必死,八股文必须被埋葬。”这代表了大部分传教士对深文言和八股文的态度。无独有偶,新文学家对文言文的批判也是主要集中在其对思想的束缚上。传教士和新文学家在对深文言的态度上呈现出一致性。
如果说深文言是中国文人的内部语言,浅文言就是早期来华新教教堂的内部语言之一。浅文言是介于白话和深文言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在向上层精英读者和下层大众读者之间传教的权宜之计。西班牙传教士瓦罗专门对浅文言进行了论述:“它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这一语体还使用某些优雅的文学词语,而且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对我们来说,在准备布道宣教时,无论面对的是教徒还是异教徒,掌握这种语体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以粗陋鄙俗的语言令他们生厌,他们就能饶有兴致地听讲,从而使得我们传布的教义更容易为他们接受。”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 - 1822)合作翻译《圣经》的时候开始准备使用北京白话,但是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选用了浅文言。因为浅文言一方面具有深文言的严肃和庄重,但避免了深文言的晦涩;一方面比较容易理解,也不会被认为俚俗不雅。因此比起深文言来,使用浅文言的《圣经》更适合晚清的中下层的中国文人,浅文言对于外国人来说也比较容易阅读。
在传教士的种种努力下,文言作为一种独白话语的支配地位开始解体,“高贵”的文言开始被迫与“低贱”的白话等语言进行交流和对话,呈现出转型时期语言所特有的众声喧哗特征。在白话崛起之前,文言从来都没有被赋予过如此重大的意义,它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的书写工具而被文人士大夫世代使用。而当白话被传教士用来作为书写和传播的语言工具时,文人才开始重新建立起对文言的认识。白话也是因为文言的存在而被相对赋予了通俗的内涵。文言文写作的传统文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权力等级。熟练掌握深文言的士大夫能够拥有特权阶层的文化权利,而下层的民众由于缺乏教育机会只能说白话,与代表高贵身份的文言保持距离。如果他们不小心触犯了这一潜规则,则会被人耻笑。同样,如果落魄的士大夫在下层民众间卖弄文言,那么他也同样会得到嘲讽。文言和白话在中国的文化等级中筑起了一堵看不见的厚障壁,成为文化权力的工具。因此,白话文地位的提升必然会遭到许多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反对,在晚清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的文化地位和特权。传教士语言运动所引起的骚动和批评,伴随着文言文作为一种语言霸权的解体。书面语的空间被其它的语言形式所挤占,而文言文的中心地位也在不断被动摇。文言文的神话即将崩溃,文化专制主义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挑战。更有活力的口语语体正在崛起,正在以一种所向披靡的阵势迅猛壮大,它将冲垮一切文言文的堤坝,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即将产生。
三
传教士偏爱白话,这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外部原因在前文已有所论述。如果从内部原因来看,则是因为文言对于外国人来说几乎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除了少数语言天才,大部分传教士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学好文言。马礼逊指出:“东方的语言一般都比较困难,但与中文相比,它们就和我们的母语一样容易,中文与天下任何一种语言几乎没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是著述还是翻译,大多数传教士都需要中国助手为其进行语言的润色。众多的教会档案显示,传教士独立完成的中文文献的语言要比和中国助手合作译著的文献浅白得多。近代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受到清廷的限制,他们所面对的教徒大部分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平民。他们使用最直白的口语,更加增强了传教士学习和推广白话的需要。然而由于中国方言的众多给不同方言区的传教士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他们在针对不同方言区传教的同时,也表现出统一白话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之所以能够在数百年间实现,不仅在于传教士、启蒙者、革命者的奔走呼告,也是近代中国最迫切的需要,因为白话承载了将极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普及到急切期待了解新思想的大众中的重大任务,是救亡图存的希望。
识时务者为俊杰,传教士所做的语言工作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也应该被历史所铭记。
传教士对白话文充满了热情。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就偏好白话,在布道中多使用白话;晚清传教士们也多选择白话进行布道、宣教、演讲,以增强其影响力。
传教士库思非(C. F. Kupfer)更是呼吁道:“每一个基督教工作者的心中都应该有一个燃烧的愿望:为所有长着耳朵的人培养这样一种语言。让所有的教科书、杂志、教会报纸和小册子都用官话来写吧;在所有的教育机构中都设立辩论会;说方言的地方也应该聘用官话老师,那么两代人之间的变化就会很显著了。官话在未来可以广泛地运用于 18个省,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获得成功。”传教士要推广的官话并不是传统的官话,而是带有欧化色彩的官话。他们在翻译基督教经典时将欧化的语法和句法也带进了官话,长句子、新术语层出不穷。虽然传教士在学习官话的时候尽量模仿传统的白话,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欧化。阅读早期传教士所翻译的白话书籍,会感受到其语言文字的拗口,这种拗口就来自于欧化因素。而欧化白话文也是新文学家所提倡的现代白话文,不同于传统白话文。
传教士的种种言论和行动表明,白话文是他们理想的中国语言,他们希望能够大力发展白话文来与文言文抗衡。他们对白话文的提倡言行直接提高了白话文的地位。有人统计,在清末大约刊行了 1500 种白话小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新创作的白话小说;1876 年申报馆出版的《民报》基本上采用白话;从 1895 -1911 年,创刊发行的白话报刊总数为 140 份之多。这些白话报刊中有不少为传教士所办。传教士使口语成为了书面语,大大提高了白话的地位。写比说更具本原性,白话从口头语言变为书面语,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传教士语言运动和晚清启蒙运动在提高白话文的地位、开启民智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五四白话文运动才能在短短几年间产生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影响。
不仅是传教士推广白话,基督教信徒也大都支持并推广白话。洪秀全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创立了拜上帝教,他和他的支持者们竭力反对文言,提倡俗语,创作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诛妖歌》等通俗易懂的白话诗歌。1853 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更是提出了“其语句不加藻饰、只取明白晓畅,以便人人易解”的白话语言主张,大大提高了白话的地位。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开明知识分子也逐渐加入到白话运动中来,两者在这一议题上达成了共识,相互对话、沟通,从而使得汉语白话文获得了完整的主体性。
四
白话文地位的提高对中国传统文人造成了一种威胁。几千年来,由于文人士大夫牢牢把握住知识话语权,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文化霸权传统,成为中国语言的大传统,而白话小传统则一直在“不入流、边缘化”的处境中挣扎。传教士将白话的地位大大提高,白话文学的地位也随之纳入到正统的文化谱系之中了。在社会矛盾冲突激化、文化发生剧烈动荡变迁的晚清中国,白话和文言分别被赋予了主体性,被人为地分割成势不两立的两个极端,两者分别在各自所代表集团的构建下确立起了各自的主体性。文字书写是将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截然分开的表现,中国知识分子写文章是一种精英主义。文言是知识分子的内部语言,而白话则是知识分子的外部语言。要用白话取代文言,就是要突破中国知识分子原有的精英主义,必须在知识分子内部进行一次书面语的革命。在近代中国,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了传教士和中国传统文人的语言矛盾上。虽然在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内部,白话文作为一种书面语已经拥有了很高的地位;而在中国传统文人内部,白话文依然是引车卖浆之流说的下等语言。传教士提高白话文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他们正在积极引领说白话的下层阶级加入文化统治阶层,试图以白话来分化、改造文人阶层的纲领,这严重威胁到了传统文人的政治文化地位。当中国文人集团的文化统治地位和知识道德领导权被动摇时,他们是无法容忍社会上一部分人可以使用未经他们认可的“下流”白话来书写,因为那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权力受到严重挑衅。
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1924 - )致力于研究阶级和语言的关系,他的研究显示,英国社会的低等成员持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与中产阶级精致的语言符码相比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阻碍了他们对社会和经济改善的要求,因为学校(社会流动的主要力量)要求使用精致的符码。以阶级为基础的语言并不是简单的变化,它反映了英国阶级系统中的等级制,其结果是一些语言在社会和文化中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一现象在晚清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文言一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语言,属于优势语言。只有能够熟练运用文言的人们才有可能考取功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要掌握文言,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校教育和苦读,通过逻辑和抽象思维的运作才能达到。白话———这一属于下层阶级的语言过多地受到语境的束缚,白话的使用者不能从传统的教育中受益,也无法进行高层次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因此文言和白话的使用者明显地分属于两个阶级。
因此,对中国传统文人而言,维护文言的纯洁性不仅是维护他们精英地位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民族自尊心和文化传统的需要。中国文人在晚清中国依然是建构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阶层,也是行使国家职能和社会文化霸权的代理人。他们左右着下层市民社会的视听,也引导着中国语言文化的走向。传教士明显地察觉到:中国的文人对民众有决定性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阶层可以与文人的地位相较量。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文人对外国人都抱有敌对态度。
因此传教士往往把中国文人看作敌人。传教士所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阶层与中国传统文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由于各自利益和目的的差异,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抵触和矛盾,文言和白话之争便是其中的一个显著表现。
强调传教士对白话文的影响并不是要否定新文学家在白话文合法身份之获得中的关键作用。传教士代表的毕竟是一种西方文化,中国群众对他们倡导的知识理念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要完成文化传统的革命性转变,还是要依赖于中国有影响力的上层知识分子。白话文是一种新的文化符号,与提倡、阐释它的人的身份与形象息息相关。然而新文学家们所提出的一些白话文观点并不是完全准确,也有许多值得斟酌和推敲之处。传教士所写的白话文,是怎样说便怎样写,反而是中国助手为了文雅起见,将白话修改成文言,传教士常常抱怨助手们深受八股那种艰深文体的毒害而无法用简单明了的中文写作;传教士使用白话也没有“老爷”和“听差”之分,白话和文言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带有贵贱之分的。
传教士的语言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很多方面其实都极为相似:首先,传教士和新文学家都不以精英主义自居,他们提倡白话,并没有将自我和大众分开,这与提倡白话而仍用文言的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启蒙者是不同的。其次,传教士和新文学家都是有意地推广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话怎样说便怎样写。第三,传教士和新文学家都致力于提高白话的地位,将它的对象从下等社会提升到中上等社会。胡适认为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也是全国人都该赏识的好宝贝。传教士在演讲、布道、教学、出版、翻译、创作等过程中始终重视提高白话文的地位,实实在在地将白话从下层推向了上层。
传教士的语言运动冲击了士大夫阶层的语言习惯和思考模式,模糊了阶层的界限,改变了文言文作为书面语的垄断局面,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森严的文化等级制度,为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铺平了道路。传教士的言行撼动了文言的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解放了长期受压制、受歧视的白话,顺应了中国文学言文合一的发展趋势。白话是实现精神文化现代化的语言载体,白话代表了一种文化现代性。白话文学革命可以让人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白话可以说出真的声音,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语言的变革总是会带来文体革新,而文体革新正是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教士而言,语言的变革主要是为了推广基督教文学,以感化更多的中国人。语言的变革有两个层面:文字符号层面和文体层面。当语言的变革尚处于文字符号层面时,对于文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而当语言的变革达到文体层面的高度时,就会对文学变革产生极大的影响。白话文地位的提高带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同时明清白话小说地位的提高又巩固了白话文的地位。由此可见,文化形态的转换与语言的更新紧密相连,语言的革新也意味着一种文学文化形态的转变。新的语言形式带来新的观念思想,白话文的形式带动了新文学的诞生,推动了新内容的呈现。
参考文献:
[1] 胡适. 建设理论集导言[C]/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Our Attitude to the Literature of China[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97,(6).
[3]Silsby,John Alfred. The spread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Missionary Journal. 1895,(11).
[4]Ament,Williams. A Periodical Literature for China[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95,(80).
[5][西班牙]瓦罗. 华语官话语法[M]. 姚小平,马又清,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6][英]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2)[M]. 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8.
[7]Kupfer,C. F. Our Attitude to the Literature of China[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97,(6).
[8] 天情道理书[M]/ /太平天国印书(下).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9] 鲁迅. 无声的中国[M]/ / 鲁迅. 鲁迅全集:第四卷,三闲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