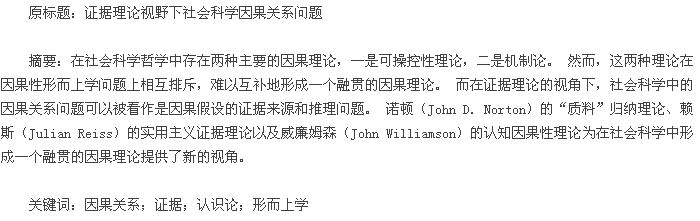
一、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问题的一个特点
休谟在《人性论》中对因果关系的定义是:“它是先行于、接近于另一对象的一个对象,而且在这里凡与前一个对象类似的一切对象都和与后一个对象类似的对象处在类似的先行和接近关系中”〔1〕193(定义 1);“把一个原因下定义为一个先行于、 接近于另一个对象的对象,而且它和另一个对象在想象中密切地结合起来,以致一个对象的观念决定心灵形成另一个对象的观念,而且一个对象的印象也决定心灵形成另一个对象的较为生动的观念”〔1〕193(定义 2)。定义 1 中提出因果关系是如此这般的类似关系和接近关系,是要阐明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不是解证和直观得来的,进而因果关系并没有绝对的形而上学必然性。 定义 2 则从彻底的经验论出发,要求在认识论或心理上定义因果关系,以避免产生绝对必然的形而上学定义。 于是,以此为基础,看待因果性形而上学问题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是彻底否认因果性的存在,罗素早期就是如此认为的:“因果律…是过去时代的遗物,就像君主制一般,它的残存,只是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它是无害的。”〔2〕1其二是从认识论上得到的因果关系特征后,反过来从中形成一个因果性形而上学的规定。 可以说,后一种思路就是从休谟的定义 2 反推定义 1.由于因果关系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上述前一思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罗素后来也放弃了这一思路。 而后一思路在自然科学中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这是由于在自然科学中找到一种认识论特征往往同时揭示了其他认识论特征的合理性,从而完整揭示了因果性。 例如,发现电现象与磁现象之间的反事实依赖关系,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操作使这两种现象相互转换,那么也就同时发现了电磁转换的机制。 但是,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问题的一个特点是复杂性, 例如某段时期内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增发货币与失业率降低这两个事件之间体现为复杂的结合:即使我们认识到了增发货币与失业率降低之间的某种共变“规律”,或者认识到了两者之间的某种触发和反馈的链条,也不能确定是共变“规律”还是触发反馈的链条,或是它们共同揭示了所要探寻的因果性?
这一问题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据问题,也就是将休谟的定义 2 看作是对因果关系的证据推理。 从证据理论的视野来看,社会科学哲学中有两种理论为因果关系提供了相对可靠的证据, 一个是可操控性理论(manipulabilitytheory),另一个是机制论(mechanism theory)。
二、两种证据
可操控性理论的基本理念是原因可以被用来操控结果。 从证据理论的视角来理解,首先,在建构因果贝叶斯网的工作中,佩尔(Pearl)和格里莫尔(Glymour) 等人将数据处理为一系列概率独立性和概率依赖性关系并以其作为相关因果假设的合理证据。 为了使这些计算顺利进行,需要目标系统满足一系列条件和假设〔3〕12-29. 这些条件和假设共同排除了许多虚假的或非因果性的概率相关。 赖斯(Ju-lian Reiss)将这视为一个排除虚假证据而获致真实证据的过程:“命题 e=‘随机变量 X 和 Y 是(样本上或经验上)相关的’是假设 h='X 和 Y 是因果上联系的‘表面证据。 如果所有替代假设 hia(例如,’由于样本误差造成的相关性‘、’由于 X 和 Y 的数据产生过程是非稳定性的‘ 造成的相关性、'X 和 Y 是逻辑上、概念上或数学上相关的’)可以被排除,那么 e就是 h 的真实证据。 ”〔4〕15第二,伍沃德(James Woodward)认为,科学中的因果效应广泛地体现为结果对作为原因的其他变量或要素的反事实依赖,尤其是在社会和行为科学中〔5〕8. 于是他将这种可操控的概率相关视为因果假设的唯一合理证据,并将其定义为“介入下的不变性”, 这就使得对因果关系的一种认识过程被定义为因果性形而上学规定。 当然,为了保证介入下不变性对所探寻因果效应的充分性,伍沃德对“介入”概念做了很多限制。
第三,然而,在社会科学的说明和预测中,还存在其他作为因果假设的证据,如机制结构。 如果将因果关系在形而上学上唯一地规定为可操控的概率相关, 那么机制结构就不能被视作合理的证据,这明显有悖于社会科学的实践。 例如要说明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总是要通过货币政策、市场运行、民众行为等等一些要素之间的机制来进行说明,并且认为这种机制就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潜在因果关系。 对此,伍沃德认为,被视作因果关系的机制实际上是由一系列“介入下不变性”关系组成的,归根结底因果关系仍是一种可操控的变量间相关性,没有可操控性,机制既不会被认识,也不存在。〔6〕44-46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机制性因果关系说明的往往是观察数据,而非实验数据。 就如上述对一次经济危机的说明,对于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一些政策行为和市场现象的数据,回溯过去进行介入而形成反事实依赖关系是不可行的,而且对于整个社会复杂的运行进行介入也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伍沃德将机制结构还原成一系列可操控的变量相关是不可行的。
机制论的因果理论则认为能让我们把握到两个对象之间的结合关系并将其认作是因果关系的是这两个对象之间存在的某种机制。 从证据理论的视角来看,机制论有如下特点:第一,与可操控性理论相同的是,机制论也是从认识论层面将两个对象之间在时空中的结合作为因果关系的证据;不同的是,机制论并不认为这种结合关系表征为反事实的概率依赖关系,而是应表征为产生这种依赖的实质过程或活动。 第二,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社会机制各部分之间的生成过程和相互作用活动的证据组成了因果假设的证据。 赖斯认为,过程或机制的每一部分都是在自身的假设语境中建立起来的,这些假设形成了一个关于过程或机制的复杂假设,这个复杂的机制假设再形成对原初因果假设的支持。〔7〕350
可以说,机制概念的生成性含义〔8〕98-99为社会科学中多样的因果关系形式提供了合理的辩护,这一点克服了可操控性因果理论以反事实概率依赖“过度决定”因果关系而造成的困难。 第三,机制概念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的内涵,这就反过来将因果关系的认识论特征定义成了其形而上学规定。 第四,机制论的困难是,许多生成过程和相互作用活动不能用形式化语言来表达,这使得在机制论因果性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单纯的依赖关系或函数关系就不能被视为因果假设的证据,这有悖于具体的科学实践。
可操控性概率依赖与社会机制作为社会科学中因果假设的两种证据,同样是从认识论上对因果关系的规定,可以说,它们互补地支持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假设。 然而,可操控性理论和机制论各自都将这两种证据视为相互排斥的,这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这两种理论各自试图从两种证据在认识论上乃至方法论上的有效性重新建立唯一的因果性形而上学。
三、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证据
根据休谟彻底的经验论观点,从证据到因果假设的推理不能是演绎推理,只能是归纳推理。 那么一方面,归纳推理得到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性,就这一点而言,可操控性理论对“介入下不变性”关系做出了限制:这种不变性是在一定时空区间内的不变性;机制论则将因果假设看作是由机制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支持的,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相关因果关系的局部有效性。 另一方面,归纳推理框架本身不具有普遍有效性,上述两种因果理论都违背了这一点,它们都将从各自证据到因果假设的推理框架视为一种普遍框架,从而定义各自的一种因果性形而上学。
从科学哲学史上来看,密尔(John Stuart Mill)提出的推理因果关系的五条归纳规则就是试图为因果关系的推理建立一个普遍有效的推理框架。 亨普尔的“律则模型”实际上是诉诸演绎推理的有效框架来解决归纳推理的难题。 而贝叶斯方法则是用概率计算来建立普遍有效的推理框架。 这些寻求普遍有效的推理框架来解决归纳难题的推理理论可以被称为形式归纳理论, 与此相对应, 诺顿(JohnD.Norton) 提出了一种 “质料” 归纳理论 (MaterialTheory of In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