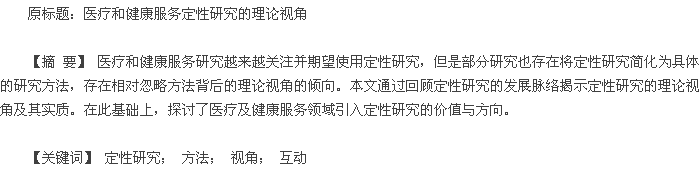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 伴随健康服务研究( health service research) 的兴起,英美医学界逐渐关注源自社会科学 ( 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代表)的定性研究,倡导将定性研究引入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而心理卫生领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英美医学界对定性研究的兴趣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定性研究能够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探讨定量研究不能回答的问题[1]; 其次,定性研究能够桥接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更好地将知识转化为有效的服务[2].在此基础上,英美医学界对定性研究的倡导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 从使用定性研究作为定量研究的补充,整合定量与定性研究,到建立以多学科合作为基础的综合研究体系[3].然而,时至今日,整合定量与定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倡导和探索层面,建立多学科合作的综合研究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当前医疗和健康服务领域中运用定性研究存在的问题
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在引入定性研究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以及整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障碍,在当下医学与社会科学的探索性接触中表现为: 一方面,医学界在引进定性研究的过程中既有对 “异域风情”的热望和期待,也有一种基于丧失自我而产生的忐忑和焦虑,禁不住追问定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界在输出定性研究的过程中既有被认同的自豪与满足,也有一种基于 “嫁女”而产生的疑虑和不安,为定性研究可能在转介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而焦虑。这种相互怀疑和张力构成双方合作的潜在障碍。
出现这种局面,医学和社会科学双方都难辞其咎。一方面,医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将定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视角进行切割,将定性研究简化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技术,并移植到自身领域。这种移植的实质是在维系本学科传统 ( 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合法性基础上的削足适履。其后果是采用定性方法收集资料,却又希冀对定性资料进行定量处理和分析。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界在潜意识里将定性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升到理论层面,淡忘了定性研究本身存在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不仅怀疑其他领域的研究者理解、接受和操作定性研究的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拒绝 “他者”发展定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2 关于定性研究的认识误区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在方法层面 ( 包括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从资料收集的层面来看,定量研究使用统计抽样法则确定研究对象,采用问卷、量表等结构化调查方法收集数据资料; 定性研究则采用理论抽样规则确定研究对象,采取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档案等半结构或开放式方法收集文本类资料。从资料分析的层面来看,定量研究基于数理统计使用推论的方式对研究问题及假设进行检验; 而定性研究则基于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 ( 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等) 使用归纳的方式得出结论。
深入考察,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绝不仅仅存在于方法层面。换句话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张力虽然更多表现为方法上的大相径庭,但双方基于不同知识传统建构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对立才是形成这种张力的根源。借用人类学的视角,这种对立构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为 “他者”的局面,也是阻碍双方相互理解、认同和接纳的根本原因。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部分医疗及健康服务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在方法差异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区别[1].在他们看来,这种深层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问题、研究目标以及秉持的社会理论这三个方面。在研究问题方面,定量研究回答的是数量的问题 ( 例如某种现象出现的频次和频率) ,定性研究回答的是定性的问题 ( 例如某种现象的性质和实质,发生的原因和机制) ; 在研究目标方面,定量研究侧重可靠性,定性研究侧重有效性; 在社会理论方面,定量研究的出发点是结构理论,定性研究的基础是行动理论。这一比较分析不能说完全精准,但不乏洞见,已经触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自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研究问题关涉的是问题的类型和意义: 什么样的研究问题是有意义的? 研究目标是关于知识生产和评价的标准: 什么样的回答是有价值的? 社会理论则指出了研究者的世界观对研究本身必然产生的影响: 研究问题和方法背后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这一洞见揭示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分属两个不同的知识传统,各自有着自己生产问题、知识的路径以及评价标准,同时暗示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普遍的衡量和评价标准。
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领域对定性研究的重新认知意味着崇尚科学主义的自然科学霸权的一种内省,这为开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平等对话提供了可能。这种平等对话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基础之上: 定性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研究方法,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指引和设计具体研究方法的理论视角。因此,如果医学研究者希望引入定性研究,那么他们不仅需要了解和掌握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定性研究,更需要理解、认同和采纳定性研究背后的理论视角。
3 定性研究的理论视角
从历史起源来看,定性研究源自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接触和碰撞,具体表现为西方文明在认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试图理解非西方文明的努力。19 世纪末,伴随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的确立,定性研究也被确认为必要且合法的研究方法。相对于西方文明来说,非西方文明是作为一个异文化的“他者”而存在的。人类学强调以 “他者”的视角来理解 “他者”,而西方文明在理解异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习得并借助 “他者”的视角来反观己身,实现对本文化的理解。20 世纪 20 年代,经由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努力,定性研究被引入社会学作为研究西方社会、城市文明的一种必要研究方法; 60年代之后,定性研究逐渐扩展到经济学、文化研究、心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领域。
梳理作为人类学分支之一的医学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透视定性研究的理论视角。早期的医学人类学致力于描述和理解异文化 ( 包括现存的原始部落、非西方文明传统) 的医学知识体系,比如疾病名称、分类、病理解说和治疗手段。在与西方的生物医学比较之下,这些非西方社会的疾病知识往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迷信,而相应的治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毫无科学依据的巫术。文化相对论的出现使得西方文明能够将非西方文明置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重新考察,从 “他者”的视角,而不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想当然地以简单 - 复杂、落后 - 进步、原始 - 文明的框架来解释非西方与西方的差异。当然这一过程对于西方文明来说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经历过两次大战的冲击,西方文明内部的问题逐渐凸显,在扩张和殖民过程中得到强化的文明自信受到挑战,西方社会秉持的信仰、价值甚至科学体系越来越受到来自内部的质疑和批判。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兴起则进一步促进了针对西方文明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的真实、客观与科学的反省和解构。
医学人类学通过跨文化研究,将西方的生物医学体系与非西方文明传统 ( 比如中国、日本、印度和伊斯兰) 中的医疗体系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 医学知识和实践是一个社会 - 文化系统,是特定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产物。在此基础上,医学人类学通过反思、批判西方生物医学体系( 包括教育、临床、科研、技术和卫生政策诸方面) ,揭示了生物医学体系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暗示了生物医学体系的相对性。简单地说,从医学人类学看来,生物医学只是西方文明在工业化基础上建立的一套关于健康、疾病的解释和应对方法,并不具有所谓的普遍真理性。
医学人类学认为,以工业化逻辑为基础,生物医学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将人看做一部机器,疾病则是导致人这部机器抛锚的问题,其结果是将 “病人”与 “正常人”区分开,将 “病”与 “人”分离开来,将生物医学的疾病知识与患者的疾病体验切割开来,使用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范畴替代患者的疾病体验,并且赋予生物医学定义、解释和应对疾病的霸权,相对剥夺患者感知、叙述、解释和应对自身疾病的合理性。最终将 “治病”和 “救人”切割开来,或者将医疗的终极目标从 “救人”转化为单纯的 “治病”.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指出病 ( disease) 与疾 ( illness) 分别是医生和患者对于同一现象 ( 疾病) 的两种解释模式: 前者是基于生物医学的概念和理论的解释模型,后者则来自患者基于疾病体验 ( 具有社会及文化内涵) 的解释模型。不同之处在于,科学主义赋予前者以描述、定义、解释和应对疾病的唯一合法性。病与疾的分离以及对后者的忽略甚至否认是生物医学面临的核心问题。要纠正这一问题,凯博文认为,必须在承认生物医学建构疾病体验的相对性的基础上,关注患者关于疾病的叙述和体验,即从患者的视角出发,通过患者关于自身疾病的解释模型来理解患者的疾病知识与体验[4].这一理念显然是以人类学的基本理论视角 ( 从 “他者”的视角出发来理解 “他者”的生活世界) 反映在医疗及健康领域中运用的产物。其实质是承认和恢复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近年来,生物医学包括精神医学愈来愈强调患者参与医疗的过程,强调从“治疗”到 “康复”的理念转换,包括提倡社区康复及同伴教育,不能不说是西方社会沿着这一脉络反思整个生物医学体系的产物。
4 定性研究的实质
当下,经由多种学科 ( 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 的参与和发展,定性研究的运用领域大大扩展,具体方法也不一而足,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文献法、话语分析等等在内的研究方法都被贴上了定性研究的标签。不论这些方法的形式如何变化,定性研究的实质在于如何通过研究对象的视角来理解研究对象。
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根据自身在异文化地区的研究经历提供了如下方案: 学习当地人的语言,长时间 ( 至少一年) 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并掌握当地人的风俗和习惯,才能学会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他们的生活。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实地工作( fieldwork,人类学领域常见的另一个译法是 “田野工作”) ,其核心是参与观察。简言之,参与观察的实质是把研究者当做研究工具投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以参与的方式进行观察,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互动,经由研究者的亲身体验来收集研究资料,最终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人类学认为,只有通过研究双方的高强度互动,才能帮助研究者摆脱基于自身文化价值观念的先入之见,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真正理解,而不是从研究者的视角出发,使用研究者既定或预设的概念框架去剪切、翻译研究资料。
不难看出,人类学实地工作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存在重大不同。在自然科学中,研究工具是可校准的、外在于研究者的; 而在实地工作中,主要的研究工具就是研究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必须避免的,以期获得客观的资料; 而在实地工作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互动被视为获取有效资料的唯一途径。在自然科学中,研究场景是受到研究者高度控制的 ( 比如实验室,或者通过结构化问卷的方式进行控制) ; 而在实地工作中,研究者应该尽量避免施加控制,使研究在接近自然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进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研究者得以聆听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叙述,观察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行为,了解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状态下的思维模式,而不是通过结构化的问卷获得研究对象在特定时点和场景下对自身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的公开表达 ( public statement) .在人类学看来,日常生活是复杂的,作为行动者的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的语言、行为和思维既受到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的形塑,同时也必然操弄、改变和塑造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研究对象在特定情境下的公开表达往往并不反映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和思维,很多时候只不过反映了他对社会规范的认知,或者对研究者需求的感知。因此,人的语言、行为和思维之间既不具有一致性,也不具有可替代性。参与观察强调通过研究双方的深度互动来收集资料就是希望在最贴近日常生活的状态下,综合比照考察研究对象的叙述、行为和思维,以期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这一点对于医疗和健康服务研究来说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治疗依从性的问题为例,在人类学看来,人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并不具有同步性。掌握正确的知识不一定带来态度的改变,而态度的改变也不一定就会表现为事实上的行动。因此,患者治疗依从性的状况既不完全取决于患者对疾病、药物知识的掌握和对服药重要性的认知,也不完全取决于对治疗效果的感受,而是很可能受制于其他诸多因素,比如医患沟通、患者的工作性质、生活模式、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等等。相应的,如果要改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单纯强调疾病和药物知识教育的干预模式显然是不够的。
当然,定性研究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实地工作,并且由于学科制度和规范的原因,在医学及健康服务研究中引入原汁原味的民族志 ( ethnography)研究方法必然存在诸多客观限制。比如人类学要求的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在特定的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中可能就不具有可操作性。事实上,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经历了发展和变迁,被引入到不同研究领域 ( 包括健康服务) 中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研究方法[5].重要的是,在具体方法差异和变迁的背后,定性研究的内涵和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仅不回避研究双方的互动,相反就是借助这种互动,通过研究者的亲身经历来收集研究资料。比如在深度访谈中,定性研究强调访谈双方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对话者,访谈是对话性质的双向交流,而不是由研究者按照预先拟定的问题向研究对象收集自认为需要的信息的单向调查过程 ( 即研究者主动提问,研究对象被动回答) .同时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收集的也不仅仅是访谈对象讲述的口述信息,还应该结合观察的方式,通过观察访谈对象的表述方式、表情和肢体语言来实现对叙述的综合理解。
5 医疗和健康服务领域运用定性研究的价值和方向
回顾历史,医学与定性研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并不是由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健康服务研究催生。公共卫生与社会医学理念的诞生早就将医学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甚至世界体系中进行考量,健康、疾病和医疗等概念也早已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范畴中得以重新定义。医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 20 世纪中叶的国际公共卫生项目不无关系[6],50 至 60 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及贫困地区推介先进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以期改变这些地区糟糕的健康和医疗状况。在此过程中,具备生物医学、公共卫生专业训练的西方医疗专家遭遇了意料外的困难: 这些 “落后”地区不是欢迎、接纳先进的医学知识、技术和设备,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拒绝和抵制行为[7].在西方专家看来,这是荒谬和不可理喻的:难道这些人不想改善自身糟糕的健康和医疗状况吗? 他们认为,这些落后地区的人们由于无知和迷信表现出拒绝和抵制的不理性行为。如何改变这一状况? 既然人类学是研究 “落后”的 “异文化”的专业领域,那么让人类学家参与到这些项目中来就顺理成章了。人类学家认为,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项目的目的,其次需要理解的是当地人的需求。在人类学家看来,国际公共卫生项目的理念实质上是西方文明秉持的技术至上的意识形态: 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8],而当地人未必认同这一理念。因而,国际公共卫生项目失败的根源是文化冲突,具体表现为地方医疗文化与西方生物医学文化之间的冲突。因而,在传递和接纳生物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这一文化互动中存在着一种文化障碍 ( cul-ture barrier) ,解决的办法则需要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理解当地人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发展具有文化适应性 ( cultural adaptability) ,具备文化能力( cultural competence) 的国际公共卫生项目。人类学介入国际公共卫生运动的这段历史对医疗领域运用定性研究具有相当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今天看来,如果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国际背景置换为一个特定国家甚至地区,并且承认不同人群( 比如以性别、年龄、民族、社会阶层和生活地区等特征进行划分) 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化差异,不难发现各种疾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健康意识和服务模式的推广项目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当年国际公共卫生项目的遭遇是如此的相似。医学、公共卫生与社会科学在历史上的交汇不仅证明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合作的可能性基础,而且展示了定性研究的引入带来的实质性变化是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的扩展,让研究者可以看到原有的视角和框架忽视甚至否认的那些因素和变量实际上与研究主题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
在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中引入定性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孰优孰劣的问题。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着各自擅长回答的问题。定性研究的特长在于通过类似解剖麻雀的个案方法来回答 “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一类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或者适合采用定性研究。是否采用定性研究取决于研究问题的性质。对于特定的研究问题来说,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最适合回答该问题的方法[9].
那么,一个更具操作意义的问题是,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中的哪些环节适合引入定性研究? 简要梳理英美医疗及健康服务领域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的明确使用定性研究的相关研究文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
第一,定性研究可以帮助定量研究提炼并优化研究问题与假设。定量研究往往过于专注方法本身,具体表现为日益强调发展完善、精细的数理分析模型,相对忽略研究问题和假设的生产过程。事实上,定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问题和假设的意义和价值。定性研究的特长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在定量研究之前,如果以定性研究为先导,提炼出研究问题和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定量研究方案,不仅可以避免研究者的先入之见,打破从主观假设出发收集资料验证假设的循环论证,而且可以提升定量研究问题的意义和价值。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主题: 患者关于特定疾病 的 叙 述、态 度[11]、体 验[12]和 应 对 方式[13-14],从患者的视角重新理解作为致病原因的某些日常行为和生活习惯[15],患者就医选择[16],参与治疗的体验[17],特定疾病的社会和文化内涵[18-19],健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第二,定性研究可以帮助桥接定量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从研究到实践的环节。健康服务研究的焦点在于设计健康服务的体系和模式,而设计出来的体系和模式最终是否能转化为有效的实践,则有赖于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的互动。这一环节也是定性研究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定性研究不仅可以参与到服务体系和模式的设计过程中,而且可以参与对服务实践效果的评估,进一步帮助健康服务专家修正和完善相关体系和模式。相关研究侧重关注消费者需求[21],服务资源[22],服务体系和模式[23],医患互动[24].
第三,部分研究既追求对特定现象的量化描述、分析,同时也希望解释现象的性质、原因和机制,也可以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研究主题包括特定患者人群的生活状态[25],健康与社会因素的关联[26],一般人群关于特定疾病防治措施的认知与接受状况[27],特定人群的健康观念和态度[28].
参考文献
[ 1] Pope C,Mays N. Reaching The parts other methods cannot reac-h: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methods in health and health serv-ices [J] . BMJ,1995,311( 6996) : 42 - 45.
[ 2] Jones R. Why do qualitative research? It should begin to close thegap betw een the sciences of discovery and implementation [J] .BMJ,1995,311( 6996) : 2.
[ 3] Lambert H, McKevitt C. Anthropology in health research: fromqualitative methods to multidisciplinarity [J] . BMJ, 2002, 325( 7357) : 210 - 213.
[ 4] Kleinman A.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M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 5] Savage J. Ethnography and health care [J] . BMJ,2000,321( 7273) :1400 - 1402.
[ 6] Polgar S. Health and human behavior: areas of interest common tothe social and medical sciences [J] . Curr Anthropol,1962,3 ( 2 ) :159 - 205.
[ 7] Scotch NA. Medical anthropology [J] . Bienni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63,3: 30 -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