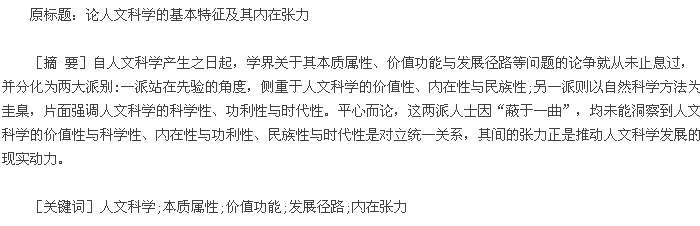
“人文科学”一词,是 20 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舶来品。但在西方,“人文科学”却产生甚早,可以追溯到 17 -18 世纪之交堪称近现代“人文科学之父”的维科。嗣后,经过狄尔泰、李凯尔特、卡西尔、韦伯、胡塞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努力研究,西方的人文科学观渐趋成熟、完备,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纵观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以维科、狄尔泰、李凯尔特、卡西尔、韦伯等人为代表,主要是基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界定人文科学,比如韦伯说道:“我们已经把力求根据其文化意义认识生活现象的学科当做文化科学'(指人文科学———引者注)。”
第二个阶段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他们突破了第一阶段的现代认识论藩篱,转向生存论角度来为人文科学奠基,比如伽达默尔曾言:“我们的整个研究表明,由运用科学方法所提供的确实性并不足以保证真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精神科学(指人文科学———引者注),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科学的科学性的降低,而是相反地证明了对特定的人类意义之要求的合法性,这种要求正是精神科学自古以来就提出的。”
由上观之,尽管人文科学的合法性基础从认识论过渡到了生存论,但伽达默尔仍与韦伯一样,主张人文科学以“特定的人类意义”或者说“文化价值”为主题,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底蕴。
在人文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中,科学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分别构成了对人文科学发展的重大挑战。在科学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是科学知识的标准模式,故人文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必须做自然科学式的探讨与研究,并以自然科学的知识形式来规范人文科学的问题。较之科学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从特殊的人文主义精神出发,不仅批判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性,而且“否认各种形式的哲学世界观与价值体系”,“否认科学观、真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根本上挑战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人文科学而言,科学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是一种内部挑战,而非外部挑战。亦即是说,关于人文科学的本质属性、价值功能及其实现途径等问题,学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莫衷一是。
一、人文科学的本质属性:价值性与科学性的张力
虽然人文科学是以文化价值或者说人类精神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自然科学则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但由于人文科学是产生于自然科学兴盛之日,自然科学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在斯时的文化世界中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欲要证明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亦即建构人文科学的合法性基础,就必须接受自然科学的话语系统。
就人文科学接受自然科学的话语系统而言,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种显性层次,指人文科学应像自然科学一样,以经验事实与逻辑方法为基础,如韦伯在确立人文科学的合法性时,主要诉诸“科学有效性”和“科学结论有效性”两个方面。所谓“科学有效性”,是指将人文科学限定在事实判断之中与价值判断之外;所谓“科学结论有效性”,是指以“逻辑的和实践的方法”所推导出来的“经验真理的有效性”。第二个层次是一种隐性层次,狄尔泰、李凯尔特、卡西尔等人虽然力主人文科学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即以价值而非事实为对象、以理解而非逻辑为方法,一如李凯尔特所言,“通过与价值的这种联系(这种联系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把两类对象区别开,而且我们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作到这一点,因为撇开文化现象所固有的价值,每个文化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与自然有联系,而且甚至必然被看作是自然”,但毋庸讳言的是,狄尔泰、李凯尔特、卡西尔等人仍然是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出发,秉持主客二分,是故,他们在潜意识中并未摆脱用科学主义的眼光去看问题。
要之,当代学人普遍认为,上述两种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的思路,均无法把握人文科学意义的真谛。
那么,能否通过社会科学来证成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呢?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具有可行性,因为:一方面,相较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在价值性方面与人文科学具有更强的亲缘性;另一方面,自 18 世纪始,诸种社会科学通过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开始确立起来,并且赢得了毫无争议的科学地位,如亚当·斯密运用经验观察与逻辑推理方法创立现代经济学,摩尔根运用实地考察方法建立现代人类学等。从事实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真正地确立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正是由于把人文科学植根于社会科学之中。实质上,人文科学所要研究的“文化价值”或“人类精神”,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最终为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犹之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所以,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尽管要充分考虑到个人的体悟、内省、直觉、想象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
历史虽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在人文科学传入中国之初,亦出现了关于人文科学合法性基础的论争,这集中地反映在 1923 -1924 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一)胡适、丁文江等人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主张人文学科科学化与自然科学方法化,如是,他们在运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等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哲学、史学、文学等研究,进而取得诸多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无疑地损毁了人文科学的价值根基。(二)张君劢、林宰平等人站在西方的生命哲学立场,高扬人文科学的独特性,主张“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此处的“科学”意指自然科学,“人生观”实指哲学或人文科学。
(三)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唯物史观既是社会科学,因为它揭示了贯穿一切历史阶段和一切社会生活方面的根本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是人文科学,因为它提出了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体,自然史、社会史归根到底都是人的活动史,并且是人不断地实现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历史,尤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近些年来,随着启蒙理性反思与现代性批判的深入广泛开展,当代学人都已然放弃了胡适、丁文江等人的人文科学观。他们或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立场,像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那样把人文科学深植于社会科学之中,实现人文科学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或者站在先验的、抽象的人文主义立场,像张君劢、林宰平等人那样宣扬和鼓吹人文科学的“价值性”。后者比如,毛丹在论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价值立场的分歧时说道:“在学科气质上,人文学科直到今天,一样可以认同乃至于提倡不屈从非正义现象———事实的批判精神,可以直接表达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虽然不见得所有人文学者都能做到)。”
再如,王忠武认为:“人文科学是对现实的某种批判、拓展和超越,它同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文明程度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诚然,从毛丹、王忠武等人的旨趣或出发点来看,他们力反人文科学沦为社会现实的附庸,犹之西方中世纪时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主张人文科学应具有独立性、批判性与前瞻性,借用中国古代哲学名词来说,就是人文科学要有“道尊于势”的高贵品格。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结果无疑会重蹈颜习斋所批判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之覆辙。
二、人文科学的价值功能:内在性与功利性的张力
所谓人文科学的内在价值,是指人文科学对于人(主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价值。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是建立在“人是什么”这一命题的基础之上,惟有符合人的本质的发展,方可谓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因此故,西方自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基督教的“原罪说”,再至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从未停止过对人的本质的追问与反思。中国亦是如此,从孟子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1史。要之,无论是古代西方还是古代中国,关于人的本质或者说人生的价值几乎都是从道德价值的角度立论的。
虽然内心的修养和精神的提撕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以及克服诸种“异化”的解毒剂,但可惜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对其置若罔闻、熟视无睹,以致在大学的人文科学教学中,学生时常会提出“哲学有什么用”“学历史能干什么”等疑问。对于学生的这类疑问,老师或以“哲学乃无用之大用”与“读史可以明智”晓之以理,或以泰勒斯利用哲学知识投机橄榄油生意发财致富、王阳明与曾国藩等人凭借心性之学建立丰功伟绩等事例动之以情,此外别无他途。由是观之,在竞争日益激烈、生活压力渐趋沉重的现代社会,人文专业和人文学科的生存处境是多么尴尬,青年学子对于实用价值和功利价值是多么渴望。有鉴于此,党和政府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施素质教育工程,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学内容与方式,改革考试招生制度等;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所有这些方针与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还原教育乃“人”的教育之本真,而这里所谓的“人”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人文科学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离开历史的实际、历史的变迁、历史的环境,抽象地讲人文科学的价值,是不能真正说明人文科学的价值的”。纵观人类思想文化史,尽管对“人是什么”的理解言人人殊,但以人文科学来提高人生修养和丰富完善精神生活的核心诉求却是一贯的、稳定的。反之,人文科学的外在功利价值则会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的变化,而表现出较大的变动性和多样性。如是,在人文科学的发展中,一些原有的外在价值会在发展中消失,而另一些新的外在价值又会在发展中产生出来。在当今社会,人文科学的外在价值,主要是指人文科学对于外部的物质和社会生活的间接性的作用,比如经济发展、政治生活以及环境保护等。
在人文科学的外在价值中,政治价值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最长,并且也最为引人注目。无论是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言人利用人文科学为政治服务,还是被统治阶级以人文科学为“批判的武器”,一定程度上都会导致人文科学的政治化倾向。因此,对于人文科学的政治化倾向,既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深入分析其出现的社会政治背景,又要有正确的阶级立场,审慎辨别思想本身的是非曲直。历史表明,在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或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人文科学的政治化倾向尤其强烈,社会思潮的分化与交锋尤其显着,因为此时政治生活正直接而有力地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和关注的焦点。比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有鲜明的政治化倾向,非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学说、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理论、韩非子的“世异则事异”历史观等彰明较着,即便是貌似远离政治喧嚣的道家哲学、名家哲学等,亦不外“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与政治价值不同,人们关注和研究人文科学的经济发展价值,是肇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彼时,诗歌、艺术和哲学等通过认肯和高扬人的俗世生活,进而批驳“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的神本主义意识形态,为商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更有甚者,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指出,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使得市民把精于职业和精于赚钱视为“天职”,并且合理科学地计算收支和安排生产,无疑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当历史进至 19 -20 世纪之交时,资本主义由于过度地崇尚科学主义和物质文明,不仅导致了惨绝人寰的“一战”,而且直接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在这种情势下,柏格森、奥伊肯等哲学家高举“生命哲学”“精神生活哲学”等,力图以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为西方的现代化重新贞定方向。要之,人文科学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既能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和价值观念,又能针砭和匡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弊病。
应该说,人文科学的外在价值是由其内在价值派生出来的,内在价值是第一位的,外在价值是第二位的。因之,人文科学首先追求的应是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生的修养,然后再考虑转化为外在的功利价值,明乎此,方可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如若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生的修养作为手段,而视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斗争为目的,只会致使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走入歧途,变成一个吞噬一切文明的漩涡,人格、尊严与价值将统统化为乌有。例如,中国时下流行的地方经济发展口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非但不是在拯救和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反而是用“GDP 至上”观念绑架和作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至于近些年不断传出关于炎帝、舜帝、诸葛亮、曹雪芹等名人故乡之争的闹剧。
三、人文科学的发展径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张力
人文科学的民族性,意指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要基于本民族的现实国情和对传统人文资源的批判继承。人文科学的时代性,则意指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二者既相互差异、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因此,我们在发展人文科学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
关于人文科学的民族性,往往存在着一种误解,以为其仅仅是对民族根性和精神内核的继承,而忽视现实的国情和民情亦是一种民族性。如其然也,不仅会致使借鉴和吸收先进的时代文化变得犹如沙中建塔、水中望月,更有甚者,文化的民族性会沦为政治保守派阻碍社会变革的口实。比如,在 19 -20世纪之交的社会大变革中,“国体由君主而民主矣,近年小家族之制益推广,祭祀之诚敬远不如二十年前,今女子有财产继承权,且常提出离婚诉讼”,而张之洞等人仍坚守“三纲五常”之说,提倡所谓的“中学为本,西学为辅”,岂不是借文化“民族性”之名而行阻挡中国历史前进之实? 与之相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时,不仅遵循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在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之基础上,正如艾思奇所言:“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见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
从逻辑角度看,人文科学的时代性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一是指低级社会形态与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人文科学所形成的时代性差异,如资本主义人文科学与封建社会人文科学、社会主义人文科学与资本主义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异;二是指同一种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文科学所形成的时代性差异,如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两种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异。
相较而言,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人文科学差异,不仅相去悬殊,给人一种震撼之感;而且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其兴衰存亡即取决于此时的文化选择。纵然,在社会形态的转型时期,人文科学的时代性(即先进文化观念)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但也不能将传统的人文科学弃如敝屣。实际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成为接引新文化的桥梁和中介,成为培育新文化的土壤,关键在于后人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做出了表率。诚如李维武所指出,李大钊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他自身的思想因素上看,在于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经通过吸取儒家民本思想资源,如《诗经》所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尚书》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形成了重视人民大众在历史中作用的民彝史观”。
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下,人文科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斗争与转化,虽说会表现得相对平缓一些,相对圆融一些,但也是无止无休的。平心而论,民族文化发展的活力,就在于它能够将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人文科学不断地转化为本民族自身的人文资源,从而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文化转化的能力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因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
当然,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走出去”的过程,亦即是一个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转化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时代性之过程,以及不断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之过程。
四、结语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了人文科学的价值性与科学性、内在性与功利性、民族性与时代性之统一;但恩格斯本人亦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唯其然也,我们可以断言:不仅在一切私有制社会,人文科学的价值性与科学性、内在性与功利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因为缺乏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基础,而长期处于分裂和错位状态;即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因发展阶段或生活领域的不同,而导致对于人文科学的价值性与科学性、内在性与功利性、民族性与时代性之侧重点各异。比如,在 20 世纪初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坚定地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一种“古今之别”(指时代性差异),而与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持守的“中外之别”(指民族性差异)针锋相对;但时至今日,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却主张“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其缘由何在呢? 究其实质,主要在于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 20 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断形成和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恢复了久违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6.
[2]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626.
[3] 欧阳康.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J]. 江汉论坛,2001,(11):30.
[4] 李凯尔特.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1.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