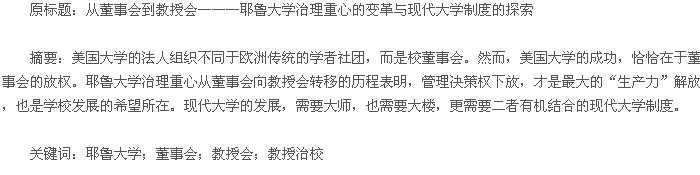
美国教授虽为大学所招聘,却并不认可自己的“雇员”身份,其中的根源就在于,教授治校观念为许多大学的立校之本。尽管美国大学已不再是欧洲原生态大学的学者社团,但大学创立者并没有因此而唯我独尊,教授治校的精神依然得到尊重。那么,美国大学权力是如何从创办人董事会过渡到教授会手中的呢?这对于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意义何在呢?
当今中国许多大学不惜重金延聘名师,然而,大学建设毕竟不是布置风景,如果不能建立一种内生性活力机制,其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耶鲁大学治理结构的历史变革,应该说非常富有启发,这也正如美国着名的高等教育专家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赞赏,“在 美 国,是 耶 鲁 率 先 将 大 学 的 权 力 赋 予 教师”。
一、创办人耶鲁董事会
作为教育机构的耶鲁,其成立之初更属于一场宗教事件。公理会1636年创办的哈佛学院,本意就是要实现清教徒政教合一的“天国”理想。不料哈佛的发展却是越来越走向宽容,一神论盛行,自由主义之风蔓延。在公理会看来,哈佛宗教思想失控的原因就在于世俗政府掌握了管理大权。这是因为,哈佛的最高管理机关校监委员会(Board of Overse-ers)成立之初就是由6位地方官员和6位公理会牧师联合组织,更是鉴于学校财务的依赖,能够主导哈佛命运的显然属于地方政府。
1701年9月,担任哈佛第六任校长的公理会牧师英克里斯·马修(Increase Mather)最终被辞退。以此为契机,并从哈佛走出的几位牧师为主,共有十位公理会牧师决定另起炉灶再创新校。这一思路得到马塞诸萨近邻的康涅狄格殖民地政府支持,以使当地年轻人“可以学习文学和科学,为教会和国家服务”。为了实现宗教的纯洁,同时也表明与哈佛的不同,学院创建者坚持自己的独立领导,十位建校发起人自成董事会,成立所谓的“单院制”管理模式,区别于哈佛的“双院制”管理。耶鲁创办之初既非大学,也 非 学 院,仅 仅 名 为 “高 等 学 校 ”(CollegiateSchool)。如此低调的名称,一方面意味着当地殖民地是否有权批准成立学院法人的权力模糊,另一方面也表明,学校目的就是为了纯正的宗教教育,无意过于张扬。盾牌形式的耶鲁校徽,在书本和缎带图案上分别写希伯来文和拉丁文校训———“光明与真理”,以示他们尊重古典的正统的基督教立场。
学校特许状规定:学校托管人拥有学院所有权,并负责管理学院事务、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来做出各种规定。因此,尽管董事会推举了亚伯拉罕 · 皮尔森(Abraham Pierson,1701-1707年任职)牧师作为校长(Recter),但实际的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十人的董事会之中。诸如学校在聘任教师、遴选校长以及定制教学内容方面,显然都是董事会最终拍板决定。
随着教派多元化以及宗教宽容思想的发展,各学院也是为了争夺生源与社会资助等现实需要,逐渐放松了对宗教的要求。其重要的表现就是教会对学院控制的松动,这也表明多由牧师组成的董事会权力开始松动。特别是随着宗教斗争的加剧,董事会无暇顾及学校的事,校长就自然填补了这一权力地带。此外,董事会领导通常实行多数表决制度,如果赞同与反对票数相同的情况下,校长则拥有最决定性的权力。
二、校长的权力转换
第五任校长托马斯 · 克莱普(Thomas Crap,1740—1766年任职)牧师执掌耶鲁期间,是耶鲁历史上少有的校长执政时代,这也是董事会权力向校长过渡的时代。他对耶鲁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标志就是修改了耶鲁章程。新章程不仅再次明确了学校的法人地位,而且明确将校长纳入到了董事会。校长的称呼也从过去的“Recter”改为 “President”,以示权力的增强。实际上,“Recter”为欧洲大学校长的通常称呼,不过,欧洲大学的传统是教授治校,校长权力并不突出,重大事务都是教授会来决定。哈佛校长亨利·邓斯特(Henry Dunster)最先采用了“President”称谓,个人也从幕后走向了前台,权力大振。克莱普再次以“President”来称谓自己的工作,有哈佛立此存照,一切不言而喻。
托马斯·克莱普在耶鲁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位“有影响和无所畏惧的人物”。他执意扩大校长权力,应该说是当时的形势所迫。克莱普上任之际,正是殖民地“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的高涨时刻。这是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其源于殖民地世俗化发展所带来的宗教淡化以及相应的道德虚无。克莱普校长最初同样是热切地期盼这场运动能够带来民众的宗教复兴。然而,这场宗教复兴并没有沿着他所设想的方向复兴,而是进一步导致了宗教的多元化,引发了公理会以及长老会新旧派别的分裂与冲突。新的宗教混乱局面,也令殖民地政府大为不安。因此,与殖民地政府的立场一样,克莱普坚决抵制“大觉醒运动”。他重新将耶鲁学院定义为宗教社会,认为学院“比其他任何宗教社会优越,鉴于教区是培养普通人的社会,学院就是神职人员的社会,培养担任神职工作的人”。托马斯·克莱普为了进一步推进耶鲁的正统宗教传统,1753年他又要求所有的教职员工遵守更严格的信仰声明要求,而且还保留有可以询问、评估和解雇任何宗教信仰值得怀疑教员的权力。对于学生,他更是严加管理,要求学生只能在校内参加他所主持的礼拜活动,禁止学生到校外教堂。的确,克莱普校长执行的是一种严格的宗派主义,他执掌耶鲁的27年也一直以思想保守而着称。
然而,校长一权独大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不良后果的出现。例如,1741年耶鲁的一位学生因宣传“大觉醒运动”并指责导师而被克莱普校长开除,两位教师为其求情却依然于事无补。正是这两位教师,一气之下另外创办了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前身),所谓“如果没有这一件事,新泽西学院根本不可能成立”。此外,由于克莱普校长坚持正统的宗教检验,并为此解雇了一些有异端嫌疑的教师,疏远了很多的朋友。甚至有批捐赠的图书,也因为有异端的嫌疑而被其拒绝。这时,殖民地立法机关发出了切断资金来源的威胁,学生开始出现了流失。
一些人要求殖民地政府出面干预校长的专断行为,发挥政府的“视导人”(Vistors)权力,并由此引发了耶鲁历史上着名的“公堂大战”。殖民地政府试图干预耶鲁的行为,引起了克莱普校长的强烈回应,他将问题提交到了法院裁判。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有权进行这种干预行为。克莱普校长坚称,殖民地政府虽然对学院有投资,但这种投资并非意味着合伙人。耶鲁法人成立在先,政府投资属于一种资助行为,是一种值得感谢的赞助。法庭上他振振有词,载誉而归。然而,他毕竟积怨过久,树敌太多。到了1766年,克莱普校长在一片反对声中宣布辞职,耶鲁随之结束了历史上少有的校长个人时代,其本人也在几个月之后离开人世。
此后的校长,大概是吸取了克莱普校长的教训,注重个人威信的树立和师生和谐的营造,少有锋芒毕露。特别是美国独立后,注重与地方政府的和睦相处,追求更多的资金援助,成为了学院发展的基本策略。
1817年 耶鲁迎来了其第九任校长杰 里 迈亚·戴(Jeremiah Day)牧师。戴校长是耶鲁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也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倡导者。不过,其在大学史上的名声,主要源于其1828年任校长期间所颁发的《耶鲁报告》。在当时大学课程改革乱纷纷的年代,该报告强调了古典教育的意义而稳定了教育局面。这也使得人们对耶鲁产生了保守主义的印象。然而,保守的耶鲁又是如何缔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呢?
其实,耶鲁的教育立场虽然有时保守,但是他们对于教育工作毫不保守,甚至还比较“敢于出手”。
耶鲁在学校的人力资源建设方面毫不吝啬,1802-1805年先后又聘任了本杰明 · 西利曼(BenjaminSilliman)、杰里迈亚·戴和詹姆斯·金斯利(JamesL.Kinsley)三位教授,这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教授阵容。后来杰里迈亚·戴教授出任校长后,对于西利曼和金斯利等同事非常尊重,逐渐恢复了耶鲁过去的教授咨询制度,甚至直接让教授们负责各自学科的发展和建设[6]。当然,也有人认为杰里迈业·戴缺乏调配事情的能力,将所有教授当成可以商量的对象。无论怎样评说,戴校长的民主作风颇得人心,执掌耶鲁长达29年,这也创造了耶鲁校长任期之最,而且其退位之后又被挽留作校董事。
三、教授会立法
戴校长之后,老同事西奥多·德怀特·伍尔西任校长,“问政”教授的治校模式在耶鲁得到广泛的认可并基本固定下来,这也赢得了董事会的尊重。
经过这样接连三任校长的坚持,耶鲁董事会逐渐疏于校务管理,教授会治校渐成气候。没有教员们的推举或赞同,即便是董事会也难以采取任何行动。
没有教授同意而不得任命教授或者与教学相关的管理人员的原则,可以说自此一直耶鲁人被小心谨慎地呵护着。到亚瑟·哈德利牧师(ArthurT.Hadley)任校长时,耶鲁“教授会立法,校长同意,校董会批准”的格局,基本上成为大学惯例。后来经耶鲁董事会的同意,耶鲁每个学院都设置了教授会,并规定每增加一个研究生院或系,就增加一个教授会。耶鲁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的全体教师则构成了文理科教授会(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耶鲁教授有职有权,工作顺心,对学生也格外关心他们乐于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与学生交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充分发挥了教授的管理以及学术能力,体现了耶鲁的人性化管理。在耶鲁大学,院系一级的课程设置、教学组织等较为具体的学术事务往往由教授或学术人员自己负责。同时,教授治校的传统也使耶鲁形成了学术自主、中立、自由的良好风气。此外,教授们还可以通过校评议会或教授会等校级学术机构,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所以说,在耶鲁,教授就是学校的主人,即是管理者,也是教学者、研究者。也正是这种教授治校的传统,为耶鲁节约了庞大的行政人员队伍,乃至专门的行政大楼。
如今,尽管法律上校董会是耶鲁最高权力机关,但耶鲁的治理特点在于,大学的具体工作却是以其12个学院为基本单位进行的。各院的政策方针都是由教授会制定,后经校长或教务长推荐,校董会审批。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徽帜和风格,独立开展教学、科研及其他活动工作。特别是在耶鲁学院,教授会是管理耶鲁学院的“终极权威”,每个教师都是代表,共合体的活动由每个教师亲自参加。
四、教授治校:学理分析
当然,对于耶鲁是否真正实现了教授治校,人们还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因为,即便教授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作为法人的耶鲁董事会也并非就是橡皮图章。教授虽然在教授理事会或者评议会中享有发言权,这也只是在院系人事安排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因之可以说,教授争取“教授治校”的斗争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或者只能说是耶鲁教授与董事会的合作。然而,无论何种程度上来理解教授治校,美国大学的治理,普遍地从创办人转向执行人校长,乃至 “局内人”学者,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学者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mbaum)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学院的早期,规模有限,校董大多也为牧师,基本上是在忠实地执行学校创办人的职能。随着学院事务的繁杂,他们就将一些实际的权力赋予了校长。随着学术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学校的一些课程、学术与人事权力进而放权给教师们。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对于法律上的董事会 权 力,如 今 学 校 各 方 人 员 似 乎 都 有 主 张 的根据。
实际上,美国大学教授争取权力的故事由来已久,耶鲁并非个案。哈佛教授争取权力的斗争,也是比较具有历史意义的。从18世纪早期在“双董事会”之外就萌生了被称为“直接管理者”(ImmediateGovernment)的第三方组织,作为独立力量的教授们发挥着校管委会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ry)。有证据表明,这种教授会早在1708年就已出现,1725年的活动已被正式记录在案。
1824年,哈佛9名教授联名抗议教授被排除决策机构之外,董事会经过认真考虑后,终于接纳了一名教授代表进入董事会,并修改了哈佛章程,赋予教授负责学生考试、选拔以及教学有关的权力。这充分反映了美国当时教授地位的提升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
应 该 特 别 注 意 的 是,曾 在 查 尔 斯 顿 学 院(Charleston College)担任10余年校长的圣公会牧师贾斯珀·亚当斯(Jasper Adams),1837年最早系统地论述了教授治校的原则,对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贾斯珀·亚当斯认为,美国当时之所有尚没有能够持续繁荣的高校,主要就源于董事会不愿意向那些应当属于自己位置的教授、地位、尊严、荣誉及其影响所让步。相反,那些教学与管理最大程度地向教授倾斜的院校则最显生机。历史证明,董事会粗暴干涉高校管理的事例全是失败的。
他认为,尽管就教师与董事会关系的法律地位而言是模糊的,但就这种法律和道德关系应当如何处理,他有着自己的清晰理论。建立在董事会法人实体基础上 的 教 授 会,形 同 于 准 法 人 (quasi-corpora-tion),就任何学院的内在特性而言,他们都是该实体机构的管理者。他曾提出,学院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法人的存在,而是为了使得让法人组织更好地聚拢学者及优质教育。既然其目的就是聚贤汇能,若再让这些英贤屈尊于董事会,这就有些不合常理了,本末倒置,目标与手段错位。就公众的理解而言,教授自然拥有学习优劣的奖惩权力,他们自然有权选择自己的方法、机构及组织,但他们若无权就无责任可言。因此,董事会不应直接介入高校的教学与管理。在他看来,教授与董事的关系,并非是工人与老板的关系,而应是律师与客户或者牧师与教堂的关系。个人在这种关系中保留着某些特定的技术、经历和质量,从而使其居于建议、某种意义上指导客户的地位。
历史证明,耶鲁的教授治校精神,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认为,到了1830年,至少东部那些发展较好的学院,新教师的招聘基本上都需要经过教授会的推荐。当然,美国教授权力地位的最终确立,更是得益于20世纪以来美国大学教授会(AAUP)的成立以及其所发出的一系列原则声明。特别是其1967年所发表的《关于学院和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提出了共同分担责任的治理思想。其在任何董事会和校长合法权力的同时,又明确提出教师应当对课程、教学、教师地位以及学生生活的学术方面等事项负有首要责任(pri-mary responsibility),这就是说,除非特殊的例外情况,董事会和校长应当同意教师的判断。应该说,特别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教师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的逐步兴起,无论是美国大学教授自身的工资、福利,还是有关的学术晋升与科研管理,在与董事与校长的权力角逐中,美国大学教授应该说至少赢得了“三分天下”的权力制衡。更为可喜的是,赋予教师权力,这在美国不仅仅是大学的改革,也成为了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思潮。近些年美国基础教育界兴起“赋权增能”(empower),正是教师权力 与地位的回归。
现代大学的建设,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更需要能够将大师和大楼凝结在一起的软件环境,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美国大学的历史演进中,管理重心逐渐下移,逐渐寻找到了大学发展的活水源泉,形成了董事—校长—教授分工协作的权力制衡机制,这才赢得了如今的世界一流。中国社会向来等级鲜明,特别是在教师聘任制改革的背景下,视教师为“雇员”,潜意识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教师的权力及其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如果说民族振兴的希望在于教育,那么,教育的希望在于教师。能否真正尊重并赋予教师的“当家作主”地位,这正是教师的动力之源。可以说,教师赋权就意味着教师生产力的解放,这才是教育振兴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Clark Kerr.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2]Brooks Mather Kelley,Yale:A History[M].Yale UniversityPress,1974.
[3] [美]劳伦斯A.克雷明着.美国教育史(2):建国初期的历程[M].洪成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美国着名大学今昔纵横谈[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