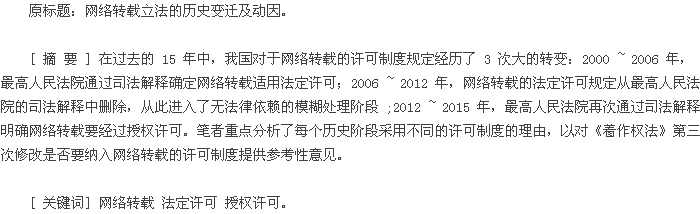
2015 年 4 月 17 日,国家版权局发布了《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了着作权法意义上网络转载的含义,指的是网络媒体转载他人作品、网络媒体与报刊单位之间、网络媒体之间的相互转载。
这个定义规定了网络转载的 3 种形式,囊括了新媒介技术带来的网络转载的新形式。但新媒介技术的演进不仅导致了网络转载的形式趋于多元,更重要的是使其法律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也因此,无论是在司法领域还是在行政执法领域,关于网络转载的争议从未间断过,国家对此方面的法律规制措施也经常出现摇摆。2000 ~ 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了网络转载,像报刊转载一样,适用法定许可 ;2006 ~ 2012 年,网络转载的法定许可规定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删除了,但又没有通过其他的法律法规明确是否适用授权许可,从此网络转载进入了无法律依赖的模糊处理阶段 ;2012 ~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了网络转载要经过授权许可,2015 年 4 月,国家版权局通过发布通知的方式强化授权许可制度的实施。短短 15 年时间,关于网络转载的法律制度经历了 3 次大的转变。我们不禁要问 :为何出现这种转变?转变背后的具体缘由是什么?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分析也可以为《着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是否要纳入网络转载的许可制度提供参考性意见。
一、司法解释确定法定许可阶段(2000 ~ 2006 年)。
2000 年 11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着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指出:“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着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着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解释》实际上是将《着作权法》关于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扩大适用于网络环境,即网络媒体转载、摘编传统媒体或其他网络媒体的作品也可不经权利人的事先授权。
最高人民法院确立法定许可成为网络转载中的“交通规则”,并不是当时拍脑袋制定的立法条款,可能存在如下 3 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社会各界基本达成共识。老实说,当时对于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是否适用于网络环境并不是不存在分歧,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的蒋志培就撰文说,司法实践部门的同志多数支持网络转载适用法定许可 ;而版权行政部门的同志多支持网络转载适用授权许可。综合考虑,法定许可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在 2001 年 2 月 11 日,由上海新闻出版局主持、《法学》月刊承办的“网络着作权法律保护理论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网络传播中的法定许可是解决网络侵权的理性选择。
二是考虑到法院司法承受力。当时互联网虽然是新生事物,但由此引发的网络着作权侵权案例已经越来越多,具有反响的判决如 :陈卫华诉成都电脑商情报社着作权纠纷案(1999 年)、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着作权纠纷案(1999 年)、上海榕树下计算机有限公司诉中国社会出版社着作权侵权纠纷案(2000 年)。正如蒋志培法官所说,应当分阶段地逐步规范网上使用作品的行为,如果简单地绝对禁止,不但社会各界、当事人一时不好适应,面对急剧增加的侵权案件数量,法院也难以承受,实际上并不能有效保障着作权人权利的行使。1990 年的《着作权法》丝毫未提及网络着作权,也就说明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法院在配置司法审判资源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新技术的来临引发的网络着作权纠纷。
三是海量作品难以一一授权。传统报刊之间的相互转载、摘编,毕竟数量有限,取得着作权人的授权操作起来比较容易,成本也不会太高。但在网络环境中,想要传播的作品实在太多,如果都要经过着作权人的授权,不仅授权花费的人力与财力等成本巨大,而且如果传播的作品是时效性很强的新闻作品的话,那等到授权的环节完成以后,作品的时效性早已时过境迁,传播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这是《解释》出台时反对网络转载适用授权许可者提出的最重要的理由。还有,2000 年我国的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完善的程度,当时只有音乐着作权协会一个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如果要在着作权交易中,实施授权许可并且能够让此制度得到真正落实,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必须承担重要的交易中介角色。此外,在 2000 年,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远不如今天这么发达,为了实现着作权人的权利保护与互联网产业之间的平衡,法定许可似乎是不二的选择,它既有利于实现着作权人的获酬权,也能保障互联网产业的繁荣发展。值得注意的是,2001 年我国在修改《着作权法》的时候,由《解释》确立的法定许可网络转载制度并未在《着作权法》中得到体现,其间的原因值得推敲。为了保持与 2001 年修改后的《着作权法》相契合,200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也第一次相应修改了《解释》的一些条款,但确立法定许可网络转载制度的第三条仍然在列,并没有被删除,[6]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06 年 11月。这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解释》进行第二次修改,这次唯一修改的就是删除了确立法定许可网络转载制度的第三条,其他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由此,在网络转载领域,我国进入了无法律依赖的模糊处理阶段。
二、无法律依赖的模糊处理阶段(2006 ~ 2012 年)。
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要删除确立网络转载法定许可制度的第三条?笔者认为可能来自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2006 年 5 月公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与网络转载法定许可制度相冲突。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国务院在《着作权法》的指导下颁布的一部行政法规,也是规范网络空间版权秩序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关于此《条例》中法定许可制度的设置,相关部门是这样解释的 :为了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条例》结合我国实际,规定了两种法定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