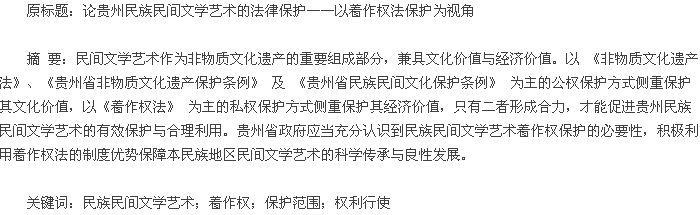
民间文学艺术,通常是指由特定民族集体创造、能够较好地彰显来源地民族群体的精神特质与文化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其需要借助一定的表达方式加以体现,主要包含戏曲、民间故事、舞蹈、绘画等。[1] (P4-6)贵州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在各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发展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大汇合的多彩贵州。当前,贵州已经成为中国原生态文化集聚展示的重要基地。[2] (P14)例如,贵州苗族的古歌、飞歌及笙箫舞、侗族的琵琶歌和大歌、布依族的八音坐唱及盘歌、毛南族的打猴鼓舞、彝族铃铛舞、水族的马尾绣、思南县的花灯戏、黎平县侗戏及安顺地戏等都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中。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了贵州民族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诉求,熔铸着贵州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是建设贵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和源流。在法治语境下,构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对于较好地促进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而言意义深远而重大,需要借助法律手段加以科学引导与有效保障。目前,对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发挥主要调整作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以及 《贵州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 等公法保护方式。这些公法保护方式主要是促进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与传承事宜,但没有明晰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所享有的权益,即忽视了创作主体的权利内容。[3] (P60)因此,还需要借力知识产权法为主的私权保护方式尤其是 《着作权法》,只有公法与私法的保护相得益彰、形成制度合力,才能较为充分地推进贵州民间文学艺术的较好的保护、继承、合理利用。
一、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着作权保护的必要性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开的“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上,绝大多数与会国家均明确认为,必须采取相关法律措施保护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用以维护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所彰显的人文精神与内隐的经济价值、防止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不当公开及诋毁滥用、激励后续创新与文化传承并通过赋予产权的方式有效保护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财富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然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是否采纳着作权保护模式,理论界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否定说”认为:第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应主要关注其文化价值,而着作权法侧重于保护私人产权,二者价值取向不同,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权利主体、客体、保护期限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也不适宜统一纳入着作权法保护范畴。与之相对,“肯定说”认为:第一,虽然民间文学艺术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文化价值,但是文化价值的维护与传承离不开其经济价值的发挥,而这种经济价值的实现需要借助着作财产权的激励力量。第二,尽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一般作品而言具有特殊性,但这并不妨碍将其纳入到开放式的着作权法体系中。实际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一种集体创作的智力成果,符合独创性要件,而且能够以有形载体加以固定,因此,完全可以纳入到着作权保护中。此外,民间文学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代表着一种文化主权。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境遇,我国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不断遭遇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与侵袭,甚至某些珍贵的传统民族民间文化正濒临消失的危机,而且国外公司不当歪曲、贬损及商业性无偿使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行为愈演愈烈。我国作为民间文学艺术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必须坚决维护国家文化主权,防止本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被不当歪曲、贬损,且理应从他人的商业性利用行为中分配到应得的那部分收益。保护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必然要借助于着作权法的制度优势,关键是要协调好民间文学艺术持有人、传承人及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着作权保护特殊性与兼容性
民间文学艺术兼具群体创作性与个体传承性、传统稳定性与时代变异性、信息地域性与文化扩张性,是集众多矛盾性格于一身的奇特统一体。[5] (P18-25)由此可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在创作、流传、表现形式等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性,呈现出群体创作、口传心授、延续性长等突出特点。[6] (P66)具体而言,第一,作品集体创作性。民间文学艺术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且其动态传承与发展特性使得作品呈现出跨区域、跨时代性,即使特定表达形式的民间文学艺术最初是由个人或几个特定的人创作完成,但经过历代传承人与使用人的不断演绎与再创作,作品已经融入了大量新的元素,很难分离出或最终确定原型作品。第二,作品保护无期限限制。依据 《着作权法》 第20条及21条规定,对于一般作品而言,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发表权和相关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然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集体创作及其动态发展特性,使得作品的保护期限不能局限于特定的一段时期,其保护期应该与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一样不受期限限制。第三,构成着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有限性。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都可以纳入着作权保护范畴中。依据 《着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2条对作品特征的相关界定可知,作品欲获得着作权法保护,必须满足独创性的实质性要件。虽然诸如民歌、神话、民间故事或民间舞蹈等符合作品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都可以界定为着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如那些没有浓缩为物质表现形式的传统仪式、典礼等很难界定为作品。
虽然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一般着作权保护客体而言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与着作权体系并不冲突,扩大着作权体系的兼容性完全可以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关键是要合理界定着作权保护范围并解决“集体作者观”背后的权利行使难题。
三、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着作权权利行使路径
(一) 权利行使主体
既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为集体创作的产物,那么,着作权主体既可以是特定区域如“安顺地戏”,也可以是特定族群如“仡佬族高台舞狮”,甚至可以是整个中华民族如“盘古神话”。对于这种集体权利主体而言,权利行使问题成为难题。从实践来看,存在两种权利行使进路。第一种进路,通过民间文学艺术来源地政府代为行使权利。根据2011年颁布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统筹全国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各级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保护各自辖区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本质上说,民间文学艺术归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其来源地与行政区划通常相吻合,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着作权权利行使及保护工作也可以由来源地地方政府集中行使。[7] (P12)例如,在“乌苏里船歌”案及“安顺地戏”案中,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贵州省安顺市文化体育局分别以原告身份对侵犯本区域内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不当使用行为提起着作权侵权诉讼,致力于维护来源地民族群体的合法权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机构基于这种“法定代理”的职责代为行使权利,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的私权利益,另一方面也最符合效益原则,降低交易成本。[8] (P63)第二种进路,通过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为行使权利。根据我国着作权法相关规定,着作权与着作邻接权的权利主体可以依法将自身的有关权利内容对外进行授权,让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为行使全部或部分权利。当发生侵权行为时,集体管理组织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进行诉讼。此外, 《着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 在充分研究域外有关着作权集体管理相关规定的基础之上,原则性规定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旨在进一步促进作品合法、高效的传播与使用。因此,可充分发挥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中间人作用,由其对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实施延伸性管理,代为行使相关着作权。
(二) 权利行使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 注重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根据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的有关规定,非物资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秉承“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并满足民族团结、国家富强、社会和谐等要求。同时,应注意维护非物资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价值与精神操守,坚决与损害我国民族文化主权的行为作斗争。来源地政府及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代为行使来源群体的着作权时,应当确保作品本身的客观性、完整性,督促他人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标明来源并防止他人尤其是外国公司在作品使用过程中进行恶意歪曲、贬损。此外,作品创作具有累积性,任何作品的创作都是在吸收前人智慧及日常生活素材基础上完成的。因此,权利行使过程中还要合理权衡作品保护与作品传承、创新之间的利益关系。
2. 注重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来源群体的利益分享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已对我国民族民间文艺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该纲要指出,应努力加强对民间各民族群众集体创作的文艺作品的保护力度,深层次挖掘民间文艺作品的内在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科学构建民间文艺创作人、保存人和后续创新者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努力协调创作群体与传承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有效促进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如前所述,民间各民族群众集体创作的文艺作品,不仅显现着创作群体重要的精神特质与文化诉求,而且也具有商业化生产的无限潜力,能够为权利主体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因此,在开展对民间文艺作品的具体保护工作时,需要认可并有效保障民间文艺之来源群体的利益分享权。来源群体以外的他人以复制、演绎、表演等方式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应根据作品使用情况支付合理使用费。这些许可使用费、维权获得的损害赔偿金以及通过政府拨款、社会捐助或国内外捐赠等渠道筹集的保护经费,都应该继续用于来源群体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研究、开发和整理等项目。
四、结语
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贵州各民族独特的文化认知心理,体现出其基本的精神理念。因此,实现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效传承,并对其进行有力保护至为重要,有利于增强来源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高贵州整体的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增强竞争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及 《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
作为公权保护方式侧重保护的只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文化价值,而对经济价值的保护相当匮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体系,而以 《着作权法》 为主的私权保护方式正是这其中的关键一环。依托着作权保障民族民间文艺事业,不但可以有效防止不当使用者尤其是外国不法分子对本地区民间文学艺术实施的贬损、诋毁及滥用等行为,同时,也有助于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生产性活动”提供一个生态性法律空间。
参考文献:
[1] 张玉敏. 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J]. 法商研究,2007,(4).
[2] 田 艳. 试论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J]. 贵州民族研究,2014,(1).
[3] 吴汉东. 论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对象[J]. 中国法学,2010,(1).
[4]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on IP and Genetic Resourc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Folklore: ThirdSession: Geneva,Final Report on Experiences with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Expressions of Folklore,2002,at 48.
[5] 张 耕. 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 张 今. 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思考—兼评乌苏里船歌案[J]. 法律适用,2003,(11).
[7] 马忠法,宋秀坤. 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着作权主体及其权利行使主体[J]. 民俗研究,2012,(4).
[8] 张 耕. 论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主体制度之构建[J]. 中国法学,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