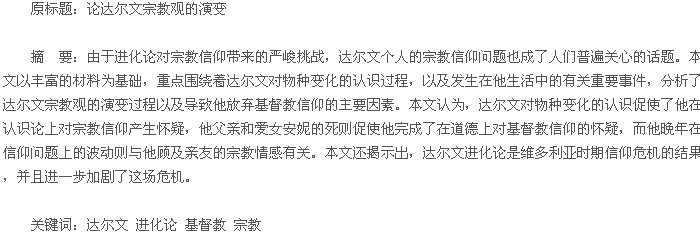
詹妮特·布朗(Janet Browne)在她获普利策奖《查尔斯·达尔文:航行》一书开头说道:“一些人说他是个天才般的魔鬼,另一些人说他只是个天才。不过大家一致认同他的才智。没有哪一位思想家,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以自然选择理论为机制的进化论那样,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造成如此强烈的冲击。”的确,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像达尔文一样,对众多学科领域产生如此持久、深远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像达尔文进化论那样,对宗教神学带来了如此严峻的挑战,以至于达尔文个人的宗教信仰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本文以达尔文的手稿和信件等一手材料为基础,结合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重点分析达尔文对物种变化的认识过程以及发生在他生活中的有关重要事件,尝试回答如下问题:什么原因导致达尔文放弃了宗教信仰?达尔文在什么时候放弃了他的宗教信仰?达尔文晚年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还是无神论者?进化论和达尔文的生活经历或社会因素对他放弃宗教信仰起了什么作用?达尔文进化论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信仰危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一、早年的“正统”
达尔文自幼跟随着母亲和姐姐去教堂,并在母亲去世后定期参与教堂的活动。他在1826年进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希望像他父亲一样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后来,由于他对医学缺乏兴趣,他父亲建议他转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将来当一名乡村牧师。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在爱丁堡读过了两学年以后,我父亲了解到或从我姐姐那里听到我不喜欢将来当医生,所以,他建议我将来应该成为一名牧师……并给我一些时间考虑他的建议。尽管我喜欢成为一名乡村牧师的这种想法,但是,由于我在这方面的所闻所思是如此地少,以至于让我宣誓我坚信英格兰教会所有的信条令我感到心有余悸。于是,我认真地学习《皮尔森论信条》以及其他神学书籍,而且我在当时对《圣经》中每一字的绝对和字面意义上真理性没有一丝怀疑,我说服我自己必须全部接受这些信条。在我脑海里从没有闪现过这种念头,认为我坚信我不能理解并且实际上不可理解的东西,是多么不符合逻辑。我也许说过,对于具有绝对真理性的东西,我不希望怀疑任何信条,但是,我从来不是像傻瓜一样会相信并且说‘我相信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想到我曾经被激烈地抨击为正统,以及我还打算过当一位牧师,似乎挺滑稽。”
关于达尔文早年宗教信仰的“正统性”,研究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根据达尔文在《自传》中的描述,认为达尔文早年的是正统英国国教徒;而另有学者则认为,达尔文的爷爷伊拉斯莫·达尔文是一个有神论的进化论者,他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则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并且推测达尔文的所谓的“正统”是“有名无实的”;还有的学者分析认为,对达尔文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加入英格兰教会不过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态度的象征,并非是严格遵守基督教教义的一种承诺,而达尔文所谓的正统也是一种相对不严格的英国式正统,它是以威廉·佩里(William Paley)的设计论为基础的自然神学。
在剑桥学习期间,达尔文对佩里的自然神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认为它是剑桥教育中的少数亮点之一。达尔文不仅按照课程要求认真地学习了佩里的《基督教的证据》和《道德哲学》,还自学了他的《自然神学》,并且完全相信佩里的论证:从钟表推论钟表匠的存在,从大自然中事物的复杂构造(设计)推论出上帝的存在。因为“设计一定有一个设计者,而这个设计者一定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上帝。”佩里的自然神学不仅理性地证明了有神论和宗教信仰的合法性,而且还赋予科学研究以独特价值,即科学研究的目标之一是发现和证实上帝的智慧。因此,对于当时希望将来当牧师并且对科学研究十分感兴趣的达尔文来说,无论是它的论证逻辑,还是它赋予给科学的特殊价值都令他容易接受。
达尔文在剑桥另一大收获是认识了植物学教授兼牧师的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后来他成为达尔文一生中的良师益友,并且也是经过他的推荐达尔文才成为贝格尔号博物学家的。此外,达尔文由于定期参加在亨斯洛家举行的小型科学研讨会,认识了矿物学教授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和地质学教授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他们不仅是英国着名科学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
二、放弃当牧师
达尔文自己回忆认为,在环球旅行期间甚至返回英格兰后的最初几年,他的宗教信仰没有发生变化。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去教堂,还参加船上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他还提到他曾因引用《圣经》作为不容争辩的道德权威而被同伴取笑为过于“正统”,甚至还描述了旅行至巴西时曾有过宗教情感的体验。他写道:“从前,类似刚才说过的那种情感曾使我(虽然我认为宗教情感在我心中从未有过强烈的发展)坚信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朽。我在《航海日记》中写道,当我站在一处宏伟壮观的巴西森林之中时,惊奇、赞美和对神的崇敬这些比较高尚的情感占据了我的脑海并且鼓舞着我,但是不可能把这些情感用适当词语描绘出来。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坚信人远不只是身体会呼吸,还有更多的东西。”
但是,从达尔文与家人的通信中不难发现,在环球航行期间,达尔文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一个明显的征兆是,达尔文在这一时期与家人和朋友通信中已经流露出放弃将来当牧师念头,希望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在1832年11月在一封写给表兄福克斯(W. D. Fox)的信中谈到大型动物灭绝的感受时说:“我希望我的彷徨不会使我不适合过一种安静的生活,而且将来有一天我可以像你一样幸运地成为一位合格的乡村牧师。”在1833年5月,达尔文在写给妹妹凯瑟琳的信中说:“我在自然史方面工作非常努力(至少为我),我收集了许多动物,观察了许多地质现象。我想如果不继续把我所有的力量用在我最喜欢的追求上可能是一个遗憾,我确信这种追求在我一生中将会继续保持下去。……在我看来,与人们对任何可能的追求一样,一个人不管能对人类知识宝库做出多么微小的贡献,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令人尊敬的生活追求。”达尔文的这封信让凯瑟琳十分担心,她写道:“当你兴高采烈地谈论热带地区的事情时,我不禁感到忧虑。我担心这仍然是一个强烈的征兆,我不知道我们使你重新打消这种念头还需要多长时间。我感到极度不安,你的立场离平静的牧师生活相去甚远,而你过去说过回来后将成为牧师的。”就在达尔文即将结束环球旅行前不久,妹妹苏珊也在信中写道:“因为我担心你回来后还能进入教会(当牧师)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爸爸和我们经常为你将来做什么这件事伤脑筋。”由此可见,达尔文想成为一位牧师的想法,随着他5年的环球旅行逐渐消失。
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我离开剑桥作为博物学家加入贝格尔号时,这种打算以及我父亲期望也都没有正式放弃,而是慢慢地没有了这种想法。”
达尔文的传记作者布朗认为,导致达尔文发生这一思想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赖尔《地质学原理》的影响,它使达尔文从一个灾变论者变成了均变论者,使他开始思考物种可变性问题。此外,赖尔本人相对自由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达尔文对宗教信仰的立场。达尔文在航行期间的通信中,几乎没有直接谈论他的宗教信仰是否发生动摇。他后来回忆中承认,在此期间渐渐开始对《圣经·旧约》产生了怀疑,不再认为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不过,在航行期间达尔文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三、信仰危机
达尔文的宗教信仰发生动摇是伴随着他对物种可变性的认识开始的。在结束环球旅行后的第二年,即1837年,达尔文在红笔记(the Red Notebook)首次提到他确信物种的可变性。他在1838年通过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识到了生物世界的生存斗争,并构想出了自然选择作为解释物种变化的机制。
达尔文在10月初记载道:“整个9月份,我阅读了不同主题的大量书籍,围绕着宗教思考了很多。”后来,达尔文又在《自传》中印证了这一说法,认为自己从 1836 年 10 月至 1839 年 1 月,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很多思考。在这一时期,达尔文阅读了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和《人类理解论》,了解休谟有关认识论和批判设计论方面的论述;他注意到当时在《爱丁堡评论》上一篇关于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的评论文章,其中提到孔德认为可预言性是科学的本质,以及关于人类心智发展阶段的论述,即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阶段,并在红笔记的第N卷中批注道:“动物学本身现在纯粹是神学的”。在“论神学与自然选择”这篇被认为是在1838年10月到11月期间撰写的手稿中,他批评创世论既不能作出预言,又不能解释许多已知的现象。
在1838年11月底,刚刚与达尔文订婚的艾玛(Emma Wedgwood)在一封信中谈到,达尔文将自己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告诉了她,并且担心他们在这件“最重大的事情”(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上的分歧会影响他们后来的生活。艾玛写道:“我的理智告诉我,诚实和凭良心的怀疑并不是罪过,但是,我感觉它很可能会成为令我们痛苦的隔阂。我从内心里感谢你的坦诚,并且我害怕你担心给我带来痛苦而隐藏你的观点。或许关于这事我说这么多有点愚蠢,但是,我亲爱的查理,我们现在的确属于对方,我也禁不住地对你坦言。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我确信你会的。就是从《约翰福音》第13章最后开始阅读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离别时的对话。这段经文充满了(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奉献以及各种美好的感情,它是《新约》中我最喜欢的部分。”这封信表明,第一,达尔文在宗教信仰上态度不仅令艾玛认为他是一个怀疑者,而且还希望通过她的爱以及阅读她精心挑选的这段基督教核心经文使达尔文回心转意;第二,达尔文是一个坦诚的人,他并没有听取他父亲的建议,对艾玛隐藏他对宗教信仰的态度;第三,艾玛坚信《圣经》中关于耶稣复活和救赎的观点,属于比较正统的基督教宗教观,这很可能跟与她朝夕相处的姐姐芬妮(Fanny)早逝有关。一方面,艾玛坚信天堂的存在,希望将来她和姐姐可以在天堂重逢;另一方面,她对达尔文的宗教信仰动摇表示极度忧虑,是因为她担心他们将来不会一起进入天堂。
令艾玛感到欣慰得是,达尔文在回信中不但承诺认真地阅读《圣经》中这一部分内容,而且还告诉她他会“最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
然而,到1839年初,达尔文的新婚妻子艾玛显然觉察到达尔文宗教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她再一次写信给达尔文。艾玛在信中首先说,达尔文表现出的科学怀疑精神并没有错,然后表达了她的忧虑。她写道:“你的精力和时间充满着这些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以及那些最吸引人的想法,即继续追求你自己的发现……但是,这种对发现的追求使你很难避免把其他类别的思想作为干扰因素而排除在外。然而,这些其他类的思想看似与你正在追求的无关,它们却能使你对所研究问题的两方面都进行全面的考虑。……在我看来,你的探寻之路可能会使你认识到了一方面的主要困难,而你却没有时间考虑和研究另一方面的诸多困难,我坚信你在提出你的观点的时候没有考虑你的(宗教)观点。在科学探索中不相信任何未经证实的东西这种思维习惯,不应该对你思考其他事情有过多的影响。其他事情也许不能以同种方式被证实,即使它们是正确的话,也很可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尽管从另一方面来说启示可能不存在,但是,我还想说放弃启示是一件危险的事。启示曾有益于你并且也有益于世界,要放弃它你会感到自己忘恩负义。因此,你对此应该格外谨慎,或许为了避免使你忍受所有这些痛苦,你能正确地评判它。……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我并不希望得到任何答案——对我来说,把它们写出来就是一种满足,而且我担心要是当面跟你谈论这一问题我不能准确地说出我想说的,尽管我知道你对你自己亲爱的妻子会有耐心。别认为这不关我的事以及它不会对我有多大意义。关于你的每一件事对我都很重要,如果我认为我们不能永远属于对方我一定会非常痛苦。”
达尔文与艾玛于1839年1月29日结婚,该信大约写于1839年2月。艾玛的这封情理并重的信使达尔文陷于两难的境地:一方是自己深爱的、虔诚的妻子和社会责任,另一方是自己孜孜追求的“伟大的物种理论”以及钟爱的科学事业。在这封信结尾空白处,达尔文沮丧地写道:“当我死了以后,(你要)知道我多次亲吻过这封信,并且多次对着它哭泣。”他还加了标注“,我自己妥善保存她这封优美的信,(此信写于)我们结婚不久。”可见,这封信对达尔文有很大的触动。
实际上,令艾玛感到不安的是达尔文对正统基督教教义中启示、神奇、救赎和永生等方面的怀疑,达尔文此时还没有放弃他的基督教信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达尔文对物种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他已经踏上了背离宗教信仰的不归之路。布朗对此评论说:“没有人比他更知道他关于物种可变的观点会引领他在放弃信仰的道路上走多远,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他与一个完全自然的人类起源(的理论)结缘有多深。每当他打开他的任何一本笔记,他就能感觉到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向他发出的极具有诱惑力的召唤。”在马尔萨斯“生存斗争”的利剑下,“在这种冷漠的生命世界观中几乎没有留给神圣或道德救赎多大的生存空间。”
四、放弃信仰
关于达尔文何时放弃他的宗教信仰,西方学者存在着严重分歧。有的学者认为达尔文“大约在1840年的某个时候,成了一位坚定的不可知论者”,也有的学者认为更明确地强调“到1839年达尔文确实成了一位不可知论者(甚至有可能是一位无神论者)”,还有的学者认为直到1859年达尔文完成《物种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之前,他一直是一个“有神论者(或进化的自然神论者)”。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达尔文在30年代末的信仰危机后,在40年代出现有所缓和,并且直到完成《起源》之前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有神论者,只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才陷入不可知论”。
关于什么原因最终促使达尔文放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西方学者也存在着严重分歧。早期的有关研究更多地强调了达尔文对物种变化问题的思考,而近年的有关研究则强调达尔文对爱与死的道德思考。综合这两种因素,人们有理由相信,虽达尔文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时有波动,但在19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初他基本完成了在认识论上和在道德上方面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
在1842年5月至6月间达尔文撰写了长达35页(对开纸大小)的物种理论提纲。达尔文根据赫歇尔和休厄尔所教导的科学方法,首先给出已经确立的事实,接下来通过类比或外推提出理论构想,然后再给出支持这一理论构想的证据,解释说明它为什么是正确的或至少是一个有价值的假说。达尔文甚至还列举出了可能的几种反对意见,如杂交不育和像眼睛一样的复杂结构的起源等。但是,他却没有提到一种最明显的反对理由,即他这篇手稿自始至终没有提及过上帝,也没有提到过人类宗教的特殊地位。而这一反对理由,不仅是艾玛最为关心的,而且在他科学界的好友,如赖尔和亨斯洛看来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达尔文当时也认识到,这个提纲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它不能解释变异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人们推测,达尔文当时撰写的这个提纲,既没打算给别人看,也不认为他以后会有机会将其扩展和完善。然而,达尔文在1844年1月写给胡克的信中提到,他又重新开始思考他的物种理论。达尔文写道,“我几乎确信(与人们的观点完全相反)物种不是不变的(这像是在承认是一个谋杀者)”,并且还提到了自然选择。1844年初开始着手他的物种理论提纲。与撰写提纲时的潦草、紊乱不同,达尔文撰写的这一稿提纲字迹清楚,结构严谨,补充了大量事实证据,篇幅达230页。这项工作于1844年7月完成,只有少数几位好友(包括胡克)知道其大概内容。也许达尔文认为它过于非正统或不够完善,他并没有想立即发表它,而是给艾玛写了一封类似遗嘱的信。达尔文在信中写道:“我刚刚完成我的物种理论提纲。
如果,正像我坚信的那样,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如果它哪怕被一位判断能力的人接受,这将是科学上的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因此,我写这封信,万一我突然去世,就像我最郑重的和最后的请求一样,我确信你会像对待我合法的遗嘱中的内容一样对待它”,他请求艾玛拿出足够多的钱,并请求她亲自或委托可靠的人监管出版他的这本书。他还列出了一大串有资格担任该书编辑的候选人名单,并且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总之,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该书的出版。这封信表明,“达尔文宁肯自己死也不愿意被他引发的争论所吞没,他宁肯自己死也不愿意伤害艾玛感情,或者更糟的是成为艾玛遭受社会排斥的原因。”实际上,在14年后的林耐学会上与华莱士的论文一起被宣读的达尔文的那篇论文,就是这本书的摘要,它也是《起源》的雏形。
在这本提纲中,达尔文用大量的证据,通过共同祖先、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等解决了物种变化问题。
他在结论中写道:“现在,我的理性使我坚信,具体的物种种类不是不变的创造物。博物学家所用的术语,如亲缘关系、类型的同一性、适应的性状、物种变形和器官的萎缩,将不再是隐喻的表述,而成了可理解的事实。我们不再像未开化人把船看做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那样,或者把生物看作另一个伟大的艺术杰作,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产品,并且我们能够对其过程进行探究。”
关于这段话,相似的内容也出现在1842年的提纲和1859年《起源》的结论部分。在1842年,达尔文没有明确表述,生物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品,并且人们能够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而只是说“我们觉得研究它非常有趣”;在1859年,达尔文则更明确地强调“大自然的每一件产品都具有历史过程”,这句话在后来 5 个版本中原样保留下来。
不难看出,到1844年,达尔文已经明确地描绘出了一个自然主义的生命历史观。在那里,不仅正统基督教神学中启示、救赎和奇迹等完全没有地位,而且佩里自然神学中作为设计者的上帝也成了“多余的假设”。用达尔文自己的话来说:“佩利根据自然界中的设计而举出的那个陈旧论点,过去对我似乎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现在这个论点已失去了它的效力,因为人们已经发现了自然选择的法则。”因此,不难看出,尽管此时达尔文的物种变化理论还不够完善,他的这个提纲只是《起源》的雏形,但是,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作为主要机制的自然选择思想已经确立。因此,可以说,达尔文对宗教信仰在认识论上的怀疑已基本完成。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达尔文的父亲和爱女安妮的死引发了他在道德方面对宗教信仰的怀疑。达尔文称他父亲是“我所知的最好的人”、“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他是一位正直、善良和睿智的人,是一位具有自由思想的并且相当成功的医生和理财能手,也是一位不信教的人。尽管达尔文的父亲在1848年11月逝世时已82岁高龄而且也并非突然,但是,父亲的离去仍然使达尔文感到无比悲痛和内疚。达尔文把他父亲的死与他不信基督教联系起来,他在《自传》中写道:“的确,我几乎不能理解人们怎么应该相信基督教是正确的;如果是因为圣经的经文似乎表明要对不信仰基督教的人进行惩罚,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我几乎所有的最好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惩罚。这真是一条该死的教义。”让达尔文更加痛心的是,在两年半后他最宠爱的、年仅10岁的女儿安妮去世,达尔文甚至因过于悲痛而不能参加安妮的葬礼。25年后,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只有一次感到万分痛苦,那是在1851年4 月 24 日,年仅 10 岁的安妮在马尔温去世。她是一个非常可爱并且非常温柔的孩子,我相信她长大一定会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但是,在这里关于她我不需要再说什么,因为对于那件事在她死后不久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现在我有时想到她可爱的一举一动,仍会落下伤心的泪水。”关于安妮的死对达尔文宗教信仰的影响,布朗评论说,“达尔文对上帝的感觉伴随着安妮的死几乎消失”。詹姆斯 · 莫尔(James R. Moore)认为,达尔文的理性怀疑只是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而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在道德上对基督教的怀疑,因此,达尔文最终放弃基督教信仰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进化理论,而是由于他父亲和女儿安妮的死唤醒了他在道德上对基督教的怀疑。正像达尔文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自幼被反复灌输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要想放弃它是很难的。
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很难接受把包括具有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能力的人在内的浩瀚而奇特的宇宙看作是从偶然性或必然性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当这样想时,我就被迫指望有具有类似于人类智慧的一个第一因存在。于是,我称得上是一个有神论者了。就我所能记忆的时间来说,大约在我写《物种起源》一书的时候,上述结论在我的头脑中还是强有力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这种想法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并且伴随着许多次波动而变得越来越弱了。”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所使用的“有神论者”一词,比较准确地说应该是“自然神论者”。也就说,大约在1856年他还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自然神论者”,然后这种信仰才逐渐减弱。
五、成为不可知论者
关于达尔文在发表《起源》后的宗教信仰,弗兰克·布朗(Frank Burch Brown)认为,“在达尔文的余生(最后20多年)中,他关于某种类型的上帝存在可能性的信念既从未停止过波动,他也没有对这种信念的优点进行过任何评价。可以说,在低潮期,他基本上是一个非教条化的无神论者;在高潮期,他是一个犹豫不决的有神论者;在其他时间,他基本上是一位不可知论者——在这样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上他同情有神论但又不能或不愿意承认自己。总之,在关于宗教问题上他的想法用他自己的术语‘杂乱无章’来描述最为合适。”的确,当人们翻开达尔文这个时期的科学论着、通信以及达尔文的《自传》时,不难发现达尔文对宗教的态度有所波动,但是,总的说来,达尔文并没有怀疑过自己放弃宗教信仰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在《自传》中回顾说:“怀疑以一种很慢的速度在我内心中发展着,但最后还是完成了。它的速度是那样地慢,以致我没有感到什么痛苦,而且此后我对我的结论的正确性也没有过一丝怀疑。”
注意以下几种情况也许会对人们理解所谓的达尔文宗教态度波动有帮助。首先,达尔文涉及宗教问题的情景和目的。例如,《起源》第一版的最后一个句子是,“这个星球在按照固定不变的万有引力法则旋转的同时,通过最初将几种力量注入少数几种或一种生物,从一个如此简单的开端,形成无限多样的最美最令人惊奇的形式,并且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进化着,这是多么美丽壮观的生命观。”但鉴于批评,达尔文在从第 2 版中把“注入”(breathed into)改为“由造物主注入”(breathed bythe Creator into)并且在以后各版予以保留,这似乎不能说明此时达尔文的宗教立场又发生变化。因为在当时看来,最主要的是让科学界接受他的理论,这种修改很可能是策略上的。有一点很明显,在《起源》各版中,达尔文一般回避使用“上帝”(God)一词,而代之以较为中性的“造物主”(theCreator),而且除非引用他人语句,从不使用“主”(the Lord)或“神”(Deity)等词。其次,关于达尔文的私人信件。就像普通人给不同的人写信一样,达尔文在写给不同的人的信件中解释进化论的宗教蕴含或他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看法,也会根据与对象的关系或对象的立场而有所不同。往往对关系最密切或最信赖的人会谈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对其他人尤其是科学界以外的人为了避免麻烦可能会有所隐瞒,这也是人之常情。第三,应该对科学界当时反对达尔文理论的强烈程度有足够的认识,有些科学家在批评达尔文理论时也常常涉及到宗教方面的问题。即便如此,达尔文只是成功地让人们接受了进化这一事实,而作为他的进化理论核心的自然选择理论则由于过于激进,在他同那个时代的人中只有胡克和华莱士等少数几个人接受它。古尔德有句评论也许对人们理解达尔文当年困境会有所帮助。他说,今天的科学家至少在他们科学研究上普遍接受了唯物主义,而19世纪的科学家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类唯物主义的准备。此外,还应该理解达尔文对艾玛及其好友的宗教情感和信仰的顾忌。例如,在1861 年艾玛觉察到了达尔文所忍受的理智上和疾病缠身的痛苦,写了关于宗教信仰问题的第三封信,希望他把进化最终看作是出自“上帝之手”,缓解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达尔文在有关理解自然选择的信件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宗教立场。达尔文在美国最重要的支持者格雷(Asa Gray)担心强调自然选择的随机性和无方向性不利于人们接受达尔文学说。因为这个学说不但排除了作为设计论基础的宇宙目的论,而且还否认了进步观念,格雷希望在自然神学的框架下解释达尔文理论,把自然选择理解为第二因。达尔文在回信中写道:“关于这一问题的神学观点,这件事一直使我感到痛苦——使我感到困惑——我并没有打算以无神论的方式去写。但是,我承认,我和其他人一样痛苦,并且希望我能看到设计的证据,而且这对我们各方都有好处,但是我看不到。世上的苦难似乎太多了。
我不能说服我自己相信一个仁慈的、万能的上帝带着给毛虫(caterpillars)喂食的明确目的故意地创造了姬蜂(ichneumonidae),或者猫就应该戏弄老鼠。因为我不相信这种论点,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相信眼睛是特别设计的。另一方面,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满意把这个奇妙的宇宙,尤其是人类的天性以及万事万物都归结为残酷的力量产生出来。我倾向于把所有事物看作由事先设计好的法则产生出来的,它们在具体细节上有好有坏,留给我们称作偶然性的东西去解决。当然,这种观点也不完全令我满意。我最深刻地感受到这整个主题对于人类的智慧来说太深奥了。一条狗或许也会猜测到牛顿的想法。——让所有人抱着希望并且坚信他能做到吧。”达尔文在写给赖尔的信中也说:“我不能相信造物主对每一个物种形成的干预比对在行星运行的干预会多那么一丁点。”不难看出,在1861年的上述两封信中,达尔文关于自然事物的自然解释方面态度是坚定的,他不允许把任何自然神学的设计论思想引进他的理论。
在回答普通公众所关心的进化论与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有关问题时,达尔文会顾忌到对方或他人的宗教情感一般采取回避的态度。在1866年,一位有5个孩子的母亲写信询问达尔文对自然选择与基督教信仰是否冲突。达尔文在回信中非常巧妙地避开谈论自然选择的宗教寓意,而是强调他“更倾向于把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灾难,看作是有关的自然事件(例如普遍定律)带来的后果,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上帝的直接干预,而且我认为将其与万能的上帝联系起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并在附言中补充道:“神学与科学应该各自按其自身的道路发展,如果说它们有交汇点的话,这个点应该很遥远,而且这也不是我要做的。”有趣的是,达尔文在1873年对一份长达7页的问卷所进行的回答。该问卷由高尔顿(Francis Galton)设计,调查主要对象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此基础上高尔顿出版了《英国科学名人:他们的本性与教养》(1874)一书。达尔文在早期教育与后期科学研究一栏填写了“我认为我所有的有价值的知识都是自学的”;在“特殊才能”一栏填到“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技能,如大家都知道的做好记录,写信,以及在投资理财方面比较成功,生活习惯比较规律之外,无特殊才能”;在回答“早年学习的宗教教义是否对你的研究自由有所影响”一栏填写了“无”;在隶属的宗教团体一栏则填写了“名义上的英格兰教会”。
至于达尔文晚年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有些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关于这个问题,达尔文在他那本“从来不梦想出版”的《自传》中,尽管对正统的基督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它跟野蛮人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达尔文在《自传》中也写道:“我不能假装对这样一个深奥问题给出了最低限度的解释。万物起源的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人们必须满足于做一个不可知论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1879年,达尔文在一封信中也写道:“我自己的观点(对宗教——本文作者注)可能是一个除了对我自己而对他人没有意义的问题。但是,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我的判断经常波动……在我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在否定上帝存在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我认为,总的说来(随着我越来越老),尽管不总是,不可知论者是对我的心智状态更准确的描述。”1881年,《资本论》的英译者之一、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夫林(EdwardAveling)访问达尔文,试图说明达尔文是一个无神论者。艾夫林说,“不可知论者不过是无神论者文雅的说法,无神论者不过是不可知论者攻击性的说法。”达尔文则回答说他更喜欢“不可知论者”这个词,并且说:“在40岁之前我从没有放弃基督教信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是一位无神论者。
艾夫林还与关于马克思与达尔文的一个误传有关,即马克思曾想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被后者谢绝。
达尔文传记作者布朗认为,实际上,马克思与达尔文仅有的交往是,马克思因为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中添加了一个高度评价自然选择的脚注而送了一本给达尔文。达尔文给马克思写了一封表示感谢,他在信中写道:“尽管我们的研究领域如此不同,我相信我们非常认真地希望增进知识,并且从长远来看这些知识肯定会促进人类的幸福。”事实上,是艾夫林在1873年要把他自己写的《学生的达尔文》一书献给达尔文被谢绝了。
总之,达尔文从一位英国国教徒、一个希望当牧师的青年,转变成了一位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的不可知论者。在这个过程中,有达尔文不信教的父亲和哥哥对他的影响,也有休谟论宗教和孔德论神学等思想对他的影响。但是,促使他的宗教观发生改变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物种变化的认识坚定了他在认识论上对宗教信仰的怀疑,而他父亲和爱女安妮的死则促使他在道德方面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这些原因相互作用促使达尔文最终放弃了宗教信仰,成为一位不可知论者。达尔文放弃宗教信仰既是维多利亚时期信仰危机的结果,又是这场信仰危机的催化剂。因为人们会自然地把他放弃信仰与他的伟大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它们为维多利亚时期信仰危机提供了一个具有科学权威而没有意识形态痕迹的合法依据。
它们使维多利亚后期的一些不信教者不再需要寻找其它任何理由或借口,也使一些虔诚的教徒在发泄内心的恐惧时不再需要寻找其他对象。于是,在一些人眼里达尔文是天使,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就是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