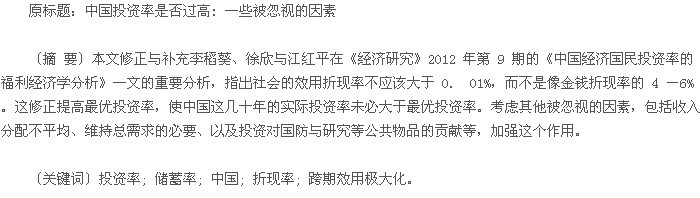
最近读到李稻葵、徐欣与江红平在《经济研究》2012 年第 9 期的《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一文( 下称李 - 徐 - 江文) ,〔1〕认为显然是一篇很有分量的作品,一口气读完后,颇有感触,特书本文加以评论与补充。
李 - 徐 - 江文“首次系统地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前沿计算方法,试图回答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这一重要问题。……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上世纪 90年代平均境内投资率低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6% …… 2002 年后,平均境内投资高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 5% ……1990 - 2008 年实际投资相对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总福利损失约为 5. 9%,相当于每期损失约 3. 8% 的 GDP。”李 - 徐- 江文不但用了现代正统福利经济学分析与前沿计算方法,又作出了数据分析,得出明确的重要结论。在这几方面,都对这方面的现有文献有明显的突破。因此,本文肯定不是要批判李 - 徐 - 江文,而是要对这篇有重要贡献的文章做一些补充,使其结论更加全面,更符合实际,对政策的制定有更好的启示。局限于笔者的能力,本文只能够提出有关的因素或问题,以及其对有关变量或关系的影响的方向,未能进行量化,希望有这方面能力的学者,能够更上一层楼。
本文提出的因素,提高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因而至少减少实际投资率高于福利最大化投资率的百分点数。这与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明显过高的观点不同,而与王稼琼等的结论“中美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可以在一个毋需偏好差异假设的逻辑框架内得到解释”相融洽。
〔2〕李 - 徐 - 江文采用传统的 Ramsey 跨期效用极大化模型。比起只看产量,不看效用( utility) 或福祉( welfare) ,这模型肯定有巨大的优越性。不过,如下所述,这模型也有很大的局限。在讨论这些局限会如何影响分析的结果之前,先讨论给定这个模型下的一些问题。
第一,先指出一个表述上的小问题。李 - 徐 - 江文的结论包括: “20 世纪90年代,实际投资在福利最大化投资之下,并逐渐上升……90 年代平均福利最大化投资率高于境内投资率 6%,高于国民投资率 4%。2002 年以后,实际投资率明显高于福利最大化投资率,平均福利最大化投资率低于境内投资 5%,低于国民投资率 12%”。〔3〕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所有“%”,都不是“百分之几”( “per-cent”) ,而是百分点( “percentage points”) 。例如,根据李 - 徐 - 江文的图 6,上世纪 90 年代时福利最大化投资率大约等于 38%,而境内投资率平均约等于32% ,前者高于后者约 6 个百分点,不是百分之 6,因为 38% 比 32% 高约百分之18. 75,这个纠正,加强李 - 徐 - 江文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因为有关的差异更加大。
第二,让我们来讨论李 - 徐 - 江文对跨期效用折现率 ρ 的取值,以及这取值对结论的影响。这评论与其说是针对李 - 徐 - 江文,不如说是针对绝大多数采用这模型的文章,因为它们大都采用与李 - 徐 - 江文类似的跨期效用折现率 ρ的取值。
虽然 Ramsey 本人不赞成对将来的效用( 或福祉,本文忽略它们的可能差异; 关于这可能差异,见 Ng 1999〔4〕) 打折,但几乎所有应用 Ramsey 模型者都采用( 年度) 跨期效用折现率 ρ,对将来的效用打折。笔者虽然与 Ramsey,Meade 等一样,认为,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我们应该对现在人们的效用与未来人们的效用一视同仁,〔5〕但由于将来的效用的实现有一些不确定性,应该根据这个不确定性来对将来的效用打折,就像或然率比较低的事件应该赋予比较低的权重一样。
对于一个垂亡的人,从他本人的观点,应该对几年后的效用大打折扣,因为实现这效用的或然率很低。然而,当我们讨论国家的最优投资率时,我们应该采用从全社会的观点。我们( 包括 Ramsey 模式) 采用的时间范围是从现在到无穷久远。但由于不能够完全确定能够在将来体现这些效用,因此应该用一个跨期折现率,对将来的效用打折。理论上,这个年度效用折现率可能随时间的进展而改变,或者说,近期的折现率与将来的折现率可能不等。原则上,这个年度效用折现率应该等于当年的整个社会( 如果讨论全人类的问题,则是全人类) 的死亡率。由于我们很难知道这死亡风险怎样随时间而变化,通常采用一个不变的年折现率 ρ。这也使数理运算容易很多。
李 - 徐 - 江文对年度跨期效用折现率 ρ 的取值是 ρ = 0. 02 - 0. 06,中位值是 0. 04,或 4%。李 - 徐 - 江文指出,这是中外许多学者对这参数取值的范围。〔6〕笔者同意这点。然而,笔者认为这个 2 -6%左右的 ρ 的取值是大得离谱。
即使只是 2%,这表示这个社会生存到 100 年后的或然率只有 13. 262%,几乎有87% 的高度或然率会在一百年内死亡。即使只用 1% ,这表示这个社会生存到100 年后的或然率只有 36. 6% ,有 63. 4% 的高度或然率会在一百年内死亡; 生存到 1000 年后的或然率只有 0. 004317%,几乎肯定会在一千年内死亡。这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中国几乎肯定不会在一百甚至一千年内死亡。即使国名改了,版图变了,但将来的那些人还是现在的中国人的子孙,社会并没有死亡。然而,死亡的危险是存在的,甚至全人类也可能死亡,包括全球生存环境变坏,与大型小行星撞地球等。以年度算,这些可能性很小,每年肯定不到万分之一,或0. 01% 。( 根据 Chapman & Morrison 1994 的估计,或然率比这小几百倍以上。
〔7) 根据这 0. 01%的每年死亡率,有将近 10% 的或然率在一千年内死亡; 有大于 63. 2% 的或然率在一万年内死亡; 有超过 99% 的或然率在十万年内死亡。
我们知道地球上的生命有约 35 至 40 亿年的历史,哺乳动物有 2 亿年的历史,灵长类有 4 千万年的历史,大人猿有 1500 万年的历史,人属类( Homo) 也有 250 万年的历史。超过 99% 的或然率在十万年内死亡,这显然是偏高的,也就是说0. 01% 的全社会或全人类的年死亡率是偏高的。因此,肯定不应该采用比0. 01% 更高的年度跨期效用折现率 ρ。
为什么许多学者采取比 0. 01% 高几百倍的效用折现率呢? 笔者怀疑他们是混淆了效用折现率与金钱折现率。例如,他们多数只讲折现率,没有区分效用折现率与金钱折现率。即使你肯定会活很多年,对明年的 100 元( 不论是现款、收入、消费、财富等) 应该根据你能够借贷的无风险利率打折。如果利率是 5%,今年的 100 元,放在银行生息,明年会变成 105 元。所以,明年的 105 元,应该打折等于今年的 100 元。( 简单起见,不考虑物价上涨,或只用实质数字计算。) 根据 Ramsey 方程式,当人们在消费与储蓄的选择是最优时,对将来的金钱的折现率 r 等于 ρ 加上 gθ,其中 g 是消费量的每年增长率,θ 是消费的边际效用随消费的 1%增加而减少的百分比。( 简单起见,不考虑人口增加等因素。) 如果 g 是正的,表示明年的消费比今年高,而消费的边际效用随消费量的增加而以 θ 的速度下降( 假定效用函数本身不变) ,因此,应该对明年的消费以 g 与 θ 的乘积来打折。如果对将来的效用的实现有不确定性,这折现率还应该加上这不确定率 ρ。
当利率 r 等于 ρ 加上 gθ 时,人们的跨期消费的安排就已经把跨期预期效用极大化了,是理性的均衡。
多数的学者对 r 的取值比较接近,约为 5% 左右,因为有比较客观的银行利率为参照。如果不考虑像中国高速发展的特例,g 多数是 2 -3%,而 θ 多数估值为 1 -3。因此,接近零或 0. 01%的 ρ 值,是与约为 5%的 r 值符合的。把 ρ 本身取值为 4%左右,多数是混淆了金钱的折现率 r 与效用的折现率 ρ。
如果把 ρ 的取值,从约 4% 减少到 0. 01%,会大量减少金钱的折现率,从而大量提高投资的利益。这会改变李 - 徐 - 江文关于“2002 年以后,实际投资率明显高于福利最大化投资率”的结论,〔8〕至少大量减少实际投资率高于福利最大化投资率的百分点数。
现在讨论 Ramsey 跨期效用极大化模型的一些局限。应该把人们的跨期福祉极大化这个原则是合理的,这里所讨论的局限,是一般简化模型的局限,包括Ramsey 的原始模型与李 - 徐 - 江文的应用。这模型把每期的效用等同于当期的人均效用,而这效用只是当期人均消费的函数。这忽略了消费与效用的跨期影响,例如今年的效用也受今年相对于去年的消费量的影响。但考虑这类复杂性可能还须留待将来,本文不讨论。
只看人均消费量,是忽略了收入或消费上的分配问题。这分配的问题,包括人际分配,也包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分配。这些方面的分配太不平均,是中国当今的一个巨大问题,不但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人们消费的意愿与能力。这应该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的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包括,由于各种原因,人们要把大量收入储蓄到将来才消费,包括应付预期与不期之需。若然,应该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增加将来的生产力,使人们能够实现将来的消费。
储蓄率与投资率很高未必是一个问题。与其鼓励消费,不如处理分配不平均等真正的问题。
其次,Ramsey 跨期效用极大化模型忽视不完全就业的问题,尤其是不考虑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实际总产量低于潜能总产量的问题。例如 2008 -2009 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致包括出口的总需求大量减少,成长率大量下降,使政府匆忙推出 4 万亿元的财政支出,使投资率大量提高。根据忽视不完全就业的问题的跨期效用极大化模型,这投资率可能远远偏高,但这可能是必要的。可以说这是短期波动的问题,而李 - 徐 - 江文讨论的是长期的问题。长期而言,短期波动应该大致相互抵消。然而,即使根据李 - 徐 - 江文的结论,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投资率太低,而在 2002 年之后投资率太高。可以说,长期而言,大致不太高也不太低。如果加上上述关于对效用折现率 ρ 的取值的显然过分高估,很可能可以得出很不同的结论。
还有,由于把效用看成只是私人消费的函数,忽视了投资对公共物品的贡献,尤其是对国防与研究的投资。简单起见,如果只让公共物品的总量进入效用函数,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尤其是,国防与研究的投资主要是增加将来的效用,因此,考虑这因素应该会提高最优投资率。如果根据上文把效用折现率 ρ 的取值大量减少,会明显增加这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比较低的折现率下,将来的效用的现值比较高。
李 - 徐 - 江文指出一种可能,通过把占 GDP10% 的境外投资转为国内消费的方法,使投资率减少,而不大量影响 GDP。
〔9〕应该指出,虽然 GDP 可能不会大量减少,但 GNP 则会减少。不过,这个建议还是可以考虑的。是否应该把境外投资转为国内消费或境内投资,主要看境外投资的回报率。这回报率大概非常低,因此,这转换应该是有利的。一个方法是让人民币适度增值,减少大量的低回报的境外投资。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不利。其实,当人民币被低估时,让人民币增值对中国利大于弊,就像当产品的价格被低估时,提高价格对企业有利一样。〔10〕





